高考失败,我是怎么逆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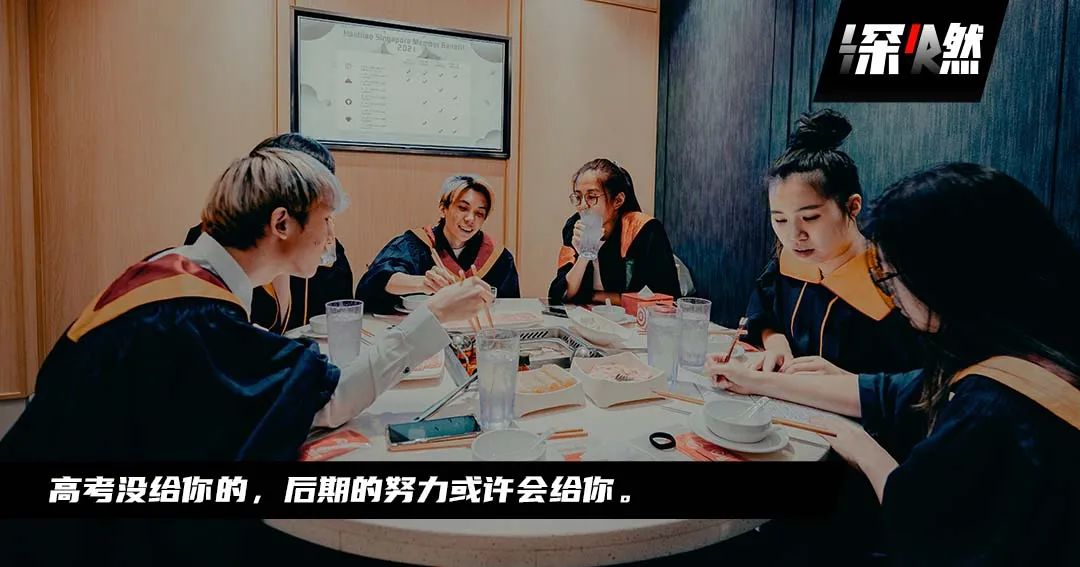
01

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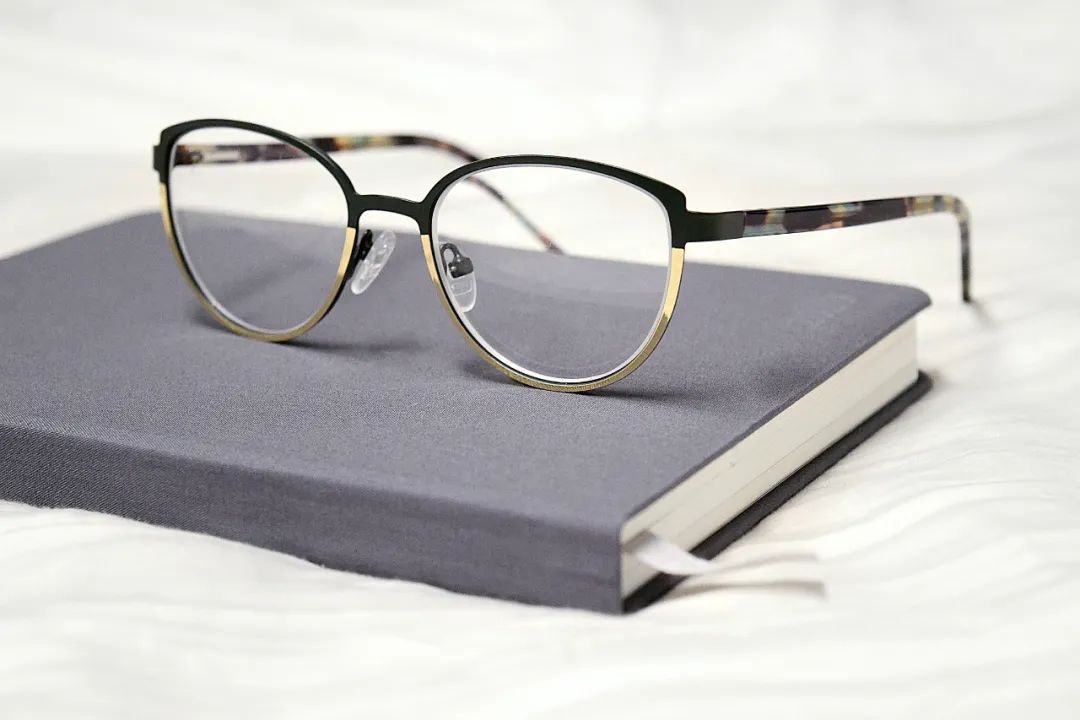
03

04

05

*题图及文中部分配图来源于Pexels。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周珂、宁远、安静、何坚为化名。
======================================================================
回不去学校的女博士,成为一名骑手

和周南约在深圳华强北某商场的一家饮品店见面。奶茶送到,她猛吸一口,目光投向窗外:“不做骑手以后,就发现这地方还是没那么讨厌的。”
五米外的电动扶梯数次见证她争分夺秒的奔跑。“柜台上那些‘屌毛’速度太慢,有天下午磨磨蹭蹭做不出来,被我们几个等餐的骑手轮番‘屌’。”周南即兴回忆着,叙述偶有卡顿时,一些华南男性劳动者中通用的词汇就会跳出来填补真空。
周南是香港一所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候选人。2020年初,受疫情及陆港边境管制影响,周南滞留深圳,无法返校继续学业。“为生计考虑”,她曾在撰写博士论文之余加入深圳华强路一个外卖配送站。4个多月骑手体验在她行为方式中留下的痕迹至今仍清晰可见。
譬如,离职后,她再没选择过非实体店提供的外卖服务,“心理阴影”来源于经常取餐的一处外卖“黑作坊”:污水横流的地面堆满蔬菜与餐盒,雇工叼着烟赤膊作业,与墙上贴着的某网红轻食LOGO形成对照。穿过人行道时,她会本能地靠里行走,“让小哥们的电动车快点过”。
但周南的目标并不止于“体验”。她展示了一个自己拍摄的同事——满大街随处可见的工作服下,是“牌牌琦”式的紧身裤和裸露脚踝。她试着观察算法、“劳动的游戏规则”与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张力,并以女性的特殊视角,为奔忙在系统中的“工蜂”画像。
以下是周南的自述:
01
我的外卖骑手生涯开始于2020年4月,先是做专送,即接受平台派单的正式员工。适应期期间,系统会以一个商圈的四边为界,非常智能地向我派发各个方向的订单,以此锻炼我的能力。
等到不同区域都熟悉得差不多了,我的工作也随之步入正轨:菜鸟们一般被安排跑正班,每天早上9点半,我喊着“XX外卖,送啥都快”“XX外卖,越吃越帅”在配送站前开晨会,常引得周围晨练的老头老太太举着手机上来拍照。
随着午高峰(大约以10点半作为起点)临近,我和同事们开始接单、跑单,脑子里的发条逐渐拧紧:去厕所的间隙基本被排除掉,当然,重体力劳动之下,我喝掉的大部分水其实是转化成汗液蒸发了;生理期期间,经常是连坐垫都湿透了也觉察不到,这种情况理论上可以请假,但如果恰逢运力考核,对出勤人数有要求,我也不好意思让站长难做,只能硬着头皮上。


图 | 华强北某商场楼下,姜文巨幅海报与奔驰的骑手

图 | 骑手和行人正在通过斑马线
类似的状况在我们的工作中比比皆是:保安和骑手之间的“世仇”自不必说,因为华强北一度禁止电动车经过人行道,有保安试图用脚绊倒骑行的骑手,引起轩然大波,我本人也曾经“中招”,上厕所回来被锁了车,只好打的送完餐;作为菜鸟,我经常“踩坑”——送到目的地,才发现是某些政府、事业单位大院,不能随便进,或者路被挖得一塌糊涂,需要绕好大的圈子才能和顾客接上头。
许多摩天大楼则堪称“地狱难度”。像华强路商圈最高的赛格数码广场,我接到过那里66楼的订单,因为电梯数量有限,没有半小时根本上不去,由此养活了许多“代送”阿姨。她们候在入口,通常没等我们的电动车停稳,就抢过十几二十袋外卖爬楼梯向高层冲去。我每单外卖拿7元,得分出至少一半来回报阿姨们的辛勤。

图 | 华强北赛格广场附近,有不少这样的“混搭型”骑手
然而问题在于,阿姨们并不专业,洒餐、送错的事情时有发生。于是某次求助“代送”之后,我很快接到一个男人的电话,告知我被他打了差评,并义正词严地谴责我不应该“不尊重自己的职业”:“连自己的分内事都不认真做,还能干什么?”这算是我以200元罚款为代价交的智商税吧。
我由此意识到送餐路上的种种不确定因素,最终都是要由骑手买单的。这使得我一到雨天就焦虑——手上攥着十多个单,点完一个送达,啪啪啪又进来两三个,众包(任务安排更自由的兼职外送服务)骑手下线之后,许多原本属于他们的“黑作坊”订单不受控制地涌过来。我从来没去过那些“黑作坊”,也不知道要耗费多少时间,才能从城中村的犄角旮旯里把它们找出来,焦虑的来源正是未知性。
所以在我看来,骑手工作之所以难做,是因为他们必须穿行于城市治理的毛细血管中,与林林总总的微观权力单元对话,与各自为政,却又犬牙交错的“条款”“规定”角力,甚至承担各种运作瑕疵、痛点带来的消极影响。这种复杂性在中国社会里明明比比皆是,却在系统规定的送餐路线中几乎没有显示。

图 | 天桥远眺,骑手可能是最了解城市层次的人

图 | 两个外卖小哥擦肩而过

图 | 马路边的骑手们
“日言日语”

图 | “女人世界”广告牌与正在跟顾客联系的女骑手
与他们相处得久了,我也开始本能地将“日”挂在嘴上。有男同事就私下提醒我:“女孩子不能这样说话噢!”那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女骑手的微妙位置——既是劳动者,又是被凝视、评价的对象。
首先我不可否认的是,女性身份能为工作带来很多便利。一个女骑手向我展示过她的打赏记录页面,亮眼的数据下,是满坑满谷的“小姐姐辛苦了”“小姐姐真漂亮”。一些保安看见我是女的,也会表现出惊奇:“你怎么干上外卖了?”然后饶有兴致地和我唠上几句。有对话就有沟通和交流嘛,果然过不了多久,他们会悄咪咪地给我把院子的后门打开,或者给我指出公寓楼的方向。而男骑手就很可能会被“公事公办”。

图 | 在路上奔驰的女骑手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我曾经见证过我的男同事“发际线”对一个刚入职的小师妹展开疯狂攻势。小师妹身材瘦弱,没法推着电动车上天桥。“发际线”就赶到天桥的另一头,让小师妹拎着外卖过来,再搭他的电动车去送餐,几乎每次都随叫随到,耽误了自己的事也不在乎。
而说到我自己,虽然我戴口罩,穿雨衣出去跑单的时候经常会被叫“师傅”,但做骑手的几个月里还是数次收到来自男同事的交往请求。离职后被男同事删除或拉黑,也基本上是因为我拒绝了他们的交往请求。某次外出聚餐,我甚至还被男同事借着酒劲摸了屁股,那种时时刻刻被“觊觎”的感觉,让我很困扰。
值得注意的是,我发现他们并不是逢场作戏,而是有认真在脑海中“配置”身边的“异性资源”,希望能在繁重的工作之余顺便解决掉婚姻问题。置身常年流动下,传统社会中作为人生尘埃落定标志的“成家”一再推迟,成为他们脑海中绷紧的那根弦。

就像去年母亲节,我在群里询问同事们都给妈妈买了什么礼物,“发际线”就公开艾特我,说:“买礼物有什么用,你这么大了还不结婚,你妈该给你气死了。”无论是那些多少带着点厌女色彩的开车行为,还是对于当“接盘老实男”的担忧(这也是男同事们常在群里发表的抱怨),我觉得都是对不安全、不稳定现状的本能反应。

图 | 华强北商场楼下,一位女骑手快速驶过

图 | 快速行进的骑手
像“眼镜”那样“负债上岗”的骑手,我们站占到三分之一,平时会公开在群里交流剩余债务的数额,以及预计“上岸”的时间。运营网络赌博公司遭遇政策打击;玩比特币失败;在老家斥巨资修建豪宅;因为赌博而将开淘宝店赚的钱挥霍一空……他们入行之前的经历中,能看到清晰的起伏趋势。
换言之,英国学者盖伊·斯坦丁提出的概念“不稳定无产者”(Precariat)未必能精准描摹骑手们的状况。因为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虽然嘴上总嚷嚷着“要喝西北风了”,但在位于三线以下城市的老家,都是拥有或曾经拥有一定社会资源(小产业、体制内职位),可以为生活兜底的。经济、社会转型冲击着他们的既有生活方式,更多的人以主动选择流动作为成本追逐这场浪潮带来的机会,也免不了要以有限的能力吸纳、消化由此产生的风险。
相应地,与2010年代初我在流水线上接触到的那些辛苦劳作,同时又抗拒、恐惧一辈子打工的农民工相比,我的骑手同事们对自己经历的“命运无常”“此一时彼一时”,以及零工经济缺乏保障的本质还是作出了更好的心理建设,也不会因为身处物质、资源匮乏状态下,就主动压抑自己的需求。这或许源于移动互联网时代对观念的重塑,也源于“90后”后一代更为强烈的自我意识。
有不止一个性格内向,社交恐惧(甚至明确自我评价“轻微反社会人格”)的同事就提到,虽然辛苦,弹性工资,送外卖还是比进工厂自由度大,“在工厂里和一个拉长打交道就够伤脑筋的,送外卖可以自己玩自己的,可能和一百个顾客打交道,只会遇到一两个奇葩”。
的确,传媒中的外卖骑手常常会以以下形象示人:自由驰骋在大街小巷,为美好的生活与未来奔波。平台也会锁定自带“反差亮点”的典型进行宣传,以强化这一形象中的传奇色彩,我所见过的,就包括见义勇为、名牌艺术院校钢琴系毕业、日语流利等等,当然,还有常被提及的“月入万元”。


- END -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边码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