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名电影编剧陈以文在舞台剧《死刑犯的最后一天》中饰演死刑犯,透过访问众多死刑犯的感受,让舞台剧呈现更深度的思考。(曾原信摄)
「假如今天是你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你想做些什麽?」

知名电影编剧陈以文表示,舞台剧《死刑犯的最后一天》发想自法国文豪雨果所着小说「某个死刑犯的最后一天」,陈以文在剧中饰演死刑犯。(曾原信摄)
每一天都是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该如何道别?
他们是死刑犯,被判刑却不知道执行日期的死囚,在执行死刑前的每一天都是「生命中的最后一天」,当生命进入倒数计时,他们怎麽跟这个世界、亲友、爱人甚至自己道别?
囚房内,戴着脚铐、穿着囚衣的男人静静地听着囚房外的声响,每当外头一旦传来脚步及铁门声,他便脱下囚衣、换上手边另一件衣服,而当脚步声走远,他像是鬆了一口气般地换回囚衣,而等到下一次铁门声出现,他又重複着一模一样的动作,整个晚上男人就这麽穿穿脱脱了好几次,直到熄灯。
囚房内,戴着脚铐、穿着囚衣的男人静静地听着囚房外的声响,每当外头一旦传来脚步及铁门声,他便脱下囚衣、换上手边另一件衣服,而当脚步声走远,他像是鬆了一口气般地换回囚衣,而等到下一次铁门声出现,他又重複着一模一样的动作,整个晚上男人就这麽穿穿脱脱了好几次,直到熄灯。
褶子剧团《死刑犯的最后一天》 从死刑犯视角出发

「每个人都被宣判了死刑,只是无限缓刑而已!」知名电影编剧陈以文在剧中饰演死刑犯,感受死刑犯随时都在死亡阴影下的无助。(曾原信摄)
「每个人都被宣判死刑,只是无限缓刑而已!」
「每个人都被宣判了死刑,只是无限缓刑而已!」雨果的原着中,通篇多是死囚第一人称的独白,在絮絮叨叨的抱怨与回忆中,藏着不少发人深省的哲语,即使情感是共通的,但太多法国俚语及自溺式的独白,仍不免让台湾读者感到隔阂,让人难以想像要怎麽改编成一齣「将场景设定在台湾的舞台剧」。但是,一待观赏《死刑犯的最后一天》后,随即了解这是多虑的,当主角说出「每个人都被宣判了死刑,只是无限缓刑而已!」的经典哲语后,主角朋友惊讶地看着他、讪笑似的以台语接了一句「哩金价有读册喔!」(你真的有读书耶!)马上把场景拉回熟悉的土地,好像街头巷尾就会听到的亲切招呼声一般。
把法式小说改为在地舞台剧的功臣,便是曾以电影《运转手之恋》获得第37届金马奖评审团大奖的导演陈以文,在陈以文决定以演员身分重返舞台时,他突然想起了这篇朋友曾推荐过的中篇小说,于是开始为自己量身打造死刑犯这个角色,而与褶子剧团团长张哲龙讨论后,两人决定开始着手规划这齣舞台剧,经过数次的修订,才完成目前所看到的《死刑犯的最后一天》。

褶子剧团团长张哲龙本身也是思剧场的艺术总监,张哲龙说,这部剧并不是要生硬的讲死刑存废等等的道理,而是透过戏剧表现,让观众进到更深层次思考。(曾原信摄)
由于碰触到敏感的死刑议题,製作团队难免担忧让司法界人士有「外行人装内行」之感,因此陈以文及张哲龙主动联繫司改会及废死联盟,透过大量阅读相关资料,以及实地访谈曾被判死的司法受害者苏建和及徐自强等人,了解死刑犯的心理状态及真实监狱情形。
徐自强曾说:每天灯暗时才知道明天又可以再活一天
问起所有访谈中是否有印象最深刻的片段,陈以文沉思片刻后坚定地说「有」,他提起,由于台湾被判死刑者并不知道死刑何时执行,因此从被判死的那天起,他们的人生便陷入了无尽的等待中…。

陈以文所有访谈中印象最深刻的片段,是日前获判无罪的徐自强曾说过「每天灯暗时才知道明天又可以再活一天」。(曾原信摄)
听到铁门声就先换衣服 关上铁门再换下
「所以你就一直等着,今天好像开铁门,有人要来提人,因为一般进出不会开大铁门,一定是有一群人那时候会开铁门,我记得在徐自强的访谈裡也好、纪录他的文章也好,这段是印象很深的,那时候执行死刑是晚上嘛!所以每天晚上如果有人开大铁门,他就会觉得是不是我?是不是有人要来提我?他就会穿好衣服,等那些脚步声走了,提了别人、关了铁门,他又会把衣服换下来。」这段深植于陈以文脑海中的访谈,化为剧中死囚更衣的桥段,这「死前穿新衣」的习俗融入,成为雨果小说文字外、这个舞台剧的一大亮点。
「所以在那样的生活之下,他很容易形成我就好好地过这一天,因为你也没有别的选择,虽然这一天你是被关在监狱裡,但你也只能好好过这一天…」陈以文认为这是一件相当反讽的事,他说许多活在自由空气裡的人,常常用这句话来形容自己的生命观,彷彿这样讲颇有智慧,或能藉此获得5分钟甚或几小时的好感受,但却不像死刑犯每天必须真的面对「最后一天」的处境,但他在徐自强身上的确看到了这样的智慧,「他(徐自强)就真的显现出这样的智慧,你会感觉到他的确这样子实践地,不管他是主动还是这场悲剧让他变成这样,但他的确是用如何『过好今天』来过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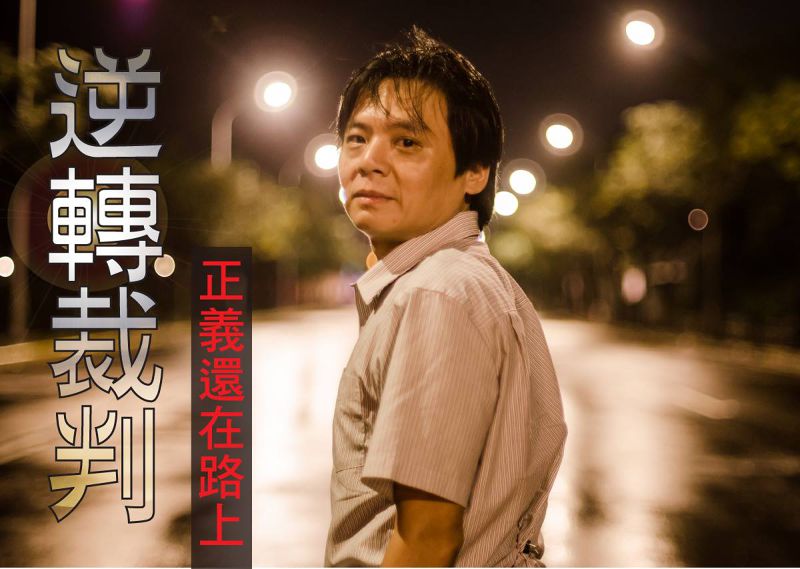
徐自强曾在访谈中表示,执行死刑是晚上,所以每天晚上如果有人开大铁门,徐自强就会觉得是不是我?是不是有人要来提我?徐自强就会穿好衣服,等那些脚步声走了,提了别人、关了铁门,徐自强又会把衣服换下来。。(取自徐自强案:正义还在路上脸书专页)
与徐自强的对谈,也是陈以文第一次那麽贴近受刑人,进而改变他许多想法,「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还满震撼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平常不会太关心司法或者受刑人,也就很自然地像雨果的小说或者剧情中提到的,我们就会当他们『本来就是一片空白』。」
从法国雨果到台湾舞台 加入人情味
在编写剧本的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是什麽?陈以文说还是「贴近台湾」的部分,由于雨果的原着作品有着很强的文学性,但如果照单全收,很容易变成主角不断朗读文字的状态,要想办法转化为事件、变化成人的感受及反应来呈现,因此最困难的就是从第一版改到第二版时,既要保留雨果的文学性、又要加入台湾的人情味,渐渐的,朋友、妈妈及妻子等原着中并未真实出现的角色才会出现,「裡面最打动我的地方并不是一个人的部分,很多地方是因为主角与人接触才感觉到,透过戏剧与人的接触才感觉到的情感状态,才会往舞台剧的方向编写。」

即使原着及剧本中都传达出浓浓的关怀及对死刑的反思,陈以文却担心会变成一齣「讲大道理」的戏剧。(曾原信摄)
不是讲大道理 戏剧就让观众用情感去感受
即使原着及剧本中都传达出浓浓的关怀及对死刑的反思,陈以文却担心会变成一齣「讲大道理」的戏剧。他说,既然透过戏剧就希望能让观众用情感去感受,至少未来在面对类似事件或是法规上争议时,观众可以因为曾经感受过小说或戏剧,而能用不同的角度及多一点的理性来看待这件事情。好比剧中加入原着中并没有的死囚与受害家属对谈,就是让现实生活中难有交集的两端能在戏剧中对话。
採访后记:听着剧中浅显易懂却透着许多哲理的对白,我的脑海中竟浮现许多过去採访过的受害家属或者受刑人面孔,也许就像陈以文说的,死刑犯从来都不是「一片空白」,他们和所有人一样,都是有血、有肉、有着思想和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