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培女校长失业后的「体面」人生

文 | 王琳茜
编辑 | 王一然
价格与价值
大部分价格不尽人意。杨晶晶得到的最高价是4000元底薪,加上绩效能多一千,依然和教育相关,其余工作均价在月薪3000元左右。夸张的是,和她竞争的都年纪更小、学历更高,“3500块(月薪)的工作,你不干一群研究生抢着干。”
她已经29岁了,未婚未育,是招聘市场上“最不被需要的人群”之一,目前的价格还是在有七八年教培经验的基础上,同时需要忍受一定的附加内容:早晨跳操、大喊口号的企业文化;朝九晚六挤地铁。这都是她从未接触过的。之前,教培吃尽红利时,杨晶晶连教师资格证也没有,但月薪是15000元。
她尝试过考公、考编,也参加过销售面试,最后都放弃了,受不了“一成不变的生活”;去年7月,赶上疫情封控,她开始留意线上工作,最终找到了一家线上数据标注公司,从此稳定接单。
现在,杨晶晶24小时都可以在家里度过:一张床上桌,白色条状、桌脚有滚轮,工作也在床上,不需要和任何人接触,交流都通过线上完成。一整天可以一句话都不说,卧室里只有键盘鼠标发出的“咔哒”声。
这份工作月薪大约三到五千元,难得的是,可以勉强保留一些“教师”的价值感。刚入行时,杨晶晶看到的宣传语是:人工智能背后的人工。还有一种说法是,这是AI的“老师”——作为一名数据标注员,给AI的算法学习及优化提供样本,她需要对着屏幕里的数据进行标注和加工,不断拉框、画图,这些图片大部分和道路、建筑有关,有点像填色或者勾线游戏。

●杨晶晶现在可以全天在床上完成工作。讲述者供图
现实时间仿佛静止了:出门的需求和说话一样,变得越来越少,某一天,杨晶晶忽然发现自己的口红已经过期了,许久没有使用,都被遗忘在角落,衣服网购了几件新的,试穿后被再度挂起来,吊牌都没摘。
一次,她看到群里跳出一条消息:完了,我今天下楼看到快递小哥都想拉他聊两句,太久没社交了。杨晶晶觉得好笑又真实,这是个“数字游民”交流群,成员在全国各地旅居、居家办公,工作时间自由,以及“都很孤独”。
但在两年前,杨晶晶无法想象这种“零交流生活”。她是个闲不住的人,做过电梯公司文员,4S店信息员,给百度公司做了一周外包,又在消防器材公司待了三天,最后留在了教培行业,“当时去补课班,学生们都挺喜欢我的。”她第一次获得了成就感。
教培机构里,杨晶晶爱笑,声音饱含情绪,认同别人的时候会认真地说“是的”,一年大部分时间,杨晶晶都在说话。尽管她只有民办大专毕业证,在这个行业干了七八年,她是成功者,最终当上青海一家教培机构的校长。
还有一个特殊的、没有明确头衔的身份,杨晶晶是学校里最难搞的学生、家长的“负责人”。同事应对不了的问题学生,都归到她手底下,甚至可以凑出一个小班。有不少家长特意找到她,付大几千元课时费,目的不是补课,“能不能跟我孩子聊一聊?开导一下他。”
直到2021年7月,“双减”政策之后,杨晶晶和所有员工谈完,她是“被自己裁掉的最后一个”。
所有的“认可”也随之消失了,她掉进了另一种生活。
被“标注”的现实
大多时候,数据标注员的生活是单调的,一个项目超过6小时没人接手,就会被传到其他人的数据库中,这由AI提供的云计算服务协助完成,为AI提供数据的工作,同样由AI进行监督,杨晶晶被监督着,这极度“减少了摸鱼的可能性”。
这也是她曾经最反感的工作状态。她去深圳出差时,住的地方离腾讯不远,每天凌晨1点,整栋楼通明,看起来还是满的,她感觉里面每个人都是高负荷状态,薪资也没高到夸张,和自己做教培差不多。那时她没想到,两年之后,和人工智能打交道的数据标注员,成为了自己最后的出路。
每天,杨晶晶至少标注5小时,期间整个身心投入工作,有时需要熬夜。她标注的是地图方面,不同属性的物品对应不同的颜色,树木是深绿色,草地是浅绿色,篮球场是蓝色,房屋是红色。这份工作反过来影响她,每次走在路上,看到小区附近的学校,杨晶晶控制不住地在心里想:教学楼属于房屋,房屋是红色的。
而面前的路,如果宽度长于5米,应该是一条道路,如果小于5米呢?可能是一条私家车道,如果在别墅区或商业区,那又是不同的标注。这是她最近最厌烦的项目。
不是每一次都能心情平静,像数念珠一样做完,她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每个项目相似,差别细微,打开图片密密麻麻,全是数据和线条,杨晶晶开始烦躁:“又要改线,又要改路宽,真的很煎熬,完全做不下去。”错误率变高时,效率也在下降,一张图可能要做上一个小时,甚至更久。

●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
这是数据标注员工作和生活的常态,在各个视频平台搜索,你都能轻易看到,他们可能在车间,可能在家里,相似的是电脑屏幕,微微皱起的眉头,以及长久的沉默。
五年前,在河南郑州某个小县城,20岁出头的李腾就开始习惯这种沉默。他们在类似电商园里的工作室,不大的房间里有二十几台电脑,李腾是第三个员工,此后赶上暑假,有刚高考完的毕业生、放假的大学生,最多有十六七个人。假期结束,只剩下五六个。
李腾干的项目据说和百度对接,每人发一份视频和文字教程,看好后做练习题,正确率达到标准,就可以开始干活。他觉得没什么难度,“也是底层工作,就跟搬砖差不多。”
工作室老板和李腾年纪相仿,很早辍学,知道的渠道多,经常干冷门活计,老板介绍,这是大数据,无人驾驶系统的基础架构,李腾觉得“怪高大上的”。
他的工作和杨晶晶类似,但那时工作内容比现在简单得多,主要是2D平面图像,导航车拍摄路上的照片,数据标注员负责标注:这个障碍物是栏杆,是红绿灯,是人,是狗,一组照片标完,钱就到手,计件结算。
逐渐熟练后,最多时,李腾一天能拉6000个框,工作将近12小时,但现在,单个框价格已经从1毛2分降到了6分甚至以下,还有些工作在项目单上消失了,李腾猜测“可能是被有背景的工作室截下了”,事实上,由于AI的自动识别能力也在进步,这些工作已经不需要人来做了。
两年下来,李腾的头发掉了一堆,他仗着年轻,把这份工作当成全职,一天最少标注8小时,到了饭点也舍不得放下电脑,只能家人送饭过来,然后抓紧扒几口,继续拉框。
高强度工作带来的,是比杨晶晶更严重的“症状”。那两年,走在路上,看到行人,身体朝向多少度、是站是蹲、身侧是一根柱子还是一片围栏,李腾都会在心里拉框。他还曾为美颜软件做过标注,眼睛、睫毛、嘴唇,每样都有对应颜色,为了提高效率,李腾反复背下这些信息。有一天,他和家人对视,发现自己在心里无意识地对熟悉的五官开始框选、填色。
他也在那时养成了听恐怖小说的习惯,为了缓解标注的枯燥和重复感,李腾一般会听语音电台、有声小说作为背景音,其中恐怖小说效果最好,汗毛竖起的时候,睡意也消失大半。哪怕现在已经从事其他行业,他的电台会员仍在续费。
老师
刚入行时,屏幕那边的培训老师比自己年轻,这时常让杨晶晶有些尴尬,尤其是当标注内容出错时——自己做老师时,她经验丰富,被所有人喜欢,现在却又变回了学生和“小白”,只能重新学习。
和杨晶晶同批入行的人,有不少都辞职了,还有的一直停留在最初水平,只能做最简单基础的工作,比如标注一些方言、语料,工资极低,杨晶晶已经开始上手中上难度的工作了,涉及到一些画图技能。
她把这归结于自己的学习能力,有时老师直播讲解的内容不甚清晰,杨晶晶判断“他自己会做,但不太擅长讲给别人”。她觉得自己的沟通和表达能力更好,可以给其他人转述更清楚,可惜大部分时候,她和同事们没什么交流机会,只有项目出错时,才会简单对话几句。
一切和做教培时太不一样了。那时,杨晶晶比大部分教培同行学历低,但学生们都喜欢她,最初教课时,她每次都要课前突击复习,或者干脆说“这道题老师也没有弄明白,我们一起研究好吗?”,学生们从来没遇到过这样说的老师;后来她被调到管理层,找她的学生更多了,求她帮忙开导心结、规划未来,下属们也佩服她“擅长和学生打交道”,这都让杨晶晶觉得自己“在机构里是不可替代的”。
她有着不少观察,学生们缺乏生活技能,因为高考而焦虑,对未来含糊不清,杨晶晶能和他们打成一片,是看到学生人格的那个人。外地参观学习时,她偶遇一个轻生的高三学生,在场的老师都不敢说话,她上去抱住学生大腿,阻止他跳楼,安抚谈话,后来离开时,那个学生给她鞠了一个90度的躬。
那是她职业的高光时刻,“大部分老师都只会教书,不会育人。”她觉得自己会育人。哪怕现在,每年高考季,还是有新的学生和家长被她的老客户推荐,请她帮忙做志愿规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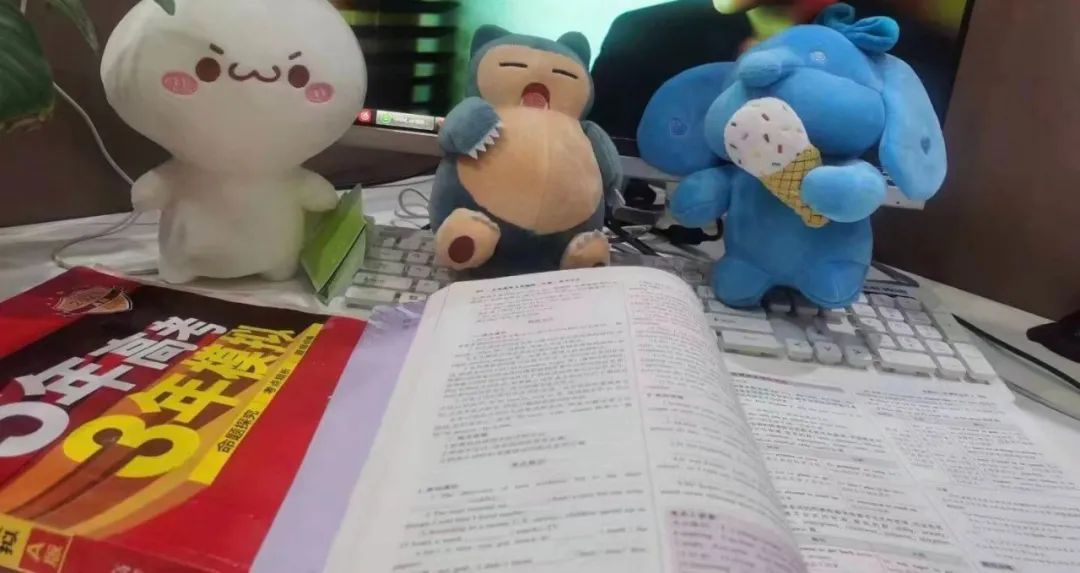
●杨晶晶做教培时的工位。讲述者供图
但现在,这些都派不上用场。数据标注不需要任何共情和感知。每一个数据标注员都面目模糊,杨晶晶和同事们都不知道彼此的长相、性格和现实生活,可能某天换了人也不知道。
有些时候,杨晶晶感到难以忍受,同事像网友,而所谓的“学生”——被标注的数据没有情绪,不会给“老师”任何正向反馈,AI更不会,她甚至不了解数据具体供应给哪些AI,国内的还是国外的——这都有保密协议,数据标注员很难知道产品如何落地。
唯一会变化的,只有随着标注数量而跳动的工资,连标准也不具体,杨晶晶大概知道,它和标注的平方米有关,有点像粉刷工。这谈不上任何价值感,更别提教育,宣传语里“AI的老师”,成为了一个轻易就能被戳破的骗局。
但她依然没放弃。她盘算着,等学得再深入一点,掌握了技术内容,就可以给数据标注员讲课,对着屏幕后的真人,自己肯定更亲切、内容更加容易理解,毕竟“我教别人学东西比他们更好,因为有时候做技术的,教课不是特别全面。”
药渣
不过,这个计划的前提是,数据标注员依然被行业需要。有一次,一个之前认识的行业“大佬”讲起,“未来哪怕是你家门前的一棵树,一片叶子,都会被标注。”语气兴奋而夸张。杨晶晶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这似乎是必然的未来,她心里也有期待,但“所有行业都被替代了之后,人怎么办呢?”
杨晶晶不止一次感受到,“它太聪明了,教会它,它就替代我的工作。”她刚入行时做过的比较基础的标注项目已经取消了,现在,“AI已经能自己识别了,它不需要(人)了。”
已经转行,但偶尔还会做数据标注中介的赵一珥说,数据标注员起初是药材,看起来平平无奇,熬制成中药却能发挥作用,可当一切都被“熬”给了人工智能之后,智慧、精力都被榨干,就成为了人工智能的药渣。
“如果你告诉他,熬的过程很痛苦,你觉得他会来吗?”赵一珥每次宣传招聘一般会说,这是前沿行业,和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相关,底薪3000块,多劳多得。事实上,大部分员工都只能拿到底薪,每天要求的标注量太大,很少有人能超额完成。大部分员工会在三个月到半年左右流失,“那就招下一批。”
这是个吸收人体智力的行业,但人从中学习到的技能有限。不过,赵一珥会描绘成:这份工作让见证了目前科技发展的最前沿,是很多科技公司最急需的内容,通过你的标注就能知道行业发展方向,以及未来趋势——你可以把握未来。
但如果听实话,赵一珥的声音抬高,带着讽刺:“没啥作用,你说你天天画个框你有啥作用?”
“他们不会意识到自己是药渣,入行(招的)就不是那种很聪明的人,很聪明的人就不会去干数据标注,你知道吗?”他说。
数据标注员的基础薪资也在下滑,虚假宣传、层层外包越来越多,赵一珥觉得,行业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但另一方面,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在提升,基础碎片内容要么被AI取代,要么单价极低,而更高价格的工作,对学历和专业的要求都在上涨。
半个月前,赵一珥刚把一个单子转给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研究生团队,那是一个涉及土库曼斯坦语的标注,“只能找研究生来做。”

“AI也在学习。”赵一珥形容,人工智能起初是一个小学生,经受九年义务教育的人就可以教它,“但现在它越来越聪明,可能差不多是高中水平了,就需要更高学历的去教它。”
并不是所有的AI都是聪明学生。和现实的学生一样,“优等生”可能出自最顶级的科技公司,背后有更高级的算法、更完备的数据支持,而其他“在普通中学就读”的AI,则没有明显的“智商”差异。
“在特定框架内教它还OK。”有四年工作经验的AI训练师宋子露说,标注最终目的是得到数据,训练出更好的模型,而人工智能想要更好适用于场景,往往需要训练师。“教机器人像教小孩,可能比小孩还要再笨点。”她说,教育孩子也一样需要规则,比如“今天就是不能吃棒棒糖,哭也不能吃”。
还有一点是非常耐心地重复,宋子露还是觉得教小孩更轻松,不用重复那么多次,机器人起码需要训练10-15次。
这些都是杨晶晶不了解的,数据被标注后的流向——实际上,杨晶晶找到的“做老师的感觉与体面”,可能是整个人工智能行业最下游的那个。
相比之下,宋子露更像AI真正的“老师”。她也和杨晶晶这种外包数据标注员打过交道,他们曾在公司驻场工作。标注员给宋子露的感觉是压抑的:工作时间几乎没有交流,很少有人说话,严格遵守上下班时间,像现实里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
近几年,宋子露和赵一珥一样,感觉行业在下滑。普通公司处境尴尬,做AI创造的价值有限,落地存在困难,放弃了又可惜,毕竟“这似乎和未来紧密相关”。
宋子露入行那几年算是大爆发时期,但具体从什么时候,风头渐渐过去,很难找到确切节点。而数据标注员们可以从单价上感知,1毛、8分再到4分,一条向下的折线,对于宋子露来说,就是去年年底,一个项目被临时取消,然后她被裁员。
紧接着,自己的AI学生也被砍掉,这让宋子露忽然对自己的价值和成就感产生了怀疑,“好像没有在这个行业留下任何东西。”
她起初以为,哪怕到不了“桃李满天下”,至少真的有“学生”长大成人,她甚至会幻想,自己的孩子长大之后,可以很自豪地告诉他,“这是你妈妈当年教的AI。”但事实是,AI被关闭后,宋子露再也找不到它。
ChatGPT的来临,多少给宋子露带来了一些信心——不少人都相信,这个行业能再度焕发生机,跟AI相关的新闻开始每天更新,世界正在飞速变化:每个行业都不可避免地要和AI打交道、AI实现商业化落地之后,需要找到客户、落地产品,然后就到了AI训练师的工作,这一切看起来并不遥远。
体面
今年1月,杨晶晶回到西安定居,旅居那段时间,她喜欢上了参加交流会,一般发生在小酒馆或者咖啡厅,不少人会分享自己的生活、工作和想法,这也是她为社交做出的努力。刚到西安没几天,她就忍不住又参加了一次交流会。
她注意到一个女孩,和她算半个教培同行,做留学工作。起初杨晶晶有点惊喜,很想和她多说几句话,但她没想到,在分享完自己现在的工作之后,那个女孩不断地否定她:“你的生活方式是错误的。”这是杨晶晶第一次在交流会上被指责,女孩把她从头批到脚,“你做着这样一份不稳定的工作,自己心里也觉得不安稳。”
杨晶晶有点生气了,她想“你和我讲稳定?经过疫情,你觉得什么是稳定?大厂都有35岁的淘汰期”。但她最后没有反驳,不想让人难堪,她找了个借口,提前离场了。
她开始想念在成都的日子,说自己是数字游民、做标注时,杨晶晶能明显感受到身边好奇的眼光、觉得她很酷;而在西安,她只好退而求其次,“前教培机构从业者”,但马上会被追问,“那现在呢?失业了吗?”
最后她只好说是“一个简单的地图绘图员”,再后来无所谓了,“我就说我是个画图狗。”
杨晶晶变得更沉默,也不愿意出门。实在标注不下去、不想干了,她就会逼自己看人们早高峰赶地铁的视频:狭小的车厢里,每个人都被挤得疲倦、失去尊严的样子,只是看着就感到痛苦。杨晶晶看了一会儿,忽然又能打起精神来,爬起来继续标注,“感觉有点变态。”

●杨晶晶近期参加的交流会。讲述者供图
2月底,杨晶晶又参加了一场教育行业面试,希望有条退路。面试前,杨晶晶给自己打了预防针,觉得“他们肯定瞧不上我”,应聘者一共8人,全是前教培机构从业者,来自新东方、优胜和学而思,他们都表情热切,急迫想要得到工作。
在那个场景里,杨晶晶忽然有个奇怪的联想,好像去了那种带服务的KTV,每个人都在被挑选,面试官的态度轻浮、不尊重,一律把他们都归为“搞应试教育的”,并要求上班时间是下午1点到凌晨12点。其他人都忍了下来,她有些崩溃了,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她强迫自己留下,但表现得很不耐烦,差点和面试官吵起来。
那之后两个星期,杨晶晶没再出门,她不得不承认,还是受到了一些打击。生活变得只剩下标注一件事,她开始尝试着在标注公司带几个“学徒”,这起码又是老师了。
但纠结和焦虑总会突然刺痛她,就像标注图片上一团乱麻的线条,半个月前,杨晶晶又换了个项目,工作也停了几天,她解释:“AI越来越聪明,原本类型的数据升级了,要更新项目。”某个下午,压力堆到一起,杨晶晶觉得太憋闷,她已经很久没有和人说话了,除了扔垃圾,连门都不怎么出。她赶紧又投了一份简历。
几天后,杨晶晶接到了面试通知,职位是高考志愿规划师。她面试表现得不错,但要求6000元无责保底月薪,提成按志愿单量给,和她竞争的另一个女孩,研究生刚毕业,只要4000元底薪就干。
很快,杨晶晶收到了拒绝回复,她无可奈何,“那个女孩还要租房,四千块钱怎么也愿意?工资就是这样被卷下来的。”
她又回到了标注的生活。一个好消息是,ChatGPT的火热是个明确机会,因为只有通过大量的数据标注,才能对AI进行算法训练,“这是一个前置动作。”杨晶晶还有另一个逻辑,哪怕AI学习能力再提高,那些最基础的工作没有几年也标不完,“我们国家这么大,光方言就有多少种。”
这让杨晶晶开始着手做培训了,先从社交账号开始,在“同城找工作”、“副业兼职”话题下,她发了几个帖子:基础地图绘制,可远程兼职,带徒陪跑。3-5天上手。西安附近可面谈。她录制了视频作为教学参考,简单讲解了些数据标注内容,配文“我只工作不上班”,标签“努力工作快乐生活”,还建了自己的培训群,在里面答疑解惑,分享一些简单的标注项目转单。
重新和人打交道,杨晶晶终于找回了那份久违的体面——视频评论区,一个加了她培训群的网友留言:“特别好,这两百花得值,以后要开始副业赚钱了,谢谢杨老师。”
(文中讲述者为化名)
===============================================
弟弟出生后,我成了家里多余的人



淑琳在演出间隙休息丨受访者供图
口述 | 淑琳
撰文|大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