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
天门山跳崖:四个决绝赴死的农村青年
4月4日13时30分许,4名年轻人在张家界天门山跳崖。经当地公安部门查明,4人为自杀。这几个年轻人,均在外务工,最小的23岁,最大的也不过34岁。
记者|印柏同 陈银霞
实习记者|顾靓楠
编辑|王珊
孤单的老三
彭志军出事后,徐明也是问了父母,才将新闻里的彭志军跟自己认识的“老三”联系在一起。彭志军家在河北省邯郸市的李谷驼村。彭志军兄弟姐妹四个,在家排行老三,村里人常年这么叫他,大名反而有些生疏。2023年4月7日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通告称,4月4日13时30分许,四名游客从天门山景区山顶西线玻璃栈道出口约10米的位置跳崖,其中三名男子已跳崖身亡,女子被及时拦下,但因跳崖前服毒,紧急送医抢救后无效死亡。这里面,就有“老三”。
根据大象新闻的报道,一名逝者的朋友提到,警方向家属透露,这4名死者通过群聊的方式沟通策划,其中一名死者是带头人。他们以一种决绝的方式离开:在跳崖之前,四人服了毒药,还从本子上撕下纸写下遗言,遗书内容很简单,只有一句话,“本人xxx,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本人是自杀,与其他人无关。”这位朋友说,遗书是4月2日写下的。

天门山玻璃栈道(图|视觉中国)
李谷驼村村子不小,有2000多人。徐明今年30岁,比彭志军小三岁,他家离彭志军家很近,只有几百米。在徐明的印象里,彭志军个子不高,不超过一米七,人看起来很瘦,也不爱说话。徐明告诉本刊,在跳崖前,彭志军已经四年没有回家。彭志军的母亲在四年前去世,去年是她逝世三周年,“三周年在我们这是个大事,要请亲戚和村里人几百人,还要请戏班子,儿子女儿是一定要在场的,要上香磕头。不来就是不孝顺。”徐明还记得,当时彭志军的家人在群里问:谁有老三联系方式?没有人回,家里人后来还报警了,“过了很久,才听说他在四川。我们村里人都在想,他是不是被骗进了传销组织。”
在李谷驼村,彭志军家条件在村里算是差的。这从房屋就能看出来,整个李谷驼村以二层小楼为主,只有彭志军家还住在一层平房里。徐明去过那个家,“村里家家户户都有冰箱、彩电,他家进去后,柜子没有,电视也没有。房子没有做吊顶,还漏水。”
跟村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彭志军初中没毕业就出去打工了。“我们那时,高中考不上就直接下工地。”徐明告诉本刊,村里人基本上去天津一个叫小南河村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劳务市场,有不少人来找建筑工,像刮腻子、刷大白等等。他们就住在工地板房,几平米,四张上下铺,厕所和洗漱都在外面。
图|视觉中国
彭志军的工作是刮腻子,这是最基础的活,他干活不算勤快,“有点磨洋工”,“工地上五六十个人,几个人一组干活,偷懒也不容易被老板发现。”彭志军比较瘦,又不爱说话,存在感也低。建筑工是个辛苦又枯燥的活,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六点半上班,一直上到12点左右才能吃饭休息一下,一天得干够10个小时。活也脏,一天下来,身上抹的都是东西,还孤单,“虽然都是熟人,但不是朋友。”
徐明说自己下班后就会去附近市场逛逛,买点衣服,吃吃饭、喝喝酒,有时也去网吧玩游戏。小南河有几百号同村人,他们经常会约着一起吃饭喝酒,彭志军很少参加,即使来了,也不怎么说话,“要么低头看手机,要么吃饭,就不回你,给人感觉爱答不理。大家也都不再叫他。”
即使如此,徐明和村里人还是没选择离开,“一个月下来工资有八九千。”徐明很知足。彭志军是个特例。在徐明的印象里,应该是在2021年秋天左右,他有一次在小南河的街上碰到彭志军,对方穿个衬衫,外面套着小西服,头发是杀马特造型,乍眼的蓝色。徐明跟他打招呼,才知道彭志军去了理发店。这在徐明看来,是“奇葩”和难以理解的选择,“理发店一个月只有3000左右,村里没其他人做这种从高到低的选择。”徐明说,他当时很为彭志军着急,他没结婚,家里条件也不好,“但我也没有劝他来工地。”
贫穷的压力
如果要寻找四个年轻人身上的共同点,贫穷带来的磨难以及不断新添的变故或许是他们的共性。四川女孩陈婷今年23岁。出去打工之前,她一直生活在四川内江的一个村子里。在初中同学孙苗苗的回忆里,陈婷个子很小,人也瘦,和班里另外两个女同学被称为“矮子三剑客”,“一样的发型,一样的身高,都穿着校服。”她胆子又小,遇到老师批评,她不敢像别的同学一样当面顶撞,只敢背后说一说。孙苗苗说,外表上看来,陈婷并不是内向的人,她很爱笑,笑点低,也爱帮人忙,“经常帮我们买东西”。
陈婷一直成绩不好,孙苗苗说,初中时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劝退了不少学生,陈婷就是其中一个。这之后,陈婷的妈妈吴丹给她找了一个学美容的师傅,陈婷跟着学了半年,就出去打工了,“她本来成绩就不好,我就想着(她)能够找个工作养活自己就好。”那时陈婷才16岁,她先后去了内江、成都、广东等地方。吴丹告诉本刊,陈婷一般半个月到一个月打一次电话给她,“我也不问她在哪个城市打工,我就问她生活好不好,就不管那些。”
2020年11月12日,湖南张家界天门山上的游客。(图|视觉中国)
作为一个还在苦苦谋生的母亲,吴丹其实有些顾不上孩子——家里只有两三亩地,七八年前包给了别人,她跟丈夫在县里的工厂打工,一年加起来有五六万的收入。去年,丈夫得了癌症,一直在化疗,治疗费用是笔不小的开销。吴丹告诉本刊,陈婷原来在的美容院,工资是底薪加提成,好的情形下,一个月有5000多收入。但有一次给家里电话,陈婷提到,工资没有保底了,只有提成,她说自己想要辞职,“她说工资很低了,想换个高一点工资的工作。半个多月前,她辞了原来的工作。”
只比陈婷大三个月的张财睿家里生活也是不富裕的。十多年前张财睿的父母离了婚。张财睿的父亲五十多岁,兄弟六个,他是老四,因为家里穷,两个四十多岁的弟弟现在都没结婚。一个邻居告诉本刊,他们的村子在福建省德化县的村子里,三十多年前开始,村里人相继往镇上搬,“就是集资建房。他们家现在还在山上,几个兄弟凑钱盖了房子,一人估计也就一间,砖头都还露在外面。”
对于出生于1990年的彭志军来说,生活给予的压力是更迫切的。村里人都知道彭志军结婚难。彭志军的父亲已经70多岁。徐明听父亲提起,彭志军的父亲年轻时很能干,除了种地之外,还会房屋修补的手艺,年轻时每天骑着摩托三轮带着喇叭走街串巷,“他挺能受(吃苦)的,我们一般晚上七八点吃完饭,会听到发动机的声音,那就是他回来了。”在农村,儿子结婚,房子是“必需品”。彭志军大哥结婚的时候,父亲把自己的房子给了大儿子用作婚房。又靠着操劳和借贷给二儿子盖了间普通的砖房。
《丈夫得了抑郁症》剧照
但十多年前,彭志军父亲身体开始出现问题,不能再干零活了,只靠种地,因为家里穷,老二也没娶上媳妇,他和二儿子、彭志军住在一起。徐明说,村里的年轻人一般20出头就要结婚。彭志军大哥比彭志军大十多岁,结婚时彩礼只有两三万。但到了彭志军要结婚时,彩礼已经翻了好几番,“现在彩礼要20万,还得县城买房,县城一套房得好几十万。”徐明说,现在村里年轻人一结婚,就开始给儿女攒钱,“村里结不起婚的,要不是家庭条件差一点,要不就是脑袋不好使。”
徐明也没结婚,每次回家都有媒婆给他介绍对象,最多的一天,他相了六次亲。他还知道有个女孩,一天见过十个。没有人给彭志军介绍对象,在农村的婚姻衡量链条里,彭志军各方面都处于最末端——他没有房子,也没有正式的工作。“在村里,他有些抬不起头。”徐明告诉本刊,没有失踪前,在村里遇到人打招呼,彭志军表现出来的都是回避的行为,“他都是低着头,很缓慢的‘嗯’一声,然后再看你一眼。”
最后一次联系
事发当天,刘志永的家人是通过警察才知道刘志永跳崖的事情的。他的堂嫂说,大家都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就在上个月他还请了三四天假,专门从广东回了趟老家看了父亲。”这一次回家,在几个邻居的印象里,似乎是刘志永出去务工十多年来,为数不多的几次回老家——以至于,他们已经不能一眼认出来这位34岁,已临近中年的老乡。

站在山脚仰望天门山(图|视觉中国)
刘志永家在河南周口市沈丘县的一个村子。2018年,沈丘县才摘掉贫困县的帽子。这一变化在这个不到2000人的村子里最明显的表现是:村子里终于修好了水泥路,墙上写上了规整的粉刷字。但对村民来说,种地和务工还是他们主要谋生的手段。
村里的邻居告诉本刊,刘志永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两人都已出嫁。“条件苦”是村里人对这家人最为直观的印象:早在20多年前,刘志永的母亲就去世了,他的父亲多年前中风,行动不太方便,奶奶已经90多岁,两个人住在一层的老房子里,守着半亩地生活,“他父亲虽然身体不好,还是坚持什么事都自己做,一个人照顾老母亲。”

《大江大河》剧照
刘志永在十六七岁就出去打工了。在村里人看来,十几岁的刘志永,离开家乡更像一场告别,“他很少回来,结婚都没在村里办婚礼,听说老婆就是广东人,说不定是倒插门。”在同村村民刘强印象里,他至少13年没见过刘志永。刘志永的堂嫂告诉本刊,刘志永平常也不怎么跟家里人联系。她对他的了解也有限,只知道他和妻子以前在一个工厂打工,后来离了婚,孩子也判给了前妻。后来,他又谈了一次恋爱,据说被骗了。上次回家的时候,刘志永跟家人提到想去外面旅游玩一下,“说情绪有点低落,其他没多说什么。”堂嫂说,后来看新闻,刘志永跳崖时候染着红发。
陈婷最后一次与家里联系是在4月1日,她告诉母亲吴丹,自己已经到了成都,打电话是为了让她安心。她说自己是去好朋友那里看工作,她跟朋友租了房子,要一起进厂,“那是她的闺蜜,小学同学,初中也在一个学校。我也没问她进什么厂。”现在能看到的有关陈婷生前最后的信息,来自她跳崖的几分钟前发的朋友圈,她拍了照片,配文是:“你好世界,再见。”
徐明上一次与彭志军联系还是在前年,当时彭志军突然加他微信,问能不能向他借一两百块钱,说是用作路费。徐明给他转了100元。他没有还,徐明也没有要。徐明记得,刚加微信时,彭志军还把他屏蔽了,“他的朋友圈背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看不到。感觉他还是挺封闭自己的,自己内心有一个小世界,很少人了解他。”
(实习记者方厚寅、王雅文对本文有贡献,文中徐明、吴丹、孙苗苗、刘强为化名。)_
==========================================================
海边的西塞罗|天门山跳崖案:
“吃苦耐劳”的社会底层正在消失
“吃苦耐劳”从不是一种美德,而只是一种无奈与被PUA。
关于天门山四人相约跳崖的事件,昨天已经写过《乐观是一种道德责任》一文,从感性上做了一点规劝,今天想再写一篇文字,从理性角度略微分析一下,这起案子到底意味着什么。
从目前报道的综合梳理看,我得知这四位相约跳崖者的身份是这样的:
彭某,男,河北人,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当地村民说其家庭是村里最穷的那几户之一。
张某,男,福建人,家中独子,今年23岁(四名跳崖者中最年轻),初中毕业后到广东打工。
陈某,女,四川人,家境普通,家中除父母以外,还有一个兄弟,一家四口,其生前性格很开朗,而陈某男朋友的姐姐也证实,印象中陈某是个很好的女生。
刘某,男,河南人,今年34岁(四位跳崖者中最年长),有一个十三岁孩子跟妈妈生活。父母身体不好,常年吃药,经常给家里生活费。
可以看出,这四位跳崖者的籍贯不同、性格不同、各自经历也不尽相同,可能唯一的共同点,就在于他们共同遭遇了同一种命运的折磨:贫穷。
是的,沉重的生活压力和看不到希望的未来,让他们感觉到贫穷将是一条延绵在他们人生路途上看不到尽头的苦行路,在这条路上他们感觉自己走的实在太累了,于是决定相约在美丽的天门山自杀,结束这场漫无止境的苦行。
但单以“受不了穷”去解释天门山相约自杀案,却也存在一个疑点——贫穷作为一种曾经中国人普遍具有的特质,不是骤然降临到这片土地上的。
我昨天的文章后面还有读者留言:小西,你说你们这一代人忍受不了贫穷和空间小,可你想想你们父母那一辈人其实活的更辛苦啊!中国人祖祖辈辈不都这么过来的么?
这个问题,有点接近前几年引发热议的“农二代”问题。很多社会调查者发现的,曾经给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最大劳动力供给的农民工群体正在陷入枯竭,与一代农民工吃苦耐劳不同,二代、三代农民工们不约而同的出现了“躺平”、少工作、不结婚、不生育、赚钱欲望低等现象。“三和大神”等新闻,其实就是这种“农二代”现象的衍生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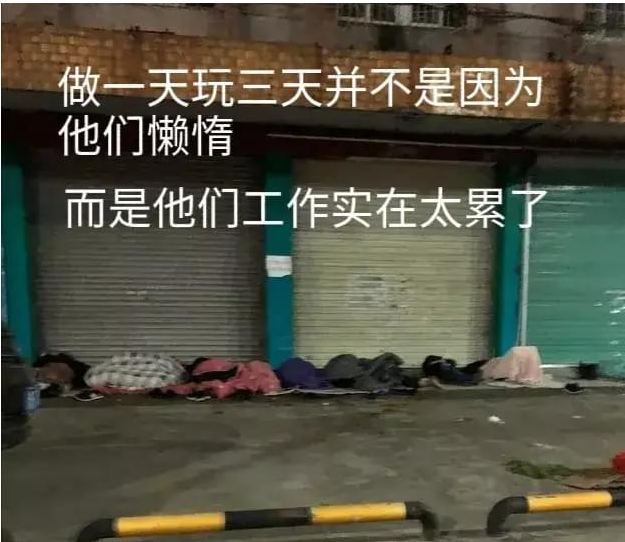
而天门山四人相约跳崖的事件则警示这个社会,受不了贫穷折磨的年轻人、“农二代”、“穷二代”们,可不仅会“躺平”,而且可能会自杀。
这就需要提供一个解释,为什么中国人曾经最鲜明的“美德”——吃苦耐劳,为了偏偏到了这一代,突然没了?
1
曾写作《乡土中国》一书的费孝通先生,在总结中国传统的农业乡村社会时,曾提出过一个词汇:他说传统中国农村一直是一种“匮乏经济”。
这种匮乏经济从本质上讲,是农业生产模式不可调和人地矛盾造成的——由于可开垦的土地一共就那么多,而人口总在不断增加,所以中国在清末最终形成了一种人多地少的“过密”状态。在这种“过密”状态下,农民们被迫进行一种“零和游戏”:你的地多了,我的地就少了,你成了地主、那我就得是佃农。那我们之间的关系,必然就是你死我活。
所以农村社会给个体的发展空间是相当有限的,于是就会广泛存在“闲汉”、“懒汉”、甚至觉得自己“穷命一条”、活着没啥指望、随时准备死的“赖汉”。而大多农民在农闲时也会呈现出慵懒的状态,聊天、打牌、晒太阳。
但你用心分析一下,会发现他们的这种懒散、绝望,是“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土地就那么多,地里能长出的财富就那么多,就是这么匮乏,你能咋办?
贫穷在这种“匮乏经济”社会中,是一种不得不忍受的命运。
以这个角度去观察最近四十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农民工进城潮,就会意识到这场变革是多么的深刻而伟大——它改变了中国农业社会几千年来不得不遵循的“匮乏经济”,打破了这个生存死局。
与农业必须依靠土地不同,工商业可以单纯依靠协作来创造财富。于是传统农民们惊奇的发现,他们的“余力”有处使了。只要进城务工,再苦再累,干一天的活儿就能有一天的收入。这对曾不得不忍受穷日子的“农一代”们来说,有着无与伦比的诱惑力。

我当年做记者时,曾经系统的采访过一些最早进城务工的农一代,发现支撑他们忍受艰辛、在城里拼命苦干的最重要原因,说来说去,无非一句话:“不想再受那种穷了。”
我当时有点不理解:这些农一代在城里日子过的也很穷,那他们所惧怕的“那种穷”又是“哪种穷”呢?
后来明白了,就是费孝通所说的有力无处使、贫穷不可改变的“匮乏经济”。
而这些苦难与痛楚的经历、让家庭成员能更好地生存,构成了这批人拼命干活的重要动力。
而明晰了这一点,再反观“农二代”“穷二代”们现在所处的困境,就能理解他们为什么在吃苦上“不及乃父”——那种发展空间有限,有力气也无从改变自己贫穷状态,正重新降临在他们的生活中。
看看三联生活周刊写这四个自杀者的报道,你就能感觉到他们就生活在这种苦境当中。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说广州的外卖送餐员居然史无前例的招满了,这其实是一个警示,说明在没有新的工商业模式被创造出来的大背景下,城市里的“可耕地”(工作岗位)也几乎被开垦用尽了。还有大量的“孔乙己”被要求脱下长衫,加入到基层劳动中去。那问题就来了——那些本就处在基层的骆驼祥子、“农二代”、“贫二代”们该怎么办呢?
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吃苦耐劳”,这在过去四十年中似乎是一个常识。但我们不应该忘记费孝通的提醒:这种“常识”也是要论经济环境的。
在一个有足够的空间发展,有一份力气挣一分钱的“充裕经济”中,农一代们可以发挥他们吃苦耐劳的本性,可是如果社会重新陷入“匮乏经济”的循环,传统农业社会那种状态就有可能重临,而在那种社会里,有力无处使的“闲汉”“懒汉”“赖汉”,也曾是传统中国农民的常态。
千万不要以为中国的底层穷人只有“吃苦耐劳”这一种性格,他们展现其性格的哪一面,是环境决定的。
2
还有另一种变革正在发生,而它更深一些:底层中国人为之吃苦耐劳的那个“信仰”,正在消失。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有一句名言:“人是一种悬挂在意义之网上的动物。”
韦伯说这句话,是为了解释新教徒为什么更容易发展资本主义:从近代宗教改革以后,欧洲就崛起了这样一批新教徒,他们拼命地工作、攒钱,却又死守着这些财产、不肯花钱,平素异常节俭的度日,宛如苦行僧。最终,他们积累的万贯家财成为了实现工业化大生产的“资本”。
以外人的眼光去看新教徒的这种“能挣不花”的行为,是有点匪夷所思的,劳动挣钱,积累财富本来就是为了享受么。只挣钱不花钱,这辈子活的有什么意思呢?
但韦伯解释说:这样做有意义,因为“人是一种悬挂在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新教徒们悬挂的那张“意义之网”就是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新教伦理。
新教伦理要求这些教徒必须努力工作、赚钱,通过积累财富证明自己的成功。而同时又需恪守节俭的生活,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他们的人生就为了这个意义之网而动,所以他们觉得自己获得挺有意思。
以韦伯的这个观点去审视传统中国人,你会发现我们的父祖辈其实就是“中国式新教徒”,他们也吃苦耐劳、能挣不花,只不过悬挂他们的“意义之网”有所不同——它名叫“家族”(或者说“家庭”)。
有一部曾经在日本引发大热的中国纪录片,叫《含泪活着》,讲述一个中国男人告别妻女、远渡重洋到日本去打黑工,每天做三份工作,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却住着最破的房子、过最节俭的生活,把维持基本日用之外的所有工资都寄回家里去。这个男人这样在日本一干就是十几年。而他这样做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女儿、为了他的那个家。
“含泪活着”的丁尚彪,是个非常典型的“中国版新教徒”。
是的,太多传统中国人就是这样悬挂在那个名为“家庭”的意义之网上的,他们的社会意义和生命意义都依托于家族或宗族的延续——换句话说,也就是为家人而活,而不为自己而活着。
“为家人,含泪也要活着”。这构成了传统中国人的终极关怀和一种准宗教信仰。
更有意思的是,这种生存模式不仅具有“内向性”,还具有“外向性”——如前文所言,传统中国的农村社会是“过密”且“零和”的,这导致邻里亲戚对你家庭的兴衰、人员和财产变动都特别的敏感。中国农村逢年过节的保留节目就是七大姑八大姨都来问你在外面工作怎么样、挣多少钱、娶媳妇找老公没有,就是这种敏感的代表。
一个传统外出务工者在外面吃再多的苦、受再多的累,只要过年回家时,能在乡亲面前展现自己“抖起来”的那一面,显示自己有身份、有地位。传统村庄社会就能给予他们尊严回馈,以弥补他的辛劳。
所以中国人特别推崇过年过回家。

这张名曰家庭、家族、宗族的意义之网,给上一代“吃苦耐劳”的中国人不竭的奋斗能量,甚至我们可以说整个中国的奇迹式繁荣,就悬挂在它之上。
但问题就在于,这些吃苦耐劳的农一代外出务工者,这些“中国版新教徒”们,**既是这张意义之网的能量发挥者,却又是它的掘墓人。**
随着大量外来务工者离开村庄,来到城市,乡村家庭的意义之网在过去这些年中恰恰是解体最严重的,甚至甚至很多村庄的亲属、邻里关系因为外出务工造成的“空巢化”,其崩解的比城市还要严重。
于是“农二代”既没有那么强的家庭联系,也不再以这种家庭联系的利益为自己最高行动指针。于是他们成为了从意义之网上掉落的“飘零者”。他们不再属于那个传统的家庭、家族,不再为家庭、家族而活。为自己而活着,又实在太辛苦,他们找不到“含泪活着”的意义。找不到把自己悬挂上去的“意义之网”。于是“躺平”、乃至轻生,就成为了很多人的选择。
我就认识这样的农村出来的青年,他们没有躺平、努力工作,人也很善良,但却是比我还前卫的“不婚不育族”。我曾问一位这样的姑娘,你为什么要这样呢?她给讲了一段她小时候吃苦的经历:因为家里穷,学校寄宿出不起自己的床铺,不得不跟同学“蹭床睡”,半夜被挤下来也不敢抱怨,只能在地上忍了一宿。因为家里穷,有一次带到学校的饭菜没吃,回家已经馊掉了,父母却因为心疼粮食,硬逼着她把馊了的饭菜吃掉……
她讲述了这些故事之后,我有点理解她不婚不育的想法了——一个忍受了这么多穷困苦难的人,对活着有一种本能的惧怕,不想再受下一代的牵累、让下一代也吃这种苦,把自己的悬挂到那个名为家庭的“意义之网”上,这是可以理解的。
而讲到此处,我们再回看那跳崖的四人,就会发现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未婚或者已经离异。
而这样的“穷二代”,正在变得越来越多。比如去年曾经引起轰动的自杀少年刘学州,身上就有这种气质——他是从家庭这张意义之网上掉落的人。

是的,越来越多的青年(尤其是农村青年、贫困青年),正在从传统家庭的意义之网上掉落。所以他们不再像父辈那样“皮实”,不再愿意为家族、家庭“含泪活着”。他们想为自己活着。
而如果贫穷和痛苦让他们实在无法忍受,他们就宁可去死。
3
综上两点,我们基本可以得到断言——“吃苦耐劳”作为一种民族性格,很可能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在中国退场。下一代中国青年从整体风貌上不会再像上一代人那样任劳任怨、只吃苦而不求享乐了,他们将对劳作、对回报和对发展空间更加敏感。
而这种民族性的改变很可能将是永久的,因为中国这几十年农民工进城的浪潮,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的乡村。
这件事的意义非常重大。
众所周知,劳动力资源充沛,且特别吃苦耐劳,一直是中国维持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大优势。有人甚至戏称其为“人矿”。如果这个比喻是恰当的,那么中国人不再那么“吃苦耐劳”,再配合上出生率的减少,四舍五入,几乎相当于“人矿”枯竭了。我们正在丧失曾赖以为系的最大发展优势。
你可以想象一下沙特如果没了石油,俄罗斯没了石油,美国没了尖端科技优势,瑙鲁没了鸟粪,阿根廷潘帕斯草原不长草了……大约会是个什么状态,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逆境。
但基于此,难道我们就应该呼吁新一代中国青年,尤其是基层“贫二代”,向他们的父辈学习,继续“吃苦耐劳”么?
并不!
有句话我憋在心里,一直没有机会说。那就是我总疑心,吃苦耐劳根本不能算一种传统美德。
就如同费孝通所指出的,能够忍耐贫穷而艰辛的生活,那是中国人在“匮乏经济”下不得不忍受的一种现实。只是因为不接受这个现实的人都死掉了,才给了一种大家都接受这个现实,甚至生活就应该这样的假象。
但这种不幸,本应已经随着近代工商业文明的勃兴而终结了。小罗斯福总统提出的人所应享有的四大自由中,之所以有“免于贫困的自由”,就是因为在这个增量世界中,不应再有人明明愿意用劳动改变自己的贫困却不得。
所以贫困不值得被赞颂,苦难不值得被赞颂。一个人若能耐劳,他就不应当忍受贫困之苦。上一代中国人用“匮乏经济”时代留下的“吃苦耐劳”在“充裕时代”中工作,创造了中国经济的奇迹。但我们不应当认为这种“吃苦耐劳”就是理所当然的。这种旧时代的“美德”一定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瓦解。
而我们社会所需要寻找的,是一个能让从传统家庭“意义之网”上脱离出来的年轻人重新挂上去,让他们为之活着(哪怕不是“含泪活着”)的新“意义之网”。
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也应该更多的去开眼看世界,因为这一代中国年轻人所经历的这种“无意义”,恰恰是很多发达国家曾经经历过的,他们对这个问题做的解答(哪怕是经常被批判的“个人自由主义”)虽然并不完美,但也好歹是一张现代的“意义之网”,可以供年轻人悬挂他们的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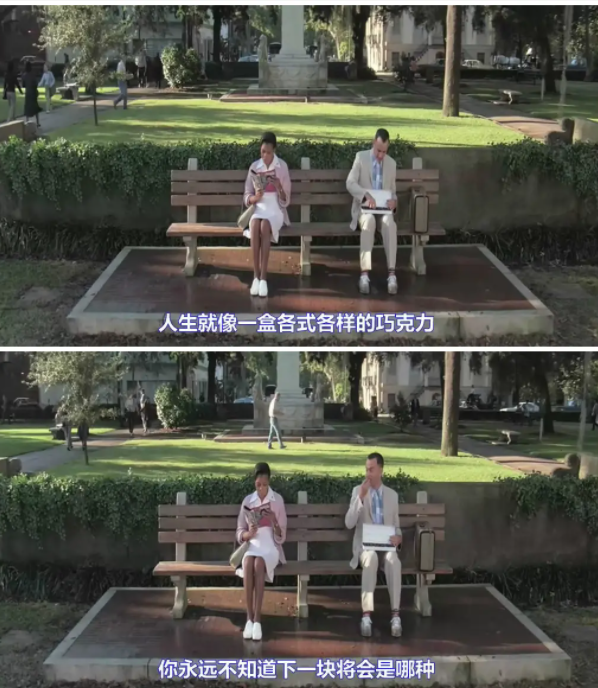
比如,你可以看看《阿甘正传》,这个故事的行进动机,
就是如羽毛般飘零的主人公在寻找悬挂他人生的那个意义。
同时,更要让那些在贫苦中挣扎的年轻人看到改变他们生活的希望,在这一点上,我想没有什么比一个活跃而繁荣的自由市场,一个开放而充满无限可能的流动社会更完美的答案了。
请实现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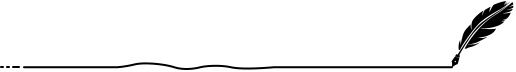
总而言之,“吃苦耐劳”的性格,也许很快将从我们的民族清单上抹去。
它曾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发展优势,但请不要怀念它。
苦难和劳作从不值得美化,它只会给人带来心伤。
所以“吃苦耐劳”并不美好,更不理所当然——没有任何人应该甘受穷困,却只劳作不抱怨的。这不公平。
对新一代年轻人,给他们呼疼的权利,给他们躺平的自由,给他们一个理由,让他们带着微笑与希望,而不是再像父辈们一样含着眼泪的——活下去。
全文完
================================================================
余秀华|小谈天门山事件:我们不配穿长衫
在文档前沉默良久,不知道如何着笔。“四月最残忍,从死了的 土地滋生丁香,混杂着 回忆和欲望,让春雨 挑动着呆钝的根。”艾略特说“四月最残忍”,残忍的是天门山玻璃栈道的悬崖下三个年轻的男孩的尸体和医院里也许在太平间叫王婷的女孩的尸体。我写下这些的时候,他们也许已经化成了灰,风把他们在人间的痕迹已经吹得一点不剩,像他们从没有来过一样。网上有限的信息让我找不到他们何以致死的有用的原因。他们默默无闻地生活过,最终以惨烈的死状把他们的名字从茫茫人海里拔了出来,让我们知道:他们,曾经来过!
昨晚和朋友谈起这件事,用了史铁生的一句话:死亡是迟早的事情,何妨再等等。而这句话放在他们身上是残忍的。这个世界哪配得上所有人都苟延残喘?我们可以残忍地说谁目光短浅,不能放眼天地心地宽,我们还可以说他们太年轻,不知道人生需要磨炼。网上说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贫穷,我想他们也许更多的是精神的孤独,甚至孤立,长期努力而得不到生活甜头的焦虑等等,所有的一切都是猜测,都是我们从这个时代的病症上推测出的不确定的因素。
而死亡,特别是自杀,有时候就是一时兴起,一个偶然的突发状况,很多人在自杀的过程中后悔。但是这四个人事先服毒了,要决然地死。要多大的悲哀才能让人毅然决然地死?其实我也有许多瞬间感到人生的虚无,人事的困顿,纠缠,想着也许死了更好呢,反正人生一眼就望到了头。好在我渡过了一个个这样危险的瞬间,希望在这样的绝望之后还是会偷偷光临,所以苟延残喘的人也会得到这样的福利。但是也有人,把绝望浓缩成死亡,用生命摘到了那样的果实。
如果说他们“目光短浅”,姑且把这当成一个说不过去的理由。但是谁造成了他们短浅的目光呢?是谁没有为他们搭建起一个健康的心理平台呢?其实我首先想说的就是现代教育,它让我们的知识越来越多,知识面越来越广,但是恰恰是对知识,刻薄一点说对学历的追求把“德”挤到了角落,让人们在掌握了许多知识后反而不会自处了,没有“儒”了,人们都急切地想用金钱证明自己的价值,而国家的,市场的经济运转又恰恰让富裕成了一个窄门,不是所有人想进就能进的。所以如我一般的底层人是绝望的。就算如此,如果能够解决一下绝望的问题,也许还不至于这么惨。
那一个悬崖,我怎么看怎么觉得它像一道人性的残墙竖立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处。放眼看,这个时代配不上那些为理想孜孜以求的人,它浮躁,短浅,急匆匆地如同去奔丧,人们停不下来,我们领受的教育也不允许我们停下来。信仰一旦坍塌,不知道怎么重建,也不知道如何重建,人心的荒漠,却没有植树之人。终于,有人用血肉之躯来祭奠了。可是,他们的死能够打在几个人脸上?有个朋友发圈说:他们脱不下长衫。问题是他们都没有学会如何穿上长衫呢。孔乙己的腐,是藏着傲骨的,我们,他们有什么呢?
科技的发达必然会牺牲很多东西。我们昨天直播的时候讨论过:如果AI取代了人类怎么办?就是说人类感情越来越像程序化,是能够编写出来的。我却觉得这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事情,就看那个“恶”在什么时候突发而出,改变历史有时候也只需要动动小指头。我也喜欢玩抖音,现在太多博主教给人的是:不要相信爱情,不要为了爱情牺牲太多,他们瞧不起恋爱脑。听起来多么理性多么好。但是深层次的悲伤和危机恰恰出现在这里:我们都不要爱情了,我们该有多粗鄙?“养大我生的,养老生我的”,一听,多少纯洁,不动凡心。就是不知道没有爱情,他们从何而来,他们的孩子从何而来?
精神的陷落!可能我杞人忧天了,但是人的精神世界也是波浪形的,不可能像股票一样一直飙升,我们恰好处在这一轮的谷底。我不知道触底反弹的机会和时间点在哪里,但是已经有人在牺牲。而相比于北宋末期,我们面对的问题更多更复杂:环境问题,机器人问题,网络问题,教育问题等等。如果把这些全部压在一个人肩上,那该如何承受?看起来,科技发达让我们成为了最幸福的一代人,但是太阳有它的黑子,人心也是。我们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仅仅是贫富差距倒容易了,但是需要解决的是为什么造成了贫富差距?
为什么那么多自媒体吧贫穷当成了重要的理由之一?什么样的贫穷是能够承受的,什么样的又是无法承受的呢?为什么孔乙己穷到只能吃一盆茴香豆的时候,依旧能够穿着长衫,而我们连长衫是什么都不知道了。 孔乙己是知道茴字的六种写法的人,我却不知道。什么是可贵的,精神!精神直接关联的是什么?生活的态度!就是人为什么而活着。为贫穷而死,应该轻如鸿毛了吧,但是越轻的东西正是要人命的东西。所以在如此丰富的时代,为什么有人愿意拿最轻的东西抵御它,因为它本身就是溃败的,是华美的衣服罩住的脓疮。
但是又能怎么办呢,似乎社会发展到这里了,没有人能够阻挡,完全靠个人的自觉性。但是“自觉”,自己都觉察不了自己,自己都不知道如何自处,哪里来的自觉性呢?拿他们的个体而言,可能贫穷只是一方面,而因为贫穷引起的精神孤独感,和社会的疏离感更深沉一点。他们活成了一座孤岛。如果没有及时的对孤独的解释和引导,很多孤独是会沉没的。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我们也是这肤浅浮躁荒唐的一部分,我们连哀悼的资格都没有。
我时常想,最后毁灭我们的可能不是环境,不是科技,不是战争,不是瘟疫,而就是我们自己。我们骨子里的悲观一旦物化,面临的就不仅仅是自杀了。我在想:那么高级的玛雅文明到底是怎么毁灭的呢?
作为这个时代虚妄,浮躁,无知的一份子,我好像只能用苟延残喘来证明我的胜利了。且让我们继续麻木下去,让每一颗心都吸食到养活自己的精神鸦片。
=============================================================
唐一水|天门山自杀青年背后的精神困境
这是我今年第二次写自杀话题。
天门山四个孤绝的青年,一人留下一封自杀声明,便和这个世界说了再见。
这四个令人疼惜的身影,又引发着舆论场大面积的悲怆共鸣,精神的孤独显然已成为你我共同的困境。
我并不喜欢单纯的贫穷归因,这是对现有底层群体的推测性霸凌,
也是用片面的阶层叙事,对独立个体行为的一种扁平和矮化。
人或许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得到完整的复原。
常年不回家,很少联系亲友,孤独单身,天门山青年们在交际上的重合项,让人很容易回顾涂尔干《自杀论》中的观点——
一个人越是被紧密地结合进社会中,就越不可能去自杀,反之则越可能自杀。
我们显然在面对一种现代性的社会关系瓦解,他们只是最新的悲歌。
社会学家鲍曼试图将社会关系分为两类,非人性化的和人性化的。
非人性化关系是指,工业化之下以交易为基础、互相功能化的关系,例如外卖,快递,企业工作,带来效率的同时也带来冷漠和孤立。使得经济越发展,人们越为渴求人性化的关系,也即家庭,爱情,友情等。
但很容易发现,非人性化的工具理性早已开始侵蚀人性化关系,亲密关系无疑面临着功利化和异化的威胁。
当代青年在社交平台上表达的,与父母家庭沟通无能、不相信爱情「只想搞钱」、社交恐惧症等话语,显然是社会关系瓦解的一种例证。
亲情成为一种,指向出人头地结婚生子的投资性关系,爱情成为一种,指向占有性资源提升社会地位的市场性关系,而许多人的友情,也在贫瘠的交友能力中干涸板结。
而对于自杀者「妨碍他人」、「要死也比打扰别人」的大规模指责,这种以所谓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声音,本质也是传统社会的人性乡邻关系,在逐渐原子化、互相工具化的社会现状中非人性化的一种体现。
就此,试图建立或拥有人性化关系的年轻人,还未开始就已投降,一点点沉沦到无爱状态,太过容易失去生的欲求。
天门山青年其中一位,是被他人异眼相待的「杀马特」。这让我想到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里对杀马特文化的温情剖析,流水线工作的年轻人们,通过夸张的发型强调自我,互相联结、共同组成「杀马特家族」,并在其中获得归属感。
这其实正是一种替代性的人性化关系。
面对非人性化关系的剥削,人通过各种在外界看来匪夷所思的行为,不断强调自己的主体性——即,我是个人,我不只是个工具,我不想被部分地、功用式地结合进社会。
人只有在人性化关系中,才能真正感受到自己的主体性。无论是游戏网络好友圈子,抑或是饲养的猫狗宠物,为什么有时比亲友更能让我们感到亲密,因为它们本就是潜意识对现实人性化关系的替代追寻。
时代的问题,实在难以回答。
我只能卑微地期盼,少一点对自杀者的指责,少一点对社会关系功利的期待,少一点将他人或自己工具化的眼光,少一点,再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