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所长|1967年,“打鸡血”是如何风靡全国的?
生活中常会说“打鸡血”。这是个形容词,表示对某件事很亢奋,或者说精力过于充沛。但这个民间俗语却是有历史渊源的。
全民“打鸡血”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从上海逐步扩散至全国。
这种给身体肌肉注射鸡血的做法,号称能治疗百病,被称为“鸡血疗法”。组织甚至立项研究,临床推广。
流行几年后,不断有人注射鸡血后休克甚至死亡,人们才慢慢认识到荒谬和危害。
现在,这个做法已经成为笑谈。那么这个荒诞不经的做法,在当时是如何得到组织重视,
并被立项研究,逐步推广到临床,随后又一步步风靡全国的?

一
坊间流传,打鸡血的秘方是来自于前国民党军统特务。
这个军统特务解放后潜伏在大陆,无恶不作。
被抓后,他声称掌握一个治病的“秘方”——老蒋就靠这个延年益寿——如果能对他网开一面,留条生路,可以无偿贡献出来。
在多方心里攻势下,特务终于招供了。
他提供的秘方是:抽取一只大公鸡新鲜血液,50至100毫升,脱离有机体后,以最短的时间注射进人体,每周一次。能包治百病。
当然这个传闻神秘而又涉及权贵,符合民间传说的特点,但可信度较低。
有据可查的信息显示,打鸡血的盛行,跟一个人有关。他叫余昌时。
余昌时1903年出生,年轻时在上海某个中专医学院学医。后来参加革命,以医生的角色掩护,搞地下工作。后来被捕了几次。
出狱后开过私人诊所,当过战地医生,在地方卫生院行医。
总结来说,他学过医,但并未接受过完整,系统的基础医学教育,也没有医学研究经历。但他断断续续的行医生涯,让他积累了一定的医疗经验。
你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医生,在人生的前50年默默无闻,但在他人生即将进入暮年的时候,突然宣称自己发现了一个世界级的医学成就——鸡血疗法。
但这个神奇的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
据他自己讲述,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他在江西南平县城的一家小医院里上班。
一天晚上,因为好奇,他给几只公鸡测量了体温,发现这些健康的家禽的体温平均都在43℃左右。
他觉得,鸡常温如此之高,表明其神经中枢的调节能力很特殊,主要是因为血液的发热机能特别高。
在中医典籍里,就有内服或涂敷鸡血,以治疗妇科病的记载。
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的脑海里产生:鸡血能治病,应该也能注射进人体吧?
于是,他先在自己身上试验。他从一只小公鸡身上抽了1.5毫升鲜血,在自己的左臂实施肌肉注射。
注射当天没啥不舒服,周身也没有疼痛、瘙痒和肿胀之类的感觉。
之后三天,他觉得精神亢奋、食欲增加。
到了第四天,奇迹终于出现了。他常年不治的脚癣和皮屑病很快痊愈了。
当然,从1950年代初期,他发现这个疗法之后近十年时间,并未见其用这个方法对外治疗。所以这个一面之词,到底是真是假,也无法考证了。
直到1959年初,余长士回到上海,在上海永安棉纺三厂担任行政副厂长,兼任厂部卫生室医生。他用“鸡血疗法”开始在工人中推广和试验。
根据他编写的小册子《鸡血疗法简说》说法,他为上百人注射鸡血后,荨麻疹,咳嗽,失眠,胃痛,胃溃疡,月经过多等症状,都有明显改善。
他的这个成绩很快引起了上海市静安区的注意。静安区组成了研究小组,设置了实验室,对此疗法立项研究。
一场即将席卷全国的“鸡血疗法”风潮,由此开始。
为什么现在看来如此荒诞不经的做法,在当时会得到组织的重视,并且专门立项研究呢?
这要结合当时的大环境来看。
二
当时,国家提出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技术革命"上来。其核心是发动群众破除对外国、对专家、对书本的"迷信",全民办科学。
尤其要批判那些瞧不起群众的发明创造、对新生事物冷嘲热讽的专家,破除对这些人的迷信,破除条条框框的限制,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土洋结合,创建祖国新医学。
当时在这种氛围之下,各种大胆表决心的医学领域口号不绝于耳。
比如,有群众提出,要在两三年内找出对十大疾病有效的药物,“让高血压低头、肿瘤让路、血吸虫断子绝孙"。
也有群众发明了据说超过当前国际医疗水平的治疗高血压、破伤风、小儿麻痹症、麻风、糖尿病、梅毒、慢性肾炎等疑难病症的中医药疗法。
做出这些“发明”的土专家,有数十位被医学科学院聘请为特约研究员。
1959年,报纸又指出,不要对中医治疗办法中暂时还不能作出科学解释的部分轻易加以否定。
因此,“鸡血疗法”作为一种新生事物,领导总体上持肯定态度,认为这是"已经出现的技术革新成果",应当"抓巩固","抓提高"。
在大政策的指引下,这个项目被充分重视,随后得以立项,研究,并且火速红遍了全国。
三
1959年夏天,静安区成立鸡血疗法研究工作组,地点设在区中心医院东院。
这个项目立项之初,没有经过专家审核,工作组也不是由这个领域的专家。
所以,这项研究缺乏科学常识,以及科学的实证体系,更多体现的是个人意志和领导意志。这在当时属于普遍现象。
研究组首先做动物试验。一是鸡血注射的有效性研究,二是鸡血注射的安全性研究。
他们给6只家兔注射鸡血,测量注射前后的各种变化。
但研究组的动物试验动物试验的样本量不大,试验周期过短,试验数据不全,研究结论大多为推测。
尽管也有活生生的病例证明,鸡血疗法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并且会发生鸡疫感染人体。但政绩冲动掩盖了理性判断,卫生部门想快速进行"鸡血疗法"的临床试用,并将试用计划上报给了上级。
临床试用涉及多家医院,为保险起见,1959年底,卫生部门先后召开了3次专家会议,意在讨论"鸡血疗法"临床试用的可行性。
尽管领导积极倾听专家的意见,让大家畅所欲言,但专家们都察言观色,并未对此项目提出异议。
没有反对意见,卫生部门批准了"鸡血疗法"的临床试验,并根据专家意见初步选定胃及十二指肠溃疡、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等7个病种进行临床治疗。
第一阶段临床试验,研究组认为,"鸡血疗法"对某些病种具有显著疗效。部分病例在注射鸡血后出现食欲明显增加、思睡、精神爽快、大便通畅的现象。
也有一些病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过敏反应,有些患者还因害怕副反应和微生物感染而放弃治疗。
但研究组认为这些过敏反应均可在短期内自行消退,未予以重视。
(余昌时1903-1994)
四
尽管这些病例中,没有1例完全治愈。但"鸡血疗法"的临床研究还是取得了初步成效,领导颇为高兴。
在“鸡血疗法”座谈会上,大家一致认为,认为这是区卫生工作中很好的技术革新项目。俞昌时因为"大胆创造试用鸡血疗法"获得了肯定和表扬。会议鼓励他要"进一步研究其疗效为劳动人民更好的服务"。
1960年初,会议指出,必须打破少数人关起门来搞技术革命的旧框框,要发动广大职工群众大闹技术革命,作到工程技术人员与工人群众相结合。
领导干部必须深入群众,深入运动,及时发现苗头,抓住苗头。
对已经出现的技术革新成果,必须抓巩固、抓推广、抓提高……将技术革命推向更高的阶段。
在这样的形势下,研究组加快了推广试用的步伐。
1960年春天,静安区卫生部门增加了"鸡血疗法"的临床试用单位,这些试用单位包括静安区中心医院、静安医院、上海广慈医院儿科、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上海公用医院等机构。
在领导看来,因为这是新生事物,不支持就可能犯错误。
这些医院甚至直接开设门诊,提供鲜鸡血注射。
"鸡血疗法"研究课题还得到了一级卫生部门的注意,领导亦提出了研究要求,研究组的干劲更大了。
但经过近2年的临床试验,研究组认为这个疗法,对功能性月经过多,消化性溃疡等病症疗效显著。但副反应问题也比较严重,一些人发热,还有出现了局部淋巴腺肿、荨麻疹等不良反应,甚至发生了较严重的休克。
研究组决定改变研究方向,逐步停用鲜鸡血注射,改用脱敏鸡血粉进行临床试治。
但是,这个研究方向遭到俞昌时反对,他坚持用鲜鸡血注射,并坚信疗效。
他私自印发了一本《鸡血疗法》,共辑录了一百多个病例,并且宣称,鸡血疗法属于国际领先的技术,中央已作出指示,要求只进行“秘密研究”,有相当多的内部人士私底下在悄悄使用。
静安区组织的"鸡血疗法"的立项研究,尤其是第二期的大规模临床试用,给俞昌时的宣传起到了背书效果。
俞昌时的小册子的传播很有效果,各地"打鸡血"现象在多地蔓延,逐步传播到南京,西安,北京,天津等17个省、市、地区。
这期间,一级卫生部门发现了这些大量的油印小册子,对宣传内容深表怀疑,责成上海调查此事原委,并妥善处置。
五
1965年夏天,针对卫生部的调查指示,上海市卫生局专门召开了一次专家会议。
与会人员有不少是生物医学领域的权威。既然中央要求调查,20多位专家们都说了实话,并且做出了以下结论:
1、鲜鸡血不安全,不推荐临床。特别是鲜鸡血治疗的均为慢性病,该病本身无多大危险性,而治疗却冒着危险更值得考虑。
2、远期疗效又不明显,且副作用较大,建议临床不使用,以免发生危险。
可能是为了给领导留点面子,他们下结论时也还留了点余地,称,还可对脱敏鸡血粉继续研究。
但此后,这项研究最终不了了之,且一直没有研究成果发表。
根据这份调查报告,卫生部门下发了《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要求各方禁止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病人治病,并劝阻群众打鲜鸡血的行为。对于群众中流行的各种传说,应进行必要的澄清和解释。
但余昌时对鸡血疗法的传播并未停止。
随后,十年探索期开始,鸡血疗法又得到了更高级别人物的肯定,到1967年,1968年,鸡血疗法成了一种真正的全国性的群众活动。
在全国各地,能看到这样的情形:清晨天不亮,卫生所或者医院门口排着长队,
每个人的篮子,或者网兜里,都装着一只大公鸡。
公鸡感觉自己命不久矣,发出刺耳的尖叫。扑棱着翅膀挣扎几下,有的还猝不及防的排泄。
可谓人群公鸡共一色,鸡屎和鸡毛齐飞。
随着打鸡血的流行,副作用越来越显现,不少人注射了鸡血后休克,甚至死亡。
慢慢地,人们认识到了危害,鸡血疗法的热潮退去,上世纪七十年代逐渐停止。
打鸡血也终于归入历史,成为笑谈。
参考资料:
《风靡一时的鸡血疗法》海*****
《1967年鸡血传奇》朱大可
《鸡血疗法医学研究始末》中华医史杂志 张云涵 熊卫民
===============================================================
北青深一度|深度报道:
告急的血库,与“找血”的患者
北京通州的献血车上,等待献血的人们
直到丈夫住院之前,王怡都未觉得,用血是一件这么“奢侈”的事——想让亲朋好友帮忙捐血,却发现身边的人都“阳”了;在网上发布求助信息之后,多位热心网友虽然主动联系,但符合捐血要求的,只有一个人。
随着寒冬到来、各类患者增加,以及各地陆续出现新冠病毒感染高峰,全国多地血库启动采供血应急预案中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多地血液中心满足不了医院的临床输血需求,不得不“卡着医院的脖子”,按比例减少血液的分发。
以往,当某地发生“血荒”时,采用从其他地区调血支援的方法,在这个冬天失效了。在深一度的采访中,各地血液中心纷纷采取措施缓解用血困难,不少地方的血液中心只能由员工上阵捐血,充当“应急血库”。
12月17日,国家卫健委《血站新冠病毒感染防控工作指引(第二版)》,修改“新冠患者康复半年内暂缓献血”的条款,确定新冠感染者转阴7天后即可进行献血。
医院给王怡丈夫开的优先用血流程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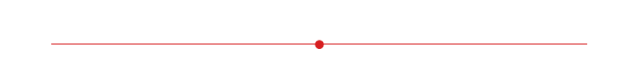
找血
“必须有人给你定向献血,给你优先用,你才能用上。”医生这样告诉王怡。
王怡的丈夫今年30岁,除10年前做过一次胃部手术外,身体一直很健康。但从2022年12月15日感染新冠后,久未发作的胃病突然又找上门来——12月17日起,他开始连续吐血、便血。挺到19日,挨不住了,才告诉王怡自己的情况。
王怡立刻带丈夫做核酸、挂急诊。12月20日,丈夫住进山西白求恩医院,彼时,他已经开始吐血块了。
住院两天,王怡眼看着丈夫的血红蛋白指数一路从70多掉到20,焦虑得睡不着觉。在办理住院手续时,医生就告诉她,以她丈夫目前的情况需要输血,但医院没给他输,“医生就一直说‘你们去找血,找到了才能输’。”王怡说。
医生给了她一个“优先用血审批单”,上半联是她丈夫的姓名、住院科室,用血需求,下半联要求写这次捐血人的信息:姓名、血型、本次献血量。当时,她丈夫需要至少400cc的A型血,医院要求“必须是1:1换”,这就意味着,王怡必须找到人去献400cc血,丈夫才能用上血。“不一定非得家属献血,也不要求A型必须跟 A型置换,但是必须是等量置换。”王怡告诉记者。
那几天,王怡自己也“阳”了,没法献血,她得找亲友去附近的献血屋献血。献血成功后,机器会自动生成一个系统码,把码条贴在审批单上,再把审批单交给血库,患者就能用血了。
但王怡向身边亲友求助了一圈,发现身边竟没有一个合适的献血人。根据医院最新的献血要求,最后一次新冠病毒检测或抗原阳性7天后才可以献血,但符合献血条件的亲友,恰好都不符合要求。
在太原找不到人“换血”,王怡甚至联系了外地朋友,但外地朋友纷纷把抗原检测的照片发给她,“他们说自己现在也阳了,过两天,等阴了一定给你献去。”王怡回复朋友,“急救呢,你这过两天是啥时候?”
12月22日,丈夫的情况陡然紧急,开始吐血。王怡实在没辙,只能请求医院协调先给丈夫输血。“他都休克了,医生抢救时给他输了400cc血。”回忆起那晚的情景,王怡胆战心惊。
丈夫抢救过来后,医生又找王怡,“你这两袋血是欠的,你还得继续去找血。”王怡说,除了急救欠下的这两袋,她还需要找更多血“备用”——丈夫随时可能需要手术,需要更多的血。
12月22日晚10点,王怡在微博上发布求助,随后陆续有人给她私信留言,但大部分热心网友都未满足“阳性七天后”的条件,真正满足条件的只有一个——一名没有阳过的大学生。确定对方满足条件的第二天,王怡和公公就带他去献血点献了400cc血。之后,公公还硬塞给了大学生1000元营养费。
血贩子跟王怡在社交平台上的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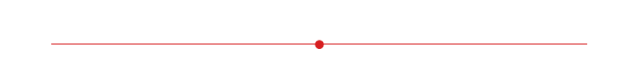
告急
“用血难”在这个冬天格外严峻。12月27日,太原市血液库存全线紧张,各种血型存量都在警戒线以下,太原市血液中心宣传科科长田斌告诉深一度,其实从11月起,血液就开始紧缺了。“一开始我们还有库存顶着,现在已经顶不住了。”田斌说。
据田斌介绍,一般情况下,太原市每日临床用血量约600—700单位,每单位200毫升,按照这个供血量计算每天应有300—350人,每人献血2个单位,才能满足临床供应。以12月25日的数据看,全天太原市采全血合计85人,165个单位,未到临床用血量的1/3。
“太原11月没有封区管理,但也是静默状态。”田斌说,那阵子太原街面上几乎没人,跨区交通需要有通行证才可以,人们也不出门。“献血的人都出不来了,可医院每天都在用血。”
11月底,太原市血库库存降到警戒线以下,库存告急。到12月29日,太原市血液中心传来消息,当日库存为2512单位。
田斌告诉深一度,血库没办法满足医院上报的用血需求,只好按比例减少分发,“比如今天某家医院上报血库需要100单位血量,只能批给80,让医院拿回去自己分。”田斌表示,这也是无奈之举,于是医院里一些临床上可以择期的手术,医生会建议患者推迟手术时间。
这并非太原一地的情况。青海省血液中心工作人员欧英估算,比起去年同期,血库库存出现了至少80%的缺口,“的确是卡住了医院的脖子,他们要10个单位,可能只给1个单位。”
“还有一种办法,比如你们家人用血,那就发动你周围的人去捐献。你们家要用,(找人)去献个血,你们家的事就解决了。”全国范围内,互助献血这一政策一直都在实行,对此,兰州市血液中心的松嵩解释道:“在献血法十五条规定了,应急的情况下,鼓励患者自体输血或者是家属进行互助献血。”
在兰州市,血库也在吃紧的状态下运行。兰州每天医疗用血量约为260个单位,血库能提供的治疗量维持在160到180个单位之间。血库缺血的直接原因是献血人数大幅减少。在天津,正常情况下,每天有500-600人献血,近期每天献血人数只有200人左右。安徽省毫州市甚至一度每天只有30多人献血。
血库告急,但在灰色地带,“血”的生意却异常活跃。为了找血,王怡在所有社交平台发布了消息,甚至到闲鱼上去发帖求血,一些血贩看到信息后联系了王怡,明码标价2500元400cc,不讲价,还告诉她“这生意在很多省会城市都可好做了”。
正在输血的患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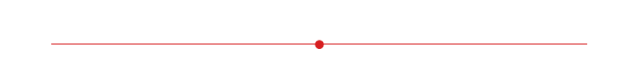
阳后6个月改为7天
“全国的血站都难。”江西省血液中心宣传科鲍丽告诉深一度,一个半月前,北京的血液中心多次给他们打电话要求调血,“突然之间,大家都不符合献血条件了。”
根据国家卫健委《血站新冠病毒感染防控工作指引(第二版)》明确规定,感染新冠病毒(重型和危重型除外),最后一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或抗原检测阳性结果7天后可以献血,并提出,接种基因重组疫苗与接种灭活疫苗后暂缓献血48小时的要求。
这一版本的《指引》于2022年12月17日颁布,在此之前,各地实施的第一版《指引》,要求新冠病毒感染者治愈后6个月内不可捐献全血和血小板。
鲍丽透露,从2020年到2022年,全国的血库大多是靠“拆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维持,“上海没血江西供,江西没血湖南供”,从时间上来看,各地的疫情暴发时间和血荒暴发时间是一致的,之前,因为各省市疫情未集中统一暴发,各地总可以通过区域调血来暂时周转。但到年底,各地集中暴发新冠疫情,这就大大增加了用血的压力。
根据四川省疾控中心近日发布的新冠感染情况问卷调查(第二次)结果显示,截至2022年12月26日,省内21个市州183个县(区、市)的158506名被调查者的感染率为63.52%。据江西省发热门诊哨点监测显示,12月9日至22日,全省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发热门诊诊疗量呈持续上升趋势,日均增幅23.45%。
鲍丽称,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未阳”的人,还是“阳康”的人,都会谨慎献血,“有些人‘阳康’了,但身体虚弱,有些人则考虑自己的亲人感染阳性,到时候也需要用血。大家只会在确有余力的情况下才会主动献血,否则都会再掂量掂量。”
深一度采访了多市血液中心,得到的反馈是,四种血型中,A型血处于相对紧缺的状态。采访中,江苏、山东、武汉等地血液中心均表示,库存A型血不到3天的临床医疗用量。
“全国可能都是A型血更缺。”兰州市血液中心的松嵩说。“如果放开使用,兰州库存中的A型血仅够使用5天。”
除去疫情缘故,冬季也向来是无偿献血的“淡季”,松嵩告诉记者,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三:首先,无偿献血占比很大的高校学生寒假放假,献血中心无法进高校集中采血;二是受寒冷天气影响,街面上的行人减少,献血车的人流自然减少;第三,各类疾病在冬季发病率更高,医院的用血需求也更高。
亳州血液中心工作人员上阵献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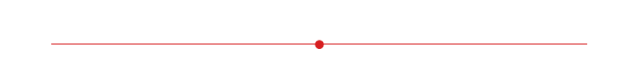
一二月份会最困难
为了增加血液库存,各地血液中心都在想方设法呼吁献血。兰州市血液中心与兰州市出租车协会合作,为有需要的献血者提供车辆接送服务。松嵩告诉记者,兰州市血液中心先给以前献过血的人打电话,询问他们的健康状况和献血意愿,必要情况下,派“爱心车队”去专程接送献血者。
毫州市中心血站专门安排了两个工作人员发短信呼吁献血,但毫州市献血中心主任田义感觉“效果不是特别好”。
除了挨个发短信、打电话,田义联系了当地晚报、电视台进行报道,鼓励市民献血。亳州血液中心还在自家微信公众号发文章,并做了广告牌立在各个献血点。“我们以前基本上不会用告急这个词,现在可以称得上是告急了。”田义说,他几乎把能用得办法都过用上了,甚至后期还可能会延长采血点员工的上班时间。
在松嵩的记忆中,上次发生血量告急还得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还是需要加大无偿献血宣传,有些人对献血还是抱有一定的顾虑,觉得有害健康。”他向记者解释道,“人体红细胞的寿命是120天,即便不献血,这些细胞也会在体内自然代谢。”
青海省血液中心动员员工和员工家属到头献血,十几年来,欧英已经献血14次了,她的爱人还获得了无偿献血金奖(累计献血8000毫升上),“基本上我们血站的员工和家属都是这样。”欧英说,“我们血站就是一个应急血库。”
这两天,青海省血液中心正在准备召开用血培训班,培训主题是“开源节流”。“开源”指得是广泛联系血源,“节流”是让医护人员们更加合理用血。“当患者的血红蛋白在60g/L时,就处于相对贫血的状态,此时需要输血。当内科患者的血色素达到了60、外科病人达到80,医院就不建议再输血。”欧英说。
王怡的丈夫还没出院,由于他的血色素尚未完全恢复,医院无法为他安排胃镜手术,这几天,他的血色素刚刚高于50, 医院就告诉王怡“不用输了”。
“现在的库存是历史以来最低的一次,没有这么低过,”欧英说,“最困难的是1月和2月,需要我们咬牙坚持过去。”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均使用化名)
================================
庄晓|我在南方住养老院:封院的日子
疫情之前,谁曾体会过养老院“封院的日子”。
三年疫情,扎实体验个够。
没办法,老年人是高危群体,应当保护好他们。尤其最近社会面放开后(机构依旧还在封院),养老院中陆续感染,死亡和重症的情况的确相较之前要严重许多。
这三年来,我们一直恪守制度及时封院。但个中心酸无奈,岂是寥寥数语可以表达。
院门口的监控连着官方系统,只要进出和经过都有记录。家属不能探视,老人不进不出,连所有员工也是24小时封闭在院内。更有甚者,有关部门在半夜来院突袭检查,数人头,看看登记在册的人员有没有都在院中。
这一切都是为了疫情防控,能理解。可还是挺难的,老人难,员工更难。
未曾封院的日子经常有家属过来探视,煲个汤送些菜,看着父母心满意足吃完。拉着手谈谈心,叙叙家常。人是情感动物,需要面对面的情感交流,需要接触和温度。要知道住进我们养老机构中的老人,当然也有时间长的,但平均在院时间不足一年,很多老人都是住进来几个月即离世,即便子女常来探望,也是见一面少一面。疫情当下,探视无望,甚至有机构被要求做玻璃“探视墙”。
2020年疫情刚开始时,还没有封院这一说。 “封院”,似乎是个时髦词语。但我们企业高层敏感度高,要求所有机构自行封院,那一年农历春节,院长和同事们都在养老院中过年。
也许封院管理曾经卓有成效,2020年,我们无一家养老院有老人和员工感染。看着国外老人的死亡数据激增,最后集中放弃治疗,甚至呼吁由老年人给年轻人让出呼吸机,我们不由慨叹西方社会中人性的利己与冷漠。
然而封院很快变得普通且频繁起来,不再是企业自行要求,而是变成一种行政命令。但凡当地发生疫情,养老机构第一时间就被要求封院管理。疫情严峻时分,院门口被搭上帐篷,日夜有人看守,所有进入物品都要进行24小时以上消杀。今年上海疫情期间,不少养老院中缺衣少粮,朋友甚至问我有无渠道给其他养老院买尿不湿。
刚开始封院时大家都很赞成,我们守护了老人的生命安全。然而三年来疫情一直反复,频繁且密集,总听说很严重,总听说离我们很近,我们一直活在听说中。然而切身感受来说,紧张过了头就成疲劳,疲劳重复,久而久之也就有点“皮”了,总之身心疲惫。
疫情刚开始时我曾感慨,我们身在养老行业如此幸运,毕竟那么多企业停工,餐厅停业,学校停学,但养老院可以封院管理,我们总不能把已经住着的老人遣散出去。在疫情最吃紧的时间里,很多地区都在静默,然而我们养老院总还是正常运营着。
封闭期间住在养老院也有不少好处,至少不用担心食物,虽有涨价和限量,但总归是有。那么多老人和员工住一起,有工作、活动、交流,不至于一人或一家独立隔离,与世隔绝的感觉。
然而封院的味道很快就变得不一样——当其他场所封闭七天、五天、三天就可以解封时,养老院的解封却变得遥遥无期。每当一个城市疫情来临之时,养老院成为了总是第一时间封院,最后才能解封的场所。
院长无奈,老人无奈,员工更无奈。有时封得太久,所有人都仿佛失去了力气,从开始还盼着解封到后来已经不再期望。每次一听说有疫情就知道必定要封院,员工甚至被迫在院中常备行李。大的院际还好,有住宿条件,小的机构员工只好临时住进仓库。
今年上半年疫情最严重时,我们全国各地的所有养老院都被迫封院,老人只出不进,员工纷纷离职,居家业务不能开展,社区服务中心统统停业,损失惨重。
有养老院从情人节封至端午节,员工穿着羽绒服住进院里,到穿短袖的季节还没能出来。实在没有衣服,社区捐献了一批。终于等到解封,好不容易招来的员工跑了大半。有员工对院长说:“我也有家庭,上有老下有小,我照顾了别人的父母,可谁来照顾我的父母孩子呢?”话已至此,我们也不知该怎么挽留她,一点办法都没有。
招人本就不易,院长欲哭无泪。院长压力最大,防疫、入住率、员工都压在身上,沉甸甸的担子,没有退路。
今年十月起又迎来第二波长时间封院,至今尚未解封。员工穿着短袖进院,在漫长的等待中迎来寒冷的冬天。
总是封院,老人不方便就医,家属不方便探视。有不少家属都没能见到至亲最后一面,遑论在临终前多陪陪他们。有老人在疫情期间过世,但子女所在城市静默,连葬礼都无法参加。疫情之下,太多伤痛。
此前我提过一些对养老院封院的看法,对于封院,反对的、赞成的都不在少数。诚然,作为养老机构,我们比任何行业都更想保护老年人,更应该对老人负责。但是封院真的能解决所有问题吗?在外部环境越来越宽松,民众终于能感到些许自由时,养老机构的封闭管理却越来越紧,甚至安排人员在院门口蹲点。有次院长因运输尿不湿的车辆进院被批评,可老年人能不用尿不湿吗?一天都不能。
2020年初疫情伊始,我们企业在没有要求的情况下率先封院,甚至组织志愿队去支援武汉养老机构,那时所有员工都觉得,身在养老行业,保护老人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武汉都能去,封在院里怕什么?只会更安全,每个员工都充满力量。支援武汉之之际,甚至有老人给志愿队捐款,他们说:“如果年轻几十岁我也希望能去武汉,但现在我们年龄大了,所以尽量呆在院里,不给国家添麻烦。”
那时候封院,大家总觉得熬一熬就会过去,毕竟眼下的困难而已,直到终于迎来被
正式要求封院的生涯。
三年来,每一年,每一月,甚至每一天,不知何时就会被封,不知何时解封,只要一有疫情就封。无人进出,无人探访,无人问津,从无数个熬一熬,坚持一下就过去了,到最终多少人见不上亲人最后一面。员工也实在熬不住了,半岁的孩子失去母乳,很难招聘的护士留着泪对院长辞职:“我连自己的家庭都照顾不了,谈什么去照顾别人的家庭?”
三年了,养老院一直都是这样封院过来,年轻人或许还有好多个三年,而对于老年人而言还能有几个三年呢?今年封院的日子超过了一半时间,几个院里过世的老人达数百位。
封到最后,真的麻木了,即便家就在马路对面也不能回去。总是封了、解封,又封了,遥遥无期,看不到尽头。有家属向上反映,得到的反馈是:“你们去投诉吧,我们也没办法,都是要求。”封院期间,院里不能收老人,家属也不愿意送过来,经营之差,成本之高,这些就不提了。从事养老行业,本就高风险低收入,但最怕的是没有未来。
最辛苦的当然是院长。我与院长愤慨:“老人活到这个年纪,也都想明白了吧?他们怕的不是病毒,而是在有限的时间里,还不能多一些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
院长感慨:“说是这么说,真感染了,家属怕又不是这个态度了。”
凛冬又至,但今年我身在南方其实未能感受到冬天的寒冷。然而社会面的放开,猝不及防的疫情,风暴一般席卷了所有的养老机构。我们所有院际无一例外都被感染,不管是员工还是老人,即便我们仍处在封院之中。
疫情对老人的残酷反而真正体现在了它看似被宣告终结的时候,许多老人重症,心衰,血氧饱和度不够,高烧、无法进食,联系家属送医,家属放弃治疗的竟不在少数。听来无情,但有些家属给出理由——仿佛这位老人活得太久,早已耗尽家中所有资源精力,他们再也照顾不动。加之老人身体状态糟糕,他们甚至觉得放弃对彼此都是一种解脱。所以人老了——到底变成了什么?只是没有价值的沉重包袱吗?连续封了三年的院,在最后一刻连续溃败,我们究竟又守护了什么?
然而我想,我们还是要努力记得那些美好的东西。即便是封院,也并不总是一无是处。今年封院期间,我们开张了“忘不了餐厅”,我给院落里搭建的连廊命名为“时光长廊”,我和老人们一起过感恩节,我在员工聚会上唱起“萍聚”。
“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
“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对你我来讲已经足够。”
南方的养老院,我想至少我曾经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