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柬埔寨电诈风云:淘金、丧命与复仇

撰文|鲁茜茜 编辑|马可
出品|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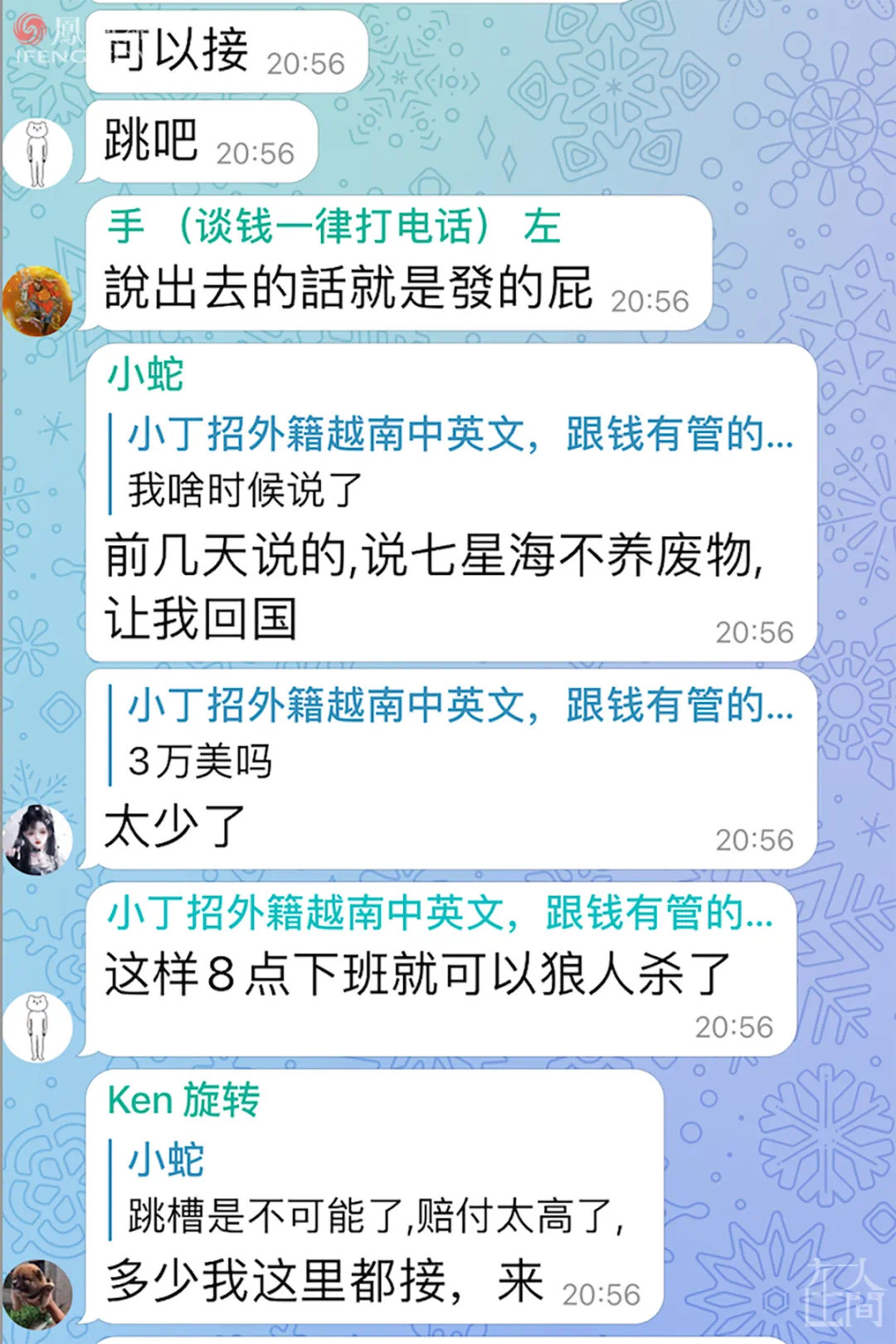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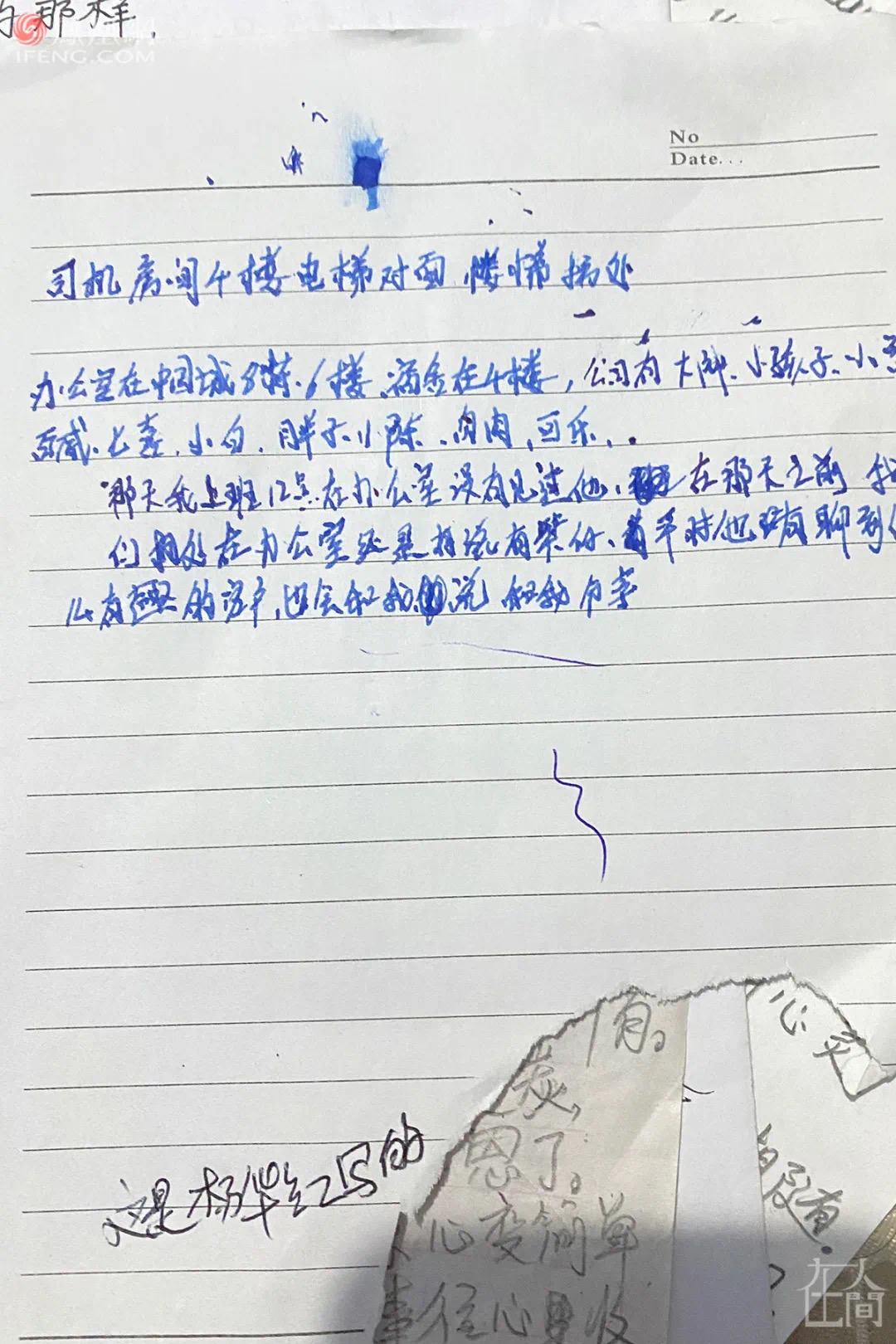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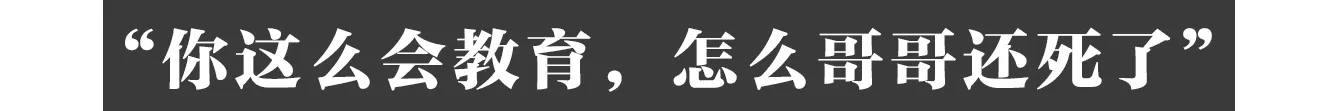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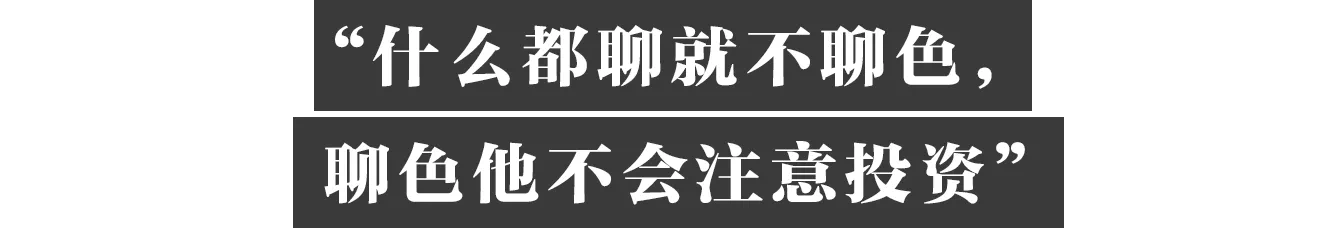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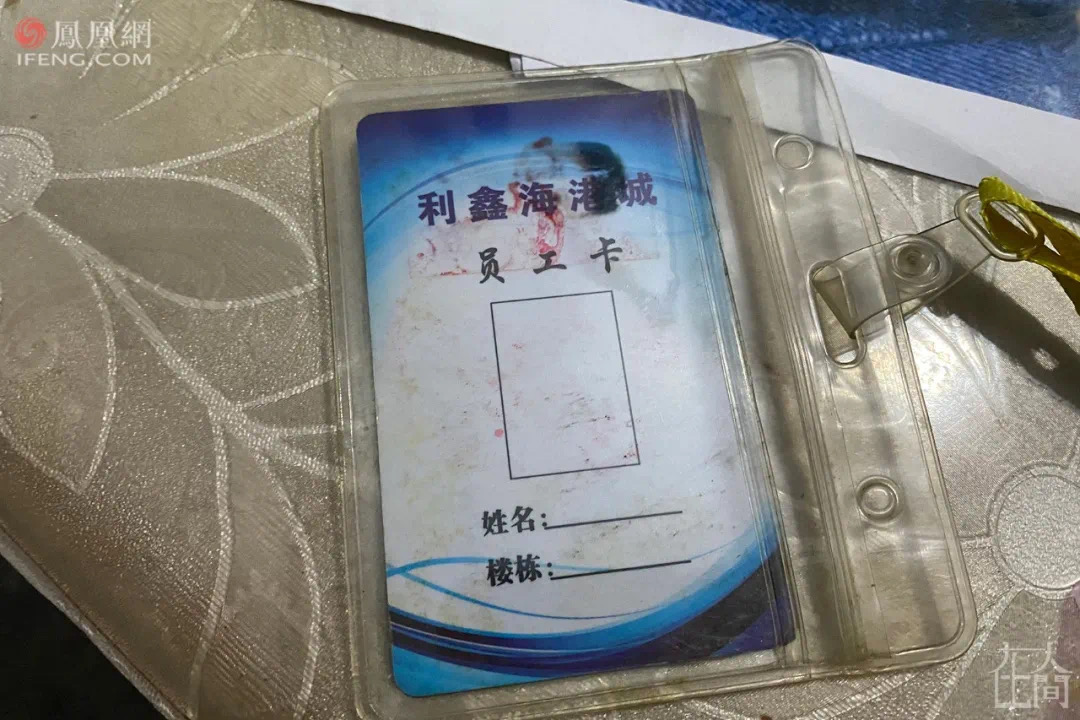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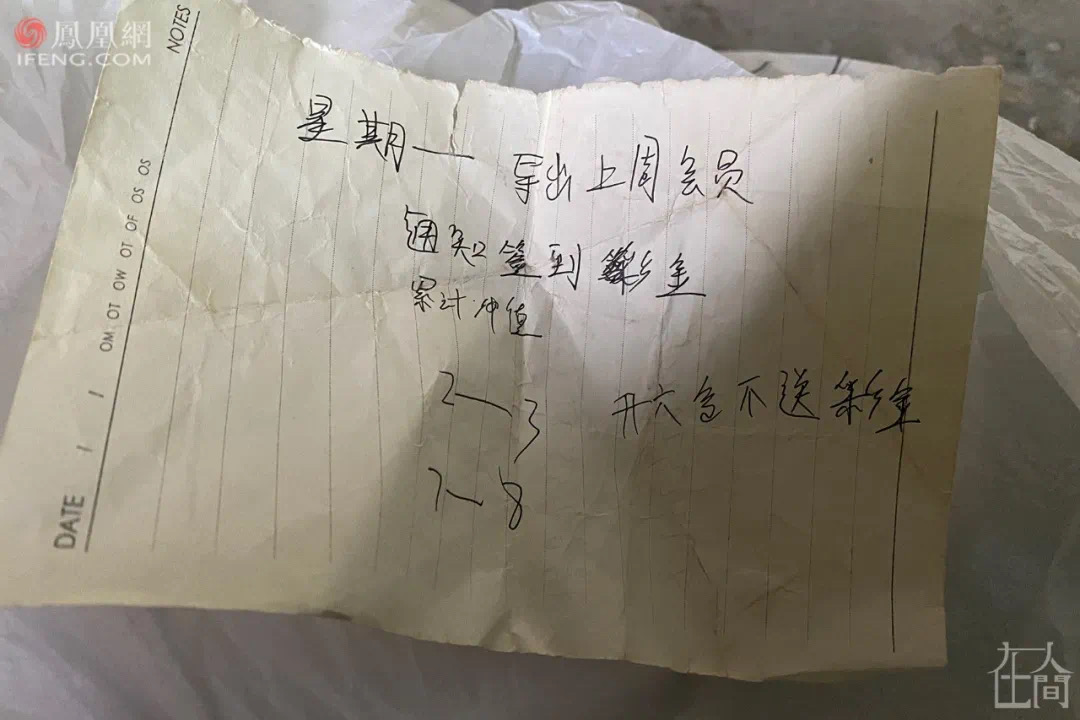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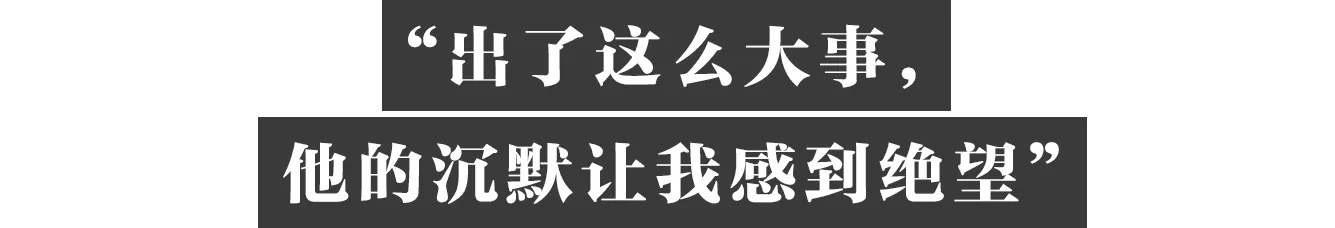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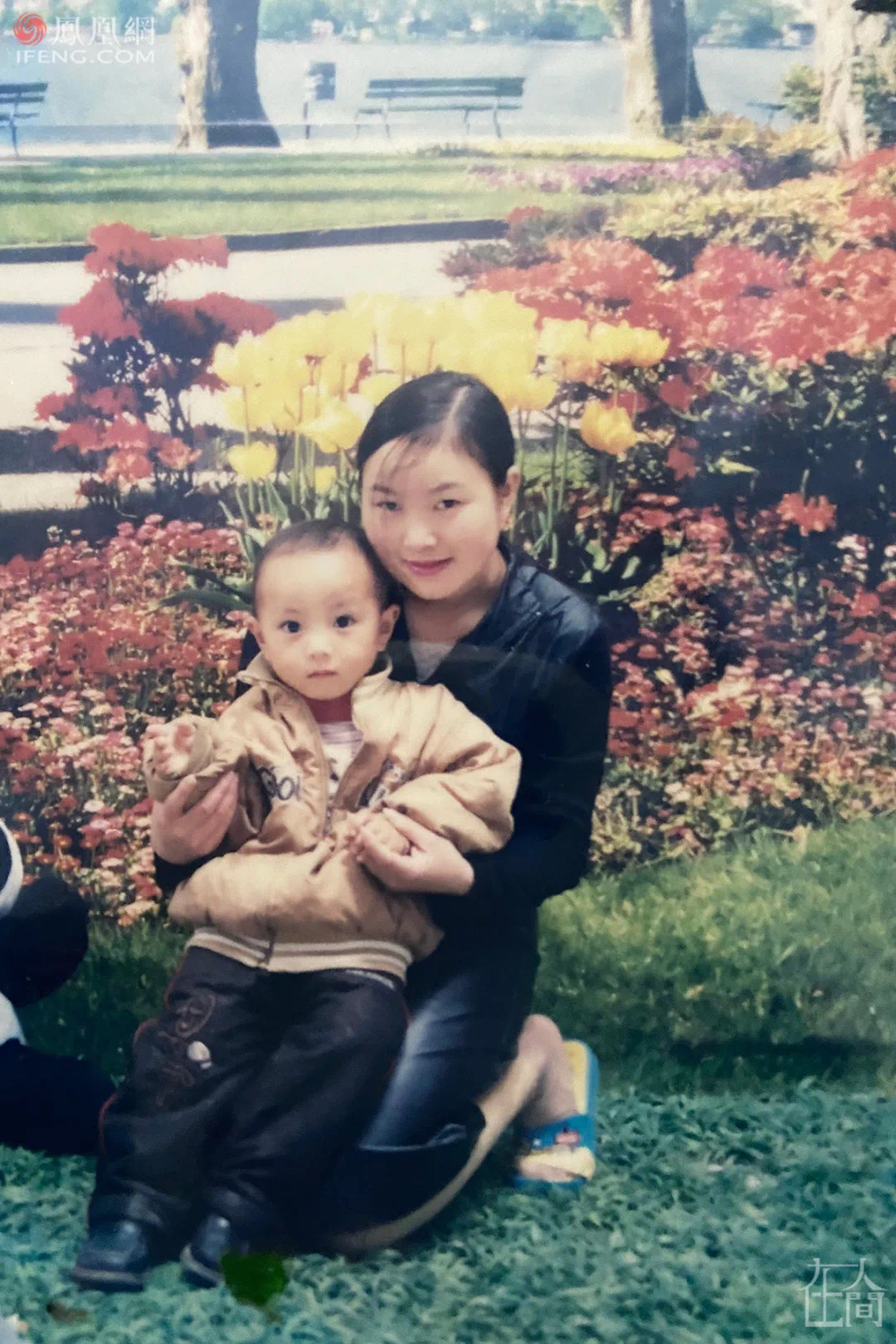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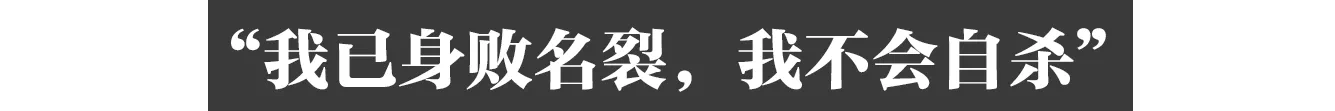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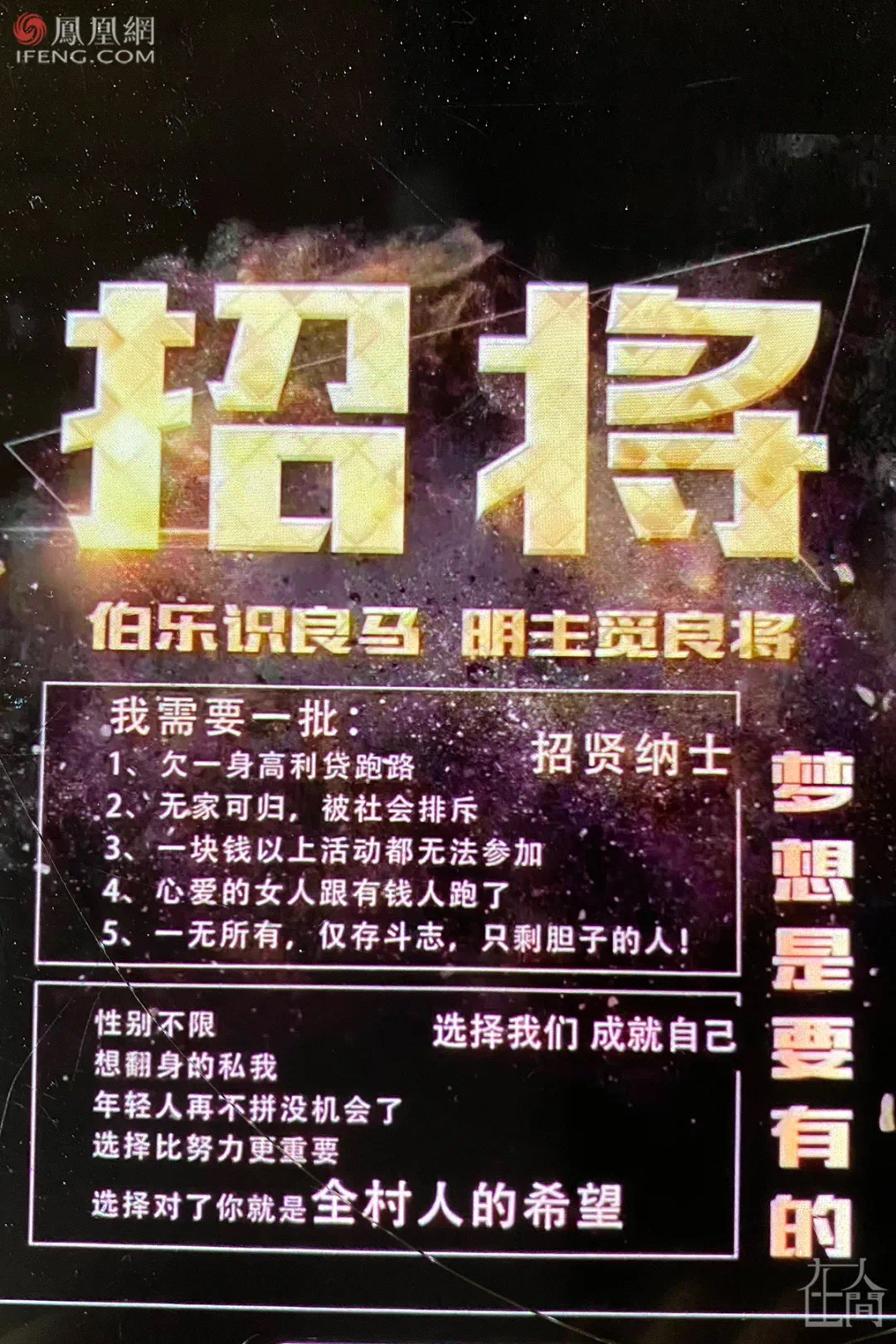



===============================================================
宣传队

弄迈的知青分别拥有手风琴、口琴、提琴、二胡、笛子、吉它、八弦琴这几种乐器,会玩的几人兴致来了便聚在一起合奏,所奏曲目多半是大家喜欢唱的那些歌曲,比如外国民歌二百首当中的歌。他们的水平还到不了分声部的演奏,只能是全体“预备起”的大齐奏,但因为长期一起合练,配合算得上有板有眼的,静夜之中听来,还颇有点韵味。
听到公社要举行文艺汇演的消息后,女生们强烈提议,老社同意,弄迈也成立了一支以知青为主的宣传队,动员玩乐器的男生全体参加,组成乐队,又由那几个能歌善舞的女生和她们训练的毕少们组成歌舞队,还吸收了相帅和鳗鱼,让这俩人专唱傣族歌曲。鳗鱼唱得不怎么样,相帅却有惊人表现。她的嗓音天生就好,音域宽、音色纯正,唱起傣歌来,不知倾倒了多少毕冒。后来县里、州里的文工团都来要过她,可惜这女孩不愿意走出家门,最终埋没了又一个“才旦卓玛”。老社很宽宏地给了他们一个月的脱产排练时间,宣传队也很争气,排出了一组节目去参加公社的文艺汇演,宣传队着实为弄迈争了点光,汇演时以绝对优势技压其他寨子的宣传队,一炮打响,获得了全公社团体奖第一名。
汇演后,附近好几个寨子都来邀请弄迈文艺宣传队去他们那儿演出,弄迈汉傣两族的年青人快乐的“走穴”演出就此开始。
到其他寨子里去演出不比在公社演,由于台下没有领导坐着,面对着的都是本乡本土的乡亲,演员心理状态极其放松,越演越随便,甚至与场下观众大开玩笑,全场气氛极为活跃。若是去的那个寨子里也有玩乐器的知青,就要邀来加入进知青们的小乐团,并且要出独奏。有唱歌的,要拉上台唱上几首最拿手的。有跳舞的,也必须上台表演献艺。傣族最爱对歌,每个寨子的赞哈(歌手)与弄迈的歌手对歌(他们对的歌当然不是那些革命歌曲,而是世代相传的情歌)成为最受傣族欢迎的节目。而知青们最喜爱的节目,便是由小乐队演奏或伴奏的那些“黄歌”,奏到兴头上,还会来个两寨知青集体大合唱。
女生们带领罕俊等毕少跳的舞蹈则比较合毕冒们的口味,傣族毕少身材苗条,跳那些《北京有个金太阳》、《舂新米》之类的舞蹈还很有点份儿。
每次演出的压轴节目是集体跳傣族舞,由当地傣族敲起锣鼓,所有演员包括小乐团成员都下到台下与观众同乐,两个寨子的人围成大圆圈,中间燃起一大堆篝火,起码要跳上个把小时才结束。
此时此刻,与其说是演出,不如说是两个寨子傣族和知青的大联欢。
弄迈宣传队越演越火,名气越来越大,前来邀请去演出的寨子排上了队。
到后来连境外的寨子也一再来请,经过层层请示直到由州里批准,才准许他们去演了几次。
第一次去境外演出之前,县里管宣传的人来审查节目。那是个面无一丝表情的中年人,姓胡,看完全部节目后,他突然冒出一句:“把你们加演的那些节目全部来一遍。”他所指的加演节目,显然就是那些小合奏的歌曲。
见知青们想找搪塞的话,他干脆挑明:“没事,不会给你们上纲上线,就听听你们有多高水平。奏吧,先奏个《小路》。”
于是,乐团专门给他来了次汇报演出。这位老兄先是跟着哼哼,到了后来干脆放声高唱,他唱歌的水平绝对压倒知青歌手,是那种真正的专业级的洋嗓子。听他唱《三套车》、《重归苏莲托》这些歌,真是一种享受。
知青们很想跟他结识,但他可能有所顾虑,过完瘾就变回冷冰冰公事公办的模样。打着官腔说了个别节目要如何修改之类的话,又补充说:到那边不许加演。说完就走了,以后再没来过。知青们到县城去见到他,跟他打招呼,他只点个头就不再搭理人。
宣传队既然给弄迈争了光,队里对宣传队便很是照顾,队员们凡有演出就不必下地干活,演出、排练都算出工,而且记最高的工分。
虽然没有出场费,也没有门票收入,但出去演出仍有不少外快。照例,邀请人得管全体演员的晚饭和夜宵,演出时还得给乐队准备好烟、茶,演出之后则会送上两刀烟丝,几大块碗状的红糖。烟当然归乐队,糖则归舞队,傣族队员自然不会要,东西就都到了知青们手里。
有如此种种好处,当然不能把那些既不会乐器、又五音不全、还手脚僵硬的南郭先生们丢下不管。凡有演出,全体出动,一个也不少。去的人都想法给派点活,光是敲木鱼的就安排了3个,还给两个擅长模仿的每人发一支不贴笛膜的笛子,让他们摇头晃脑卖力地假吹。
如此一来,弄迈宣传队的乐队阵容大增,人数已经不亚于专业文艺团体。
盲目扩张的结果,是这大锅饭自然吃不长。扩大了队伍后,没演几场,秋收在即,老社率先发难,要大家讨论是演戏重要还是种田重要,讨论结果当然是后者重要。于是明确规定,宣传队今后只能用业余时间排练演出,便宜工分也被取消了。
其时,各邻近寨子也差不多都去演遍了。虽说又排了些新节目,可人家一想,为了那么个把节目请这么大帮人吃饭似乎并不划算。再说人家也要忙秋收了,于是那些节目也就算白排了。
没人来邀请,宣传队便散了伙。
那两支没笛膜的笛子却成就了个音乐天才。笛子的主人——那两位当代南郭先生,看到再不能靠它混饭吃以后,随手将它送给了小胖墩。小胖墩贴上芦苇芯里的薄膜,在大草坪上放牛时成天地吹。刚开始吹时,连那些水牛、黄牛都受不了,见他就逃。这小子相当有毅力,有空就练,没多久居然无师自通,吹得满像点样子了。后来,他飞快地超过启蒙老师,知青们又专门找来名师辅导他,他的技艺便突飞猛进,很快便技压县文工团笛手并取而代之,成为本寨唯一进县城吃皇粮的傣家子弟,不过那已是知青走后的事了。
=======================================================
串门

晚饭后,小印度早早就来到男生宿舍,催着大家跟他走。路过女生宿舍(社管会)时,老蒜、老沙、老平正坐在凉台上聊天,小印度一招手,她们也就应邀参加了这次外事访问。
小印度家离寨子口不远,竹楼不算很大,院子却很宽。到了那儿,鳗鱼已经等候在院子门口,引领着知青们上楼。
傣家的竹楼很实用。楼上住人,楼下半边是牛栏,半边是厨房。宽大的木楼梯通到楼前的凉台,从凉台进入楼上厅房正门。
上楼后,小印度示意知青们脱鞋进屋。进门之后,一位大叔面对大门站在火塘旁,对着知青们不断辑手,口中喃喃有词。另有一位大妈躬着腰站在门边,双手垂膝,不住点头,姿势与日本妇女迎宾一模一样。知青们也急忙合手点头,只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客厅很宽大,至少有30多平方米。除正中距墙1米的地上嵌有个方桌大小的火塘之外,屋里没有任何家具。地上铺着竹皮编成的凉席,光滑洁净。
整间屋除了朝南的正门外,另外还有3道门,北边的两道门一道通向里屋,另一道是后楼梯,通向楼下厨房,西面一道通往一个小阳台。所有的门,包括正厅门,除里屋门挂了块布帘子外,都只有门框没有门板。
小印度让男生靠右、女生靠左坐到火塘边,他和鳗鱼也坐到右边。
大妈走到火塘边时的姿态很奇怪,她一直弯着腰,双手按着统裙下摆,碎步顺着墙边绕个圈,走到火塘左边,双脚放在身后,扭着身子坐下。她要女生们也学她的坐姿,女生们坐不了片刻便撑不住了,仍换为正面打坐式,她也没再管。
主宾全都坐下后,靠手势和推测进行困难的交流。
大叔、大妈显然是小印度的父母,鳗鱼是他的哥哥,可两人却长得不大像,相似的地方是眼睛都很大,后来才知道俩人是同父异母兄弟。
小印度把知青们的绰号介绍给家人,他们也就这样称呼知青们,知青们则按他们所教发音,称呼大叔为“屋弄”,大妈则称“篾巴”。
火塘正中放着一个大铁三角架,上面架着一把铜壶。壶里的水已经开了,冒着热气。大妈将铜壶提下放在火塘边,又将一个铜盘子放到铁三角架子上,随即从墙边一个竹筒里倒出一大把茶叶,放在盘子上,用一根木夹翻动着炒,一会儿满屋都弥漫着茶叶的香气,然后她将炒热的茶叶倒入一个放在三角架旁的小陶罐内,提起铜壶,将沸水倒进陶罐,听到“噗”的一声爆响后,她便迅速地用一个竹刷似的盖子塞住罐口。完成了这一系列复杂动作之后,她从那带嘴的小罐中,将浓绿的茶汁倒入几个核桃大的小茶盅里,然后将小茶盅一个个递给她丈夫,大叔用双手端着递给男生们,大妈也递给3个女生每人一杯。
知青们急忙双手接过杯子,端着,但没敢马上就喝。心想,这么喝茶也太小气了,但没敢表示出来,可能这就是所谓民族风俗吧。
主人们也各斟一杯,也端着,不住示意让知青们先喝。
老豆忍不住了,端起小杯,一口饮尽。知青们正想效仿,却听见老豆呼呼直喘粗气,看看他,嘴张得大大的,就像刚吞下一整个最辣的“涮涮辣”(一种当地特有的极辣的辣椒)。大妈咯咯地笑了起来,小印度他们也笑了。
大叔示意知青们看他,然后将小杯端到嘴边,轻轻地啜了一小口,跟饮酒似的。
老地也照样喝了一小口,香气很浓,但茶水极烫,味道又苦又涩,怪不得老豆会那样。刚想皱眉头,忽然觉得口中生出一股清凉、甘甜的津液,一直顺喉咙往下流淌,一丝丝沁入心肺之中,舒服极了。
其他人的感受可能与老地相同,大家开始议论起来,赞不绝口。
后来知道了日本的茶道、大理的三道茶、福建的功夫茶后,老地想过,如果哪天有了钱,就搞个傣家的茶室,起名为“傣家烤茶”,给真正会品茶的人喝。
大叔让知青们卷毛烟抽,知青们摇手示意不会。他以为知青们是不会卷,就慢慢地卷,示范给知青们看。卷烟的纸可能是特制的,很薄,三指宽、比一支香烟稍长。那细细的烟丝颜色金黄,闻起来很香。于是,男生们不顾女生们的谴责,每人学着卷了一支。才抽第一口,自称刚上中学就会抽烟的老猫便不由得呛咳起来,其他人更是呛得不得了。这烟闻着香,抽起来却辣得要命。
以后很长时间,男生没敢再学抽毛烟,后来是先学会抽香烟了,才敢再尝试抽毛烟。
喝第二杯茶时,后面楼梯吱吱响了起来,一个毕少抬着张簸箕似的小竹桌子走上来。男知青们认出她是昨晚担水的3个姑娘中的一个。
这个毕少是小印度的姐姐,叫罕俊,个子很高,肤色只略微有点黑,长相有点像鳗鱼,说不上漂亮,但那双大眼睛和两只酒窝很有特色,笑起来样子很可爱。她一点不拘束,放下桌子就跟女生们挤在一起,两手灵活地比划着跟知青们沟通。傣族姑娘似乎对手势语言的理解力特别强,自她来后,两个民族的交流变得容易多了。在她的教导下,知青们学到了好多傣语。
小桌上放满小吃,有花生、牛肉干、木瓜丝、一些不知名的酸果子和用芭蕉叶包成小包的糯米糕。知青们逐样尝试,好吃的就一扫而光。
知青们注意到,火塘里烧的全是干牛粪饼,烧时几乎不冒烟子,用吹火筒一吹,浅兰色的火苗就冒出来,比木炭还好烧。傣族家里不用蚊帐,就因为牛粪烧的轻烟中有驱蚊虫的气味,估计是牛吃的哪种草在起作用。这牛粪是傣家的高级燃料,怪不得大草坪上的牛粪都给做上了标记。
玩到夜深了,知青们才告辞回宿舍。
以后,知青们晚上常到傣族家串门。只是大家逐渐分为2、3个一伙,各去一家。男生们自然喜欢到有毕少的人家去,到不是有所企图,而是跟毕少们交流既容易,又很有趣。
老地经常去的是老社家,到不是因为老社家有个漂亮女儿相帅,而是老社夫人对老地特别好,有什么好吃的都来叫他。酋长则去小印度家最勤,知青们瞎起哄说他对罕俊有点那个,他也不恼。
知青们刚来时,傣族老乡们传说知青是武斗造成的孤儿。怪不得来的那天,傣族大妈们对知青们说话时都带着极其怜悯的神情。据说这些大妈们在两天之内,就将全体男知青分人到户,私下许配给有毕少的各家了,还为谁家分哪个争了起来。本来老社夫人是抢着认领酋长的,说他是知青的头,正好她丈夫也是头。
后来她却改变主意,非要认老地,也不说为什么。有好几家争着认领酋长不奇怪,也许是他长的高大而且英俊吧。而争着认领老令的也有好几家,这难免让人有点妒忌,这个说句话都会激动得手抖的书呆子,凭什么受到众多毕少的垂青?
后来知青们傣语很熟练之后,才从她们口中知道,她们喜欢老令捂着嘴轻轻地笑的斯文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