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缅北“防疫”28年,与诈骗集团抢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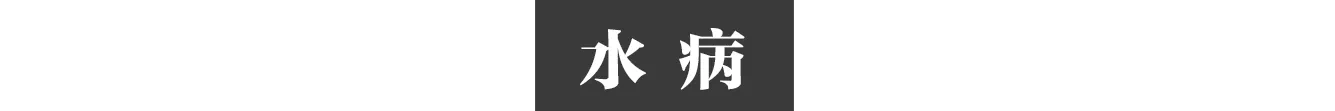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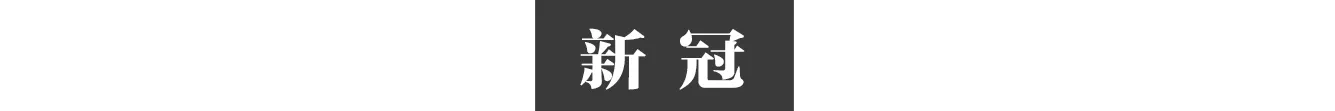
张光云和医疗队的同事把城区街道和各单位采集核酸样本装进专用的冷藏箱,再送到国门口岸,交由相邻边境县的卫健委防控人员取走样本在国内检验。检测结果出来后,张光云和医疗队还要把数据录进电脑。办公室的灯经常亮到凌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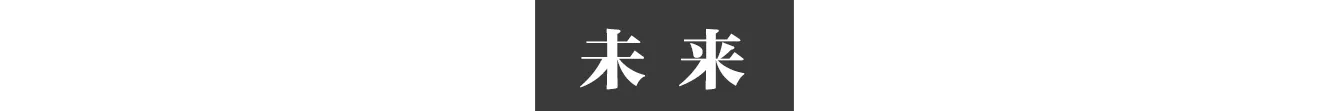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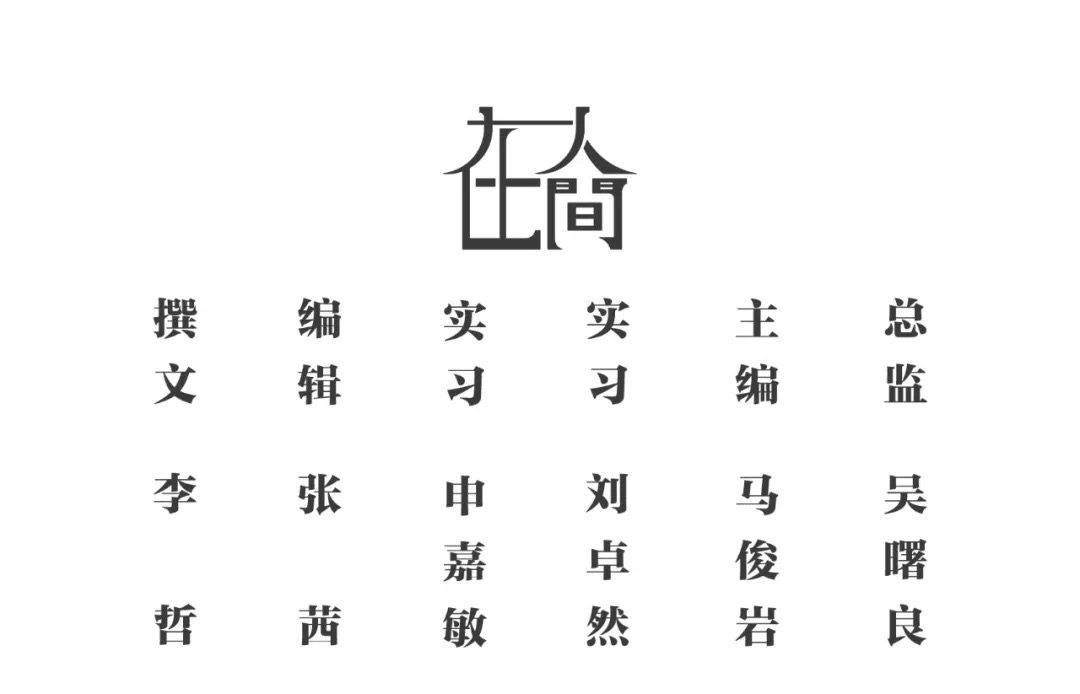
=========================================================
在金三角毒区开餐馆的中国夫妻

前 言
他的日常工作不止讲课,还要随身带着匕首,有时甚至是枪支,防止疯魔的毒贩靠近学校;平常拿着麻袋去镇上给学生们乞讨粮油米面,出门吃饭前还要检查有没有罂粟籽。
黑叶在金三角遇到许多朝生暮死的人,凶残的毒贩、不要命的赌徒、被拐卖来的少女,渐渐让他成为一个对危险气味异常熟悉的人。
认识黑叶,纯属偶然,他在全民故事计划上刊发过好几个故事,我们想让他将金三角的故事写下来,一是记录,二是警惕更多的人。
这是《哭泣金三角》系列的第3篇。
一
遇到那对中国夫妻纯属偶然。那天,我们几个人走进一间门面敞开的小店,小店是用蓝色彩钢铁皮建的,有十几平方米,很简陋。店里有两张简单的木桌,几把塑料凳,桌上摆着几种调料瓶,和四川卖牛肉粉的样子差不多。
其他几个队员要吃米线。自进入金三角后,他们已经被米线中的核心调料罂粟籽迷住了,而我却万分警惕这种罂粟的副产品。
曾经几个当地人告诉我,没成熟的罂粟籽能令人上瘾,成熟的罂粟籽没事。但我还知道,没成熟的罂粟籽放在汤里更香,更回味无穷。
店里的老板娘三十岁出头,白净利索,俏丽漂亮。几个队员中,只有我来自中国,当我告诉她并且强调,我的米线不放罂粟籽。她看了我一眼,说汤里不放罂粟籽就没吃头了。
我有些惊讶:“您是北京人?”
她犹豫了一下:“您听出来啦。”
“我在北京上过学。”我说。
煮米线的男人看我一眼。我问老板娘:“你俩是一家的吧?”
“嗯,我老公。”
就这样,我和这俩口子有了来往,而且越来越熟。每次我去吃饭都带些水果,有时还带点治腹泻及其它消炎药给他们——当地特缺西药。
老板娘叫白茜,祖上是旗人,她老公叫刘建洋。他俩两年前从北京一路辗转到了金三角,在镇上开了这样一家小吃店。镇上挺热闹的,卖各种东西的商店也多,我还碰到几个开杂货店的中国人。
在和白茜俩口子闲聊中,我断断续续得知,他俩小时候同在一个大院长大,从上机关幼儿园到小学、中学,不是一个班就是在一个学校。
白茜说她和刘建洋早恋,学习一塌糊涂,别说考大学了,中专都考不上。刘建洋说白茜早熟,初中就勾搭他,哪有心思学习。
白茜和刘建洋混完高中后,在双方父母的失望及无奈下,两个人凑了些钱,在动物园服装市场倒腾服装鞋帽。白茜说,什么都卖,名义上是外贸品,实际上都是浙江和福建的高仿货。
到动物园市场迁走前,白茜和刘建洋挣了些钱,买了车,也出国旅游过几次,北京人的玩法都经历了,前海和工体那边的酒吧也蹿遍了。
白茜说:“做生意,东蹿西蹿,就是活着呗。”
北京人说话特逗,性格又开放,见多识广,和白茜俩口子聊天,率性又舒服。
只是聊的时间长了,他俩容易疲倦,一打哈欠就溜出去,过一会儿又回来。再回屋里时,俩人精神饱满,眼睛里又放着精光。
二
在乡下忙了几个月,我走了近百个村庄,所到之处,见到的人都十分忙碌。自金三角在二十多年前宣布禁种罂粟后,在国际帮助下,香蕉、咖啡、大米及玉米成为金三角传统毒区的替代作物。
在我协助某救助组织进入金三角执行项目前,培训专家告诉我,金三角的罂粟种植始于一百年前,在气候温暖的金三角地区,罂粟种植逐渐扩大,到了上世纪中期,罂粟的种植面积达到一百万亩。
在金三角,向北至中国云南边界,向西沿萨尔温江至缅甸掸邦,有近千万人口靠种植罂粟为生。由于罂粟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作物,导致其它农作物品种单一,农业技术十分落后,还处于刀耕火种阶段。
“一百万亩罂粟不仅让那里的人成为瘾君子,也让全世界深受其害。这当然是英帝国对世界的‘贡献’,它导致的灾难远比核武器严重。”
实际上,罂粟种植并没有在金三角绝迹。几年前,据卫星观测,这里至少还有二十万亩罂粟种植地。专家告诫我们,这里有枪支、妓女还有毒品,但唯一不能去碰的是毒品。
他让我们一定要小心,在金三角围绕毒品的犯罪无处不在。
正式开展工作后,有一次,我们住在一个村庄,我和另外几个队员住在一个竹制的屋子。天黑后,我们就入睡了。
不知什么时候,我被不断推门的声音惊醒。我用力拍床提醒同伴,从枕头下抓起匕首,跳下床躲在门边向外看。
月光下,一个如风干的香肠样的男人,像游魂般在门外东张西望。我对提着棍子凑过来的同伴说,看样子像村子里吸了毒的村民。
吸了毒的人,精神亢奋地到处乱逛,犹如丧尸。我打开门,用匕首顶在那人的胸口,示意他转身,再用匕首顶着他后背送出五十米远。
还有一个白天,我们在一个有寺庙的村庄作业,突然来了几十个全副武装的军人,村子里的男女老少也惊恐地向寺庙跑。队长问恐慌的村长发生了什么事,村长说寺庙里的大佛爷不见了。后来军队和村民们搜山,在寺庙后边的山崖下找到了大佛爷的尸体。经过询问,几个小和尚说,大佛爷吸毒后,从山崖上跳了下去。
队长很有经验,十分肯定地说,大佛爷吸毒一定有些年了,过量吸毒,导致精神错乱跳了崖。
在缅甸,和尚的地位很高,没人敢杀和尚,何况还是一个大佛爷。
三
忙了一阵,完成阶段性任务,我们又回到镇上驻地休整。
这天,我来到白茜俩口子开的小店,见她正一个人坐在店里看电视。我问她,“刘建洋呢?”白茜看了眼后边的屋子说:“他忙点事。”
我和白茜聊了会儿,她有些心神不定,像有什么心事,眼睛总是不时地向后边的屋子瞟。
过了约有一个小时,刘建洋和两个男子走出屋子。那两个男人警惕地各自看了我一眼,和白茜笑着说了几句,走了。
刘建洋拿了两罐啤酒递给我一罐。我问他最近生意怎么样,他说还那样,就是混日子,吃穿够了,想发财肯定没门儿。
说了会儿话,我见他俩话不多,白茜总是拿眼瞟刘建洋,我以为他俩口子在闹矛盾,便识趣地告辞回去了。
过了几天,我们发补给,东西都是泰国来的,有鱼和牛肉罐头,还有咖啡、糖和饼干什么的。我装了一袋,打算给白茜俩口子送过去。
走到白茜的店,见她一个人在忙。我问刘建洋呢,她说他出去两天,有点儿事。我看她一个人忙不过来,就说我来帮她煮米线。
这天是赶集日,店里吃饭的人络绎不绝。
我说:“光是米线鸡蛋加猪皮也太单一了,上点牛肉面、包子饺子能多挣些钱。你俩都是北京人,弄这些还不是小菜一碟。”
白茜说:“金饺子银包子谁都知道利润大,但我那口子嫌费事。”
我告诉白茜,在大其力那边有家中国人开的饭店,油条、包子饺子还有馅饼稀粥,一色儿的中国特色,生意很好。
白茜说想挣钱就得累,挣的少也清闲。人活一辈子,差不多就行了,有吃有穿没心事也挺好。
她接着笑着说:“像你,每个月拿着二百美元津贴,跟着那些医生跑缅甸来为人民服务,不是也没图钱么。”
“你们北京人就是不一样,思想见解和南方人不同。”我听后笑了笑说。
忙完最后一拨客人,白茜双手扶腰抻了抻,满脸倦容地说让我照看一下,她快步走向后院。
过一会儿,白茜精神焕发地回来了。我看她像换了个人,好奇她进里屋到底干了些什么,但也不好意思多问。
忙了一上午,我还没顾得上厕所,一泡尿憋得膀胱疼。我向她打了个招呼说去卫生间,白茜抬手指了下后院。
后院有个水泥瓦搭的简易厕所,我刚走进去,就看见茅坑里露出半截注射用的针管,很新。
一切,我都懂了。
当天晚上,我回去开完业务小组结会,门哨在院子里喊我。我出门问什么事,门哨说,外边有人找我。
白茜站在大门外,神情很焦急的样子。我以为她碰上闹事的,刘建洋又不在家,她只好来找我帮忙。
白茜拉着我离开大门,焦急不安地说:“刚才警局来人,说建洋被抓了。在这儿我们没太熟的人,只能找你商量。”
我脑子里一闪,觉得刘建洋被抓肯定与毒品有关。
回到店里,白茜把门关好,面色苍白。她在店里走来走去,绕了十几圈,不时抬眼看我,像是有话要说,又不能说。
我想还是让白茜自己说,与毒品相关的事能不介入就不介入。这倒不是我不愿帮白茜,而是我极为厌恶沾毒的人。
终于,白茜停下脚步,然后坐在了我对面。
四
白茜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实情。
白茜有个表姐,在动物园市场做生意。她表姐是外经贸大学毕业的,工作一年后辞职,在市场干了十年,动物园和秀水街都有她的店。
她表姐把动物园的店连带着生意都转给白茜,还顺便带她和刘建洋去南方转了一圈,把中国几大服装市场的生意关系介绍给了她。
那时白茜才知道,表姐和她的朋友们都在吸毒,她和刘建洋出于好奇也试了毒品,但都是大麻,就是逗乐一玩儿。
这种自由惬意的生活,随着动物园市场拆迁戛然而止。
没了生意,现金流断了。那时白茜和刘建洋都上了瘾,北京地下市场的海洛因的价格一天比一天涨。等他俩连吸带玩,忘了现实世界,清醒时一查银行的存款,顿时都懵了。
白茜说,吸了几年海洛因,连骨头都渗着那玩意,不吃不喝可以,但离不了毒品。她和刘建洋也试过戒毒,但戒毒比骑车去月球还难。
白茜认识的朋友中,因沾毒破产甚至死了的,大有人在,还有几个熟人,常年不见人,最后就失踪了。
在白茜和刘建洋日益窘迫的情况下,两人由海洛因转向了价格低的冰毒。但冰毒是什么——沾上它就等于给自己挖好了坑,等着埋尸。
那时圈里有人说,如果真离不开毒,就去缅甸金三角。那里是产毒区,东西又便宜,吸一辈子没问题。
白茜和刘建洋没想太多,把车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揣着剩下的钱一路南下,偷渡国境让人带着到了金三角。
说到这,白茜叹了口气:“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吸毒,开店也没发财的意思,挣点钱够买那玩意儿就行。”
我直接问:“刘建洋怎么被抓的?”
白茜说:“本来这样就行了,挣点儿钱,偷着摸着过日子也没大事。但建洋鬼迷心窍,想多弄点钱留着。”
“干上贩毒了?”我心一惊。
“也不算,他是第一次,跟着人去看路,没带货。”白茜又叹气。
“你说怎么办,慌死我了。”她眼巴巴地看着我。
我心想,中国人一辈子都纠缠在人和人的关系中。一遇到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人际关系处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尽管我痛恨这一点,并常跟朋友说,社会文明难以进步,法治难以取代人情,人情是最大的阻碍,但我还是答应白茜帮她一次。
回去后,我思忖再三,硬着头皮去找队长。
队长四十多岁,长得很粗犷,黑面皮。他是当地驻军的军人,旅长为保证我们这些国际志愿者的安全,派队长带了几个兵当保镖。
我把事儿跟队长说了,特别说明刘建洋是被人拉下水,还没干上贩毒,请队长无论如何救他一命。
队长瞪着我看了半天,最后答应问一下。他又告诫我,让我远离沾毒的人。他说毒品是个看不见底的黑洞,沾上的人没一个能爬出来。
过了几天,有人找到白茜,说事情调查清楚了,刘建洋确实没贩毒,但他跟的人是毒贩,警方早就知道此事。那人告诉白茜,拿一万块钱,人就放出来。(金三角流通人民币,比缅币值钱。)
刘建洋从警局出来后,白茜非要请我去镇上最好的饭店吃饭。
那天,我去了他俩的小店,看着白茜和刘建洋不知说什么好。但我直率地告诉他俩,这种忙我只能帮一次。我劝他俩关了店门想三天,彻底想清楚,守着毒区的最后结果是什么。
其实我说的绝对是废话。对两个吸毒多年的人,这种警戒的话没有任何意义。他俩已经踏入那个没有底、只有枯骨的黑洞,而且正在往下跌,就是喊着要回头也不可能了。
我走出小店时,白茜正趴在桌上哭泣,刘建洋手里拿着根烟,低头沉默不语。我迟疑一下,头也不回地走了。
五
告别了白茜和刘建洋,过了一个星期,我随组织沿萨尔温江西行。
沿萨尔温江向西,也是英国人留下的毒区。越往西走,地势随着群山越高,空气也越冷;平坦的土地不见了,山一座挨着一座连绵起伏。抬眼看去,树木无际,峭壁乱石横垣其中。
队长告诉大家,就是在这样半原始的山区,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也种植着罂粟。这里只有两种作物:罂粟和旱稻。
进了山区,有一些竹壁草顶的棚子构成的山寨,依地势的佤族居住在山顶,拉祜族住在半山腰,傣族沿河流而居。
所到山寨,成人皆身穿破旧的衣裳,脚着被土遮住原色的拖鞋,挎着腰刀忙于生计。那些儿童见到我们,在十米外站立着,大而乌黑的眼睛紧张胆怯地看着突然出现的陌生人。
山区中极少有学校,儿童也几乎没有上过学。他们衣衫褴褛,赤脚跟随我们小心翼翼地观察,当我们对他们笑或说话,又被惊得如鹿四散逃去。
到了年底,救助组织的普查告一段落,我们又回到金三角驻地。做完一系列检查总结和资料整理后,我走进镇子去看望白茜俩口子。
进了镇子,来到白茜的店门口,店门却是紧闭着,墙角处长出了青草,门前飘落着树叶及纸片,像是很长时间没开张了。
这家店应该很久没人光顾,店墙的角落成了流浪汉栖息的地方,正躺着一个流浪汉,窝在墙角一动不动。也不知是死是活。
我站在街边一直在想,难道白茜俩口子听了我的劝告,离开这里回国了?但我又觉得这一点不太可能,吸毒的人一旦到了金三角,绝对不可能自觉离开。
想到刘建洋那次被抓,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缅甸政府和金三角占地为王的地方武装,在国际压力下不仅抓捕种毒和贩毒者,也在抓捕吸毒者。
一番犹豫下,我走到相邻的店问老板关于白茜俩口子的情况。老板神色紧张地看着我,挥手摇头表示不知道。
我又问白茜的店关了多长时间,老板又摇头,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模样。
我想,白茜俩口子一定出事了。邻居的表情分明反常,他见我是生人,肯定是害怕受牵连。
六
回到驻地,我左思右想,虽然没有答案,但白茜两口子出了事是肯定的,或其中一个出了事。我想极可能是刘建洋。
随后几天,我总是心神不定的,不管怎样,我和他俩也算认识一场。就算有什么事我帮不上忙,但总该知道他俩的去处。
我决定找队长,让他去了解一下。
这次,队长直接带着我去了镇上的警局。他领着我走进警长办公室。他们很熟,队长直接问镇上那对开米线馆夫妻的事。
警长问我是谁。队长说我是救助组织的人,是那对夫妻的朋友。
警长想了一会儿,说:“是他们啊。”
警长说,他记得那对夫妻,半年前,那个男人因可疑被抓过一次,虽然随后放了他,但警方也把他列入了嫌疑人名单。
过了一阵,警方发现刘建洋买毒并吸毒,再次把他抓捕。这次证据确凿,刘建洋被判了一年劳役。
警长随后的讲述中,透露了我离开的那段时间,白茜俩口子的生活。
服刑后的刘建洋,每天戴着脚镣,一大早就和其他犯人到街上扫大街。当然,什么脏活苦活他都要干。
白茜一个人开店,身体上受累不说,更令她倍感难受的是,每天都能看见刘建洋被警察像牲口一样赶来赶去。特别是每天街上人最多的时候,警察专门背着枪拿着棍子,把刘建洋赶到白茜这来扫街、倒垃圾。
白茜是生意人,知道警察把刘建洋赶到她面前的用意。她只能用钱让警察对刘建洋善待一些。但金三角的警察吃惯了这一口,隔三差五就把刘建洋赶过来,白茜只能再给警察塞钱。
很快,白茜手里的那点积蓄就见底了。
有一次,白茜给警察塞钱后,警察让刘建洋坐在小店墙角下歇一歇,白茜端了碗米线给刘建洋。刘建洋伸出手接过碗,看着白茜说,“别在这里了,赶快回家去。”
白茜哇的一声大哭,她紧紧搂着刘建洋,警察费了好大力气才将死死拥在一起的俩人分开。
说到这里,警长的语气变得冷冷的。
三个月前的晚上,一个吸毒的人从店门后院撬开门撞进去,把白茜强奸后又抢劫了钱财。
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刘建洋又被带到小店前干活,他见店门关着,还以为白茜回国了。那天干活的时候,他还特高兴。
几天后,邻居向警局报案,警察赶去查看现场,白茜半身赤裸着,死在了屋里。白茜没有反抗,但身上有很多伤痕,是吸毒者施暴时常见的疯狂现象。
隔了一段时间,刘建洋见警察不再赶他到白茜那儿干活,心里有了疑惑,他觉得白茜如果回国了,一定会给他留下暗示。
疑惑越来越重,刘建洋央求警察带他去小店,他想看看白茜是不是真走了。警察手拿棍子,残忍地告诉他,“你的老婆已经死了。”
一瞬间,刘建洋两眼发黑,瘫在了地上。
清醒过来的刘建洋,对警察说的话一会儿信一会儿又不信。他了解白茜,她绝对不会自杀。再说只剩下几个月,自己就刑满释放了。
刘建洋说他要见警长,他三番五次地用头撞墙,以此要挟。
警长最后答应见他,他手里拿着一张公文,告诉刘建洋,白茜被强奸抢劫杀害了。凶手也是吸毒者,已经被警方抓到。
刘建洋眼珠凸起,随后发出撕心裂肺的吼叫,双手剧烈地抓挠着自己的头发和胸口,又倒在地上昏了过去。
从此刘建洋疯了,不吃不喝,嘴里呢喃念叨着白茜的名字。警方见刘建洋精神错乱,是濒死的人了,决定放了他。
从牢里出来的刘建洋,每天在镇上跑来跑去,疯疯癫癫的,到处寻找白茜。有时他抓住某个人喊白茜,就被人踢打一顿,扔在街上。
我猛然想起那天缩在墙角处的流浪汉。
我问邻店老板,那个流浪汉是这个米线店的?老板看我一眼说,是他。我呆呆地站在街上,在异国他乡,认识白茜两口子不过一年。如今,他俩都因为沾毒而双双死去。
作者黑叶,支教老师
编辑 | 蒲末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