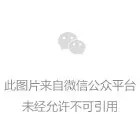欺骗人类最荒谬的一句口号
“多数人的利益”是用来欺骗人类的最荒谬的口号之一。
这句口号没有具体明确的意义。
我们根本无法从善意的角度来对它加以解释,它只能用来为那些邪恶的行为狡辩。
这句口号里的“利益”应该如何定义?无法定义,只能说是有利于最多数人的东西。
那么,在具体的情况下,谁来决定什么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呢?
还用问吗,当然是大多数人。
如果你认为这是道德的,那么你一定也会赞同下面的这些例子,
它们正是上面那句口号在现实中的具体运用:
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奴役了另外百分之四十九的人;
十个人中,有九个饥饿的人以另外一个伙伴的肉为食;
一群残忍的匪徒杀害了一个他们认为对他们造成威胁的人。
德国有七千万德国人和六十万犹太人。
大多数人(德国人)都支持他们的纳粹政府,政府告诉他们,只有消灭少数人(犹太人)并且掠夺他们的财产,大多数人的利益才可能得到保障。这就是那句荒唐的口号在现实生活中制造的恐怖结果。
但是,你可能会说,在上述的例子中,大多数人并没有得到什么真正的利益。
对,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利益,因为“利益”不是靠数字决定的,
也不能通过什么人为了别人所作的牺牲获得。
头脑简单的人相信,上面的那句口号包含着某种高尚的意义,
它告诉人们,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他们应该牺牲自己。
如果是这样,大多数的人会不会也高尚一次,愿意为那些邪恶的少数人作点牺牲?不会。
那么,为什么那些少数人就一定要为那些邪恶的多数人牺牲自己呢?
头脑简单的人以为,每个高喊上面那句口号的人都会无私地和
那些为了大多数人而牺牲自己的少数人站在一起。这怎么可能?
那句口号里丝毫没有这种意思。更可能发生的是,他会努力挤进多数人的队伍,开始牺牲他人。
那句口号传递给他的真实信息是,他别无选择,抢劫别人或被别人抢劫,击毁别人或被别人击毁。
这句口号的可鄙之处在于,多数人的“利益”一定要以少数人的痛苦为代价,
一个人的所得必须依靠另一个人所失。
如果我们赞成这样的教义,认为人的存在只是为了他人,
那么他享受的每一点快乐(或每一口食物)都是罪恶而不道德的,
因为完全可能有另外一个人也想得到他的快乐和食物。
根据这样的理论,人们不能吃饭,不能呼吸,不能相爱(所有这一切都是自私的,
如果有其他人想要你的妻子怎么办?),人们不可能融洽地生活在一起,最终结果只能是自相残杀。
只有尊重个人的权利,我们才能定义并且得到真正的利益——私人的或是公众的利益。
只有当每个人都能为了自己而自由地生活时——不必为了自己而牺牲他人,
也不必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人们才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根据自己的选择,实现最大的利益。
只有把这种个人努力汇合在一起,人们才能实现广泛的社会利益。
不要认为与“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种提法相反的是“极少数人的最大利益”,
我们应该提倡的是:每个人通过自己自由的努力所能得到的最大利益。
我们能够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
永远从你的思想、言语和情感中清除“多数人的利益”这样的空洞口号。
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是思想的教条。
不管你是否同意安·兰德的思想,当我们在思考自由、权利、幸福、创造的时候,
安·兰德的思考,会让我们获得一种难得的清醒。
也正因此,在美国,安·兰德成为了一代又一代美国人的精神教母。
香港学者卢安迪:“虽然今天的学校不会教安·兰德的思想,
但相信,几千年后,安·兰德将会跟亚里士多德并肩走进人类思想的殿堂。”
安·兰德的思想,即使我们不全盘接受,每个人都可各取所需,在思考自由、权利、幸福、
创造的时候,也会让我们获得一种难得的力量和清醒,去发现一种新的道德。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最能代表安·兰德思想的两部巨著《源泉》和《阿特拉斯耸耸肩》。
◎《源泉》(珍藏版):本书是青年志气与个人精神的象征之书。一书看尽四种人生。维基百科创始人 吉米·威尔士:我一直是安·兰德的客观主义哲学的热诚追随者。她的哲学思想,是我创建维基百科的起点。
◎《阿特拉斯耸耸肩》(珍藏版):本书指引众多创业者和CEO,震撼几代青年心灵之书,足以影响人的一生。更是仅次于《圣经》的超级畅销书。全球销量近亿册。
=======================================================

看历史,
没有左右之争,只有智愚之别
1840这个年份,一直被中国人诉说。
它是现代中国历史形成的一个特定瞬间,其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在那一刻,中国与异己者对面相撞,跌入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世界。
瞬间也成为两个中国的分界线:
一边是由自己的精神、思想喂养的自立的世界;
另一边是使异己者成为自己一部分的现代中国。这个异己者就是西方。
▍坚船利炮的威力,与制造出它的手之间具有内在关系
在中国人的印象中,西方有两张面孔:一个是它的力量,一个是它的价值。
1840年以来的中国,切身感受到的是西方资本、军事、贸易、宗教文化的扩张或征服,
这也容易被认为恃强凌弱,缺乏道义。
“洋鬼子”这个词便承载了这一切。
事实上,中国人正是从彼此力量的对比中发现了真实的自己。
差距就是差距,不能用文化上的差异为自己辩护。在力量面前,弱者的正当性不能从弱自身获得。
力量催逼着中国必须往前走,而不是囿于自己文化的独特性而通过道德评判让强者停步。
弱者改变自己的唯一出路,是从力量中寻找自己新的正当性,区别在于途径。
中国把西方的进化主义思想变成自己的武器,实现赶超便是寻获自身正当性的努力。
相对于力量,价值这一层面比较复杂,只能分别来谈。
通常被看作具有普遍意义的西方价值包括科学、理性、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法治等等。
无疑,这些价值来自西方。但它能否成为普遍性价值,除了价值自身的因素以外,还依赖于力量。
坚船利炮的威力与制造出它的手之间具有内在关系。
贫弱不能成为人类追求的普遍性价值,不是因为它缺乏德性,而在于它不具有再生产的能力。
特殊性变身为普遍性的一个必要条件是能力(力量)的介入。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
民族的只有经过(有能力代表)世界的承认才能成立,否则,它就只能归属于当地的奇风异俗。
▍改变民族习性,几乎是一件无法完成的任务
普遍主义价值也依赖“中心—边缘”这个结构。
普遍性价值是由中心生产的,然后向边缘扩散并被边缘认可接受而成立。
从理想的状态讲,人类应该是无中心化的多元存在,因为只有剔除了中心—边缘结构,
人类才能真正的平等相待。
然而,人类提供的历史和现实实践恰恰相反,人自始就在中心—边缘的结构里生活。
没有中心主义,人类似乎找不着北。
世界如此,共同体内部如此,即便小如一个单位、一个村落也如此。
中心—边缘结构是呈级数的相对化存在。相对于西方,非西方是边缘化的;
从巴格达到华盛顿的遥远不只是空间意义上的,也来自观念;
国内的普通话之所以在全国普遍通用,不是因为它多么好听,而在于它是由中心生产、提供的。
上海话再洋气,也只是一种方言;富有、发达的广东则属于较远的南方省份。
在西方中心主义这个结构里,现实的恰当做法不是先忙着去中心化,因为即便在理论上解构了它,
事实仍然存在——中心不会因为纸面上的否定就能自动消解。只在理论上抵制并不是个好主意。
可行的做法是,在观念上,先把普遍主义价值与它的传播方式、途径区别对待。
◎倒洗澡水不能把孩子一块倒了
简而言之,不能把西方的殖民扩张、征服、霸凌行为与普遍主义价值混同,一起否定。
拎出婴儿把洗澡水倒掉才是得当的做法。否定、抵抗西方的非道德性是正义的,
而把西方生产的普遍主义价值进行“翻译”,
使之成为全人类共同追求和实现的美好价值该是中国人担当的使命。
在另一个层面上,普遍主义也不能把人的多样性和具体性简单地回收到它那里去,
普遍性—具体性是它存在的另一个结构。在这一结构里,离开具体的人,
所谓普遍主义价值也只是一句口号而已。
有一个道理谁都明白:普遍性是从众多特殊性抽象而来。它依赖于“人”这个概念。
人之所以能脱离肤色、种族、地域、风情而共同被表述为“人”,
依赖的是思维对人的具体差异性的模糊处理,抽象出共通性。
而难点在于,如何验证抽象出来的共性是准确可靠的?
又如何把这种由共性推演出的普遍性投放到每一个具体的特殊性中去?
事实证明,西方价值要真正成为人类的普遍性价值——不只是停靠在意识形态层面——
就必须把问题进行反转:普遍性的成立深植于特殊性的具体实践中,而不是普遍性取代了具体性。
普遍性做不到人的整齐划一,也无法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具体差异。
事实上,人既需要普遍主义价值作为方向,又热心自己的个性化存在。
抽象与具体、绝对与相对的辩证运动,是西方价值变性为人类共同实践的普遍价值的一个途径。
譬如,来自西方的法治已成为现代人类共同的普遍价值,中国也把建设法治国家作为自己的目标。
而法治的基本要义是遵守规则,那么,假若一个人走在斑马线上遇到红灯,
而且身前身后又没有机动车辆,这个人应该是走还是停呢?
按照西方国家的经验,遵守规则就是无论是否有车辆通过,遇到红灯行人就应该停下来。
如果用这种经验来衡量,很容易得出中国人不遵守交通规则的结论。
那么,遵守和践行法治的普遍性价值,是否就必须要求全体中国人非要按照上面说的去做?
事实上,对中国来讲,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不要奢求去改变一个民族的习性
其难点不应该仅仅归结为中国人的法治意识不强,倒不妨换一个思路: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习性,而改变习性是一个几乎完不成的任务。
在布尔迪厄的反思社会学里,习性是一个关键概念。
它在人的行为中不断地被结构化,具有再生产的功能,所以改变习性基本是不可能的。
这是法治的普遍性又一次遇到具体性。
应该如何处理才是合理的呢?要求中国人一定像西方那样是一种思路,但如上所言,这个难度很大;
尊重中国人的习性是另一种思路。
事实上,多数中国人对规则的理解是情景化、语境化的。
中国人在生活世界依靠的主要是经验,而不是绝对化的规则。
把单个行人的闯红灯看作违法并不错,但这并不解决问题。
不少中国人习惯在斑马线前作判断,安全的经验决定他是否通过斑马线,
很少人会主动跟机动车辆较劲,因为这会被看作傻。
在生活世界里,人都会遇到类似问题。古人说过,一个有道德的人在特定状态下应该杀身成仁;
古人还说过,识时务者为俊杰。那一个人到底是该死,还是该活?
这不能说中国人不讲理,只是这个理是交给了具体实践的个人,在特定的情境中由他自己做出判断。
而且,中国人也愿意相信,君子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这里的意思是,价值真要成为普遍性价值,它不应凌驾于具体性之上,而是俯下身来尊重和亲近具体性。舍此,或许没有更近的路。
以上内容选编自王人博老师新书《1840年以来的中国》序言(有删减),标题为编者所加。
作者王人博老师是中国政法大学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
他的信条是:自己就是自己,没有代表也不代表任何人”,是一位“孤独的敏感者”。
《1840年以来的中国》一书从“法学视角”重述中国近代史,最大特点是融史学家的洞察、法学家的严谨、哲学家的智慧于一书。点击下图购买,还可在规格中选择王人博老师亲笔签名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