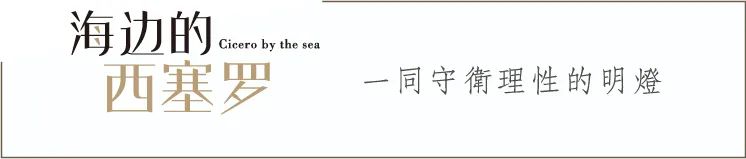
我们从不奢望单靠法律就能驱除一切邪恶,
但请至少成为一盏明灯,指示正义该前行的方向。
“如果我的养父母被判刑,我会很生气。”
最近几天,一名叫孙卓的18岁男孩说出的这句话,引得很多网友也很生气。
孙卓曾是一名被拐儿童,4岁那年,他被人用玩具车拐走。其后他的父亲孙海洋苦苦寻子14年,2014年时,这位父亲的经历被拍成了由陈可辛导演黄渤主演的电影《亲爱的》广为人知。

但凡看过这部电影或类似影视作品的人,恐怕很难不对剧中那些被拐儿童的父母感同身受。骤然而来的骨肉分离,其实后数年、十数年甚至数十年漫漫寻亲,亲子的分离、正常生活秩序的被打乱,乃至家庭和父母整个人生的破碎……

心软的人不建议看这个电影,真的太惨了……
所有这些,都让人不禁连发三问:
上天啊,为什么要这样对待那一对对平凡的父母?
孩子啊,你究竟在哪里?
人贩子和收买孩子的人,杀人不过头点地,究竟是什么仇什么怨,你们要这样去折磨那些无辜的他人?
还好,现实中的孙海洋夫妇是幸运的,在经历整整14年辛苦的找寻之后,因为另一起拐卖案的偶然破获,他们终于找到了被拐多年的儿子孙卓。

但他们又是不幸的,因为在认亲现场,与他们的激动万分、呼天抢地相比,孙卓的神情显得有些木讷。
而在拥抱过后,孙卓告诉他们,虽然亲生父母找了自己那么多年,一定很辛苦,他很感谢自己的亲生父母,但现在的“父母”不管怎样,也已经养了他十几年,所以他应该不会回到亲生父母那边……
现实果然比电影更残酷,我们无法想象孙海洋夫妻在听到这句话时是何等的心如刀绞,也许这正应了那句话:“被人贩子拐走孩子的家庭, 会失去两次孩子, 一次是被拐走时,一次是找到时。”
而更让人感到虽可理解,但难以接受的是,孙卓在接受央视采访时,为他的“养父母”说了不少话。
其中那句“如果我的养父母被判刑,我会很生气。”更是激怒了不少网友。
很多人骂他“认贼作父”,更多的人则开始追问这样一个问题:在我国频发的各种拐卖案当中,人贩子固然可恨,可是那些买了孩子“养父母”就那么值得宽恕吗?
至少在孙卓被拐案当中,显然不是的。
从该案目前公布的案情通报中我们得知,这家买主与拐卖孙卓的案犯吴某龙是亲戚。
2007年的某一天,在深圳当保安的吴某龙在街头看到玩耍的孙卓,就用玩具将其骗走。
狡猾的吴某龙先是把孩子藏在自己宿舍中,几天后,又联系家人将孙卓送走。不久之后,他又再次犯案,用同样的手段拐卖了另一个男孩符建涛。
而两个买主都是吴某龙的亲戚,这两家人家不可能不知道两个男孩是怎么来的,可是他们依然掏钱将孩子买下。理由也很简单,他们想要个男孩。
根据澎湃记者对孙卓“养母”的采访,她承认是自己拍板买下的孩子。
养母说:他们当时只有个女儿,而没有儿子。而在当地,没有男孩会被乡邻讥笑为“绝户”,受欺负,而他们不想当“绝户”。
所以他们就把别人家的孩子,硬生生当物品一样买下。
根据孙卓和养母的说法,买了孩子之后他们对着孩子确实不错,甚至比对自己亲生女儿还好得多。孙卓的要求,买下他的这对夫妻,基本都会满足,甚至不舍得让他干农活……
可是这又如何呢?跳出当事人的情感迷局,我们很容易能看清这样一个事实:这对“养父母”唯一的动机,其实就是不想当“绝户”,想有个儿子。为这个动机,他们对孙卓可能很“好”,可是却完全无视了孙海洋夫妇那被毁掉的人生。
所以这种“好”不能被认为是善,而是也仅仅是一种恶的延伸。
所以按理来说,就像绑匪不应该因为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被绑者为其辩护而获得刑罚减免一样,这对名为养父母、实为买主的人,也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
但,让人感到五味杂陈的是,按照现行法律,他们还真的有可能(如孙卓所愿)从轻甚至免于受到刑事处罚。
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第一款之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而该法条第六款还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受拐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
简单的说,就是买个孩子或买个媳妇,最高判三年,如果你不虐待被拐者,事发后不阻拦解救,还可以判的更轻。
你可能觉得这个处罚已经够轻了吧?别急,还没完。上述法条是2015年刑法新修正案实施以后才有的。2015年以前的规定则是:“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我估计下一步本案的争议焦点就会发生在这个问题上:“养父母”对孙卓的“购买”发生在2007年,那么这种犯罪到底是应该被视为当时发生的一次性行为呢?还是一种从2007年起持续十四年的延续性行为?
如果被认定为是后者,那么这对“养父母”可能还会受一点刑事惩罚。
如果被认定为是前者,那么他们有可能一点刑事惩罚都不受。
这个“三年以下”“从轻处罚”,叠加之后,会是怎样的轻微?与孙海洋夫妇遭遇相比,真的匹配吗?
现行《刑法》上还有一条罪名叫“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罪”,刑法规定该罪名可处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也就是说,同样是非法收买,你买个人比买个珍惜动物判的还要轻,而且上有封顶,最高就是三年。
这样的不合理现象,曾被讲刑法的罗翔老师犀利的吐槽为“你买一只珍惜鹦鹉,判的就跟买一个孩子或大姑娘一样重;买两只你就判的比买人还重了……买个姑娘只判三年?那这样的姑娘,给我来一打好了!”
买一个被拐妇女,量刑相当于买20只癞蛤蟆?这是什么量刑?
是的,买人的罪比买鹦鹉大熊猫的罪居然要轻,这算不算对人格的侮辱呢?
那么刑法为什么要对收买人口定刑如此之低呢?有很多人猜测,这是不是为了降低被拐儿童和妇女的解救难度呢?
拐卖妇女、儿童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条文所列八种加重情节之一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可以看到,相比收买被拐儿童妇女,拐卖儿童妇女罪的起刑点就是很高的,而且一路直通死刑。
那么问题就出现了,从法理上讲,收买被拐儿童妇女与拐卖儿童妇女其实是典型的“对行犯罪”(Begegnungsdelikte,又称对合犯罪)。
按照大陆法系的一般法理学说,“对行犯罪”是彼此依存,甚至有共谋性质的——用我们通俗的话说,也就是“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没有买家,就没有拐卖。”
所以对这种“对行犯罪”大陆法系的量刑一般都会采取“同罪同刑”或至少“异罪近刑”的态度。简单的说,就是用相近的刑罚同时惩治买卖的双方。
像我们前面所提的“买卖珍惜动物制品罪”,以及“买卖枪支罪”、“重婚罪”、“行贿受贿”等等都属于此种。
但在这么多的“对行犯”当中,“拐卖儿童妇女罪”与“收买被拐儿童妇女罪”是为数不多的量刑差别特别巨大的。
这就构成了一种逻辑漏洞——如果说是为了降低被拐儿童和妇女的解救难度,才放收买者一马,那么拐卖者是不是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从轻呢?
实际上,即便是“拐卖儿童妇女罪”也已经是从轻处罚了,这些年我国社会上一直有“对人贩子逮住就毙”,刑法之所以没有回应这种呼声,依然对人贩子慎用死刑,原因之一就是考虑到害怕人贩子在重刑威胁之下破罐子破摔,对被拐者进一步施虐。
所以现行刑法对拐卖者一方的量刑已经是权衡之后的适度考量了:即有威慑力,也没有过分,给了出路促其回头。
但对收买者呢?作为“对行犯罪”,我们对收买者的惩戒是不是太轻了些?
就像我们在无数打拐案中看到的。已经轻到了一些人可以无视法律和他人幸福,肆意妄为。轻到了一些收买者在东窗事发后不仅毫无犯罪嫌疑人的自觉,反而以“养父母”“丈夫”甚至“恩人”自居。
这帮家伙,明明就是人贩子们的对行犯、甚至是合谋犯!
当他们在每个夜晚,靠从别人偷窃的子女、妻子那里获取快乐时,他们可曾想过那些痛失亲人的家庭在屋外的寒风中漫无目的找寻?抱头痛哭?
说白了,我国现行法律对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的量刑过低,主要原因恐怕只有一个:那就是我国很多地区曾经(甚至现在依然)存在着“买人”的恶俗,和妻子、儿女是丈夫、父母私有物品的偏见。
找不到媳妇,要打光棍了?买一个呗!生不出(或者不让生)男孩,要“绝户”了?买一个呗!——曾经,在我国的很多农村,这种“买人”的恶俗就是这样公然被当地村规民俗所维护。
我觉得这个报道中最让我气愤的,还不是那个老光棍非法收买、拘禁、虐待女孩的恶行。而几十年当中,当地村民非但对老光棍给女大学生施加拘禁、虐待、强奸的犯罪不闻不问,当记者去采访时,有些村民竟然直言那老光棍“有本事”,居然能“搞”来这么一个年轻、漂亮女大学生当老婆——言外之意,似乎有机会他们自己也要效仿。
而在电影《盲山》当中,同样是女大学生被拐的故事,剧情更加触目惊心,女大学生试图求助时无人理会,试图逃脱时却遭遇全村的追捕,等到警方来解救被拐者时,村里人居然组织起来跟警方“抢媳妇”。
你能感觉到这种村庄社会中依然奉行着一种可怕的人身依附法则。这种邪恶的法则鼓励丈夫把妻子,父母将子女,视为彻头彻尾的私有财产。而因为是财产,所以无论是娶是生、是骗是拐都无所谓,只要能有就行。
而这样的村俗,是违背和践踏现代社会的基本法则的。人不是物,他人自由、尊严和幸福容不得这样粗暴野蛮的践踏。
那么什么力量能够将这些野蛮、落后、违背人性的恶俗驱除呢?可能唯有法律。
不可否认,曾几何时,由于这种恶俗在我国分布过于广泛,加之贫困、计划生育等因素的影响,严惩收买人口在我国面临法难责众的困局,一时的迁就与妥协也许是无奈之举。
但时代总要进步,一切良善法律的最终目的是逼近自然法、是彰显正义。
是至今日,社会的发展让法律无需也不能再迁就这样的恶俗了。
对“收买人口”行为的从重处罚,不仅仅是告慰那些受害者破碎的人生,更会成为一种宣誓,用以告诉那些愚夫愚妇,人不是物,不可以任由你们这样公然买取、霸占。买卖人口都是犯罪,而且是犯很重的罪!
2015年,《刑法》对“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罪”的量刑做更改时,公安部曾下发《收买被拐妇女儿童者10月底前自首可免刑罚》的通知,督促那些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的嫌疑人在新法落实之前尽快自首。当时据称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如今六年过去了,也许是时候参考其“对行犯”的量刑标准,进一步提高该罪行的量刑了。也许在新刑罚即将落地的威慑下,会有更多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的嫌疑人自首,让那些身陷“盲山”里的女孩尽早回家,让那些奔波中寻找“亲爱的”的父母们早日见到孩子。
文章的结尾,我想强调。就像您了解的,我从不是个重刑主义者,我也从没有期望过法律能够完全驱除这世界上所有恶行。
但至少,它应像一盏明灯,微弱却执着的发出一缕光,在人性的黑暗中,指示正义该前行的方向。
愿所有买卖人口、践踏他人幸福与尊严的人,都得到应得的严惩!

全文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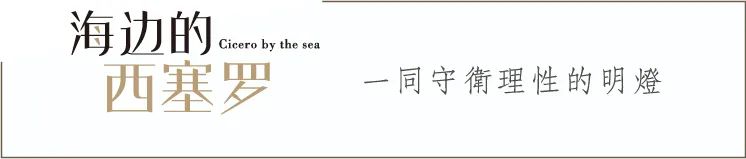
这两天,江苏南通的三星镇一下子出名了,原因是网上爆火的一段视频中,十多名身着“静通市容”制服的人员将一名卖甘蔗的老人围住,以土匪看了都汗颜的高效,瞬间将一捆甘蔗一抢而空,独留老人在寒风中哭泣。
此情此景,让很多人一下子想起了白居易的那首《卖炭翁》:
你看当年的“黄衣使者白衫儿”,好歹还知道给个“半匹红纱一丈绫”“充炭直”,而视频中那帮“黑衣使者”好像啥也没给。
也就是说,虽然都快2022年了,这帮现代城管的做派,还赶不上一群唐朝太监……
相比之下,白居易笔下那位真是“感动大唐好太监”——人家至少给钱了。
当然,事件发酵后,当地政府很快就“知错能改”了。三星镇政府回应:身着保安制服的那群人并非公职人员,为三星镇购买服务的第三方市容公司人员,其现场处置过程简单粗暴,与约定工作要求格格不入,对此深感痛心。目前,当地区纪委介入调查,对三星镇负有管理职责的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城管中队负责人、城管片区责任人启动问责程序。
同时,三星镇政府领导还亲自登门向两位受害老人(是的,当天遭抢的是两位老人)致歉,并表示将终止与南通静通市容管理有限公司合作,将南通静通市容管理有限公司列入黑名单,并根据合同条款对南通静通市容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相应的经济处罚……
视频发出来是11月6日的事情,而当地政府这一套“亡羊补牢”,11月8日就打完了。即便以“从谏如流”而论,这个“流速”也着实快了一点,前后落差之大,尼亚加拉大瀑布了属于是。
但即便“改过”速度如此之快,这个镇政府的操作还是很难让舆论夸的起来。因为今年4月,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海门街道办事处与江苏静通市容公司签署了《委托管理协议书》,合同期限共三年,费用总额为2437万余元。
也就是说,当地政府用三年2400多万,一年八百多万的价格,把对市容的管理权给委托给了一家私人企业,而一旦出了事儿,老百姓问责起来,当地政府则可以说:哎呀,我们也是受害者啊,这家企业拿了钱却不会办事儿,这不是欺骗我们zf消费者么?罚!该罚!
于是矛盾的焦点,就被转移到这个无良的第三方公司那里去了。
但我想问的问题是:买卖真的可以这样做吗?政府的管理权,是可以这么轻易的委托出去么?
比如古罗马共和国末期到帝国早期,罗马人就曾经在本土以外的行省搞过一种“包税人”制度,这种制度的具体执行方式是由各行省总督出面,在当地寻找一些地主豪强,由他们先出钱向罗马“买下”该行省中某块地区的税务征收权。而后这些地主豪强们就可以打着罗马的名义在当地收租,而无论最终能收到多少,则都会流进他们自己的腰包。
不需要深想,你就能知道这个制度是个彻头彻尾的恶政。那些肯花重金买下罗马收税权的豪强当然不是傻子,羊毛出在羊身上,包税花了多少钱,他们就一定会加倍的从被征收者那里搜刮过来。而且该制度发展到后期,“包税”甚至出现了“层层转包”的趋势,大豪强把包税权拆分卖给小豪强,小豪强再把包税权转租给当地黑帮,黑帮再把“收税”任务拆分给地痞流氓。最终分摊到穷苦百姓身上,不仅税收“溢价”非常严重,征收的手段更是残酷至极,跟黑社会收保护费没什么区别。
罗马帝国后期很多行省民众对帝国怨声载道,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这种包税制度使然。
所以,你看《圣经·福音书》当中,耶稣经常把税吏和娼妓相提并论,原因就在于那个时代罗马帝国包税制度下的“税吏”真的就是流氓的代名词。
但奇葩的是,包税制度虽然问题很严重,但各省总督却都很爱用。究其原因,是因为总督们知道在当地收税这件事是个“脏活”,不仅要跟那些异族平民斗智斗勇,能收上来还要招他们怨恨。既然这么费力不讨好,就不如把这个“脏活”“转包”给当地豪强,这样罗马与外省平民的矛盾,就变成了本地豪强与平民的矛盾。豪强们平素为帝国收了税,还挡了怨,事情闹得太不像话的时候,总督再领一帮罗马士兵去“主持公道”,惩治几个“包税商”平息民怨,外省自然就好管了。
至于这种“权力外包”政策会不会造成外省民众负担加剧?那总督们管不着:为了我能花最少的治理成本,完成元老院与凯撒给我定的KPI,就再苦一苦百姓好了。
其实同样的管理思路,同时期的古代中国也在用,法家的商鞅还将其理论化了。你看人家是这么说的:“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商君书·说民》)
如果只看这句话,你会觉得商鞅是不是脑子瓦特了,居然这么黑白颠倒、是非不分。但如果你接下来看中国其后两千年的秦制史,你会发现这一套一直在被变着花采用。
自秦以后整个大一统历史当中,正式在朝廷编制内的官员数量都是极低的。西汉时代中国人口据估计已经达到了5000万,但整个国家的官员总数不超过6500人,如果再按照西汉全国103个郡国的行政区划的划分,那么平均每个郡(国)也只有60几个“官”。即便到了清代,官员与百姓的比例,也才刚刚突破了1:1000的大关(相比之下,当代公务员与人口的比例大约是1:150)。
这么少的官员怎么能管住那么多百姓,同时完成行政、治安、税收、征集兵役、徭役等等诸多繁杂的任务呢?回答是“吏”。
早在汉代的时候,就有所谓“一衙一官而十吏”的说法,这些吏本身不再朝廷的编制内,不能从国库里领工资,而全靠县太爷从自己的薪俸中养活,堪称古代版的“临时工”,薪水当然高不到哪里去。
而奇葩的是,不仅工资低,历朝历代似乎也有意压低他们的身份,明代行走衙门的胥吏一度与奴仆、娼优一样,是三代以内若有此出身、就不能考官员的“贱民”。唐代的捕快则干脆被称为“不良人”,专门“征市井中有恶迹者充任之”。
是的,无论举孝廉还是科举,中国历朝历代的官员选拔都是搞“掐尖”式的精英选拔。而与此相反,各朝对吏的挑选却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在社会阶层中“抽底”:不仅从社会的最底层征募,而且就算当上了,还要把你地位再压低一些。
你看《武林外传》里,招个捕快还弄得跟绑票一样,这很合理,因为捕快是下九流,正经人真不愿意当。
为什么要这样呢?其实目的无非是降低治理成本、转移社会矛盾、以奸驭良。由于吏的地位极低,所以他们可以被用极低的成本征募,当上之后为了维持生计,就会用县太爷外包给他们的权力,想方设法盘剥百姓,用隐性收入养活自己。
而普通的良民百姓在遭受了这帮人的压榨之后,很自然的就会对这个群体产生仇恨,所谓“车船店脚衙,无罪也该杀”。
但百姓们不会深想一个问题:这些获得权力转租的衙役们为什么永远都是那么奸猾、狠毒、见钱眼开而又毫无操守原则?——真正原因是,无论在古罗马、还是在古代中国,这种人的产生,都是一个社会在试图通过“权力转租”来降低治理成本时,必然会付出的代价,而这个代价,被完全甩给了百姓去承受。
但我们要问题的是,这种在古代社会屡试不爽的“权力转租”之法,在一个现代国家应该存在吗?
在该书中霍布斯提了一个观点:人的天性都是自私的,对一切事物都有占有欲,而为了把人类从这种野蛮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中解救出来,个人才会把一部分自然权利转让出来组成政府。所以公权力天然是一种“必要的恶”,但人们为了不堕入更加糟糕的野蛮战争的境地不得不忍受它。
也是为了约束公权力这只“利维坦”,现代社会制定了很多法律条文以制约它。在正常情况下,公权力是不能也无法突破这些法律边界的,所以它的权力只能按规矩行使,好似一只拴上链子的怪兽,只能替人们看家护院。
可是,当公权力通过转租的方式,把自己的一部分职权“委托”出去,这就相当于怪兽使了一个金蝉脱壳计,将公权力从制度的笼子中放出来了。那些获得“转租”或“委托”的个体,无论无意还是有心,最终都必然会走向滥用被委托的公权力,为所欲为、伤害民众的事情。因为理由很简单,他们不是公权力,没有完善的制度约束,却享有了与公权力相似的职能。这就好像挣脱了链子的恶犬,你让它不咬人,那是违反其本性的。
所以被转租的公权力一定会导致绝对的滥用和绝对的腐败。从这个意义上讲,事发的三星镇当地政府该检讨的不是他们“管理”所托非人,而应该是他们把管理权委托出去这件事本身,就是不符合现代政府所应遵循的施政规范的,而是在沿袭古代政府“偷懒”的做法。
这个世界上,哪怕所有东西都可以买卖,公权力也不可以买卖、委托。这是人类历经千年,用无数苦难、无数个“卖炭翁”得到的准则。
嗯,这样说还是太磨叽了,我们不妨简单的问一句当地政府:
老百姓把管理的权力交给你,纳税养着你,为的是什么?难道不就是为了让你把权力使用、达成社会管理和民众私权保护之间的平衡吗?
假如就因为你嫌管理是个“脏活”、“累活”,就不肯自己干,直接花一笔钱外包出去。那么请问,这样做跟那些“赚差价”的中间商,又有什么区别?
花两千多万,雇一个“市容公司”“代替”当地政府管理市容,这个买卖里,有关部门是省了心,第三方是公司得了财,看起来挺双赢的——但唯一吃亏的,是那些老百姓,他们是这种转租中的代价承担者。
有关部门,请别忘了,是那些风中瑟缩的“卖炭翁”或“卖蔗翁”们养活了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