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身份证,一个人怎样度过22年

他有三个名字,
却没有自己的身份证
前方是云南边境城市瑞丽到芒市的关卡,每一个人都要下车检查身份证。他坐在租来的车上,准备好和往常一样,谎称没有带身份证,把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登记在薄。然后边境士兵点头,畅通无阻。可是这次麻烦大了,他被当做偷渡来的缅甸毒贩。
他请求士兵给他爸爸和芒市派出所打电话求证,结果都失败了。几个小时后,他通过“违法”的途径——让朋友带来冒牌身份证,上面的照片和他不是很像。不过很幸运他们过了关卡,回到离缅甸只有40公里的云南芒棒村。“太惊险了,万一露馅,两人都得坐牢”。

芒市到芒棒村路上的村民
这次麻烦是因为他没法证明自己的身份,其实在他22岁的人生中从来就没有过身份证。
一
没有身份证,
一次次命运改写
“没有身份证会怎么样?”
13岁的时候,他第一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那是一个很冷的冬天,他的脸被冻到通红。学校足球队正在为一场重要的比赛做准备。队员们的定妆照拍完之后。教练突然当着大家的面对着他破口大骂。事件的起因是所有队员必须要办理临时身份证,但是独独他没有。教练说他是“野孩子”,“有娘生没娘养”,连户口都没有。
没有成为一名职业足球队员,他人生的第一个理想破灭了。紧接着是第二个,没有身份证就不能参加高考。那时他是班里的好学生,成绩名列前茅。一个听话的13岁孩子,没想过应该为了获得高考资格做什么,“不能参加高考”似乎是个没法改变的事实。来年的暑假,他随哥哥去工地打工。在那工作的大学生总在谈论“大学无用”。他把那些话对应到自己的烦恼里,开始安慰自己:高考不算什么,不如早点放弃。

暑期结束后,他没有参加秋季入学。他甚至再也没有进过学校,哪怕是技校,因为他们也会问他要身份证。但他没有停止学习,在工地、餐馆、主顾家里,他学习装修、烹饪、家政,最后都没有坚持下去。15岁的时候,淘宝来村里做宣传,他想开一家网店。打工挣的钱已经够了,但还是败在了没有身份证上。第三个理想,也没了。
一次次挫败,让他渐渐接受了现实。他进过正规公司,但是“正在补办”的谎言只能持续2个月,最后不得不离开。他想去当兵,看到招募广告上写“必须要本人身份证和户口进行登记”,只好作罢。他也曾偷渡到缅甸,先后进了三家没过问他身份证的华人电信诈骗公司,被当地警方抓捕遣送回国。

他去镇上玩,临走前买点小吃回村里
除了工作之外,他的日常生活也被划上了一条又一条禁令。他无法实名认证买车票,离开云南的唯一办法是走国道,偷渡去缅甸。他喜欢上了一个在北方的女孩子,开心了好几天,但他不能去看她,也不敢再喜欢下去。他去镇上玩到夜里,只能拜托朋友帮他先开好房,再偷偷摸摸地躲过前台的目光进入房间,因为担心查房,无法安心入睡。云南边境执法严格,遇到警察盘问,他总被当做不守法的人,无法自证清白,好几次差点打起来。
二
无根的人,一次次更名
三年前,奶奶带他去算命。算命先生给他算都不准,但是给哥哥算却很准。回到家里,他仔细琢磨,是因为没有户籍,没有身份,所以怎么算也算不准。无根的人,命运总好不到哪去,他想。

他和奶奶
他有三个名字。第一个叫“岩赛亮”,是缅甸名字。前两个字的意思忘记了,只记得最后一个字是在说他眼睛特别亮。这是妈妈家的人给取的。
从六岁开始一直到十三岁,他总是做同一个梦。梦里是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女人,牵着他来到一片仙境般的森林,然后女人突然就不见了。有的时候,他会尝试和那个女人对话,可是听不懂对方说了什么。也有的时候,他会哭着醒来。
上学的时候这个梦一直困扰着他。这个女人是妈妈吗?他有的时候会这样想。他的母亲是缅甸人,嫁给一个在云南当兵的军人后,生下了他和哥哥。他还没出生,父母已经离婚,理由各执其说。离婚后,妈妈被朋友以打工为由拐骗到山东,另嫁他人。也是在那一年,刚刚学会走路的他被送到缅甸福利院,在那里读了四年书。一天,同在福利院的哥哥和几个小伙伴准备出逃,在路上遇到出来闲逛的他,二话没说就把他带出了福利院。他们饿了偷荔枝,晚上睡在牛棚或者路边。

他拿着奶奶的一封信,上面写着傣族语言
走了两天两夜,两个孩子终于到了缅甸的外婆家。半年后,他有印象以来第一次见到母亲。那是一个晚上,堂哥领着他到一个房间,对他说房间里的女人是他妈妈。他却充满怀疑:“那个女人一见到我就抱着哭,我心里想,谁知道这是不是我妈”。当时妈妈欺骗在山东的丈夫回缅甸看望生病的家人,真正的目的是带着两个孩子去山东。在路上,他不小心把水洒在衣服上,妈妈对他破口大骂。他当时很诧异,“不是说这人是我妈妈吗?怎么对我那么凶?”
“陈善良”是他在山东的新名字,山东继父为了给他办理入学给取的。他努力学习,为了争口气。办身份证的事,只能拜托山东继父。也只能如此,因为妈妈没有把缅甸国籍注销,也没有中国身份证。但是希望落空,继父对他的身份证问题置之不理,他猜测是因为继父与妈妈的感情出现了问题。
逃跑,在山东的那段岁月里,始终相伴。他离家出走了两次。第一次他想回到外婆家,在山东没人向着他,在缅甸起码亲人可以容忍他犯小错误。他和另一个也想逃的小朋友一起往南方走,想一路搭便车,一直到缅甸。一而再的迷路消耗了他们的体力,镇子也没出,他半天就回家了。那一次,他挨了一顿揍,打断了一根木棍。
没隔多久,他又离家出走了。这一次更像是负气,他不打算去哪,只是在镇上一直打转,累了找地方睡觉,饿了路边摘果子吃。被家人发现带回家后,他惊讶地发现一桌子的饭等着他回来吃。他很愧疚,“我在山东的家人心里还有那么一点点位置。”

他忘记家庭住址用汉字怎么写,爸爸的朋友在教他
2015年的一天,他真的失踪了。同母异父的妹妹记得那是噩梦般的几天,母亲对着他的相片止不住哭泣,平日“冷漠”的继父也跟着焦急起来。等妹妹终于打通电话,才得知他从黄牛手里买了一张火车票,已经回到了云南。在此之前的几天,哥哥先一步回到了云南,给他打电话,“来这边办吧,好歹你也是李家的人”。“终于落叶归根”,他想。
在山东的最后一天,他去了商贸城和茶叶基地,逛了一圈什么也没买。那是他最熟悉的地方,他常常会想念。但当时的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和山东的家庭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
在云南,他的名字叫“李云龙”。那是亲生父亲取的,正好和父亲喜欢的《亮剑》主人公同名。可是父亲喜欢用动物代替“李云龙”的名字称呼他。去年他感到肺部不适,为了做核酸检测,去了一趟市里,在路上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电话里喊他“疯狗”,逼他赶紧回来。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急切地一遍遍重复“我和奶奶已经打过招呼,征得同意了啊”。
比起这些侮辱,更让他受不了的是,他被父亲彻底困住了。五年里,父亲一直欺骗他身份证“正在办”、“程序繁琐”。去年他才从表姐口中得知,哥哥因贩毒入狱,父亲只有他一个依靠。不给办身份证的真正原因是“养儿防老”,把他困在云南,不要回到母亲身边。
三
寻找身份,一次次摇摆
有两次,他差点就要拿到身份证了。
第一次是在山东的时候,他十四岁。那是一个除夕夜,母亲带他和哥哥去了一个没见过的叔叔家里。他突然意识到,妈妈在山东已经背着继父组建了另一个家庭。“所有人表现得特别镇静,但是我整个人说不出话来”。那个叔叔让他喊一声“爸爸”,就能给他落户。他拒绝了。比起拿到身份证,他更愿意做亲生父亲的儿子,做一个“有道德有底线”的人。现在想来,他觉得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对身份的“归属感”,虽然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个词意味着什么。
第二次是在云南的第一年,他十六岁,在丽江一家餐厅学习少数民族菜系。那是2015年,正值山东人口普查,免费为黑户落户。他决定回到山东。父亲给他打去电话,谎称已经为他落实户口,办好了身份证,他再一次相信了,回到芒棒村发现父亲又故伎重演。他质问父亲,隔壁一家八口都是从缅甸搬过来的早就落户,他明明有一半中国人的血统为什么无法办理。“他什么也没说,但是脸特别臭”。

奶奶的小卖铺开在芒棒温泉旁边,他几乎每天都去帮忙

小卖部不远处是稻草屋简宿,由他一人搭建
已经不记得跑了几次村政府,问了多少个在政府工作的朋友,他都没有办法在没有父亲陪同或者亲子鉴定的情况下获得身份证。朋友建议他和父亲翻脸,起诉父亲,举出许多成功案例。他再次拒绝。比起父亲不情愿地妥协,他更想要父亲真心实意地给他,放走他,也是承认他作为一个人存在,而不是养儿防老的工具。

他和朋友在路边烧烤,之前他在奶奶小卖铺里做过烧烤生意,一个多月就失败了
在他的心里,还有一个不得已的下策。“我不介意去办一个缅甸身份证,一万块人民币就可以轻轻松松拿到”。做缅甸人的未来他已经计划好了,拿到国籍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朋友在仰光的公益组织工作,帮助穷人。舅舅在缅甸认识政府官员,做一个缅甸人,可能会比现在顺利。“世纪难题”又摆在他面前,是呆在没有合法身份,但是热爱的中国,还是去有合法身份,但是没有归属感的缅甸。
他皮肤黝黑,头发自然卷,身边人都觉得他有“异域风情”。两个同母异父的妹妹,加上他和哥哥,四个孩子都“长得像外国人”,以前在学校里他们都被问过“是不是混血“,孩子的好奇注视和问话没有令妹妹们烦恼。他却至今很厌恶“是不是缅甸人”的问话。十有八九,他都会怼回去“我中国话说得那么流利,你说我是哪国人?”
两个月前,他发了一条朋友圈:“现在,我会勇敢地去面对我的新征途”。所谓“勇敢”是给自己一年期限,顺从父亲的意思在家种地,改善亲子关系,做最后一次尝试。否则就入缅甸国籍。但是就在一个礼拜前,他又不再勇敢,“我不想要身份证了,就这样浑浑噩噩地一辈子下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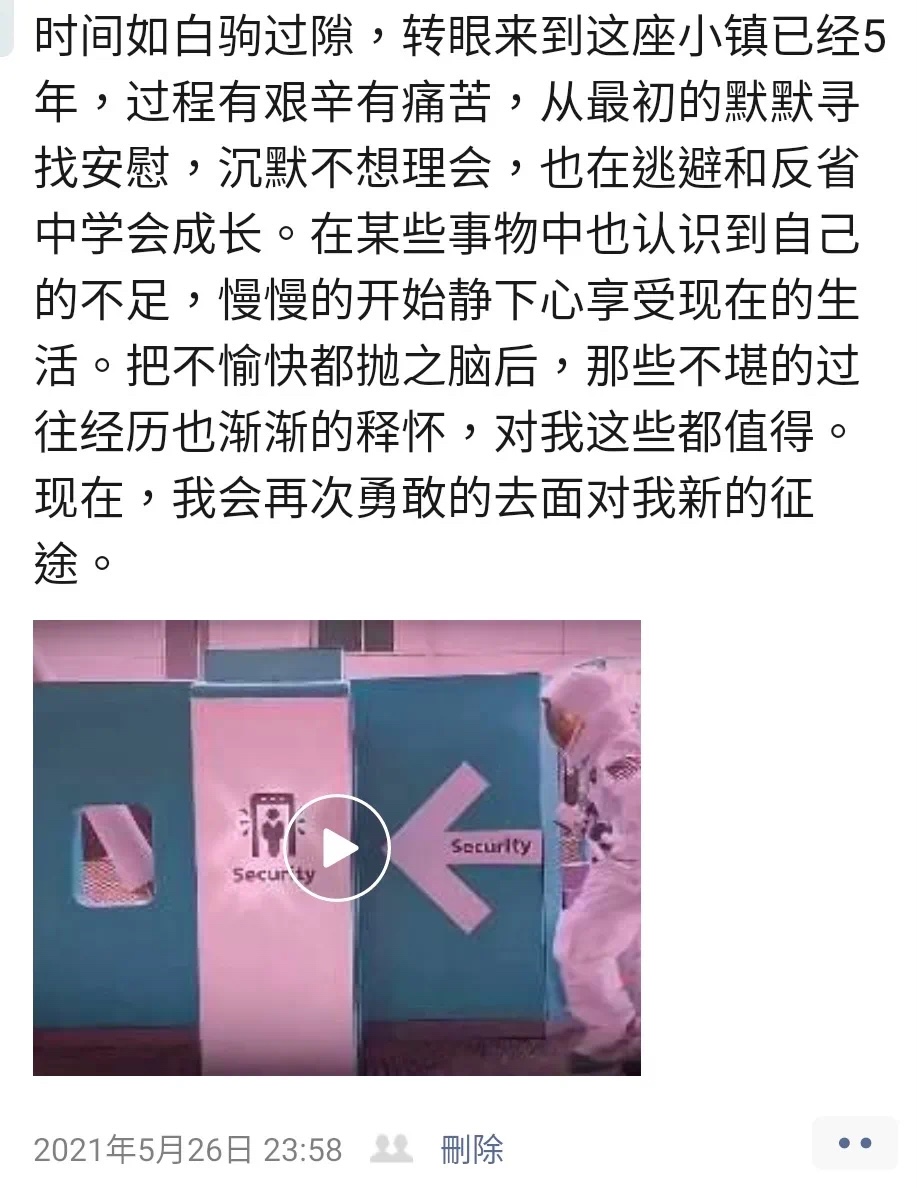
朋友圈
反反复复,情绪不稳定是他的常态。同一个问题,他会有不同的答案。同一个问题,这次夸夸其谈,下次拒绝回答。朋友万保形容他“唯唯诺诺、半途而废,永远下不了决心,这是心理问题”。他也想解决这些问题,为此他买了几本心理书,读完分析自己得了“双向情感障碍症”。
有的时候,他庆幸自己坚守底线,没有被那些可以拿到身份证的“利益”诱惑。有的时候,他也厌恶那个坚持道德正义感的自己,“否则我就不会那么寸步难行,可以做自己的事”。现在他仍旧不知道,未来该怎么办。

他爬上德宏的一座山顶
他常常觉得和周围朋友格格不入,“他们聊的是喝酒、女人、农活、打工。”相比这些,他更看中精神世界的丰富。他喜欢大卫鲍伊和猫王,因为他们的潇洒又自由。他喜欢登山,站在山顶看到的世界更开阔。他喜欢读书,手机屏保上写着“书籍像一艘船,带领我们驶向无边际的海洋”。

今年他开始认真学画画,第一幅画是猫王的头像
文/摄影 调反唱唱 | 内容编辑 程渔亮 | 微信编辑 菠萝蜜
======================================================================================
我,为了翻身,90年代去俄罗斯挣钱,现在只想回国
我是高珊,70后,家乡在延边。19岁,为翻身,我和父母告别,远走他乡去俄罗斯赚钱。那是二十八年前的事,我还是无知的女孩子。那时以为,自己会在几年后回到家乡,但事情的发展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半辈子过去了,我仍在异乡回不了国。原来只想赚钱,现在只想回家。都说出国就能过上好生活,其实不是,而是等待,等待回家。

1973年,我出生在延边乡下。父亲在工厂当工人,母亲也是工人。改革开放时,母亲开始倒钢材,父亲说她“投机倒把”,母亲说一家老小要活命,当工人能挣几个钱?母亲挣到的钱又拿去倒彩电,被骗得精光。
我有三个哥哥,母亲最后悔生下我,说女儿就是赔钱货。父亲疼我但没发言权。哥哥对我很好,可他们帮不了我什么。上高中时爱臭美了,想买什么都买不了,母亲说自己赚钱自己买。我就此犯下一个错误,高二没读完就辍学。父母忙得顾不上我,就由我去。
我先去当服务员,工资八十。然后去纺织厂,昼夜两班倒,工资二百。吃过苦头才明白,没文凭只能当纺织工,一辈子是穷人,住平房。

想换个体面工作,但当售货员都要文凭。80年代,没有高中毕业证,哪都不要我。要实现咸鱼翻身,我必须拿文凭。我攒钱报了夜校日语班,还没开课就赶上中俄恢复邦交,边贸活跃,俄语翻译突然紧缺,学校通知日语班变俄语班,报名人数暴增。每日课毕,教室就响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紧跟时代,开始学俄语。
父亲坚决反对,他就想我一辈子守一份工作,别瞎折腾。铁饭碗不要了?工龄不要了?学什么俄语?我据理力争,我才不想当纺织工,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翻译工资高,能坐办公室,学得好还能上谈判桌。
有目标了,我很努力。夜校一周两次开课,我白天上班,晚上学习,赶上夜班,我就请假。一年下来,教材只学一册半,许多学生叫苦,最后没几个挺得住,俄语班就黄了。边贸公司紧急来招驻俄办事处翻译,作为好学生,我被选中了,突然觉得,整个世界摆在我面前,我只需要抓住它。兴奋得睡不着觉,立马打起小算盘:出去干三年,最多五年,赚五万块钱就回来自己开小店。
父亲又来吓我:苏联刚解体,你去那多危险!那边都是高个子蓝眼睛,你一个女孩子,万一被骗被控制怎么办?我说,我啥都不怕,就怕穷。父亲劝我停薪留职,我立马否决!都当上翻译了,还回去当纺织工?

办护照,办签证,1993年5月 ,从图们出发。没有哭哭唧唧,家里孩子太多,母亲恨不得我快出去闯天地。哥哥送我到车站,坐大巴去珲春换车。全部家当:一千块钱,几件衣服,二十块钱的高级手提箱。
出关就是俄罗斯的克拉斯基诺小镇,公司派车接我到海参崴,安排住进公司租的房子里。之前问过老师俄罗斯什么样,老师说“苏联电影里那样”,我到哪看苏联电影去?连张图片都没看过。这会儿知道了,俄罗斯家家有轿车,住楼房,有24小时热水,喝新鲜牛奶,他们生活真高级。公司管吃住,月薪八百元人民币,等于我在国内四倍工资呢。
我俄语课程都没学完,自然是小角色,跑跑腿,接电话。有时跟着高级翻译跑,我很多都听不懂,人家不乐意带。不被重用,我就很懊恼,听别人说有个远东大学,我巴望着去学俄语,学费一年七万卢布(合两万多人民币)交不起学费。半年后,公司生意越来越差,正好朋友介绍教俄语的俄罗斯人给我,我干脆辞职。手里钱不多,但市场里轻易就能找到活,我不愁。

教俄语的是远东大学老师。俄罗斯人一般不好客,老师同意我住她家,就为赚那点生活费。老师家在俄罗斯颇具代表性:缺男人。男人不是死了就是离婚走掉了。她家三代住一起,都是女人,老师养全家。我一个月交五千卢布(合一千五百块人民币),管吃管住管学习。
住客厅,三餐吃土豆、黑面包、意大利面,零食是红茶配饼干。老师每天上班前给我留作业,下班回来检查。白天写完作业我就去市场,那里有练摊的中国人,我常去帮忙和老毛子讨价还价,每天能赚一百到一百六十五卢布(合人民币三十到五十块)。
幻想中的高级生活很快不高级。看到老师家总是把钱塞进罐头瓶再埋进菜窖里,忍不住去问。什么?钱不敢存银行?取钱要预约?要限额?银行不可靠?这是啥国家?原来,1993年7月,政府宣布,1961至1992年苏联版卢布和1992年俄罗斯版卢布一律作废,只允许流通1993年版新卢布。只给三天时间,老百姓要把手里旧卢布拿去银行换新卢布。反正结果就是,富人直接变穷人,穷人变更穷!一辈子攒的钱一夜变废纸。那时银行门口排的长龙有几公里长,我手里没钱,跟我没关系,但我真的感受到整个国家都在慌乱中。

不安的感觉一步步加深,市场里每天都在传,谁又赚大钱了,谁又被抢了,谁又被杀了,不是传奇就是悲剧。我有个老乡,来这边做大生意,现金都在库房里,这让他没了命。那天,他正在那里打麻将,一个人冲进来,拿枪把一桌人全都射杀了。我心想,赚到钱我赶紧回中国,这不是久留之地。
两个月后,我没钱了,搬出来,在市场旁边租个小房间。去另一家公司当翻译,俄语说得比以前好,月薪两千人民币。跟着经理跑,大致摸清了哪个生意能赚钱。
1997年的一天,我和一个翻译准备去客运站接经理。翻译来找我,我一开门,她就跑进卫生间,我正发愣,一个老毛子持枪怼进来,蒙着面罩,一手拿枪指我头,一手往后摆,示意另一个翻译过来,五楼又冲下一个高个老毛子,金发,边走边戴面罩。他们拿胶带飞快捆住我们,从嘴到手。推到墙角,蹲下不许动。我们不敢抬头,只看见大脚在地上走来走去。
过了很久,门铃响,经理到了。俄罗斯人在猫眼看,发现就他一个人。门打开,一只大手伸出去,一把将他拎进屋。他刚想喊,枪柄一砸头,直接倒下,地上一滩血。西服里有个鼓鼓的牛皮纸袋掉出来,老毛子一把掳走,旋风般消失。门咣铛一响,我想去阳台看他们开啥车,腿软了,挪到阳台时,他们早没影了。回头叫人送经理去医院,好在是轻微脑震荡。他的一万两千美金没了,我两千多美金没了。俄罗斯警察懒得理,弄不好去报案还被敲一笔钱。没钱又没人保护我,待下去是等死,我马上坐大巴跑回国。
在公司的东宁办事处躲了半个月,没敢告诉家人。大部分钱都被抢了,没有别的出路,我只能再回俄罗斯。以前去修车时,结识了一个俄罗斯人。他和别人不一样,话不多,只埋头干活。

后来熟悉了,知道他当过兵,退役回来在修车厂做事。看出他人很好,我很信任他,就去跟他讲了被抢的事。他说,你自己来回跑太危险了,咱俩一起做生意吧?正需要有个人来保护我,我得比他积极,说干就干。
我拿出所剩无几的积蓄,和他合伙买了日本小货车,去哈尔滨上货,把家具、红砖、陶瓷倒过来,再把这边的废旧金属倒过去,卖到河北加工厂。他开车,我采购、翻译、找代理公司、报关,最后,我负责在中国卖俄罗斯货,他负责在俄罗斯卖中国货。所以,那时我是两边跑。

他有个女朋友,到中国偶尔会带上她,我自然尽地主之谊。有一次别人给我介绍男朋友,约吃饭时碰巧他打电话说快入境了,我说那就一起吃饭吧。席间,他抽身去把单先买了。他一点没掩饰对那个人的冷淡,过后唠唠叨叨,这男的配不上你,一看就不行。我们无话不谈,关系很特别,我像他哥们儿,他像我男闺蜜。这么着,一年过去了。
我没相中那人,他也被女友分手,自然而然我们就好了。这不代表什么,我很确定。我不想嫁给他,对我来说,中国是家,外国永远是别处,这个俄罗斯男人是朋友、伙伴、情人。他心领神会,不说甜言蜜语,不说想娶我。

转眼过去七年,到了2000年。来回跑,有种感觉越来越明显,国境线两边,一个在变,一个停住不动了。中国那边像被施了魔法,平房都没了,高楼立起来了,街上各种进口小汽车,朋友从前游手好闲,突然谈起生意,个个好像大有作为的样子。俄罗斯这边,灰楼照样破,伏尔加车就像老古董。
原来说赚五万人民币就走,七年过去了,现在赚二十万了,再也不想来这了,我想家了,该结束了。

2000年1月,我请他去三亚,他请我去莫斯科,留个纪念,拜拜啦!临了,他说他问过妈妈,“我娶个中国儿媳妇,你会不会反对?”妈妈说,“只要是你爱的人就行,我不反对”。娶个中国媳妇?他周围也没别的中国女人呀?那就是我呗?
他不确定我能不能来俄罗斯生活,没有亲戚朋友,不能说母语。去三亚时他看到了,中国发展那么好,而俄罗斯生活单调,像农村。他不直接说“我要娶你”,他知道,假如我拒绝,以后朋友都做不了。我告诉他,我不可能留下,我的家在中国,我非回去不可,下个月就走。这是个瞎子似的爱情故事,分手像黑夜,总要降临,那一天异常平静。
终于回家了。二十万,我的第一桶金,翻身了。一回到家,我立刻花十一万给父母买了房,125平方米。从平房搬出来,父亲哭了,说我受苦了,对家付出太多。母亲很骄傲,四处显摆。家人欢喜,我心情稍稍平复。过了一段逍遥的日子,没心没肺玩。想开个小酒吧,慢慢发现,我不大会会应酬,融不进圈子。和朋友喝酒时,远远地,我的心总在别处。这个感觉来路不明,我回避,不敢深究。直到有一天,他打电话问我怎么样,放下电话我就哭了。

很快,他又打电话来,问可不可以陪他去哈尔滨买家具?我去了,但我知道,这改变不了最后得分手的事实。一星期后,我们又不得不再次分开,各回各家。哭也无济于事,必须面对现实:我不想离开中国,他不想离开俄罗斯。
忘了他,复又想起来。我爱他的人,不爱他的国家。痛苦,纠结,反反复复。突然发现,我怀孕了。最棘手的就是这个:他已婉转问过我,我已拒绝他。我反复想,我能拒绝孩子吗?不,我不能,我想要孩子。毋庸置疑,这是上天的安排。这个小生命,将让我回到他身边,哪怕离开中国,哪怕去我不喜欢的地方。
母亲一夜没睡,第二天早上说必须给他打电话,看他啥态度。结果他高兴得不得了,“要孩子,不许打掉,马上结婚”。这一句就已足够。母亲说啥要求没有,必须明媒正娶。父亲担心我嫁国外去,万一受气,回娘家还得走国境线。哥哥怕老外哪天不要我,中国男人也不会要我。我不参加争论,没有意义。对要嫁的那个人,我心中有数。秋天,我再次离开家,回到俄罗斯,他赶紧张罗婚礼。

他们家也是普通家庭,他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一家人互相帮扶,都是善良的人,这符合我父母的期待。
圣诞节前夕,我们结婚了。一小时仪式,双方签字,互换戒指。庄严,神圣,我们发誓,从今以后,我们将属于彼此,忠于彼此,除非死亡把我们分开。亲友在音乐中送鲜花,赴晚宴,母亲父亲哥哥闺蜜都来了,他全程安排。我们住进他的小房子,50平米大,足够了。

第二年3月,我生下大女儿。从产检到孩子出生,全部免费。没坐月子,俄罗斯人不坐月子,我也不坐。

接着我们买地、盖别墅,砖结构,内饰全实木,花了一百多万人民币,都是我们俩一起赚的钱。从平房搬到楼房,从楼房搬到大别墅,做梦也想不到,我这个穷孩子不但彻底翻身,还有自己的院子、花园、车库,美死了。

那些年,每到周末,我们都在别墅里办家宴,四世同堂,每个人对我都好。拥有爱情,拥有孩子,拥有亲情,偶尔可以回国,我什么也不缺了。我很幸福,我以为我会永远幸福下去。
我们又开始做边贸,一起穿越国境线。这回不用再分钱了,我们是一家人。他很顾家,比之前更沉着更热情,一心专注在我们要去做的事上面。

一切都稳定了,回家的念头又冒出来。家,是中国人的信仰。回家,是人的本能。他也不反对,他说中国比俄罗斯发展快。我们讨论,以后孩子在哪念大学,我们在哪养老,没有争议,一致选中国。
2007年,精挑细选后,我们在大连买了一套房,阳光,大海,俄罗斯人最喜欢。我们准备等孩子长大,钱再赚得多一点,时机一成熟,我们就回去。

2008年,小女儿出生。到此为止,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十年。有他,有孩子,有钱,有梦想,日子越来越好。
当时,我们不想拼命赚钱了,孩子更重要。我开始在家照顾孩子,他一人出去赚钱养家。贷款买了几个大卡车,他包工程,跑运输,参加高速公路建设。开始行情不错,能赚到一些钱,过不久,金融危机来了,钱越发难赚,一边要养家,一边要还贷款,突然间他压力很大。

2012年,他身体开始不舒服,去符拉迪沃斯托克检查,不确定,又去哈尔滨,还是不确定。最后到北京,确诊了,已经肺癌晚期。我们根本不相信,又回到海参崴。医生说,回家吧,就两三个月活了。我无法自控,平生第一次冲医生吼,医疗免费有什么用?技术还不是很落后!不甘心,我们又回到哈尔滨。治疗近一年,当过兵的一条汉子,强悍渐渐消失。回俄罗斯不久后的一天,他死在我怀里。
结婚十一年,吵吵闹闹时,赌气想过离婚,想家太苦时,担心他不想和我一起回国……想像过无数种将来和他分手的方式,没想到是这种方式离开。我下决心来到异国他乡,决定和他过了,钱有了,大别墅有了,车有了,孩子有了,过着过着,人给过没了。怎么会这样?怎么就发生在自己身上了呢?

我强迫自己冷静。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处理,孩子要养,债务要还,他不在了,我何去何从。他走前嘱咐我,父母年迈,要多照顾,妹妹小,给她一套房,哥哥困难,给他一台车。都是口头说的,假如我不给,谁也拿不走,但我不能那么做。
他哥说,这个中国女人肯定要拿钱跑,肯定再找别人,替他弟弟不平,不跟我说话。
我把别墅和几辆车卖了,当年就还清债务,拿回抵押手续。
他父母表态,将来孩子们要用钱的地方多,“我们放弃继承权”。我十分感动,律师也很惊讶。哥哥说给他的车要过户,我同意。妹妹小,我把一套小房子和车库都过户给她。这些都是我答应过的。然后,我和孩子们就搬到别墅对面的小房子住。

俄罗斯婆婆说,“你赶紧回国,别耽误自己,赶紧找个人嫁了。先把小的带走,大的留在这把中学读完,大学时再去中国找你们,我们先帮你抚养大。”父亲说,“你马上回国,毕竟有娘家在,一个女人势单力薄,在国外养俩孩子肯定难。”
我也想走,我是为他来的,他离开了,我为什么还要在这?可我还有孩子,怎么能一走了之?嫁过来,我始终没拿长居,因为一直想回中国。
要走,必须把孩子带走。小女儿才4岁,什么也不懂。大女儿11岁,已经在读初中,没办法转学回国内。我去征求她意见,她哭着说“妈妈,你和妹妹先别走,等我初中读完和你们一起走”,我好心酸。我的生活已经被打碎了,就可着我打碎吧。不能让她姐俩分开,我必须留下来。
我还剩下两台国际运输货车,能有一些收入,加上俄罗斯政府给孩子的补贴,每月每人八千卢布(当时合人民币一千六百元),我们应该能活下来。

他刚走的那三年,每到夜里,我就盯着对面别墅。他的生命结束了,我的也是,活死人一个。有时在厨房里哭,小的过来抱抱我,大的不出声,躲一边去了,那时她正值青春期。爸爸的走,对她打击太大,有一段时间,她把怨气撒在我身上,我也没地儿诉苦去。
她叛逆,不爱读书,不想学汉语。我吃过没文化的苦,逼迫她学,她抗拒,吵架愈演愈烈。后来我们两个都去找了心理医生,解决不了什么。做父母的影响不了孩子的命运,孩子有她自己的主意。就像我当初辍学、辞职、出国,一样是忤逆父亲。熬吧,只有靠熬时间。孩子总有长大的一天,那时她会懂一切。

一个人在异国他乡带两个孩子,辛苦是肯定的。今年大女儿19岁,政府不给补贴了,我决定做代购,贴补家用。小的13岁,很懂事,学习好,疼妈妈,给我很大安慰。
婆家和娘家一样,他们把我当女儿一样对待。跟婆婆叫了二十年妈妈了。他们住在离我们小镇十公里的村子,一周见两次。他哥哥看我把两个孩子都拉扯大,对我特别好,又把我当亲人了。即便是这样,这儿也不是我的地方。以前我每年都会回去看父母,父母现在不在了,我依然想回去。我想天天说母语、吃家乡菜,像儿时一样盼着过春节。
当初大女儿说,读完初中就走,结果现在都读完大学了。现在小的也熬到上初中了,还得等她读完才能走。丈夫离世后,我一待又是八年,而且还得不止八年。当初我离开家,说走就能走,谁能想到,现在想回国,不是说回就能回?
我准备等她们都长大后带她们回国,那时我再找个伴,照顾好自己,跳跳广场舞,逛逛菜园子,不给她们添乱就行了。婆婆不舍得我们走,但希望我们过得越来越好。
本文在今日头条首发,皆由主人公本人口述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