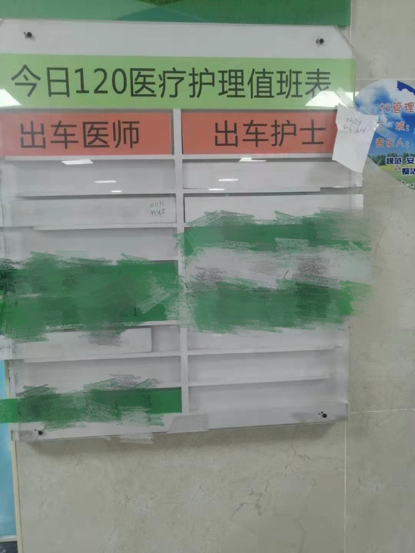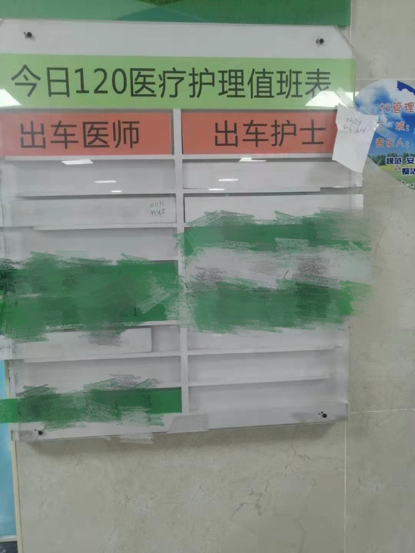孙哥喝了一瓶农药后,精神状态仍旧良好,他哄着葛姐从地上起来,还去厨屋炒了两个菜。一个青椒炒花菜、一个白菜粉条。

2020年,卫校毕业后,我正式成为我们本地中心医院的一名见习护士,跟生死打上了交道。
中心医院的科室共计31个,每个科室需要轮转三个月。到急诊科前,我已接触骨科、心内科、皮肤科。每个科室的规律不同,但紧张的氛围毫无二致。对此与我关系较好的护士长常说:“医院就像个战场,还是艰苦卓绝的保卫战,‘敌人’四面八方地涌来,每一个科室都是最后一道阵线。”
而急诊科应属整个医院里最特别的科室,分为紧急分诊、抢救室、急诊病房、急诊监护室四个板块。医院急诊科共有7辆一线救护车,3辆预备救护车,救护车标配司机、医生、护士,时间规划基本分为白4夜3——白天4辆,晚上3辆。
通俗一点说,救护车的工作安排好比服务业的“上钟”制度。一辆救护车标配3个人:司机、医生、护士。分工明确:医生负责检查情况;司机负责开车;护士听医嘱,为病患提供紧急救助。
抢救患者的第一重要要素是时间,急救科有制度规定,相关人员白天出车不能多于3分钟,晚上不能多于5分钟。平时会举行一些培训和比赛。
在工作台左侧设有一行“出车板”,名字对标当天的工作员工,前一位出车后就将出行板翻至反面,一轮一轮地重复,按顺序进行出车急救。
非突发情况,救护车的工作强度并未达到网上耸人听闻的程度,工作时间与排班休息都很合理,加班情况也常是培训或考试。传达电话响起,4辆车按序出车,有时一天出车的次数连一个轮回都达不到。当然,这也是我们最欣慰的情况。
培训初期,我接到偏远乡村的一处急救,路程近二十分钟,到达后患者已无生命体征。医生诊断为心肌梗死引发的心脏骤停,黄金抢救时间只有三分钟。即使是神医也回天乏术。死者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身边围了一圈亲属,听到宣布死亡后全场人员皆失声痛哭,我们临走时,模样像老人儿子的中年人跑到路边朝救护车不断磕头。
返程路上医生告诉我,老人在打电话时应该就已经不行了。但家人们仍期盼着那一丝希望,为老人醒来不停祈祷。我听完眼泪夺眶而出。而在见习期间,最让我难受的,是那些喝农药的人。
在我们县城,喝药中毒是急救接待里数量最多的病例,似乎这是老百姓没办法后想到的办法。
说起农药,很多人会想到百草枯。早在2014年,百草枯就因极高的触杀作用与内吸作用,被撤销生产许可,但直到2020年,国内才彻底禁止销售百草枯。然而市面上毒性与其相仿的农药品牌仍层出不穷。相关部门也对农药含毒量实行限制规定,农药成分里加入催吐剂,购买也需出示部门批准,但农药中毒的病例每一天都在发生。
药物中毒,需按摄入度来进行治疗,诸如带有强酸强碱性质的,第一步要先保护胃粘膜。可惜的是,即使如今医疗技术发展得突飞猛进,但药物中毒的救助也只受限于催吐、洗胃、血透、呼吸器吸入维持状态、输大量液体促进循环。

基础见习的第一天上午,我就目睹了一起因喝农药洗胃的现场。
到达医院后,随行护士将摄入量、摄入时间与农药毒性结构汇报给护士长。幸运的是药物含毒量低、摄入时间不超过半小时。患者喝下农药第一时间就进行了催吐,在救护车上检测的各项指标正常,进入医院后便立马拉去病房进行洗胃。
他躺在病床上跟一旁准备机器的护士透露,自己在救护车上搜索了洗胃的流程,“希望过程能够快一点,以免没死在农药上,死在了洗胃上。”
洗胃机一般设有三个管子,分为排污管、净液管、胃管。胃管需要在原先的基础上再接入一条硅胶材质的洗胃管。正式洗胃前,要测量患者眉间至肚脐长度,检查鼻孔是否有异物。
医护做准备工作时,那个高中生看到“硕大”的洗胃管后,开始紧张地吞咽口水,眼睛死死盯着即将插入鼻子的插孔。当洗胃管进入鼻孔后,患者便感到不适,眼睛紧闭,攥紧床单的手不停颤动。当洗胃管进入十五公分左右时已经到达喉咙处,患者身体反应加剧,如同溺在滚烫的河水里一般,疼痛难忍又伴随着剧烈的呕吐感。
我看着高中生的眼睛紧闭,仿佛想将眼睛融进眼眶深处,右侧的手臂不由自主地晃动起来,求生欲一瞬又一瞬地驱使他想要将洗胃管拔下。
到达喉咙处,要患者配合吞咽,到达胃底后需用针筒抽取胃液,证明胃管已进入胃部。做到这一步时,病患仿佛已经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前后吐了五次,身上一片狼藉,努力地进行喘气。
首先进行吸出,排污管源源不断地将浑浊液体排出,生理反应使患者将身体扭曲成一个弓箭形。紧接着是进行净液冲洗,这时患者反应得更加强烈,呕吐几乎每分钟就进行一次,腐坏臭味扑面而来。以此重复循环,直到排出的液体达到呈清透明状态,这一“酷刑”才宣布结束。
拔下胃管后,高中生脸上头发上都是吐出的浑浊物。他虚脱地躺在床上,哑着嗓子对家人说:“感觉命已经没了。”催问着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我在培训期间,还遇到一名女子因被厂子开除,与老板对骂两天,一气之下喝下了农药。家里人闹到厂子,老板被惹毛也喝了农药。经过洗胃、补液、急救治疗等九九八十一难后,两人最后拉着手哭成了泪人,开始换位思考与将心比心。
在我结束培训后的一天晚班,遇到了一个没有后悔机会的人。那次跟车,是去周边农村急救一位喝农药的病人,是位四十二周岁的中年男子。
男人妻子说,事发当晚,两人因男子喝酒吵架,男子一气之下喝了整整一瓶农药,喝下后当时无不良反应,二人心大,以为农药过期了,没做任何急救措施就上床睡觉了。凌晨时分,男子身体突然颤抖,流泪不止,大口大口地呕吐。起初还能说话,截止打电话时,连话都说不出了。
我们抵达后,男子躺在床上眼睛紧闭,瞳孔呈尖针样,口吐泡沫。一旁的妻子焦急如焚,一边激动得跺脚哭泣,一边给男子擦拭。男子尚有生命体征,但意识衰弱,床下一堆呕吐物。
这时距离他喝下农药接近4个小时,虽然农药毒性不强,但摄入含量高,期间还有饮酒行为,毒素大多已经被吸收,再吐下去,就是吐血了。
医生诊断后表示,男子生命体征到了危急状态。我赶紧听从医嘱,为男子挂上吊瓶,协同司机将男子抬入救护车内,为其戴上氧气面罩。
男子妻子惊慌失措地从堂屋一路小跑到大门,又仓促折返回去给堂屋上锁。到了大门,她用嘴叼着手电筒,踮脚将大门上方的插销插上。止住的泪又急了出来,一边哭一边怨恨着喃喃自语,黑中透亮的胳膊上,沾满了土色的汗与泪。
完成这些后,女人才坐到救护车座椅上,双脚分开,双肘抵在大腿,双手将脸埋在里面。司机开始往回赶,过了三四分钟,尖锐的哭泣声兀然刺来,女人的情绪y有些失控,开始往男子身上猛烈捶打。被我们阻拦后,她一屁股坐在地上。
女人头发散乱,手臂上的汗与泪凝成污渍,脸上的皱纹像一道道触目惊心的伤疤。她哭得歇斯底里,我无从安慰。在我从业以来,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如此惨烈的哭泣。在哭泣中她恍惚抬起头,对着毫无意识的丈夫说:“我的家完了。”
男子姓孙,半年前本是一位泥水匠,手艺精湛,效率极高,是工地头眼里的香饽饽。孙哥的妻子葛姐在家操持庄稼,性格有些顽横,对孙哥非打即骂,做起事情有些极端,占据家中核心地位。两人有一个儿子,在省内的一所大专上学。
孙哥有两个爱好。一是酷爱喝酒,每天下工回家总要斟个几两。二是线上娱乐,日常用儿子淘汰的手机唱两首歌,或者刷刷短视频。晚上空闲的时候,孙哥喜欢看草根直播,观看的内容多是主播坐在饭桌前,吃着粗茶淡饭与观众聊天。
时间一长,孙哥对直播有了兴趣,他观摩了几十位主播的表现,觉得这种营生自己也能做,并在“吃饭、拉呱”上对自己抱有百分百的信心。
正巧某平台的智能输送给孙哥推送了一条“特价主播训练营”的广告,孙哥认为是某种暗示,便推波助澜地交了一千五百块钱,参与了主播培训。
这事孙哥没跟葛姐商量,她对一千五百块钱的学习费有很大意见,然而随着孙哥“直播买别墅”的耳濡目染,葛姐慢慢也转变了观念,认为即使不挣钱,就当做学习一个技能也是比较好的打算。
1500的课程还算正规,一加入组织孙哥就收到十几本线上教科书,每晚还有不定时的直播课程讲解。孙哥对自己的形象认知很清晰,老师也在这一方面鼓励他,让他做垂直的“土根吃播”。
于是,孙哥白天休息时争分夺秒地学习相关知识,工作时在脑海里为自己构建经营框架,晚上便回去学习其他主播的风格。几周后,孙哥深谙直播的技巧,也为自己摸索到了一套直播风格。第一天试探开播,观看人数就有近两百人。
那天晚上,孙哥自豪地对葛姐形容:“两百个人,把咱全村的碗借来都不够吃饭。”
但是好景不长,之后几天直播人气急转而下。放着土味DJ的直播间,比这个家的人还要少。孙哥去找老师求助,老师说,现在干巴巴的聊天直播覆盖率太广,没有才艺很难拉新。孙哥便将民歌提上节目单,并在直播间开设了山东土话教学。
无一例外的,孙哥的直播间热度高了几天又通通淹没在数万个直播间大潮中。这时老师建议孙哥换个时间段直播,避免流量被大头IP抢走。孙哥早早入睡,将直播时间定在早上5点至7点,但在这时间段直播吃饭有点格格不入,多数时间孙哥就待在屏幕前发呆,直播间更是冷清。
直播没有成效,葛姐比起心疼孙哥更心疼电费,为了不浪费电,葛姐也跟随孙哥一同起床,一同坐在饭桌前发呆。有观众进来了,葛姐的反应比孙哥还要快:“欢迎老铁进入直播间!”
时日不久,葛姐没烦,孙哥却烦了。他憋着一口气,非要把直播做成不可。干完手头的活后,他将后续的活全部推掉,打算做全天候直播。
葛姐对这孙哥的这一决策信心全无,心想副业怎么跑到主业去了?何况还是不挣钱的副业。两人从早上吵到晚上,谁也说服不了谁。
葛姐脾气犟,孙哥只要还嘴就开始骂脏话,骂得孙哥抓耳挠腮,无力还嘴。有一次,孙哥真的被气急了,就一脚把家里的羊踢了个半死。葛姐见劝说无用,也不再想跟他废话。她看孙哥意志坚决,索性破罐子破摔,孙哥晚上在家直播,她就拉灯线;孙哥白天在家直播,她就大声咒骂。
孙哥没办法,就把直播间从堂屋搬到了厕所,整天除了吃饭上厕所,就是对着手机直播。
穷途末路的孙哥打电话给儿子,儿子得知父亲做直播后与母亲的反应大相径庭,他表示很敬佩父亲的创作精神,并一语中的,将孙哥的原地踏步归到没有噱头这一点上。孙哥茅塞顿开,很快将直播间改造成“酒屋”,给自己定位“酒神”。
孙哥酒量大,一次两斤不在话下,改变思路后,直播间的人数有所提高,但留存量少,因为孙哥的酒量对比其他主播实在有辱“酒神”这个称号。
一次,孙哥受观众的撺掇,一口气喝光了半瓶白酒,之后就深睡不醒。葛姐将孙哥搬到床上,扇了十几个巴掌。夫妻俩的战争到了白热化阶段。
酒不能凭空而来,葛姐不肯再给孙哥买酒,孙哥又发狠以踹羊威胁,葛姐更加彪悍,声调抬高,脏话毒恶,抱着同归于尽的态度求着孙哥踹。
无奈之下,孙哥只能偷摸找儿子借钱,或者往酒瓶里灌自来水。他每天提着几个酒瓶鬼鬼祟祟的跑向茅屋,以此来勉强维持酒神的形象。
原本葛姐要第二天早上才能回来,但那天晚上葛姐在娘家接到儿子的电话,知道了孙哥向儿子要钱的消息,连晚饭都没吃就往家里赶。
夫妻因为直播矛盾,孙哥被明令禁止不准进入堂屋开展与直播有关的一切内容。葛姐走亲戚,孙哥胆子变大,肆无忌惮地在堂屋的桌子上摆了十几个酒瓶,旁边还竖着一张写有“酒神”的横幅。葛姐赶到家时,看到这一幕如五雷轰顶,气急败坏地一把抢过孙哥的手机摔得粉碎,口中脏话不停,对着孙哥拳打脚踢。自觉做错事的孙哥一声不吭,任凭葛姐一个又一个的巴掌打在脸上。
葛姐越说越气,从头至尾数落孙哥的不是。这里就出现了致命性的转折,葛姐把电车里的农药砸在孙哥身上:“你喝酒厉害,你有能耐喝药!”
孙哥一声不吭地拧开瓶盖,将瓶盖安稳放在桌面上,清了清嗓子,随即将农药一仰而尽。
葛姐没想到孙哥如此果断,她愣了愣神,又是一阵大骂,从车篮里又拿出一瓶农药:“好喝吗?还要再喝一瓶吗?”孙哥见状就要来拿,葛姐将农药扔进羊圈里,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看到妻子哭成这样,孙哥坐在用小台灯照明的桌子旁,怯怯地说:“别哭了,酒是我兑的水。”
2021年3月11日凌晨五点二十七分,还未进行救助,孙哥已无生命体征。这个时间,一个月前的孙哥刚起床,还坐在手机屏幕前发呆。
直到孙哥的尸体被推进太平间,葛姐也不相信丈夫真的死了。她反复向我同事说,孙哥喝了一瓶农药后,精神状态仍旧良好,他哄着葛姐从地上起来,还去厨屋炒了两个菜。一个青椒炒花菜、一个白菜粉条,稀里糊涂中磕了两个鸡蛋。
葛姐见孙哥身体并无大碍,不好拉下脸关心,指桑骂槐地问孙哥农药味道咋样。孙哥想了想,还吧唧一下嘴,说没啥味道,应该是过期了。
孙哥嘿嘿笑笑,像是在考虑什么,突然开腔问:“你说你把手机砸了干啥?还得再买一个。”
医生说,那个时间段孙哥就应该出现状况了,如果早点发现并送医,说不定还能保住一条命。
编辑 | 蒲末释
=============================================================
6月的主角是17、18岁的少年,故事的内容关于梦想的追逐。2021年,全国高考人数预计超过1100万人,这批少年将在6月7日迈入高考考场,写下青春的答案。
考场之外是另一场“考试”。故事主角是考生的父母,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是第一次当考生家长。面对高考,他们又与孩子一样毫无经验。摆在他们面前的,同样有一张需要回答的试卷,关于期待,关于陪伴,也关于为人父母的再一次成长。属于他们的考试,早于6月份之前就开始了。
距离高考还有3个月的时候,河北邯郸的高三学生王晓芊彻底放松了一回。2015年春天,她告别读书声笼罩的邯郸,飞往欧洲,参加学校与丹麦一所高中联合举办的交换项目。
行程为期10天,先到两所高中与当地学生交流,随后他们有6天时间在附近几个欧洲城市游玩,全程住在寄宿家庭之中。虽然学校没有限制报名学生的年级,但所有准备与人生大考正面相逢的高三学生中,只有王晓芊欣然地去了。得知王晓芊可以出国游玩,班里的同学们惊呼一片,有羡慕,也有不理解。
她的父亲王立为她签署出行同意书时经过了几番犹豫。当时距离全市统一排名的高三年级第一次模拟考不到1个月,他担心女儿没有时间备考。所有人对此心知肚明,因此王立的妻子和妹妹都反对王晓芊在这个关头外出游学。
但另一边,王立可能是唯一知道王晓芊正经历学习瓶颈的长辈。高二时,晓芊学习优异,考过全年级第二名。高三以后,女儿依旧努力,成绩却退步到班里的中上游。“高二我只要学习用心一些,成绩和排名上立刻就有体现。但现在所有人都在努力,我再怎么努力成绩也上不去了。”王立记得刚步入高三时,晓芊曾这么失落地对自己说。
关于未来,晓芊也充满疑惑,“考个差不多的大学,毕业后回到邯郸,这一生不就这样吗?”即使王立一再劝说,她的人生有无限可能,不用去像他一样学个技术,在小城里过平淡的生活。但在心里,连他自己都不太相信。
自从学校规定,从走读转为寄宿之后,每周,晓芊会与王立通两次电话。通过电话线那头女儿的声音,王立看不见女儿的神情,但听得出孩子的迷茫。女儿的话越来越少,通话从每次半个小时缩减到不到10分钟。她不再像从前那样兴高采烈地与自己分享学校趣事,父女两人同时陷入了无言以对。但高考的日期越来越近,王立郁闷之余有点好笑:自己年轻的时候有过理想,终被柴米油盐和女儿的笑声代替,曾经一度,他觉得女儿平安长大,就是一生最好的杰作。但这一次,梦想这座山,他绕不过去,因为曾经他空手无忧,现在他牵着女儿的手。
在这种情况下,女儿胖了近20斤,这是他唯一欣慰的事。不过,王立知道晓芊需要换个心情,看看如果不在小城做题,孩子们会不会有其他可能呢?而他能做的就是帮她签字,相信她做出的决定,希望她能带回他年轻时候也没有得到的答案。
“晓芊的成绩一直很稳定,不会影响太多的。即使影响了就当作散心也好。”签了字,王立顺带宽慰了家人和女儿。
从丹麦回来后,晓芊虽然没有什么样貌的变化,但看上去,整个脸都变得有光了。她兴奋地跟王立分享着所见所闻,感叹:“他们那的孩子真的不一样,未来想去开挖掘机的都有,不像咱们这的孩子,最爱聊哪个专业好就业,哪个专业工资高。”王立笑笑:“那你觉得,你以后理想的职业是什么呢?”
“我觉得纪录片导演不错,想要子承父业的话,您再给我生个弟弟吧。”王立愣了愣,这显然不是他心中期待的自己女儿的答案。转眼间他也释然了:自己打拼半生,不就为了女儿有选择的余地吗。
他搂搂女儿的肩膀,“你妈在家给你做好吃的呢,咱赶紧回家吧,另外,从今天开始爸爸不问你学习成绩了,你已经向我们证明了你是个好学生,现在就往你的梦想冲吧。”

自此以后,王立轻松了很多,他能做的只有全心全意地支持女儿,相信女儿,在每个周日中午提前出现在学校门口,等着女儿放学。直到6月8日下午最后一门考试结束后,晓芊从考场出来,第一眼看到的依旧是爸爸,他的手里捧着一束鲜花。
她问:“爸,等我考上学,你的事儿就少了,以后闲了想干点啥?”
2015年5月,江苏省如皋市白蒲镇的小广场上每夜都会有人跳广场舞。平日里,高三备考生夏序晚自习回家后已是10点,只有周末有一天放松的时间。初夏晚风舒适,王优云带着女儿夏序跳广场舞。母亲跳男步,女儿跳女步,“男士要先出左脚,女士先出右脚。要根据鼓点走,第一步大,第二步小……”伴随着老式的交际舞音乐,王优云一边讲解,一遍带着女儿旋转,翩翩起舞。
双人舞时,母女俩双手相握,手臂触碰,离开,又触碰。来这儿跳舞的都是和妈妈年纪一般大的妇女和她们的爱人,起先,在其中格格不入的夏序觉得难堪。埋在书桌前太久,她能感到自己肢体僵硬,舞步不协调。这种笨拙在动作熟练优美的大人们中尤其明显,夏序含着胸低着头,拘谨地迈不开步子。
王优云注意到了女儿的抗拒,她放慢速度,牵着女儿的手,带着她迈出左脚,转身,再收回。就像夏序儿时她牵着小小的她蹒跚学步。
夏序渐渐进入状态,觉得自在。树影婆娑,晚风在叶子间穿行沙沙作响,身体上的放松让她暂时忘记了头脑里时刻敲起的响钟,忘记了自己无法克服的数学。对所有江苏考生来说,一提起“数学”两字心里就涌起百般滋味,对偏科严重的夏序来说更是如此。
夏序是2015年的高考生,她就读的白蒲高级中学坐落在如皋市白蒲镇,附近乡镇的陪读妈妈们汇聚于此,围绕着这所“江苏省重点中心”形成了生态圈。在高考前的模拟考试中,夏序的语文成绩是全市第一,数学成绩却是全市倒数,只有48分。王优云与邻居们的谈话也集中在女儿不均衡的数学和语文成绩。“听说你们夏序语文又考了全市前几。”听到这样的话,往往王优云的喜悦刚要跃出,她便立刻会想起旁人未提到的数学,“语文好又有什么用,数学糟糕成那个样子。”王优云总是这样回答,她显然没有一点骄傲。
随着高考的逼近,班主任要求夏序在语文课、政治课和历史课上都去补习数学。每一天,自5点40分开始早自习,朗读课结束后,从早饭后的7点20到晚上9点40晚自习结束,夏序的世界里只有数学。
直到看见夏序10多斤重的书包里,满满地塞满了数学试卷和参考资料,再想到母女两人每天的交流,就仅限于几句数学题。王优云决定,要做个改变了。她深知,女儿开朗、爱笑、活泼,她喜欢文学,喜欢青年作家林培源,喜欢文艺又有生活气息的小说场景。既然在学校已经有足够紧绷的琴弦,她的最大作用,应该是给孩子放松。
她想了一晚上,怎么样能让孩子开心,又不影响她学习。忽然,她想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一个未能实现的爱好。
第二天,王优云像往常一样5点钟起床,给女儿冲好燕麦片,剥几粒核桃。女儿5点半离开家后,她休息一会儿去买菜做饭,在女儿回来吃午饭前,她做好了一荤一素两菜一汤。往常,王优云会利用空闲时间坐在缝纫机前做一些缝纫的单子。这一天,她却想起2011年,自己曾跟着一位退休的舞蹈老师学过的交际舞。
20岁出头时,她去上海打工,第一次走进电影院,第一次在荧幕上看到男女主角跳交际舞。从那时起,王优云就对舞蹈充满向往。她算是有些天赋,不出半个月,就把“慢三慢四”跳得熟练。那些舞步在回忆里被打捞起,她一边细想着动作,一边在家里的客厅移动着脚步,再次体会着脚尖跳跃带来的快乐。当女儿出现在门口,诧异地看着她时,她说:“丫头,今天先别学了,咱们出去跳舞吧。”
夏序瞪大眼睛,“妈!你又搞什么鬼!”王优云说:“大晚上说鬼不好!你整天泡在题堆里,一天到晚总得喘喘气吧。妈妈想明白啦,数学我根本不懂,聊也聊不明白。嘿嘿,你看我整天把你照顾那么好,你应该也回报下我。”
在高考前的两个月,她带着女儿夏平去跳广场舞,母女俩从毫无交流,到无所不聊。王优云突然感觉,因数学成绩——这一横亘在母女俩之间的深沟,她竟好久未听过女儿信任地和她聊心里话。她不想以单一的成绩评价女儿,而是想让女儿能在压力下保持韧劲和快乐,“这比数学重要。”她说。

因心态渐渐稳定,高考成绩出来后,夏平的数学提高了60分。王优云跳双人舞的喜好,也逐渐被朋友知晓。她未想到,女儿的高考,竟也帮她实现了一个过去的心愿。
03
2018年6月7日,书虹已经在高考考场潍坊七中的门口等了将近4个小时。福寿街长松路的路南是潍坊七中的校门,教学楼在烈日下沉默着,书虹的视线黏在一扇又一扇窗户上,似乎能穿透窗户辨认出几百米外埋头书写的少年的身影。
11点半,铃声和停止作答的声音响起。被晒烤得恹恹的书虹精神起来,伸缩门打开了一个缺口,学生们从远处分散的各地聚集到门口,他们有相似的神情,带着松了一口气的快活,和无法泄气的紧张。在人流里,书虹看到了自己的儿子北河。
书虹挥挥手,北河也看到了母亲:她穿着牛仔裤,普通的运动T恤,马尾看上去不是那么整齐,脸颊边头发都湿了。母亲的电动车后座被晒得发烫,学校周边空旷,没有什么饭店。书虹载着儿子骑行了大概10分钟,走进了一家永和豆浆。饭菜摆在桌上时,书虹突然冒出一句话:“哎呀,我终于能放假了!”
北河懵了:“什么放假?咱家店要歇了吗?”这是北河印象里,为数不多跟妈妈吃饭的时刻,他意外地听到了,母亲说起埋藏在心里已久的,小小的愿望。
在潍坊一家市场西南角的理发店和蛋糕店中间,书虹经营着一家卤菜小饭店。在潍坊这所城市,书虹和爱人紧紧抓住开店这一谋生方式,不敢有丝毫懈怠。除了极端的暴雨天气,10多年内,夫妻俩没有一天不按时开店。
每天5点钟,书虹起床,在家里的厨房开始炖汤卤肉,先做好卤水,再放进去板鸭,猪肉,牛肉。包装后再带去市场,经过繁忙的午市和晚市,站一天后回到家基本已经是夜晚10点。洗葱拍姜的声音和卤水的香味,在北河童年的一个又一个清晨唤醒他。书虹身上常年也带着淡淡的卤菜香味,这种香味让北河感到安全。
对北河而言,这种味道无比熟悉,但能看到妈妈,吃顿妈妈做的菜却极其陌生。书虹对北河怀有愧疚,开店每天早出晚归,从上小学起,北河就已经学着自己在学校边买饭吃,或者回家自己给自己煮面。初中和高中,北河都是在寄宿学校就读,一般双周周末北河回家,也恰逢是自己生意最忙的时候,她有时都没时间给北河做顿饭吃。
儿子喜欢什么运动,平时等在档口他捧着的书是什么书,儿子和同学们的关系怎么样……这些书虹都一无所知。因为知道无法弥补儿子成长中的缺失,用食物表达爱意和关切是书虹最习惯的方式。每次去学校前,北河把自己的衣物放进行李箱,书虹再往箱子里塞满各种吃的:自己家做的卤肉,去了学校可以和同学们分着吃,儿子喜欢的薯片等膨化食品,还有儿子喜欢吃的荔枝。

在这顿母子聚餐中,书虹说:“我们啊,从你小时候忙到大,咱们全家都没出省旅游过,妈妈也想出去玩一玩啊。”这一瞬间,北河记得家庭相册里年轻的妈妈:穿着碎花长裙,小皮鞋,麻花辫松松垮垮地垂到腰间,笑容又时髦又自信。
这一顿饭,妈妈话很多,北河也陪着妈妈说了很多,他知道她很健谈,不过以往都是为了让顾客高兴。这一次,她是真的为了自己高兴,就因为一次还未开始的远行。
04
每年,中国将有1000万以上的孩子走向考场,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是真正意义上跨过成人的一步,他们有足够的压力,更需要的是鼓励。对于家长们来说,这往往也是一次蜕变。在这三个家庭里,当家长把孩子看成独立的人格,自己也找到了最好的陪伴方式,以及想要的自主人生。
有时候,陪伴是交谈;有时候,陪伴是送行;有时候,陪伴是舞蹈;有时候,陪伴是歌声。
这群即将奔赴未来的少年们,自有天性,内生热情,本就不该被鸡汤和口号束缚,伴随他们前进的步伐,大力教育旗下的中小学课程在线辅导品牌——清北网校特别邀请了国际钢琴大师郎朗,以《少年》歌曲作为主旋律,全体清北网校的教师,与家长们和全社会一起,向每一位逐梦的高考少年唱出加油。
“高考只是人生体验,你我信念丝毫未减。”在这个特别的体验中,相信1000万高考生背后的家庭,都有各自的悲喜,但每个家长、整个社会都明白:少年已经长大,未来在他们脚下。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