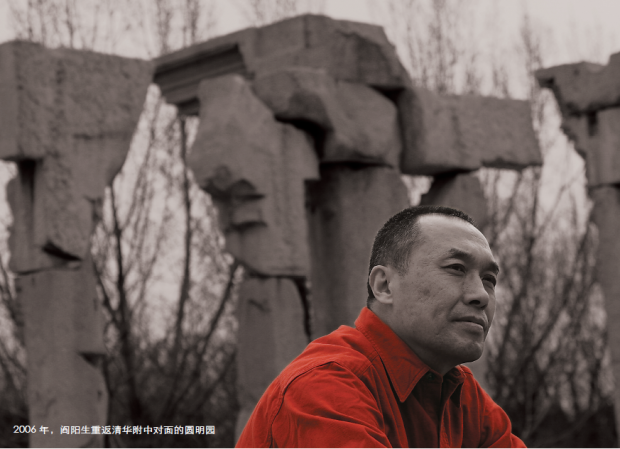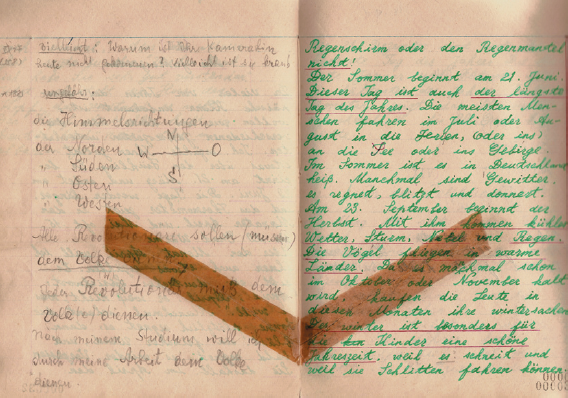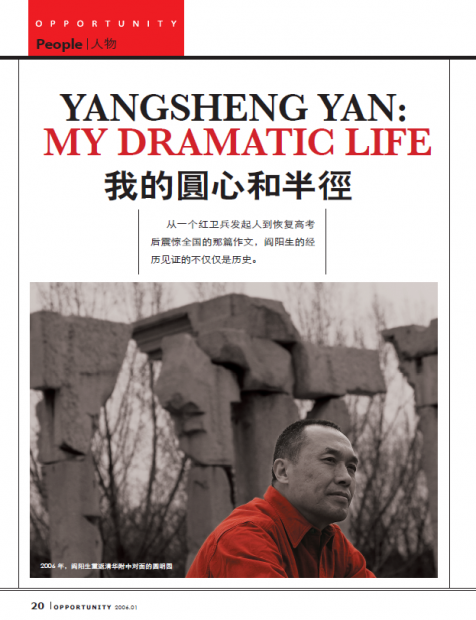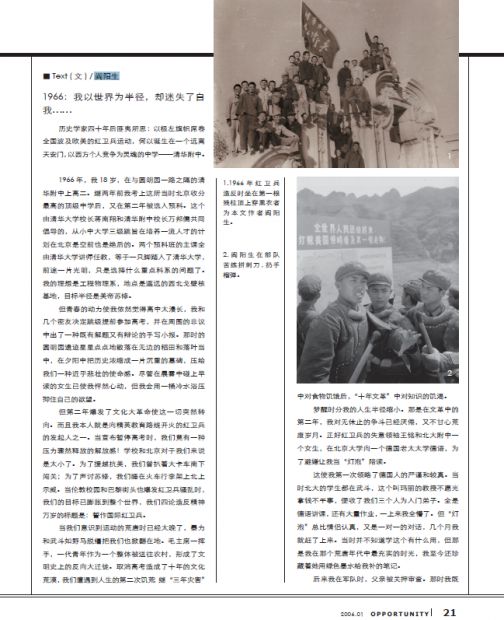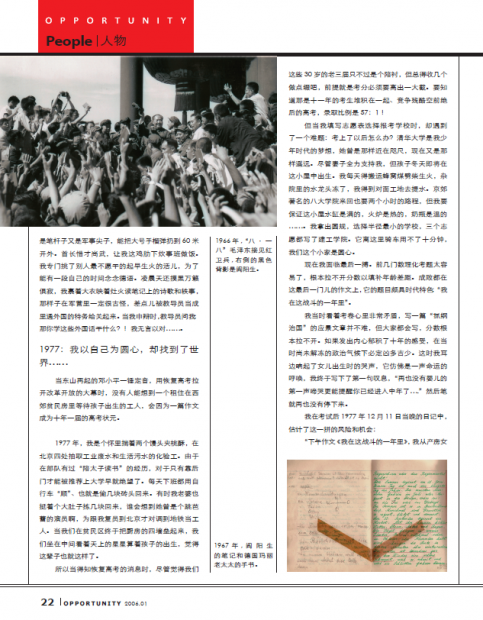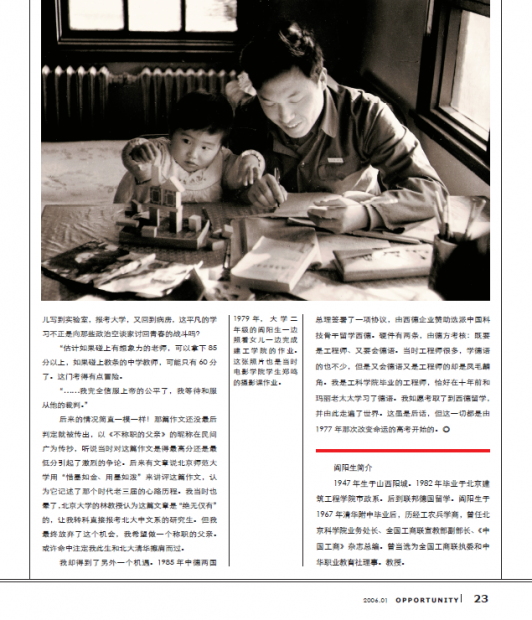阎阳生:我的圆心和半径
2021年05月28日 10:47 分类:人文 阅读:589
从一个红卫兵发起人到恢复高考后震惊全国的那篇作文,阎阳生的经历见证的不仅仅是历史。
文 | 阎阳生
1966:我以世界为半径,却迷失了自我……
历史学家四十年后匪夷所思:以极左旗帜席卷全国波及欧美的红卫兵运动,何以诞生在一个远离天安门,以西方个人竞争为灵魂的中学—清华附中。
1966 年,我18 岁,在与圆明园一路之隔的清华附中上高二。继两年前我考上这所当时北京收分最高的顶级中学后,又在第二年被选入预科。这个由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和清华中校长万邦儒共同倡导的,从小中大学三级跳旨在培养一流人才的计划在北京是空前也是绝后的。两个预科班的主课全由清华大学讲师任教,等于一只脚踏入了清华大学,前途一片光明,只是选择什么重点科系的问题了。我的理想是工程物理系,地点是遥远的西北戈壁核基地,目标半径是美帝苏修。
但青春的动力使我依然觉得高中太漫长,我和几个密友决定跳级提前参加高考,并在周围的非议中出了一种既有解题又有辩论的手写小报。那时的圆明园遗迹星星点点地散落在无边的稻田和落叶当中,在夕阳中把历史浓缩成一片沉重的墓碑,压给我们一种近乎悲壮的使命感。尽管在晨雾中碰上早读的女生已使我怦然心动,但我会用一桶冷水浴压抑住自己的欲望。
但第二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使这一切突然转向。而且我本人就是向精英教育路线开火的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当宣布暂停高考时,我们竟有一种压力骤然释放的解放感!学校和北京对于我们来说是太小了。为了援越抗美,我们曾扒着大卡车南下闯关;为了声讨苏修,我们睡在火车行李架上北上示威。当伦敦校园和巴黎街头也爆发红卫兵骚乱时,我们的目标已膨胀到整个世界,我们四论造反精神万岁的标题是:誓作国际红卫兵。
1966 年红卫兵造反时坐在第一根残柱顶上穿黑衣者为本文作者阎阳生。
当我们意识到运动的荒唐时已经太晚了,暴力和武斗如野马脱缰把我们也掀翻在地。毛主席一挥手,一代青年作为一个整体被送往农村,形成了文明史上的反向大迁徙。取消高考造成了十年的文化荒漠,我们遭遇到人生的第二次饥荒:继“三年灾害”中对食物饥饿后,“十年文革”中对知识的饥渴。
梦醒时分我的人生半径缩小。那是在文革中的第二年,我对无休止的争斗已经厌倦,又不甘心荒废岁月。正好红卫兵的失意领袖王铭和北大附中一个女生,在北京大学向一个德国老太太学德语,为了避嫌让我当“灯泡”陪读。
这使我第一次领略了德国人的严谨和较真。当时北大的学生都在武斗,这个叫玛丽的教授不愿光拿钱不干事,便收了我们三个人为入门弟子。全是德语讲课,还有大量作业,一上来我全懵了。但“灯泡”总比情侣认真,又是一对一的对话,几个月我就赶了上来。当时并不知道学这个有什么用,但那是我在那个荒唐年代中最充实的时光,我至今还珍藏着她用绿色墨水给我补的笔记。
1967 年, 阎阳生的笔记和德国玛丽老太太的手书。
后来我在军队时,父亲被关押审查。那时我既是笔杆子又是军事尖子,能把大号手榴弹扔到60米开外。首长惜才尚武,让我这鸡肋下炊事班做饭。我专门挑了别人最不愿干的起早生火的活儿,为了能有一段自己的时间念念德语。凌晨天还摸黑万籁俱寂,我裹着大衣映着灶火读笔记上的诗歌和轶事,那样子在军营里一定很古怪,差点儿被教导员当成里通外国的特务给关起来。当我申辩时,教导员问我:那你学这些外国话干什么?!我无言以对……。
阎阳生在部队苦练拼刺刀, 扔手榴弹。
1966 年,“八· 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 右侧的黑色背影是阎阳生。
1977:我以自己为圆心,却找到了世界……
当东山再起的邓小平一锤定音,用恢复高考拉开改革开放的大幕时,没有人能想到一个租住在西郊贫民房里等待孩子出生的工人,会因为一篇作文成为十年一届的高考状元。
1977 年,我是个怀里揣着两个馒头夹桃酥,在北京四处抽取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化验工。由于在部队有过“陪太子读书”的经历,对于只有靠后门才能被推荐上大学早就绝望了。每天下班都用自行车“顺”、也就是偷几块砖头回来。有时我老婆也挺着个大肚子拣几块回来,谁会想到她曾是个跳芭蕾的演员啊,为跟我复员到北京才对调到地铁当工人。当我们在贫民区终于把厨房的四墙垒起来,我们坐在中间看着天上的星星算着孩子的出生,觉得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所以当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时,尽管觉得我们这些30 岁的老三届只不过是个陪衬,但总得收几个做点缀吧,前提就是考分必须要高出一大截。要知道那是十一年的考生堆积在一起、竞争残酷空前绝后的高考,录取比例是57:1 !
但当我填写志愿表选择报考学校时,却遇到了一个难题:考上了以后怎么办?清华大学是我少年时代的梦想,她曾是那样近在咫尺,现在又是那样遥远。尽管妻子全力支持我,但孩子冬天即将在这小屋中出生。我每天得搬运蜂窝煤劈柴生火,杂院里的水龙头冻了,我得到对面工地去提水。京郊著名的八大学院来回也要两个小时的路程,但我要保证这小屋水缸是满的,火炉是热的,奶瓶是温的……。我拿出圆规,选择半径最小的学校,三个志愿都写了建工学院。它离这里骑车用不了十分钟,我们这个小家是圆心。
现在我面临最后一搏。前几门数理化考题太容易了,根本拉不开分数以填补年龄差距。成败都在这最后一门儿的作文上,它的题目颇具时代特色:“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我当时看着考卷心里非常矛盾,写一篇“抓纲治国”的应景文章并不难,但大家都会写,分数根本拉不开。如果发出内心郁积了十年的感受,在当时尚未解冻的政治气候下必定凶多吉少。这时我耳边响起了女儿出生时的哭声,它仿佛是一声命运的呼唤,我终于写下了第一句叹息,“再也没有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更能提醒你已经进入中年了….”然后笔就再也没有停下来。
1979 年, 大学二年级的阎阳生一边照看女儿一边完成建工学院的作业。这张照片也是当时电影学院学生郑鸣的摄影课作业。
我在考试后1977 年12 月11 日当晚的日记中,估计了这一拼的风险和机会:
“下午作文《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我从产房女儿写到实验室,报考大学,又回到病房,这平凡的学习不正是向那些政治空谈家讨回青春的战斗吗?
“估计如果碰上有想象力的老师,可以拿下85分以上,如果碰上教条的中学教师,可能只有60 分了。这门考得有点冒险。
“……我完全信服上帝的公平了,我等待和服从他的裁判。”
后来的情况简直一模一样!那篇作文还没最后判定就被传出,以《不称职的父亲》的昵称在民间广为传抄,听说当时对这篇作文是得最高分还是最低分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后来有文章说北京师范大学用“惜墨如金、用墨如泼”来讲评这篇作文,认为它记述了那个时代老三届的心路历程。我当时也晕了,北京大学的林教授认为这篇文章是“绝无仅有”的,让我转科直接报考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但我最终放弃了这个机会,我希望做一个称职的父亲。或许命中注定我此生和北大清华擦肩而过。
我却得到了另外一个机遇。1985 年中德两国总理签署了一项协议,由西德企业赞助选派中国科技骨干留学西德。硬件有两条,由德方考核:既要是工程师、又要会德语。当时工程师很多,学德语的也不少,但是又会德语又是工程师的却是凤毛麟角。我是工科学院毕业的工程师,恰好在十年前和玛丽老太太学习了德语。我如愿考取了到西德留学,并由此走遍了世界。这虽是后话,但这一切都是由1977 年那次改变命运的高考开始的。
原载《机遇》2006-01期。

阎阳生
阎阳生,1947年生于山西阳城。1967年清华附中毕业后,历经工农兵学商,1982年毕业于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市政系。后到联邦德国留学。曾任北京科学院业务处长、全国工商联宣教部副部长、《中国工商》杂志总编辑。
一份曾经轰动的高考作文:
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当年,北京市环保所工人阎阳生的高考作文《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曾因其“另类”而引起轰动,成为那个大变革前后的注脚。据作者介绍,阅卷时,年轻的老师只给70分,年老的要给85分。争论之余,全体评定,评95分,立为北京市范文。
由于评卷老师的激烈争论,该文后来传入社会,引起轰动,被民间称为《不称职的父亲》。1978年5月30日《北京日报》首先全文发表,并以半版登刊作者文章《我们要珍惜有春之年》。以后海内外各报刊纷纷给予刊登和相关文章。1978年7月17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由林如、铁成播送全文和张秉戍的评论《一篇独具个性的好文章》。

阎阳生高考作文
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再也没有比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更能提醒你已经进入中年了。这是个女孩儿,皱着眉头哭着。大概她也像门口的那个护士一样,不相信这个挎着书包、满脸胡茬的人就是她的父亲吧。
常言道:人过三十不学艺。而我却好像故意和年龄作对一样,日夜埋头在做十几年前应做的事:投考普通大学。当然啦,鼓励支持,冷嘲热讽,各种反应都有。但是激励我干下去的却是这样一件小事。
开春的时候,一些外国的技术人员和厂商要来修理一台进口的色谱仪。这台仪器已经好几年没有人动它,在角落里发着令人生畏的幽光。当它得以重见天日的时候,我们花了好几个月的日日夜夜,却无法使它正常工作。由于在保修期,根据合同请原公司派人来修。
这些外国人几天的检修,机器正常了。而我既不知道它是怎么坏的,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好的。在和这些外国人的座谈会上,在他们友好的外表下面,在他们彼此会意的眼神中,我感到他们无法掩饰的轻视,像针扎一样。回家的路上,我和老陈我们的技术员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在分手的时候,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惭愧呀!我理解他的心情,作为祖国培养了这么多年的技术工作者,再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在他的话里不仅有内疚,更感到一种力量。从这儿以后,我们不约而同地开始了一个钻研学习的热潮。我们的口号是:向四人帮讨还时间,为祖国争气。而我更给自己立下了一个目标,要在一年里拼命拿下本行的专业和外语。
学习是困难的。眼前的线路图像蜘蛛网一样,而单词忘的比记的快。在深夜,当我眼睛发疼,头脑快要胀裂的时候,我也常想,何必呢!快30岁的人了。但我一想到那个外国人眼睛里流露出的嘲笑,便感到一股不可遏制的力量,用冷水冲冲头,继续看到天色微明。半年的时间,我虽然能捧着字典看说明了,但仍无法弄懂它的原理。有时我想:如果能在学校里系统地学习一下多好啊!但马上又打消了这个念头,那是有门路的人去的地方,再说,谁要你这个老学生呢?
所以,你可以理解,当我知道像我这样30岁的人也可以有一次最后的机会考大学时,是多么的振奋了!我拿起学生时代的课本,好像看到了久违的朋友;当我用铅笔解题的时候,就好像以往老师站在背后盯着我,心里扑扑直跳。开始我还不好意思把中学课本拿到单位去看,但我一想到那洋人的眼神,便一下抛弃了全部包袱。年纪大,水平低,并没有什么可羞的,可羞的是关键时刻你拿不出东西来,丢祖国的脸。我很快瘦下去了。
母亲,她是一个退休的教师,望着我深陷的眼睛摇着头。但她总是在半夜给我端上一碗热鸡蛋挂面,轻轻地说:别累坏了,哪能十年的功课一下子赶上呢?我感到她走了,却给我留下了难言的温暖和鼓励。她是支持我的,但心疼。
考试的日期一天天近了,我的孩子也一天天快要出世了。如果不是别人在图书馆里找到我,别说孩子出世,就是孩子她妈住院了,我都不知道。当我冲进病房时,差点把阻拦的护士撞了个跟头。我站在这婴孩面前,那种惊喜和惶恐的心情是每一个第一次做父亲的人都可以理解的。但我站在这疲惫的母亲面前的另一种心情,却是别人没法体会的。在这一年里,我干了些什么呢?别说当个好丈夫,更不要说当个好爸爸了。我捏着自己油污的帽子,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我应该干点什么呢?什么也不用你了,她吃力地张开苍白的嘴角:你去温书吧。
当我回家摊开书本的时候,窗外正飘下最初的雪花,我想起了这一年。我感到尽管在家庭里我是这么不称职,但我是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着:坚实、有力。我想,亲人和这刚出世的姑娘会理解我的:不战斗,再年轻也已经衰老;战斗,再年老也会永葆青春。谁说人过三十天过午,我感到自己身上正复苏着一股新鲜旺盛的活力。我感到自己年轻了,朴实了,振奋了。这平凡的、有时往往是枯燥的学习,不正是向那些政治空谈家讨还青春的战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