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祖父的「科举舞弊案」,究竟是怎么回事? | 短史记
问:请编辑说一说鲁迅祖父科举舞弊的事情。
一、周福清的如意算盘
这桩案子发生在1893年,也就是光绪十九年。
鲁迅的祖父名叫周福清,生于1837年。他填给官府的资料少写了七岁,说自己生于1844年,目的是推迟退休之日以便多做几年官。1871年,周福清以三甲第十五名考中进士,四年后被分配去江西金豀做知县,很快又因“办事颟顸”被两江总督沈葆桢弹劾丢了职务。为维系官场生涯,周福清不得不出钱另捐了一个正七品的“内阁中书”,这是个没有油水的小京官,主要负责撰写翻译公文。
从1879年开始,周福清在内阁中书这个没油水的职位上,干了十余年没有挪窝,直到科举舞弊案爆发。这期间,周福清的经济状况相当窘迫,“虽然还不要用到家里的钱,但也没有一个钱寄回来”。同乡王继香在日记里说,众人知道周福清没钱,出门是不肯坐车的,所以聚会时都不坐车,以免因分摊车钱给周福清增加压力。
改善经济上的窘境,是周福清在1893年筹划运作科举舞弊的重要动力之一。
1894年是慈禧的六十大寿。作为庆祝,清廷决定在这年开一场恩科,录取一批读书人进入体制。按制度,京城里要开恩科,地方上就得提前一年进行乡试选拔。周福清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第一,他的母亲在1893年初去世,他以丁忧的名义回家奔丧,不受日常文书工作的约束,有大量的时间用来筹划运作。第二,此次派往浙江主持乡试的主考官殷如璋,是周福清的科场同年。
周福清是一个很谨慎的人,没有选择在浙江境内操办此事。他带了一名叫做陶阿顺的仆役,赶去苏州的胥门码头等候殷如璋,那里是前往杭州的必经之路。寻到殷如璋的坐船后,他也没有亲自出面,而是先命陶阿顺带去了一封信。
据浙江巡抚崧骏1893年10月13日给朝廷的奏折,信中除一张周福清的名片,一张写有“外年愚弟”的帖子之外,还有两张纸。一张纸上写着贿赂的出价是“凭票洋银一万元”,另一张纸上写着舞弊受益考生的姓氏,分别是“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第八”,意即除了马、顾、陈、孙、章五人外,还有周福清的儿子周用吉(也就是鲁迅的父亲)也参加了这次考试,要请殷如璋一并照顾——前五人是贿银的出资者。按周福清的计划,此行不但可以捎带着让儿子金榜题名,还可以在事成后从五家人那里得一笔不菲的酬劳,可谓如意算盘。
没想到的是,接到信的殷如璋,先是命人将送信的陶阿顺扣了下来,然后又把写信的周福清给告发了。

图:绍兴鲁迅故居所藏周福清像
二、烫手的贿银
殷如璋为什么要告发周福清?
有说法称,这是因为陶阿顺办事稀里糊涂,将行贿的帖子送错了。周福清计划里的行贿对象,不是主考官殷如璋,而是副主考官周锡恩。殷、周二人当时都在船上,陶阿顺误将帖子送到了殷如璋手里,“殷知道周锡恩涉嫌卖关节,好处他自己独吞;周则要撇清自己,必须装作毫不知情,于是坚持严办”,二人都要彰显自己的光明正大,周福清就只好倒霉了。
这个说法捕风捉影,与实情相去甚远。据官方留存档案,周福清的信内有一张“外年愚弟”的帖子,可见他的行贿对象是殷如璋没有错——周锡恩并不是周福清的科举同年。
之所以找对了行贿对象,却仍被行贿对象举报,是因为行贿被人给撞见了,而撞见者,又恰是副主考周锡恩。1894年底,周锡恩给自己的老师赵次珊写过一封私信,里面提到,自己不但是陶阿顺送信行贿的撞见者,也是揭发周福清的主张者:
另据周作人《知堂回忆录》里讲,周福清派陶阿顺(周作人误记为徐福)去送信,“那时恰巧副主考周锡恩正在正主考船上聊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乡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边叫喊,说银信为什么不给回条?这件事便戳穿了”。周作人的说法或来自家中长辈,与周锡恩的私信,恰可互为佐证。
也就是说,周福清行贿被揭发,纯属操作上出现了失误,是一个偶发事件。对主考官殷如璋来说,为了一万元贿银去搞定副主考周锡恩,是一件非常不划算、且存在未知风险的事情。所以他宁愿不要这烫手的银子,而是跟周锡恩一起,将周福清给举报了。
三、又不是只有我这么干
陶阿顺被扣押后,周福清先是遁逃到上海观察形势;该案由江苏移交给浙江审理后,周福清又主动前往杭州投案。
在杭州知府衙门的公堂上,周福清似乎并不认为自己犯了多严重的罪行。他甚至说出了“交通关节者已不止一科”(又不是只有我这回这样干,之前的历届考试都有人行贿舞弊)这种话。但让他没有料到的是,苏州码头上的“登船行贿未遂事件”,已被苏浙官场中人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迅速传开,也进入到了朝中御史们的耳朵。御史林绍年在1893年底,就把周福清“交通关节者已不止一科”这句话写进了自己的奏折;更早一些时候,御史褚成博也在奏折里对皇帝说,苏州“登船行贿未遂事件”已在苏浙两省到处传播,正派的读书人个个惊叹愤慨,连京城里的士大夫也在传这个事。
周福清有这种认知并不奇怪。有清一代,尤其是到了中晚清,朝廷为科举舞弊制定的刑罚虽然严厉,但绝大多数的科举舞弊者并不会得到惩罚。因为他们大概率不会被揭发。今人所能知晓的中晚清时代的科举舞弊案,或是因为政治斗争的需要而成案,或是因为某些极偶然的因素而暴露——周福清“登船行贿未遂”,就是偶然因素所致。
另一个常被拿来举例的嘉庆年间“樊顺承科举舞弊案”,案发也极为偶然。岳麓书院的学生彭珴,被考场的工作人员樊顺承割了考卷,移花接木给了另一名考生傅晋贤(让后者重抄一遍)。没想到傅竟中了头名解元,考卷被公开张贴出来,于是案情曝光。即便曝了光,彭珴也曾被说动私了,若非岳麓书院院长不肯松口,案子仍会消弭于无。樊顺承在临刑前,也说了与周福清相似的话:
大意是:姓彭的只考了一次,只被我割了一次考卷,根本不算什么。之前新化县有一个姓戴的,考了八次都得中,八次都被我割卷换成了别人。萧穆《敬孚类稿》里说,监斩官听到他说这些话,“虑生旁案”,立即让刀斧手快快行刑。
四、奏折里的玄机
御史上奏后,光绪皇帝下了谕旨,要浙江巡抚崧骏“严切根究”,从严从重好好查一查这个事,看看背后到底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内幕。
对崧骏来说,周福清是生是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事不能牵扯太广,谁的屁股都不干净,一旦往深了查,火很可能会烧到身边人甚至自己身上。周福清那句“交通关节者已不止一科”并不是虚言。所以,处理好此事的关键,是将案情止于周福清,不能让它蔓延到主考官殷如璋的身上——此案最直接的疑点,就是周福清与殷如璋之间是否早已存在勾结。
为了将主考官殷如璋从案中完全摘出来,崧骏在10月份和12月份给朝廷的两次回奏中,完全抹去了副主考官周锡恩在案件中的角色,只字不提是周撞见了陶阿顺前来送贿信,也只字不提是周主张告发周福清。只给皇帝留下了一个“殷如璋拿到贿信后就正气凛然告发了周福清”的光辉形象。周锡恩后来在私人信函里说,崧骏这样处理之前,曾征求过自己的意见。自己不想得罪人,于是就答应了:
大意是:如果在奏折里写上是我撞见,然后主张揭发,那就等于将身为正考官的殷如璋推入一种“与周福清早有勾结”的嫌疑处境。崧骏和我商量这个事,我同意他这样处理。
除了让殷如璋成功上岸,崧骏还得致力于如何不扩大案情。在1893年10月份给朝廷的回奏里,崧骏已然发现陶阿顺本是绍兴府陈顺泉家的佣工,是被周福清临时借用,然后一同来到苏州的。这并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他没有循着这条线索继续查下去,而是告诉皇帝,行贿信里的“马(官卷)”已经查出来了,因为这届考生里只有一个叫马家坛的人是官卷。周福清的的儿子周用吉也查出来了。其他顾、陈、孙、章,只有姓氏没有名字,实在没法查。得等将周福清捉拿归案,才可能有结论。
稍后,周福清主动投案自首。崧骏在1893年12月第二次给朝廷回奏案情。这一次,他完全删去了“陶阿顺本是绍兴府陈顺泉家的佣工,是被周福清临时借用”这个情节,只说陶阿顺是周福清的仆人。回奏里还说,周福清去向殷如璋行贿,完全是临时起意。他从绍兴北上,本来是要去京城里探亲。走到上海听说自己的同年殷如璋是乡试的主考官,就“一时糊涂”想要为自己的儿子买通关节,又想到亲友当中有马、顾、陈、孙、章五家有钱人,也都有子弟参加考试,并不和他们商量,就把他们一并写上了。反正“各亲友家道殷实,不患无人承应,事后必有酬谢之资”,这些人家都很有钱,不愁事后收不到行贿的银两,也不愁事后他们不给自己酬劳。
这种说法,实在是鬼都难信。不经人同意,就替人去行贿,行贿的数额又不能算小(每户二千洋银),本就不合情理。人家并不需要,或者有其他更好的舞弊渠道,都是可能。而且,人家事前不知有行贿之事,得中后认定是自己学问过硬,将跑来“报销贿银”的周福清打出门去,也是有概率发生的事。崧骏之所以审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只有这样处理,才能避开一场大案,才能免去拔出萝卜带出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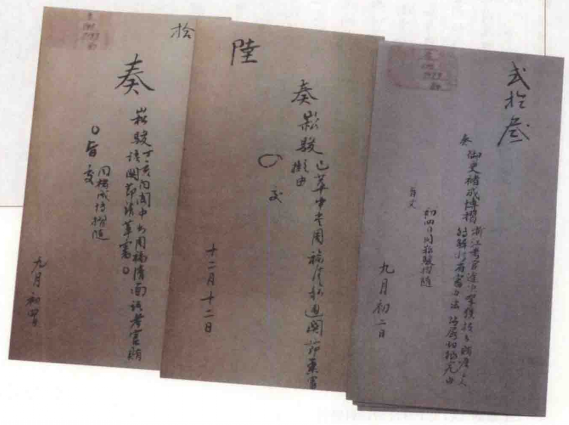
图:崧骏等人关于周福清案的奏折
五、副主考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让副主考周锡恩没想到的是,自己主张告发周福清,结果却成了“周福清科举舞弊案”中最无辜的受害者。崧骏为保殷如璋,将周锡恩的名字从奏折里略去,产生了两个后果:
这些后果,直接导致周锡恩被言官们风闻弹劾,要求调查他究竟有没有问题。虽然调查没有结果,但在晚清士人的笔记当中,周锡恩已成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卖功名之人。这让他非常郁闷。
至于主犯周福清,崧骏在奏折里主张对他从轻发落,理由是他行贿是临时起意,贿银也没有真的送到殷如璋手里,事后又主动投案自首。刑部不愿做恶人,表示同意崧骏的主张,“拟杖一百,流三千里”。但光绪皇帝很愤怒,不肯如此轻拿轻放,御批“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没人为周福清辩驳,大案发生的可能性已经消弭,他的生死是无关紧要的。
顶着“秋后处决”的圣旨,周福清在狱中战战兢兢地熬日子。万幸的是,1895年,光绪皇帝的愤怒已经消失,没有在他的名字上打勾。五年后,作为对八国联军攻陷京城之事的反思,清廷决定释放一批死刑犯,周福清也在其中。他回到家中,发现长子周用吉已经病故。
周福清活到了1904年。他的孙子鲁迅后来在自传里说,祖父的这场“科举舞弊案”,让原本有四五十亩水田的家里“几乎什么都没有了”,也让自己成了一个寄居在亲戚家里的“乞食者”。
参考资料
①房兆楹,《关于周福清的史料》。
②朱正,《周福清科案述略》。
③《周福清科场案资料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④陈春生,《周福清科场舞弊案的另一方——从新发现的一则资料说开去》,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⑤黄恽,《李超琼所记周福清贿案》。
=======================================================
「戊戌六君子」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理念分歧 | 短史记
“戊戌六君子”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近代史概念,指的是在戊戌年被慈禧下令杀害的六位维新派士绅: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其中,谭、林、杨、刘四人是光绪皇帝新任命的军机章京;杨深秀是山东道监察御史;康广仁是康有为的胞弟。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六君子有着共同的主张,是一群志同道合的维新志士。其实,这是一个大大的误解。揆诸史料,六君子的意见与立场,分歧是非常之大的。
一、清廷的草率定性
六君子被定性成“一个志同道合的小团体”,最早始于清廷。
1898年9月28日,清廷下达杀害六君子的上谕,内中给他们定的罪名和刑罚是“大逆不道,着即处斩”。
次日,内阁所奉朱谕进一步将六君子的“大逆不道”罪名具体化。朱谕说:康有为宣扬邪说,利用变法的机会包藏祸心,竟然策划了“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这样胆大包天的计划,还私下成立保国会,宣扬什么“保中国不保大清”,实在是罪大恶极。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写了许多“狂谬”的文章;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则是“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
慈禧当时急于以杀伐掌控局面。所以,这份朱谕非常草率地将六君子集体定性成了“康党”。但事实确是:杨锐与刘光第二人,对康有为和康党相当厌恶;林旭在被捕之前也曾试图撇清与康党的关系。杨深秀的情形如何较为模糊。只有谭嗣同高度拥护康有为的主张,是一位无疑义的康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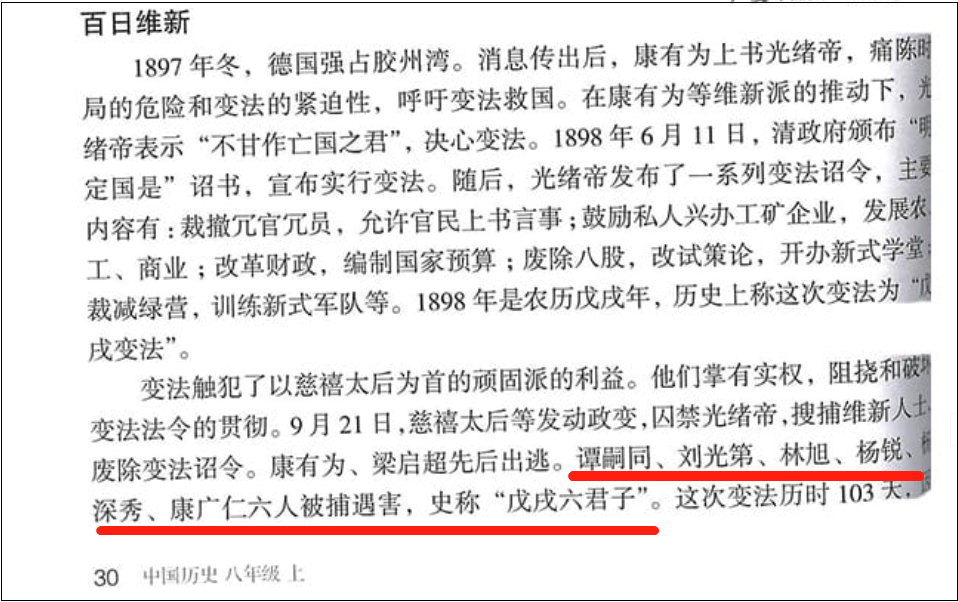
图:现行初中历史教科书对“戊戌六君子”的表述只有一句话
二、杨锐与刘光第不支持康有为
在戊戌年,杨锐与刘光第,大体可以算作张之洞门下之人。张之洞看不上康有为的学问,斥之为伪学、野狐禅。杨、刘二人的学术旨趣,与张之洞大体相近。
杨锐早年对康有为颇有好感,认为他上奏的某些条陈“透切时弊”。1897年12月,杨曾鼓动御史高燮曾上折子,推荐康去参加瑞典的“万国弭兵会”。但在戊戌年,杨锐对康有为和康党的态度,已从欣赏转变为不满与鄙视。在给张之洞的一封密信中,杨锐给了康有为一个“缪妄”的评价。信中说:
另据唐才质《戊戌闻见录》披露,谭嗣同在给唐才常(唐才质之兄)的书信中提到,在军机处担任章京一职期间,因为杨锐公开表达对康有为的鄙视,谭嗣同与他发生过正面冲突:
“伯兄”指的是唐才常,复生即谭嗣同,刘裴村即刘光第,叔峤即杨锐,南海即康有为。这段话的意思是:谭嗣同去军机处值班,与刘光第排在一起。刘没什么,做事不积极,但也闹腾。最让人担忧的是杨锐,这个人嚣张跋扈,成天取媚旧党,对康有为非常排斥。谭嗣同愤愤不平,与杨锐公开争执,他也不肯采纳。
嚣张跋扈、取媚旧党之类的负面评价,只是唐才常个人对杨锐的一种成见。但他所提到的杨锐与康有为一派不合,引发了谭嗣同的不满,则是一个重要的客观事实。
杨锐的好友高树,也在《金銮琐记》里记载称,杨锐对同为军机章京的谭嗣同、林旭二人相当不满,私下里评价谭嗣同“鬼幽”、林旭“鬼躁”:
参考戊戌年谭、林二人的行状,可以知道,杨锐之所以评价谭嗣同“鬼幽”,是因为谭与康党多有密谋而不令杨锐、刘光第等人知晓;之所以评价林旭“鬼躁”,是因为林年少轻狂,“日夜谋变更一切甚亟”,也就是不稳重,求变之心太急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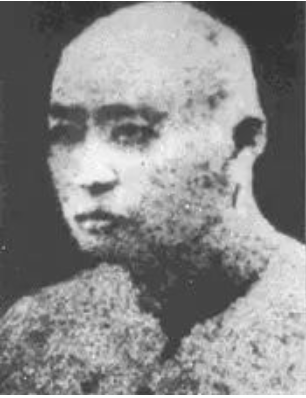
图:杨锐
杨锐担任军机章京,是张之洞请托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荐的结果。刘光第的情形,与杨锐大致相似,他任职军机章京,也是借了张之洞的力量由陈宝箴推荐。或许是因为不像杨锐那样是张之洞的心腹之人,所以刘光第事前并不知道自己会被推荐去做军机章京,入职之后也没有像杨锐那样积极活动(杨很希望促成张之洞入京,来主持变法)。
不过,刘光第对康有为和康党的恶感,与杨锐并无区别。康党开设保国会,刘仅前往一次,因不喜欢康有为等人的言论,再未有过交往。他还在家信中里感叹说,朝中新旧两党相争让人寒心,而自己是一个“无新旧之见”的人:
刘光第这封家书里“无新旧之见”的自述,与唐才常对他的观察——说他是一个“愿者”,两面不得罪人,在军机处做事,虽然不积极,但也不闹腾,可以说是一致的。
戊戌年朝中的新旧两党之争,源头在于光绪与慈禧之间的权力斗争。光绪将有关新政的奏章,一概越过军机大臣,交由新任的四章京办理,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表现。刘光第在军机处值班,知道自己被迫卷入了高层权斗,稍有不慎就会倒大霉,所以“仍以要件商诸大军机,又曾请于德宗,为言不能潜越大军机之权”——有什么重要的奏章,仍然拿去和“大军机”(也就是军机大臣,当时把军机四章京称作“小军机”)商议,还找了个机会劝说光绪皇帝,希望他不要将军机大臣们的权力架空。这些做法,在在显示出刘光第的政见与立场,与康有为和康党大不相同。
故此,当入军机处值班不过十余日的杨锐与刘广第二人,被清廷定性为“康党”而惨遭杀身之祸后,时人皆视之为奇冤。张之洞也曾急电京城,试图营救杨锐。他在电文里打包票为杨锐做担保,说他绝对不可能是康有为的同党。电文如下:
刘光第死后,他的家被查抄,结果搜出了一份尚未写完的弹劾康有为的奏疏。
事实上,在被捕之前,杨、刘二人已隐约觉察到了时代的车轮可能会从自己身上碾过。所以均动过辞官退隐的念头。杨在给弟弟的家书里说,自己没办法和林旭等人共事,军机章京这份职务实在是无法继续再做下去:
刘光第也想要辞职。他很担忧自己长期处在军机章京这种敏感职位上,“终以憨直贾祸”,会给自己招来祸端。他原本的计划,是待下一次被光绪当面召见时,就痛陈一番“新政措理失宜”,对新政来一番批判,然后就辞官回家。可惜没等到那一天,变故就已经发生了。

图:刘光第。
三、林旭、杨深秀等人的情况
林旭任职军机章京时,年仅二十四岁。他对康有为的看法,多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并没有什么定见。
1897年11月,林致书李宣龚,谈到自己与康有为的交往,称“康长素适来,日有是非,欲避未能”,所谓“是非”,大约是此时政、学两界的主流人物,均不喜欢康的学术与政治理念;林是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孙婿,以世家子弟身份在京寻求政治机会,自然是不太愿意与风评不佳的康有为和康党扯上关系。
到了1898年5月,康有为已得到光绪的青睐。林旭在为康的《春秋董氏学》作跋时,则颇为自豪地明言已做了康有为的学生,说康将他的学问“授旭读之”(传授给了自己)。
林旭进入军机处,可能与他在1898年6月被荣禄招入幕府有关。光绪选拔军机四章京,既希望贯彻自己的意志,也必须平衡满汉新旧——杨锐、刘光第与汉臣领袖张之洞关系密切,林旭与满臣荣禄有来往,又与康有为交好,谭嗣同也有湖广官场的背景,同时也是康有为的拥护者。
据时人披露,林旭当值期间,“欲尽斥耄老诸大臣”,“凡建一策,僚辈不能决者,旭大呼奋笔拟稿以进”,可见他确实是一个非常积极、同时也相当冒进的人。这种冒进,曾引发了荣禄的担忧。他写信给林,劝他在新政事务上“虚怀下问”,多与军机处的老臣们商议,不要躁进,动不动就要改这个变那个。但林当时深受康有为变更中枢决策机构主张的影响,没有接受荣禄的劝告。
据郑孝胥日记记载,变故前夕,京城空气空前紧张之时,林旭曾深夜来找郑问计。林与郑谈论良久,“自言不得以康党相待”,觉得自己也许算不上真正的康党。但这种自我安慰是无用的。另据章太炎讲,林旭被捕之前,还“哭于教士李佳白之堂”,尝试向外国传教士求助。《异辞录》里则说,林旭在被捕前一天,曾求告到李鸿章的幕僚马建忠车前,希望马建忠帮自己找李鸿章“乞命”。与张之洞急电营救杨锐不同,林旭被捕后,荣禄没有对他施以援手。

图:林旭
康广仁是康有为的胞弟,自然支持康有为。不过,在政变前夕,康广仁也曾致信友人,抱怨过兄长的许多做法是在一意孤行:
大意是:康有为做事,目标定得太高,打击面又太广,身边的支持者太少,恐怕不会成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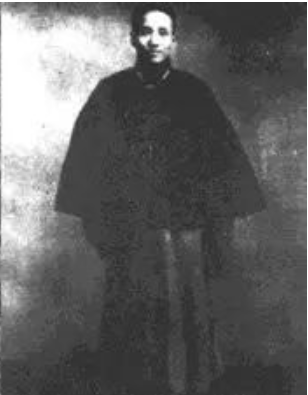
图:康广仁
杨深秀的身份是御史。他被当成康党遭到杀害,是因为他在戊戌年与康有为过从甚密。杨锐在给张之洞的密函中曾提到,御史圈里面,“惟杨深秀、宋伯鲁最为康用”。
康有为在戊戌年写了许多奏章,大多以杨深秀、宋伯鲁二人的名义呈递。结果是杨深秀被杀害,宋伯鲁逃往外国使馆得免一死。
杨深秀被杀的直接原因,是他于9月19日呈递了一份康党拟定的奏折。奏折要求光绪皇帝调袁世凯军队入京,还提议聘请李提摩太和伊藤博文为新政顾问,甚至建议皇帝考虑与英、美、日三国“合邦”。该折的附片中还有一个建议,说是颐和园内存在一个“秘密金库”,请求光绪皇帝允许募集300人,于9月23日入园正式发掘,挖出来的金子可作为变法的经费。这个建议,就是著名的“围园杀后”计划——所谓“秘密金库”,本子虚乌有。编造这个谣言,是为了有一个正规的名义将武装人员带入颐和园。在杨深秀呈递该奏折之前,谭嗣同已致信唐才常,要他带会党人马秘密入京,等待时机伪装成掘金工人,入园起事杀死慈禧。
杨深秀卷入这样的密谋,而慈禧又知晓了这个密谋,自然不会放过他。不过,杨在呈递奏折的时候,是否知晓“入园掘金”的实质乃是“围园杀后”,笔者所见资料有限,尚难以判断。

图:杨深秀
也就是说,六君子中,杨锐与刘光第二人,算不上康有为的同道。林旭与康有为的关系是摇摆的。杨深秀是否知晓康有为等人的惊天策划,也尚缺乏证据。康广仁对康有为的做事方式颇有异议。只有谭嗣同与康有为的立场最为一致,也是其各种计划的鼎力支持者。

图:谭嗣同
四、康、梁的虚假宣传
遗憾的是,六君子被清廷杀害后,康有为等人为宣传需要,刊布了许多回忆、纪念文章。这些文章,将杨锐与刘光第二人,打扮成了康有为的忠实拥趸。
如康有为写过一首《六哀诗》,里面说杨锐“与我志意同,过从议论熟”;梁启超也在《杨锐传》里说:杨锐“久有裁抑吕(后)武(则天)之志”,于是“奉诏与诸同志谋卫上变”。其实,杨锐并不知道康党的“围园杀后”计划,他的立场是调和帝后关系,而不是向慈禧夺权。康的《六哀诗》,梁的《刘光第传》里,也对刘光第做了类似的虚假描述,将刘光第对康有为的不喜欢,说成了对康有为极为敬佩。
康、梁的这种做法,与清廷对六君子的草率定性,构成了一个虚假的“呼应”。也让历史的本来面貌,发生了不应该的扭曲。
(参考资料: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 康有为〈我史〉鉴注》;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蔡乐苏等,《戊戌变法史述论稿》;王夏刚,《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