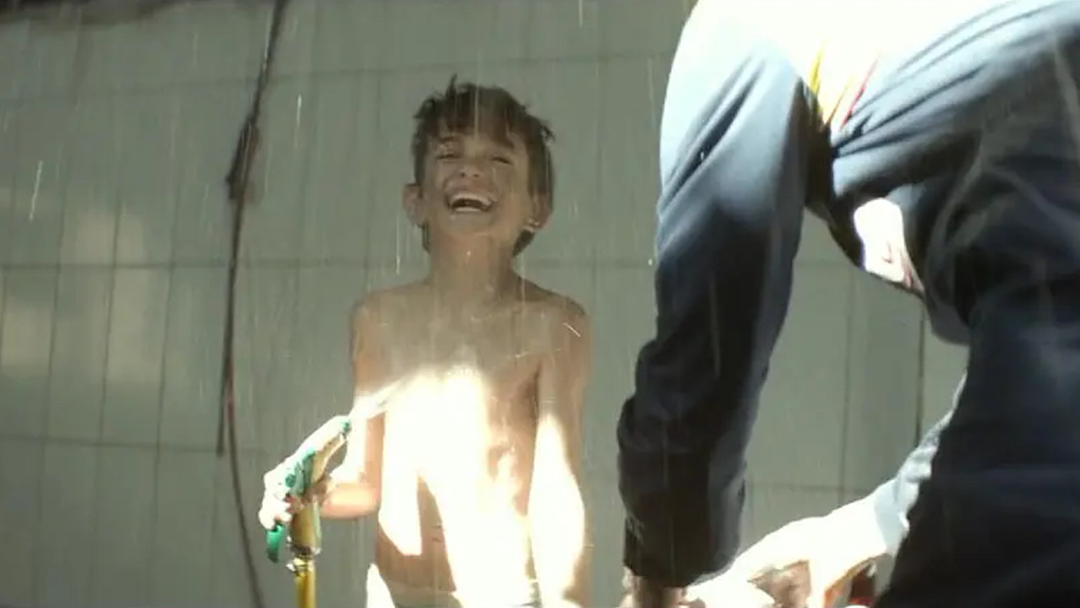女孩认真对我说,欠的钱我一定会还,你们不要打电话给我父母,不然我就去死。

2020年5月,我陷入了网贷的催债轰炸中。
每天醒来后,我看到的就是手机上狂轰乱炸的催款短信,为此我已经拉黑了好几个号码,但我知道不用过多久,就会有新的号码找到我。
火烧眉毛下,我在网上搜寻这些借贷问题该怎么处理。几番搜索后,我没找到合适的方法,却无意在一个群里发现一条招聘信息——招收的正是被我们这些欠债人称之为“狗催”的人。
对于这些狗催,我十分熟悉,催债的话术我早已滚瓜烂熟,“您的欠款已经逾期,请在下午五点前联系,否则我们会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在XX日前如未还清欠款,我们会对您进行起诉处理。”
怀着忐忑的心情,我拨通招聘号码,聊了几句后,对方就直接让我去公司报道,对于我自己欠款逾期的事情,他笑着说:“现在疫情严重,你欠的钱又还不上,不如给我们公司工作,说不定要回来一笔款子,你的债就有希望还上了。”
因为疫情,很多公司的员工无法正常到岗。而这场疫情也让不少债权人急疯了,要是欠钱的人还不上钱,他们的生活也陷入困顿,因此这种讨债公司的业务一时之间竟然变得格外繁忙。
而像我这样因为还不上钱,找不到工作成为“狗催”的人不在少数。好在公司就在我们本地,提交了体检报告后,我顺利进入了这家公司。
虽是被叫做催收公司,但明面上这种公司大多叫做“XXX信用管理公司”。我入职的这家公司已经营快8年,业务也覆盖大多数信贷渠道,包括信用卡的催收业务;公司按照一定比例提成,一些欠款金额巨大、时间久的单子,提成特别高。
这家公司办公室的面积不大,但每个人被小小的隔断分开,宛若一个独立的世界。当我进去的时候,不少催收员正情绪亢奋地打着电话。
我被分配给一个姓王的主管,他把我引到一个独立的办公室,给我介绍公司的基本情况。
自从国家扫黑除恶以来,催收公司成了重点关照的对象,因为这种工作在以前几乎和黑社会脱不开关系。但现在这些公司都基本走向正规化,九成以上的工作都是靠线上的催收员完成的,仅剩一个线下的催收部。“不到万不得已的那一步,线下催收是不会发生的。”王主管笑着解释道。
“对大多数人来说,亲戚朋友知道了,那他的生活就完了。”我听到这句话,不禁为自己捏把汗。
经过几天的培训,我正式成了一名催收员。公司严禁工作期间使用自己的手机,所有员工的手机都被锁在一个柜子里,我被分配到“支付宝花呗欠款催收部”,主要负责花呗欠款逾期的债务人。
王主管很快给了我一份欠款金额在5000元以下的名单,这些欠债人的电话大多都打不通,但因为欠款金额较小,公司也不愿意花费太多的精力,因此交给我们这些刚来的新人练练手。
我对着第一个名单连续打了几个电话,终于在第八个电话打通了,接电话的是个老年人,她告诉我,她不会使用智能机,没听过什么花呗。这是她儿子给买的老人机,她自己根本不会上网。
我估摸着,应该是她的儿子用这个号码开通了花呗。没等我把话说完,电话那头就挂了。
我问了同组的一个工作两年的催收员,要是这些人实在不还钱怎么办,他给了我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只要能打通电话,早晚会有办法让他还上的,实在不行了,就打通讯录的电话号码。”
这意味着要爆通讯录。自从2019年315晚会曝光催收行业的乱象后,公司为避免在风口浪尖上成为典型,催收手法柔和不少,一般不会对催收人的社会关系造成影响,但去年这股风声过去,一些实在不还钱的欠债人,催收员只能不断骚扰对方留下的通讯录联系人,直到这个人还钱。
手上这批5000元以下的欠债人名单,我全部打完电话后,接通的寥寥无几,同组的同事告诉我,“这种情况太常见了 ,大多数欠债人都会拉黑我们的电话号码,多换几个电话打打就好了。”
按照不同等级的催收员和员工自身的工作能力,公司会给我们安排不同任务,规定每天必须拨打一定数量的电话。当然这些业务量和我们的工资挂钩,不同等级的催收员,工资差距就越大。像一些资深催收员,他们拿回一笔大单子,提成甚至比我们这些小催收一年的工资都高。
度过新手期,我拿到第二批名单,这些人的欠款在2万到5万之间,档案上标注着每个人的姓名和工作,以及一些背景调查。按照每个人的欠款情况、逾期日期和金额,公司给每份档案里的案例从大到小排序,有些会在后面特意备注“重点”,意思是这个人要着重关注;有些标注着“学生”,意味着这个人的欠款还款能力强,因为在校学生一般到最后,父母会帮忙还上;有些标注着“文化水平低”,意思是我们可以在催收的时候使用一些话术来震慑,比如“上征信,列入失信人执行名单,不能坐飞机高铁,会影响孩子入学……”
我快速扫了一眼名单,发现年轻人几乎占八成以上,有不少都是刚毕业没两年的大学生。
“别再给我打电话了,我没钱,今年就去南方赚钱。”电话那头她的声音十分疲惫,哭着说:“我求求你们别再打电话了,我有钱肯定还。”
“我连北京的房租都交不起了,”她说她只要赚到钱,第一时间就把钱还上,以后再也不借了。我心头一软,想起自己的欠款,有些同情,但还是问道:“那你父母能帮你偿还这笔欠款吗?”
听到“父母”后,电话那头的她声音瞬间变得歇斯底里,“我告诉你们了,这钱我会自己还的,你们不要打电话给我父母,不然我就去死!”
我背后一凉。一般能联系到债务人的,就不会骚扰第三方去追讨。但根据这个女孩过往的催收记录,公司的催收员已经给她打过48个电话了。
2016年,她大学毕业,校园贷正处在疯狂阶段,周边同学考研后准备着毕业旅行,她出身农村,又没有多少钱,工作也没有着落,于是她有了第一次借款,之后就是第二次,第三次。
很快,高额的利息让她不得不借各种校园贷。后来国家打击校园贷,这些欠款才让她松一口气,但毕业后工资3千多,又让她开始了网贷。
共债意味着她同时在几家平台借贷,拆东墙补西墙,最后导致几家平台全部逾期,墙塌了。同事告诉我,像这种文化水平高,对法律知识有一定了解的人,一般的话术没多大作用,尤其是有共债情况的,更是对这些东西了如指掌。
当然,也是让催债人最头疼的,法催(用法律手段包括上征信、列入失信人)的手段对这类人没多大效果,而情催(给家人、朋友通知)往往会引起债务人的投诉,反而使得平台对公司问责,到头来,处罚的还是我们这些催收人员。
我仔细看手里的单子,最多的债务是来自年轻人“超前消费”,自从支付宝花呗借呗开通,年轻人负债上升,尝到贷款的甜头后,更加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各种网贷,以此支撑高额的消费。
我打通她的电话,她的情绪十分激动,告诉我,要是再给她打电话她就跳楼。等她的情绪稍微稳定一点,我才问她:“你还能还上这笔钱吗?”
她叹了口气,“还不上了,除了花呗和借呗,我所有银行卡、网贷都被冻结了,一分钱都贷不出来。我的朋友圈已经臭了!”她近乎崩溃:“你们要想起诉就去起诉吧,反正我什么也不怕!”
之后的好几天,我按照单子上的电话,一个接着一个打过去,接通的几乎没有。事实上,在催收系统里,90%以上的电话根本打不通。我只好用公司申请的微信开始再次联系债务人,对于这种情况,同事们都已司空见惯,大多数时间里,我们都在做一件事,就是想办法找到债务人。
又过了几天,我终于加到那个有自杀倾向的案例债务人的微信,她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哥,我最近新买的苹果11PRO,你看你要不要?”
我想知道她花这么多钱,究竟做了什么,她的资料里,在各平台的欠款接近30万。她却反问我:“我跟你说了,你们能不能不要天天打电话?”
对于情绪极不稳定的债务人,公司只能采取怀柔的政策,万一真的逼出什么事,就麻烦了。
女孩平静地说,三年前,她看上了一个包包,需要8000块,在淘宝上做了分期付款,十二期,很快就拿到了包包,她觉得这一切太容易了。
从那之后,她就开通了各种白条、信用卡,开始疯狂购买那些奢侈品,而当时在各种借贷平台上,她能借到的钱数总额,最后逼近50万。
眼看着这么多钱借到了手里,她竟然一头扎进了股市和基金,迷信网上所谓的“钱生钱”的方法,但几乎没有金融知识的她,很快就赔光了。
一开始,她还能拆东墙补西墙,直到后面所有的借贷平台还款到期。她的通讯录被打爆,身边的所有人都知道了,年纪轻轻的她负债累累。
她很快回了消息:“像我们这样的人,没有以后了,这辈子就这样了。”
这次是过了一会儿她才回我:“我买了份保险,大概能赔偿50万,只要两年的自杀等待期过了,我把自己了结了,爸妈就能得到这笔赔偿。”
“到时候网贷的钱和朋友的钱都能还清,爸妈还有一点儿养老钱。”
我原本以为,在她的资料上写的自杀倾向是受不了借钱的压力,情绪不稳定,可没想到她做了周密的计划,竟然想要通过这种方式“上岸”。
作为催债员,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所有的话都于事无补,现在她只是缺钱。后来这笔单子再没转到我手里,我不知道她后来怎么样了。
互联网金融协会有规定,催收员在进行催收贷款时,一天内催收电话不得超过3个,但许多借款人的电话根本打不通,只得多次换号码拨打。
有些催收员面对业绩压力,只能通过通讯录来联系上借款人。但根据规定,我们是不能贸然联系通讯录上的第三方催款,为此有不少同事都接到了投诉,借款人会以此为由拒绝还款。
“其实我真的没有拨打他的通讯录,”同事说起这事会很无奈。这种事很大可能是别的平台做的。网贷公司会委托多家催收公司,有些公司会考虑规定,但背地里不少公司会跨过这条线。
11月,蛋壳公寓资金链断裂,无数租客被房东赶走,导致大量的借贷逾期。12月,公司下通知,凡是涉及到蛋壳公寓的债务人,停止催收。
这让不少人有一丝喘息的机会,而一些深谙此道的“老手”,会谎称说自己是蛋壳公寓的受害者,由此也躲过了好多催收。更有甚者会故意激怒催收员,用侮辱性的话语逼迫催收员对骂,而后暗中录音投诉至平台,以此为由拒绝还款。
因为我催收的人迟迟没还债,业绩一直不行 ,12月底,我离开公司,跟爸妈坦白了一切。
回望这几个月,我像是给自己上了一课,那些借贷人欠款最多的原因在于贪婪和懒惰。许多人为了一件奢侈品,或是最新款的苹果手机,年纪轻轻的,就走上了网贷的不归路,再难上岸。
我见过一份征信报告,A4纸打印了104页,王主管惋惜地说,“这个人,这辈子算是废了。”
他对我说:“小吴啊,其实我们公司在催收行业算是口碑不错的了,你的信息也在我们公司。”
我无比惊讶,因为我从没在公司见过我的信息。虽然一开始面试时,我就说了自己欠了钱,但这不代表公司其他的催收员,不会催到我头上。
我疑惑他这样做的原因,他接着说:
我不知如何开口,王主管一直是个和蔼的人,他推了推眼镜,笑着说:“我看你的欠债不算多,公司跟这些平台也有些关系,你还6万就行了。”
撰文 | 萤火
编辑 | 蒲末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