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亿个情绪订单在闪送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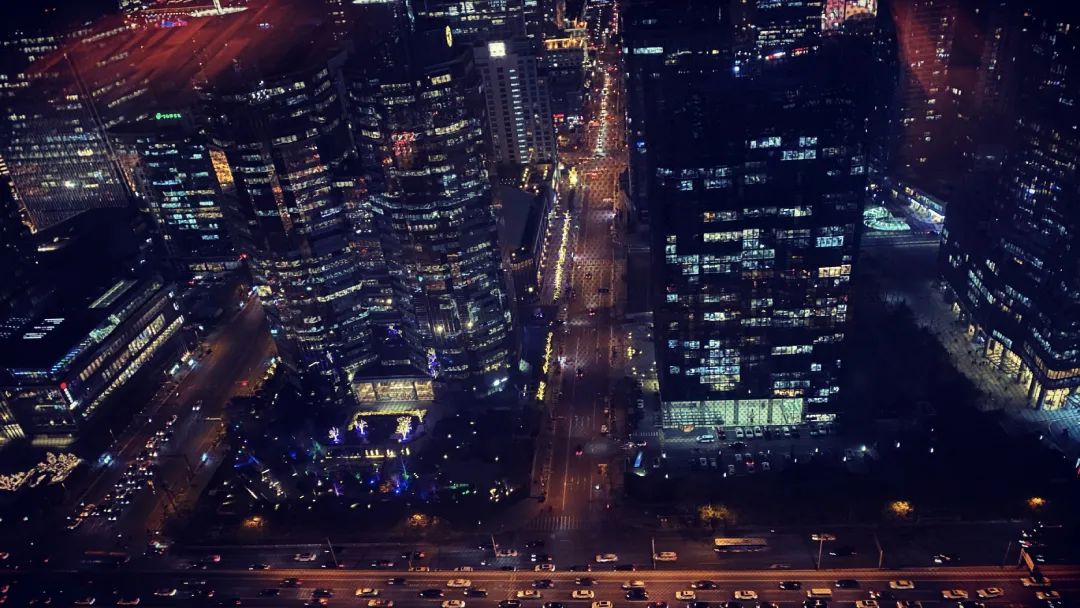
天涯的都市传说有这么一个话题:如果把北京比喻成一个人,那他(她)应该是哪种人?帖子翻了很多页,人们留下形形色色的描述:冷峻、忧郁、珠光宝气、老气横秋,混杂着一切可能的印象。其中一个答案十分颠覆:北京像一个青春期孩子,冲动情绪化,粗心不靠谱。——这个答案来自一个20多岁的同城速递员,他每天听到各种“离谱”的诉求,这一切堆积成一张散发焦灼的面孔,仿佛时刻注视着他。



意外
翻开闪送员的订单,会发现人们的绝大多数焦灼和工作密切相关。尤其在北京这样的魔幻都市,工作生产焦虑,就像车轮会碾出尘土,节奏越快,越混乱,越疯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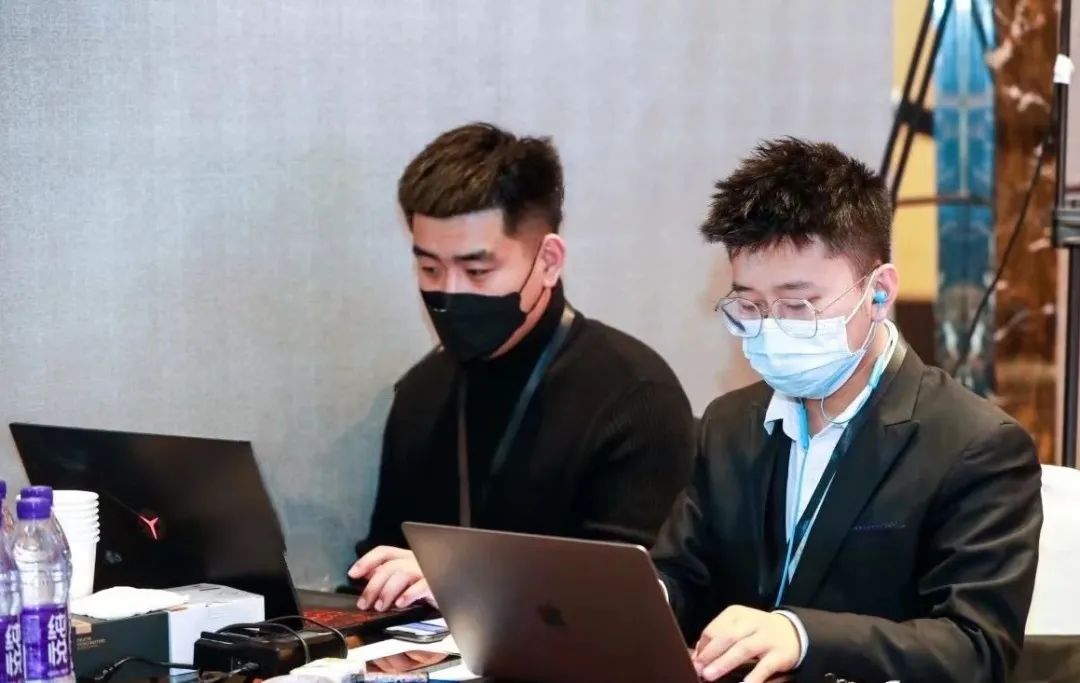

解救

图 | 闪送员在送单地点拍摄到的春天

温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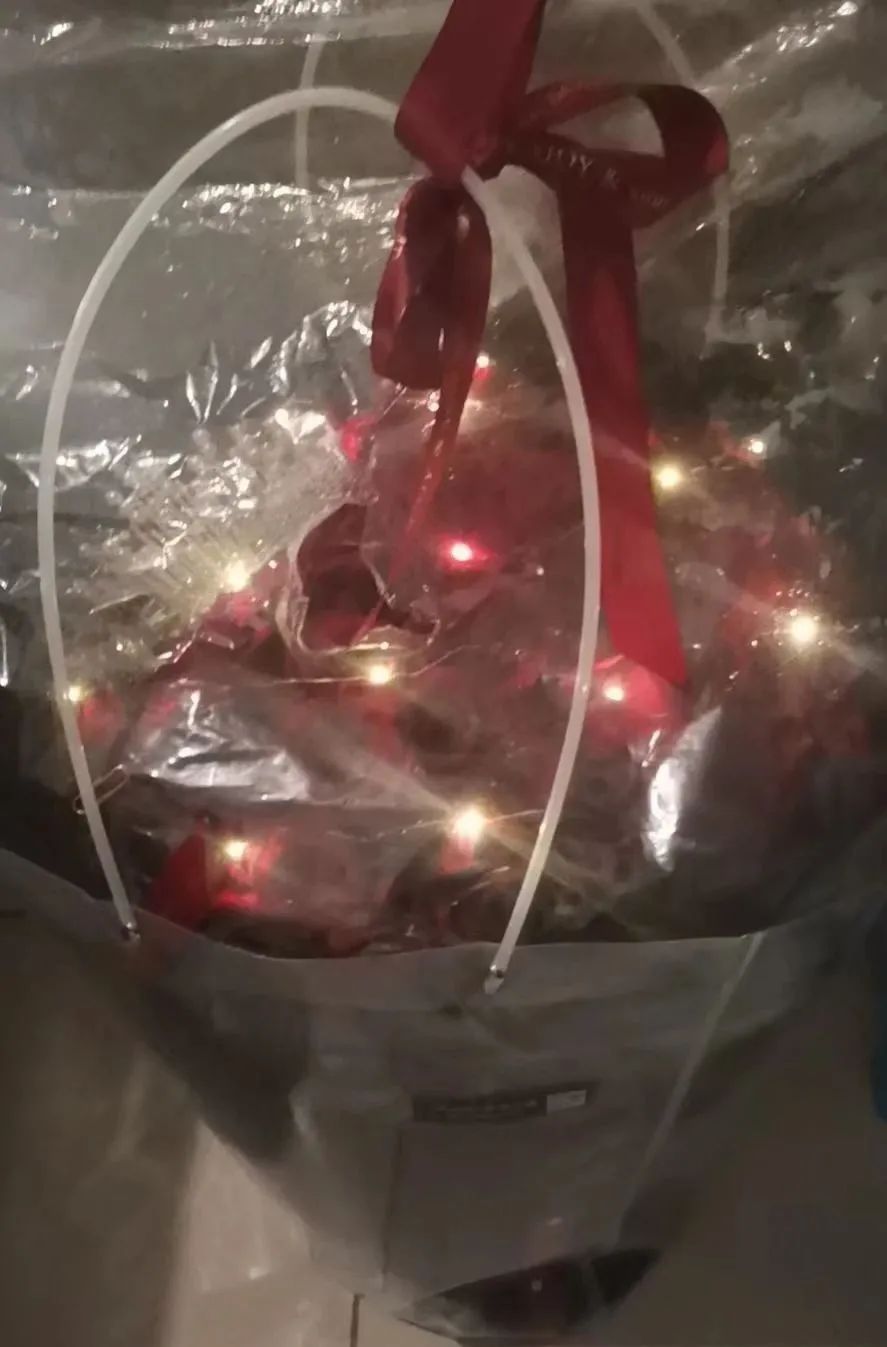
图 | 闪送员从垃圾桶里找到的玫瑰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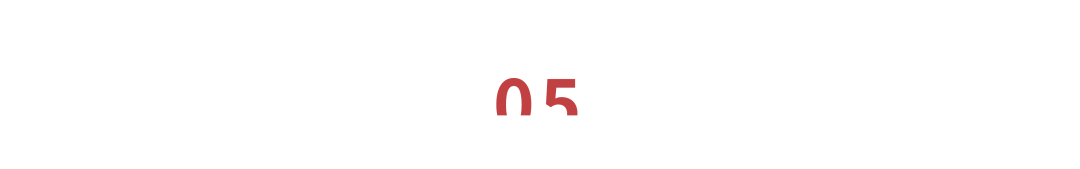
相遇

图 | 闪送员手机里的情感类订单
一句“新年快乐”,曾让大年三十还在送单的李飞湿了睫毛。那次,他从市区开摩托车到房山,给一个病人送胰岛素,对方发给他一百元红包,和一句“新年快乐”。因为过年加班收入高,李飞选择留在北京。可这时他突然想家了,心底的冲动怎么也控制不住。他干脆不管了,开启摩托车,加速到80迈,上路,整整开了八个小时,直接从北京开回河南老家。敲开门,看着父母震惊的表情,李飞心里复杂的情绪涌动,却尽力保持脸上调皮的笑。他听到自己的声音在说,新年快乐,妈妈。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 END -
撰文 | 石润乔
编辑 | 林扉
===================================================
夜行记——鬼灯

信则有,不信则无。
——壶口钓鱼
农闲时是知青们互相串门的好时节。一个深秋的日子,上枣园村的邹同学顺访桃曲村。说是顺访,因为他的目的地是下面的上堠村。上堠村离桃曲村二里地,到上堠村必须通过桃曲村,邹同学走到桃曲村时忽然想到这村里还有几位倒灶鬼的插队同学,于是就寻过来了。
当年上堠村的“老红卫兵儿”知青们交游甚广,经常有一拨拨的知青穿过桃曲村,一拨拨膀大腰圆而且看上去都不是善岔的人呼啸而来让老乡侧目。而这些到上堠村的访客多半要在桃曲村知青处翻捣(当地方言,玩的意思)一番才走。
村里老乡对外村知青来访意见很大,因为外村知青来访桃曲村的知青就要做饭招待,虽然吃的是知青的粮食,但老乡们却感觉桃曲村的利益受到了侵害。可能是怕把知青的粮食吃光了,要救济,最终还是桃曲村的负担,桃曲村的老少爷们向来是深谋远虑的。但知青们很好客,远来的同学和客人给死水般的山村生活添点微澜,不亦悦乎。
邹同学是景文北大附中的同年级校友,虽不同班,但在学校时就常见,一脸凶气,一身煞气,以武力强悍在同学之间有名气,说实在的景文对武力强悍的同学心里总是有些畏惧,敬而远之。
见邹同学到来,知青之间惺惺相惜,校友同学从几十里外来访喜悦之情多于畏惧。大家谝了半晌闲传,景文动手和面、擀面,下了一锅面条,每个人美美的餮了两老碗。天黑以后,邹同学准备去上堠村,他不认得路,让景文送他到上堠村,于是二人一起出发。
出了桃曲村走进下坪里,下坪里的路两旁的地畔有一人多高,形成一条巷巷。深秋的夜晚,天气阴沉沉的。没有月亮,连一丝星光见也不见,只有无边的黑暗笼罩大地。景文和邹同学两人在下坪里曲折蜿蜒的巷巷深处前行,前后左右一片漆黑,方物难辨。庄稼已经收割,阵阵秋风吹过原野却是一片寂静,只觉阵阵寒意袭来。
走了一里多地,上一个小坡就出了巷巷,前方是一大沟。站在坡上遥望沟对面一里地左右是上堠村的场院,沉沉黑夜中,场院上有一点亮光。景文对邹同学说,你看那灯光处,就是上堠村的场院。景文心中奇怪,这时节,秋庄稼都打完场入了库了,场上没有庄稼,不用人照看,大冷天的,夜半三更的谁还在场上啊?
二人沿沟边的路继续前行,小路时而绕过土坡,看不到场院,时而又出到沟边,再次又看到场院。离场院越近,看得越清楚。初时是看到场上有一盏马灯,再走近点,看清是一盏马灯,边上还坐了一个人,戴了一顶草帽。
再走近看得更清楚,不是在场上,是在场的稍下方。这场在沟边上,从灯光的映照可以看出,在场边上的畔畔的土壁上有一个小窑,是那种高度和深度仅有一米多,仅能坐进两三人避雨的小窑,一人坐在小窑里,脚前放了一盏马灯。越往前走看得越清楚,最近的直视距离大概只有三四十米远,在沉沉黑夜中,那盏马灯显得格外明亮,那人戴个草帽坐在马灯前,灯光映照下,侧影如剪纸一样轮廓清晰。
然后二人又进入一个小土坡后面看不见场院了。从小土坡后方拐出来,离场院只有10多米了,眼前却见一片漆黑,哪里还有马灯?哪里还有小窑洞,哪里还有戴草帽的人?
景文突感毛骨悚然,看看邹同学表情也有些紧张。二人拿手电筒向刚才所看到的亮灯之处照过去,不禁大吃一惊,哪里有什么畔畔?哪里有什么小窑?窑洞是要打到畔畔的垂直的土壁上的,但刚才亮灯并显现出垂直土壁上打的窑洞和人的那位置上是一片漫坡,长满蒿草,没有畔畔,没有垂直土壁,也不可能有窑洞。那位平时如凶神一样的邹同学此时表情茫然,口中嗫嚅道,大概是一种野兽吧?他大概也是心神慌乱,语无伦次了。
再看场上,一片漆黑,只有秋风带来阵阵寒意。
二人不敢多探究,赶紧走人,好在上堠村知青的窑洞只有200米远了。到了窑洞里看到胡波兄才长舒一口气。
景文本想在上堠村过夜,但一看,只有两套被褥,天冷了,三个人不够铺盖,只好硬着头皮告辞。
走上窑坡,向沉沉的黑暗中走去。经过场院时,见场院上一片漆黑,场院沟边上的土坡也是漆黑。
向前走到绕过路上的一个小土坡,前行几十米,走到沟边上,回头一望,三四十米外,那马灯、那戴草帽的人影、那小窑洞在沉沉黑夜中赫然清晰可见。那马灯明亮,余光中甚至可以看到后上方场院的窝棚。
阵阵秋风袭来,景文被吹得透心凉。景文连忙转头不看,深吸几口气,定住神,心里反复念叨:不要害怕,不要紧张,不要害怕,不要紧张……不管身后,向桃曲村走去。一路走去,不敢慢,更不敢快,怕一快走反而慌了神。直至走到桃曲村下坪的巷巷口的土坡上,回头遥望,一里地外,一点亮光在场上闪烁,在黑沉沉的天幕下,分外清晰。
景文走进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的巷巷,目不斜视,匀速前行,口中默默念叨有词,不要紧张,不要害怕……最后总算走出了黑暗巷巷,看到了东窑坡上知青窑洞的灯光。
此后,景文曾将此事告诉上堠村的胡波兄。他说,他也曾看到过那鬼那灯。那时候胡波兄单相思公社所在地桑柏村插队的一位女知青,经常在晚上收工以后从上堠村出发走两里地到桃曲村,穿过桃曲村再走两里地到桑柏村去看那位女知青。
胡波兄非常勤快,到了知青窑洞里帮着做饭,帮着几位知青收拾窑洞,干各种各样的活。到晚上10点告辞回村。三天两头跑夜路,夜路走多了就看到了那个鬼和灯,胡波兄说第一次见到时也很害怕,后来还见过几次,也不怕了。
胡波兄说,上堠的村民也有不少人见过,村民称之为鬼灯。胡兄告诉我们:听老乡说,那个小漫坡上埋了一位当年二战区部队的一位军官。抗日战争中阎锡山任二战区司令长官,带领数万部队沿黄河西岸布防,上堠村离黄河只有5里地,驻扎了部队,当时有一位连长因病去世就埋在了那里。
胡兄认为那是磷火。景文,邹同学和上堠村的老乡们看到的可不是星星点点的磷火,是明亮的马灯,是戴草帽席地而坐的人,是一个小窑洞。应该是一位不能回乡的孤魂野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