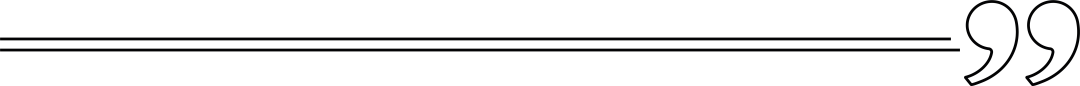之前刚见到我时,她曾微笑着劝说,“你就去看看,不买也没关系”。此刻我明确表示不买,她立刻变了脸色,再次挽住了我的胳膊不松手:“你再看看,再看看。”一旁那个晒茶叶的男人也直起身来,眼神略带警告,朝我观望。
我有些怂了,看了看四周,并没有路人经过,于是立马表示:“我可以付茶水费!”她挽着我的手放松了一些,“你去外面买肯定吃亏的……你说说吧,能付多少茶水费?”我放下15块钱,她最终放开了我的手。
去年8月,95后男孩贾青独自到杭州旅行,遭遇了一场由三位老奶奶主导的魔幻骗局。
贾青性格随和,喜欢“顺其自然”,出游前,他并没有做详细的攻略,只是粗略地计划先到灵隐寺转一转,再买一些茶叶带回去。
天气炎热,在火车站附近的公交车站,他先是遇到了第一个老奶奶,建议他改变路线,不要去灵隐寺,而是“去九溪玩水”,凉快之后再顺便去附近的龙井村买茶叶;紧接着,在换乘车站,他遇上了第二位老奶奶,告诉他要去本地茶农家里才能买到正宗的茶叶;随后,他被这位老奶奶带到了一家茶店,第三位老奶奶已经等候多时,她拿出两种茶,称一个是“雨前龙井”,一个是“雨后龙井”,给贾青沏了两杯。10分钟后,对茶了解甚少的贾青花费700元买了一斤茶叶。
这场经历宛如接力赛,三个老奶奶一棒接一棒,最终把贾青传到终点。事后,他觉得不对劲,在网络上搜索,看到相似经历的帖子,才得知被卷入一场精心策划的“茶叶销售大赛”。贾青懊恼,但也觉得无可奈何,毕竟,“她们实在是太高明了”。
高明之处首先在老奶奶们的外形打扮:她们头发花白,脚蹬运动鞋,手里挎着一个买菜用的布兜,看起来只是出门去市场。
其次是她们的耐心,每一位奶奶都有恰到好处的热情,话题从指路切入,再来一场和茶叶毫不相关的闲聊,让贾青放松警惕。她们保持着随意、平静的态度劝说贾青,直至他走进茶店。
网络上几十篇相关的帖子看下来,贾青发现网友们的经历与他相似,但多数只遇到了一位老奶奶,没有他那样丰富。至于他高价买回来的“龙井茶”,最终变成了“薛定谔的茶叶”——到底值多少钱,只有上帝知道。
为了体验一把这样贾青帖子里“精妙”的茶叶骗局,这个清明节假期,我去了一趟杭州。
正是采春茶的季节,市区道路两侧常见“龙井茶店”,走进去就有人来讲述龙井茶的历史:相传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曾到龙井村狮峰山下的胡公庙品尝西湖龙井茶,赞不绝口,将庙前十八棵茶树封为“御茶”。

▲ 传说中的十八颗“御茶”。图 / cfp
上个世纪,龙井茶价格水涨船高,冒充的事也不少见。到了2008年,GB18650—2008《地理标志产品 龙井茶》正式实施,确定了龙井茶的质量标准,也划分了三大产区:西湖产区、杭州产区、绍兴产区。
在西湖产区,根据茶树生长的地理位置,茶叶被分为“狮峰龙井”“西湖龙井”“梅坞龙井”,其中“狮峰龙井”最贵,有行家告诉我,它的价格在每斤5000元以上,而龙井村正是它最大的产地。
我先去了贾青那次旅行的起点:火车站。在我的预想中,火车站是老奶奶出现的重灾区,但没想到的是,我在那里晃悠两个多小时,甚至主动搭讪了所有出没的老奶奶,她们要么说起杭州方言,我压根听不懂,要么对我爱答不理,冷漠得根本不像骗子。
又一位老奶奶出现,我立马上前询问:“您知道去哪里买茶叶吗?”一旁的小孙女拉了拉奶奶的衣角,示意她不要理我,两个人迅速走远,孙女嘴里嘟囔着:“是不是骗子?”
寻找骗子,却被人当成了骗子,这让我有点想流泪。两小时过后,我开始怀疑,这种老奶奶骗局是不是已经消失了?但等我离开火车站,坐上出租车时,骗局终于露出一角。
我告诉出租车司机,我要去龙井村,原本沉默不语的司机听说我要去买茶叶,顿时变身“话痨”。在等红绿灯的间隙,他拿起手边的保温杯向我示意:“西湖龙井,一斤2000块,我每年都买四五斤。”言辞中带着得意。
除了向我铺垫价格,司机还试探着问我要买多少,作出一副仗义的架势:“你给我说说要买多少,买得多了我让他给你打折!”同时还告诉我,可以慢慢看,“我把计费表停掉了,不费钱的,你买完我再带你回去。”
穿过一条隧道后,远处的环山和大片的茶田映入眼帘,车子拐进一条小路后停下,两家名为“龙井问茶”的茶馆就坐落在那里。司机带我走进其中一家,仅有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两盘茶叶,一个三十岁左右、老板娘模样的人走出来向我介绍,左边的茶叶750元一斤,右边的1000元一斤。她熟练地拿出两个茶杯,分别捏了一小撮给我沏了两杯,让我“感受一下两种茶的不同”。

▲ 店内唯一的桌子上放着两盘茶叶,和一杯泡好的茶水。图 / 徐晴 摄
一罐茶二两,150元,为了套话,我还是买了一罐。等借故让司机先走后,我问买茶的老板娘:“拉我来的司机是不是跟你们有合作?”她也不掩饰:“双赢嘛,他接送客人能赚两份钱,还有我们这里的免费茶叶喝。”没多久,又有一拨被带来的新客人走进了茶店,也许是担心我泄露“商机”,老板娘看买完茶叶的我没有要离开的意思,就索性把我的杯子拿到室外的桌子上,客气地将我“请”了出去。
看着这一拨新来的游客,我不禁产生了一丝同情,但很快,我就被“打脸”——原来我才是小丑,以为看穿了“套路”,实际上,还有更深的“套路”等着我。
沿着这个村子小路往里走了几百米,一位偶遇的阿姨把我拉到家里,叫我看看她家的茶叶。攀谈中她告诉我,我买到的并不是西湖龙井。村口的那两家茶店,一家是外地人开的,一家是20公里外另一个村子的人开的,他们租用了本地村民的房子,每年的租金高达60万,给到司机的回扣能有60%。
她让我拿出刚买的茶叶和她家的龙井茶对比,“外地的茶叶颜色碧绿,叶片大大的,真正的龙井茶小小的,绿中带黄,没那么好看的”。她还拿出了一个小布袋,里面装了一沓“西湖龙井”的防伪标贴纸。她家里有三亩地,每亩地茶叶的产量在40斤左右,炒完后数量会变少,一共领到了120个125g规格的防伪标,“只有双峰村的本地人才能去村委会领取”。
我看了一眼我刚买的茶叶,果然没有什么防伪贴。等等,双峰村?“什么村?”我追问道。阿姨看着我的目光带着同情:“小姑娘,你太天真了。”我郁闷地打开百度地图,才赫然发现,这里并不是我要去的龙井村,龙井村在山顶,这里只是半山腰的双峰村——我彻彻底底被出租车司机骗了。

▲ 真正的“西湖龙井”、“狮峰龙井”都有防伪标。图 / 徐晴 摄
此时是下午4点,站在双峰村的我五味杂陈,眼看着一辆接一辆的车驶来,流水线一样:停下,放人,买茶,离开,重复着同样的一套流程。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和我一样,原本想去龙井村,结果,最后被带到了双峰村,买了一堆不知道哪里来的茶叶。
等离开双峰村后,我还是不死心,想去真正的龙井村一探究竟。
等我真的走在龙井村的主干道上,心里不禁乐开了花——这里到处都是贾青描述的“头发花白、手上戴着银质或玉质的镯子、看起来慈祥又热情的老奶奶”,她们散布在茶店里、小路边和巷子口,有人经过,就会凑上前去询问:“要不要我家去看看茶?”
在这里,骗局也变得更加隐晦。
以清明、谷雨两个节气划分,龙井茶分为“明前”“明后”“雨前”“雨后”,“明前”品质最好,卖的价钱最高,可以达到几千元至几万元一斤。上个世纪,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出了新品种龙井43号,除了产量大,比过去的老茶树(又叫“群体种”)多1/3,它的开采时间也比老茶树早10天左右,这样也相对降低了龙井茶的价格。
当地人告诉我,因为种茶、采茶、炒茶的成本太高,即便是当天新采、新炒的43号茶树,想要赚钱,最低也要卖到750元一斤。但在龙井村的茶店里,200、300、400一斤的茶叶十分常见。
5分钟后,一个阿姨挽住了我的胳膊,带着我走进了小巷深处。和双峰村一样的剧情再次上演:两个竹盘、两种茶叶、两个茶杯。区别只有定价,左边一斤400,右边600一斤,她反复建议我,“买400的,性价比高”,还对我比了“3”和“5”的手势,表示“如果买的多,可以这个数给你”。
当被问起这些茶是不是狮峰龙井时,她反问:“不是狮峰龙井还能有什么嘛?”我说没有防伪标啊,她狐疑地看了我一眼:“这是政府规定的,1000块以上的茶才有防伪标,懂不懂?这是政府的规定。”

▲ 同样的套路,还是两种茶叶先给你泡好,没有防伪标,但有“特制包装袋”。图 / 徐晴 摄
之前刚见到我时,她曾微笑着劝说,“你就去看看,不买也没关系”。此刻我明确表示不买,她立刻变了脸色,再次挽住了我的胳膊不松手:“你再看看,再看看。”一旁那个晒茶叶的男人也直起身来,眼神略带警告,朝我观望。
我有些怂了,看了看四周,并没有路人经过,于是立马表示:“我可以付茶水费!”她挽着我的手放松了一些,“你去外面买肯定吃亏的……你说说吧,能付多少茶水费?”我放下15块钱,她最终放开了我的手。
后来我又询问了两家茶店,一位奶奶告诉我,她家的茶叶分为300、500、800三档价格,“都是狮峰龙井”。当我问起有没有品质更好的茶叶,她才找出一个小布袋,“这个2000元一斤”。而村口那家,一位大叔称自家的狮峰龙井5000元一斤,我问他,别家怎么有便宜的茶叶,他隐晦地表示:“每年狮峰龙井的产量就那么多,那些300、400一斤的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 龙井村的每一家茶馆都卖“西湖龙井”、“狮峰龙井”,直接装在后面的黄色塑料袋里。图 / 徐晴 摄
那个下午,我四处晃荡,两手空空,两个一直在路上招揽客人的女人隔着马路,不满地对我喊话:“走了好几圈了,买不买啦到底?”
从龙井村回来后,我通过帖子和贾青联系上了,他跟我讲了魔幻骗局的后半段:得知自己被骗后的第二天,他又去了公交站,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他遇到的其中两位老奶奶居然结伴出现了。
他拍下了两位老奶奶的照片后,坚决地踏上了去龙井村维权的道路。因为证据在手,无法辩驳,最终,茶店店主把钱退给了他。
离开杭州前,我托朋友介绍了几位双峰村和龙井村的村民,终于弄清楚了两个村子骗局的起源。
在多年前,龙井茶骗局是有时令的。杭州的春天是公认最美的季节,等春天过去,游客骤减,龙井村的老奶奶才会组队出去拉客人,“闲着也是闲着,不如赚点钱”。
双峰村的村民也佐证了这个说法:“20年前的骗局很夸张的,我小时候去上学,公交车上一堆龙井村的老太太,买好了月票,每天出来拉客人,当时27路公交的每个站点都是那里的人。”
网络上的“老奶奶骗局”,也大多发生在5年前。最近几年,年轻一代的龙井村人外出工作,不仅种茶、采茶、炒茶的技术面临失传,“老奶奶”也要后继无人了。
贾青返回龙井村维权时,茶店店主解释说,老奶奶们负责揽客,茶叶卖出去,她们会拿到20%的报酬。原本他自家的茶叶向来销路不错,已经很多年没用这种方式招揽客人,但2020年受疫情冲击,销量大跌,才又“重蹈覆辙”。
而双峰村发生冒充龙井村的骗局,更多是因为茶的销路困境。
一位村民告诉我,双峰村虽然产“西湖龙井”,但对外宣传一直是个问题,在西湖产区的几个自然村里最没有名气,村口连一块明显的标识和广告牌都没有,唯一一块导游石碑碎了不知道多久。一位在市区里开茶店的双峰村人说:“每次和别人聊龙井茶时,大家只知道翁家山、龙井村、满觉陇,根本就不知道双峰村,以为我在瞎忽悠。”
他还告诉我,外地人在双峰村开起茶店后,可以说是雪上加霜,他们会刻意阻止游客跟本地村民接触,这样一来,游客既不知道自己在双峰村买了假茶叶,更发现不了这里并不是龙井村。

▲ 外地人开的茶店门外,一位老师傅正在炒茶。门内是出租车司机带来的游客正在品茶。图 / 徐晴 摄
这样的骗局在村子里人尽皆知,存在了十几年,但“没人能管”。一方面,外地人办理的营业许可上写的是“龙井茶”,不是“西湖龙井”,租村民的房子也合法合规;另一方面,当地村民也因为高额的租金和可观的人流量,默许了这种行为。
总有“漏网之鱼”走进村子,被本地人拉到家里“科普”,买到真正的西湖龙井;或者走进餐厅消费,给村子创造营收,钱最终也能落到每个村民的钱包里。
离开的那个下午,游人依然络绎不绝,每一辆公交车都是爆满。看了看,叫车排到了34位,无奈之下,我只好走路下山,到半山腰的双峰村时,终于拦到了一辆出租车。
司机是又一位大叔,接上我之后,他不断地问我有没有买茶、买了多少。得知我已经买过,隔着口罩,他仍然亢奋说道:“孝顺!带回去给老爸喝,那给老妈带什么?”他几乎是两只手“啪”得一下拍在了方向盘上:“要带丝绸!丝绸博物馆你晓得吧?我们等一下就路过,打85折,晚一天活动就没有了!我等下把表停掉,不费钱,你去买,我等你好吧……”
疲惫的我立马精神了,想起来我在网上翻阅过的另一个帖子:年轻人小童被司机带去“丝绸博物馆”,到了地方,才发现是“丝绸工厂店”,那里的丝绸质感粗糙,但价格高得离谱,一件短袖上衣一千多元。
原来这个司机也是“托儿”。这次体验,我真是被骗够了,于是绞尽脑汁地想了3个理由:玩得太累了、有人在等我、我妈妈不喜欢丝绸。司机终于放弃了劝说,沉默着一脚油门踩下去,全速离开了龙井村。
======================================================
回去后,兵哥几乎天天问我大舅的近况如何。我能怎么说?——“你爹跟我要了一个一人多高的大锯做八仙桌呢”?
2019年春节,因为3倍加班费没舍得回家;2020年春节,因为疫情没能回家——快两年没回家的兵哥如是对我说——东北的冬天又很长,家中两年没见面的老父亲也不知道怎么样了,过年对于老人来说就像一种仪式感,一年到头来全指着这一天呢。
兵哥是我的远房表哥,比我年长许多,我们从小就是玩得很好的发小。他是我身边许许多多出外打拼的兄弟中的一员,也是为数不多的扎根外地的成功者。
兵哥的父亲、也就是我的远房大舅,比我父亲年长许多,是同辈人里的老大哥。大舅一辈子都在农村,他面孔忠厚,手上布满老茧,是带相的老实人。
每年过年我都要去探望大舅,害怕今年疫情再来又封城,进了腊月我就开始挨家挨户地走亲访友。按照往年的礼数,我要给大舅送一箱酒、一条胖头鱼和两只鸡,满满的三样礼——他一个人生活,倒是吃不下许多,反倒每年都掐算着时间,给我准备他自己做的豆包和自家种的花生。
今年我刚进院门,就看到一棵柳树在院子中央直直地立着,已经没了叶子,中间空出一个树洞,被风撕得越来越大。大舅远远地招呼我:“来啦小子,今年来的早啊。”大舅其实还不到70岁,但常年的劳作让他看着极其苍老。
我熟练地推门让步,进了房,屋里的摆设一切如旧:热融融的灶台边上垛着一捆捆苞米秆,大木桌子上摆着早上吃剩下的馒头,黄底黑边的搪瓷碗上扣着一个盘子,旁边的洗手盆底沾着一层黑泥油,水龙头被一个自行车红内胎套着,边上还拧着几圈铁丝。屋里屋外,只有一台38寸的电视机算是比较现代化的物件了。
与往日不同,屋里还摆着一大盆酸菜、半扇猪肉和两大盘圆滚滚的豆包,是为过年特意准备的。我打算撂下手里的东西就走,却在门口被大舅一把拦下:“小子,今年疫情你大哥能回来吗?”他把我往屋里推,好像有更多问题要问。
“今年中央倒是提倡就地过年,但是非要回来估计也没啥——我大哥没跟你说啊?”
“他没给我准信儿,一会儿回来一会儿不回来了,再问就是‘不知道’。”大舅边说边拍大腿,不知道他的厚棉裤穿了多少年,氤氲起了好多灰。
“去年都没回来,今年肯定说啥也得回来了,我回头问问他,大舅你放心吧。”我赶紧挣脱大舅的手,迈步往外走,大舅跟在后面喊了几句什么,我也没怎么听清。
随后几天,我都快忘了大舅,远在北京的兵哥突然发来微信,让我过两天去大舅家串门前告诉他一声。
我回复他“早就串过门了”,随即就接到他打来的电话:“兄弟你倒是快啊,今年我怕是回不去了。”兵哥的语气略带寒暄,却有托付之意。
还没等我说什么,他就一气儿说了一大堆:“兄弟啊,你岁数小,多跑两趟。糖就要点散装的冰糖就行;碧根果多买点,我家老爷子爱吃;烟就买几条红塔山就行;保暖衣买两套,一套加绒一套不加——哦对,帮我看看厨房水管好没好,能整你就帮我整整吧。”
其实兵哥回不回得来与我关系不大,但一个独居老人码排了那么多猪肉、酸菜,还有自己唯一能展示的豆包手艺可能就落了空。我顿了顿口气,问道:“那你没跟我大舅说不回去了啊?”
“最近天天视频打预防针呢,两年没回去,我也怕他想啊。”兵哥解释说自己拖家带口,3个人来回得做6次核酸、还容易隔离14天,花销之大,麻烦至极。
“但是‘怕他想’他就不会想了吗?”我心里想着,嘴巴里有一个独居老人和他的酸菜、猪肉和豆包,但是说不出口。
收了兵哥的钱,我按照吩咐去市里给大舅买了一切应用之物,也再次开车到了大舅家。
这次,大舅正在院子里打磨一把生了锈的木锯,他边磨边念叨:“老了,不中用 。”看见我,他只点了点头,没那么热情了,想是已经知晓儿子一家不能回老家过年了。
大舅放下木锯,接过我手里的一大袋子,弯着腰往屋里走,我跟在他身后,打量着饱经沧桑的锯和那棵破洞的柳树。进到房间里,地上的猪肉不见了,切好的酸菜不在了,豆包也被分成一份一份的。
“去年啊——说起来是前年了,你大哥十月一(国庆节)带着老婆孩子回来了,我也没多寻思。没成想啊,过年就不回来了,说过年加班给得多。”大舅打量着手里的保暖衣,叹着气,随后熟练地换好新衣服,对我“嘿嘿”干笑——可能每年过年,兵哥都会给他买两件新的吧。
厨房里被红色内胎裹着的水龙头还在“滴答滴答”响——我完全忘了水龙头的事,没有买零件,悔得直拍脑袋,这意味着我又要跑一趟了。
这时,大舅在我背后发出一声惊叫“哎呀!”我赶紧扭头,见他把衣服恭恭敬敬地端在手里,看着价签,随即又把从超市买来的各类东西挨个翻找价签看。
“没多贵啊,你这件衣服200多一套,打了折不到500,不算贵了。”我一时没琢磨过味儿来,没明白大舅平时是不会花这些钱的,这些东西的价格明显超出了他的想象。
“原来也是买这些东西,你哥都没让我看见过价钱,我问过几次也不说,没寻思这么多钱啊,我这也不用吃这些个东西啊。”大舅喃喃地说。
我本以为应该仔细点留下价签和小票,如果兵哥打电话问大舅,人家父子好核对。亲戚之间人心难测,人家找你帮忙,也难保提防着你,找不到票据核对账目,钱多钱少是一回事,心生隔隙是大事——但是现在看来,兵哥每次买东西都撕下价签,倒是我狭隘了。
端详完价格,大舅把一袋被自己撕开的糖果又仔仔细细地装了回去,然后指着那个半冻半滴答的水龙头说:“你大哥前年十月一走以前就一直在修这个水管,我就跟他说不着急,过年回来修也行,你哥也没跟我说过年不回来了。”
“哎呀,又是钱啊,你帮我堵死吧,我打水上隔壁老刘头家就行。”大舅又往房子的北面指了指。
老刘头我知道,贵州人,说话时一口不太流利的东北话夹杂着云贵的方言。他二十来岁就来了东北,在这个村子里结婚生子,在贵州可能也没有亲故了。跟大舅一样,老刘头几年前也没了老伴,他有一个远嫁的女儿,听说很少回来。
“猪肉让我扔后屋雪堆里埋起来了,酸菜留了点,剩下的分了,豆包还没分呢,你要不再多给你妈拿点吧。”大舅赶紧拎起两大兜子豆包。
我含糊其辞地说“都够都够”,拔腿便走,我打算在晚饭前把新水龙头给大舅换上,也就能安心回家了。
进了院子,我发现大舅和老刘头都在院子里。他俩一个弓着身子,在磨锯子;另一个身子弓得更矮,在磨斧子。大舅向老刘头介绍我,老刘头满脸带笑说记得,只是不知道我现在居然都能开车来回跑了。
“大小子,你啥时候有时间还来啊,再来帮舅带一个好点的大锯啊,能砍树的锯。我这把锯太小了,也钝了,不中用了。”大舅憨憨地拍着我的肩膀说。
“这是干啥啊?锯树干啥啊?这树好好的。”我看着那棵秃柳,一脸疑惑。
“啥时候来,想着点帮大舅带把就好了,五金店要没有,农机店估计有,大舅给你钱。”说罢,大舅便收起工具进屋做饭了——这两个空巢的鳏夫,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搭伙过日子了,看灶台上的东西,两人也吃不了多少。
一转眼就到了小年,我猛然想起伐树的锯还没给大舅买,便赶紧买了送去——我以为,老年人的世界有时不适合年轻人去揣测,因为没必要。他们想要什么物件,很可能是出于某些爱好或习惯,如果年轻人过分打探,有时反而会使他们被迫打消那点念头。
“大舅,你要的东西带来了。”我边说边从车里拿出一把大锯,这锯是两人用的,中间宽两边窄,因为太大,得整个从后排斜插进副驾驶才放得下。
大舅见了心喜,老刘头更是喜上眉梢,我却不知道他俩喜个什么劲儿。大舅看出我的疑虑,说:“你刘大爷要做一个八仙桌子。”
“我们贵州,人死了要准备八仙桌,好几张八仙桌摆得高高的,请人做法事。”老刘头看了看外面的柳树,接着说:“法事要做好几天,儿孙们要跪几天几夜嘞,我这离开贵州也快50年了,别的什么我都不记得了,就是这桌子我记得真亮(清楚)的!我想自己死的时候也有,正好你舅同意啊,不然我一个人也做不成啊。”
大舅十分轻松地说:“我打听了,一个村子也没有相当的桌子。我打算把门板和我这饭桌毁成两个桌面,去年西屋房塌了,房子大梁做几个桌子腿儿,今年这个树也开口了,趁着里面还没空,也改个桌腿儿,余富出来几块好的(木料),就做两个骨灰盒。”
大舅的语气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我想打断他这种懈怠人生的想法,直说这是没影儿的事,毕竟大舅才不到七十岁,想这种事实在太早了。
“大小子,你不是我,你想不到这一步,你刘大爷跟我都身边没啥人,我俩互相照顾着日子还凑合,你刘大爷也跟你爷岁数差不多,该想这步了。十年二十年的日子,我也是一个人,在还能动弹的时候做好了打算,(到时)不让你大哥麻烦。”
其实,我能理解大舅的心情,这种“空巢老人”守着一个村子的荒凉,一个时代的荒凉,满眼望去都是荒凉。他哪里是为另一个老人还愿?分明是把自己的事情也想好了。
大舅年轻时是种地的好把式,他学过木匠、泥瓦匠和厨子。以前谁家盖房子,总少不了他帮忙进料;谁家结婚,总少不了他帮忙做菜出席面;谁家老人过世,也总会找他帮忙钉个祖宗板或骨灰盒。可就是这样一个年轻时处处要强的人,去年看到自己当年盖的房子塌了,想必是个不小的精神打击。
老刘头拍了拍那棵柳树,说:“等我啊,我家还有点虾米,我拿来咱俩炖点酸菜。”说完他走出院子,又走进自己的院子,剩下我与大舅无话,我心里仍然觉得大舅为自己准备后事,太早太早了。
没多久,老刘头拿来一罐虾米,还有许多红的绿的条布,以及他用铅笔画下的要在八仙桌上刻的画。
“你来看啊,这个地方要画这个女的,这个女的手里应该拿一个甚么子东西我忘了,能弄个花就花,拿个别的什么东西也没关系……其他的我都不记得了,我再找找看,有没有什么布条,多扯点吧,我印象里应该有可多东西咯,就算只有一个桌子,我也好知足啊。”老刘头对大舅比划着,边笑边幻想,感觉如果一张做好的桌子就摆在眼前,他会毫不犹豫地当即赴死,且毫无遗憾。
如果老刘头也走了,我很怕大舅也会想着离开。他们都是阡陌大地上刨食的蚂蚁,坚强无比,也许会忍受孤寂的二十余年如一日的生活,也可能万事看开,便一去不回。
眼下,还有六七天就过年了,两个离群索居的老人,就这样准备着给自己的礼物。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要不要把这件事跟兵哥说,我觉得有必要,但是又觉得没必要。这事可大可小,你可以当作老人的消极状态,但也可能是没事做,做点小手工。
那段时间,兵哥几乎天天问我大舅的近况如何,我能怎么说?——“你爹跟我要了一个一人多高的大锯做八仙桌呢”?
这件事在我心里纠结着,难以化开,一直到大年三十,还想着那两张八仙桌的我决定再去大舅家看看。
到院子里时,那棵大柳树已经横躺在地上了,四处摆着它的“残肢”。一个被锯出来的木墩子上摆着我第一次来看见的那半扇猪。
进到屋子里,是两张大桌子,圆桌子是原来的饭桌改的,方桌子是一扇厚厚的门板改的。八条桌子腿儿布着走向不同的纹理,桌子侧面贴着要刻上去的八仙画。桌子细闻闻,还有木头的“生”味儿。看来,两个老人家准备用这桌子摆酒菜过年了。
老刘头对我说:“大小子帮我买几个香炉吧,我太爷死的时候有一鼎老大的香炉,那么大的香炉才能插得稳香。”
大舅对老刘头炫耀着:“做工不错吧?跟你印象里差不多吧?”
老刘头扁扁着嘴,睁大眼连连说:“差着不多咧,知足啦!”
我细细地抚摸着这两张承接生死的桌子——也许是老刘头魂牵梦绕故土的样子吧。人为什么一定要有所寄托?大概是同他一样,老伴走了,孩子不在身边,就只能远远地从前半生里硬找出一个故乡的样子,渴望用人生最后一刻对故土的追思去弥补人生的完整。
而大舅则是借着老刘头的所需,弥补自己生活的完整。有些人要权要钱,有些人要幸福,有些人只是要完整,这两张八仙桌就是横架于“完整”之间的桥梁。
刚到中午,大舅已经准备吃除夕的最后一顿饭了。他觉得自己年龄大了,不必非在大晚上包饺子,年也不算团圆,也就没必要准备年夜饭。
“大小子在这吃吧,我们就两顿饭,你吃完这顿还赶得上回家吃下一顿呢。”大舅说。
那顿饭有猪肉炖的酸菜,里面烩了一层虾米;有我买来的各种干果;有韭菜炒的鸡蛋;还有许多豆包——都说谁家过年还不吃顿饺子,可大舅家只能吃豆包——因为他准备的豆包太多了,邻里都会做这东西,送不出去,就只能自己吃。
老刘头和大舅互相倒酒,两个老人家怕我尴尬,就把电视打开了看。一经烘托,气氛还真就上来了,情到深处酒到浓时,老刘头也开了肚肠,满口一杯酒,抓住我的手,打开了腔。
“孩子,我真得谢谢你啊,没有你来来回回跑这么多趟,我这事儿办不成啊。”他呷了一口酒,看了看我,“我来东北那年刚也就二十多岁,二十几我都记不太清了。”
他眯着眼睛,边对我说话边看着电视。我问他咋不回家,这么多年跟老家还有没有联系。
“想啊,刚来东北的时候是被押来的,想回家不让回啊。那个年代家里也不太平,我四五个兄弟都找不到了,家里老头也被关起来,天天写检查。”老刘头说,他的东北之旅是在那个动荡时期开始的,他们一家先是定居北京,几年后又因为历史原因,兄弟四散,家道中落,他被一路下放到了北大荒。
“那个时候只能给家里写信,写了好多哇,都没得回信,后来才知道,好多信都是托人送的,人家根本没给我邮出去。但是我也不失望,那个年头失望的事情太多了,这种事情不值得难过了。”老刘头点上烟说:“后来啊,那都是好多年了,我认识了我老伴,稀里糊涂地就结了婚生了孩子,也没跟家里说。但是好在跟一个同乡联系上了,回了家一看,只剩下兄弟两个和老妈了。”
大舅打断了老刘头的话,说大过年的就不谈这种事情了,但是老刘头心里的苦水淌出来,就没那么容易轻易止住了:“上一次见面是二十出头,再一见面我都有孩子了,我妈给我做的蕨菜根炒肉,临走又给我拿了好多蕨菜和辣椒酱,说让我路上吃。我也记下了新家地址,在一个小县城里,从东北到那儿,要先到遵义再坐板车到毕节金沙县,再咋个走,我就记不清咯。”
老刘头尽力地在脑海中翻找着回家的路线,驴车套着板车,一路晃晃荡荡,可是再往下走,那段回家的路就迷失在了他的脑海中,翻找不清了。
“那你没再多回家几趟啊?老娘不还在呢吗?”大舅好像也在回忆自己的人生。
“没啦,没回家过几次,那个时候家里总得种地,哪有时间回贵州啊,路途也太远,走一趟要花很多钱呐,在我妈走以前,也回去了八次,第九次赶回去奔丧,就再没回去过了。”
老刘头叹着气,又突然说起自己的女儿:“我闺女在外地嫁了人,我也不要求她把我接走,我也不去。我看明白啦,有些事情没办法的,也不给儿女添麻烦,多养活一张嘴是多大的负担啊。”
老刘头眼中含着泪,喝下了一杯酒,“东北也有蕨菜,东北的土地比我们家乡的好,种出的庄稼黄莹儿的,真好”。
大舅说,老刘头年轻时候也是种地的好手,土地和家人一样,都离不开他。他深知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才能收获,为了让这片金黄哺育妻儿,他只能慢慢淡薄了母亲与家乡。
或许说起来,这有些“不孝”和“薄情”,但是只有身处其境的时候,才会明白自己只能选择放下一头。现在的兵哥何尝不想接大舅去北京安享晚年,但他的儿子、老婆都要养,对老父亲的关怀,就只能隐匿于撕掉价签的保暖衣上了。
连续三年都没有回家的兵哥,明年会不会也不回来了?大概率是可能的。这并不代表兵哥对父亲态度失衡,只是人之常情罢了。以“理中客”的高度审视“空巢老人”的孩子们是容易的,却鲜有人体谅。他们哀叹农村的落寞,又拍手叫好城市化建设的速度,可每一个大都市的繁荣背后,都有无数人肩负着两头,一头是嗷嗷待哺的家庭,一头是垂垂老矣的父母。两头都在跳着脚地望啊望,可是都望不见另一头。
时代疯狂前进,注定要撞倒一些人,老刘头就被撞倒了,他选择理解和包容,就像他母亲当年理解他一样,他也理解自己的女儿。
大舅给我夹了好几筷子酸菜,不停地打岔,老刘头才咽下了继续讲述的欲望。其实老刘头说了那么多,我也没记住多少,关于他的一生,我仍是知之甚少。
我特意在机顶盒里调了一个“历届春晚精品展播”,才算把饭桌上的气氛调节的舒缓一些。饭毕,我和大舅收拾碗筷,只听见电视里传来了当年黄宏的声音:“工人要为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
出门的时候,已经日落黄昏,我沿着水泥路一个弯一个弯地绕过一片片土地回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打工了,村头已经没了狗吠,这些老人越来越孤独。
车子开过一片庄稼连着的坟地时,我想:人一苍老,就像颓圮的土墙、崩坏的石磨、纤毫毕现的土地,坍塌,无力,荒凉。人们总祈求和死去的亲人在天上相见,实际上哪个升天了?他们都被埋在地里,每当夜晚来临,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一同躺下。
快进城时,夕阳已经被夜色压得很低很低了,我们的生活也差不多,大部分的日子都被压得很低很低。
到今天,北方万物开化,冰雪早已消融,我不知道大舅家的那半扇猪肉还剩多少,豆包有没有吃完,他有没有打算开春种点什么。
也许,大舅也一点点接受了儿子已经成家立业、回家的次数会越来越少的事实了吧。那两张八仙桌子,此刻应该稳稳地立在屋子里,和它们还是一棵树、一扇门的时候一样,被风吹彻。
相信自己灵魂的
高贵和诚实,并且用生命
和不完美的世界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