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穷养长大,总会觉得缺爱

慢慢 30岁 西安
独立赚钱后,我开始报复性消费
对我来说,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就是花钱,最可怕的事情则是没钱可花。
2017年,我的工资上了6000。有天下班,我直接去商场,买下一件1200元的风衣。刷信用卡的感觉太爽了。
当时,我的信用卡已经欠了好几千块。我告诉自己,这是我辛苦工作的犒劳,应该的。
我工作超级拼命。那时我在广告公司上班,几乎所有时间都放在工作上。最忙的时候,我加班到凌晨三点,再赶早上六点的飞机飞去另一个城市。打电话跟母亲哭,也从没想过停下来。
可以说,我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赚钱,我特别害怕自己会没有钱。很大程度上,这种焦虑来自于童年记忆:我一直是小伙伴里最“穷”的一个。我羡慕他们的自动铅笔,羡慕他们可以吃上方便面,可以用零花钱购买各种新鲜东西。而我从来没有过一分零花钱。
我永远是站在一边看着的那个孩子。
其实,小时候一起玩的伙伴家境都差不多,要较真,我们家可能还更好些。爸爸是一个小包工头,我家是附近最早买电视机的几户人家之一。在大人的记忆里,他们也没有亏到我。举例是理直气壮的:只要和学习有关的事情,他们一定爽快给钱。比如,我想买一本《辞海》,40多块,那时候也不算小钱,他们不眨眼就买了。
但零食、玩具永远被视作无理要求,大人认为这是无用的东西。一次在集市,我因为太喜欢一个五块钱的电灯笼,想要买,开口哀求他们,被厉声责备到在集市大哭。
印象里,那是我最后一次“任性”,从那开始,我识趣地不再向父母要什么,只是默默幻想自己长大赚钱后,自由购买所有喜欢的物件。
工作后,我拼命赚钱,拼命消费。工资一千多块的时候,我用两三百的化妆品;工资近万,我就用两三千的 SK2。任何时候,我出门就打车,每月月供、各种卡账加在一起,要还款六七千。后来,我越来越发觉拼命赚的钱只够勉强生活,甚至填不上债务,我没有一点积蓄,这些事情让我陷入深深的焦虑。
这种循环持续到30岁。我意识到自己的收入已经到达了瓶颈,很难再进一步。我原本的收入目标是30岁能自由购买一万块以下的物品,但我当时拥有的,只有茫茫无边的债款。
我只能承认,无论再怎么努力,我也永远也过不上自由花钱的生活了,这个事实让我整个人崩塌了。
我辞去了广告公司的职位,在家里的床和沙发上整整躺了两个月。几天一出门,暴食,偶尔和男朋友出去散步,还整天想着去死。但想到如果我死了,很多人会为我伤心,就坚持了下来。
现在,我把所有钱都还清了,找了一份钱少事少的工作,带薪抑郁着。我仍然没有积蓄。这种感觉,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的自己,兜里从来没有过一分钱,站在一边看着小伙伴们买这买那。

图 | 为工作奔忙的夜晚
慧寂 23岁 北京
家有四套房,我去超市偷泡面
上大学的时候,有那么三四次,我逛超市,看看身旁没人注意,就把泡面和其他一些小东西藏在手提袋里,从收银员的眼皮下溜走。
大学四年,家里每月给我1000块生活费,到了学校我就发现,再怎么省,一餐也要10多块,钱完全不够用。
但我太害怕向父母要钱了,那种画面是我从小到大的噩梦,是地狱。
小时候,只要我对父母提出他们看来“不合理”的要求,就会遭受打骂。不是普通的教育惩罚,是被逼到墙角,按在地上,在小孩子记忆里堪称“惨痛”的真正的殴打。伴随记忆深刻的羞辱:我就不该把你生出来。
父母定义的“不合理”包含学习之外的一切。那时,不少同学都有游戏机,一个小男孩要战胜那种诱惑太痛苦了,印象里,因为羡慕朋友的游戏机,我会躲在被子里悄悄流眼泪。
其实,我家里一点也不缺钱,属于标准的中产。爸爸在外企工作,妈妈是老师,两人加一起月收入超过2万,家里还有4套房。但在我身上,全家人的教育理念一致:男孩必须穷养。爷爷说,这是家风, “穷家出孝子,白门出公卿”。
这种穷养一直延续到大学。我几乎没钱参与社交,和室友关系也不好。最后没办法,父母答应我搬出去住。起初,租房900块费用是父亲付的,但后来,由于(父母认为)我变得叛逆,就把钱停掉了,我靠帮同学代课,负担起自己所有的生活费。
现在,我在北京做着一份月薪7000多的工作。但除开租房,我每月都会将生活费尽量控制在800块以内,和大学里一模一样。多余的花销会让我本能地紧张。去年,因为胃病严重,我需要按疗程吃胃药。但胃药33块钱一盒的价格让我十分不舒服,那感觉比胃疼还难受。第一个疗程的药吃完了,我没有再买。

图 | 这个3月,在北京的开支
曾小花 31岁 深圳
我以为家里特别穷,妈妈却掏出十万块买车
小时候,我是父母眼中最懂事的孩子,始终把“我们家穷”铭记于心。七八岁,妈妈带我去买凉鞋,我一眼相中一双60元的绿色凉鞋,但看到标价,我很小声地跟妈妈说:“我买那双10元的就好了。”当时,我脚上的鞋子早就小了,拖了很久很久,脚疼到受不了,我才小心翼翼地告诉妈妈。
我记得,从小妈妈就反反复复地说:家里穷,要省吃俭用过日子。实际的境况也是如此,有的时候,饭桌上全是青菜,没有肉。长身体的我,看到姑姑家吃剩的鸡屁股都在咽口水。
认定自己家里穷,我总觉得低人一等。有一次,老师发了家庭调查表,父母亲那一栏填职业,我填了“无业”,总担心老师看到后鄙视我。就连英语老师在课堂上提问:what’s your father?我都觉得不知所措。
我发现家里远没有妈妈说得那么穷,已经是大学毕业之后了。当时,妈妈突然说想买车,我觉得简直玩笑,家里连2万块都拿不出来。可是妈妈却一下子拿出十万块,和姑姑合买了辆20万元的车。
这简直天方夜谭。
追问之下,妈妈一开始搪塞说,是借了好朋友的钱,再问,她又说并不是。那之后,她逐渐对真实的家庭条件松了口,解释我们周围都是有钱的深圳土著,担心我和弟弟同别人攀比,才故意说家里没钱。
往日回忆一点一点揭开,爸爸妈妈确实没有“朝九晚五”的工作,但他们在深圳经营一家米铺,后来又经营了一间麻将馆。我读幼儿园3年学费是2万块,家里的沙发是2千块。
骤然知晓事实,我的第一反应是轻松:家里原来没那么穷,那我也不用再想着帮父母承担什么。只是,多年积累的自卑已经形成惯性,我发现我已经不可能像别人那样洒脱地生活了。跟同一圈层的人比起来,我的穿衣打扮,言行举止,已经不再是同一个“档次”。现在我的月薪过万,可我永远是带着烙印生活的人,烙印的名字叫贫穷。

图 | 十年前的旧衣,我还当做睡衣在穿
小龙 27岁 北京
爸爸教我体验生活,我与死亡擦肩而过
我差点死在18岁那年的暑假,是爸爸叫我去的。这件事他可能都不记得了。
我的爸爸对我的“穷养”是理论式的,他特别认同苦难教育那一套东西。他坚信,男孩子必须在真实的困境里学会独立,没有困境也得给我创造个困境。
上了高中,爸爸可能觉得那标志着我长大了,立马实施把我赶出家门的事儿。当时,他经营一家测绘公司,要求我每个假期跟着员工去荒郊野外、高山深谷学勘测,一待就是个把月份。
18岁暑假,我跟着测绘队去金昌,有个测绘点在特别陡峭的山上,我独自扛着好几斤重的仪器,不小心走到了悬崖边的小路,进退两难,往前跨一步就是近五十米的落差,那一刻背上的仪器变得特别特别沉,就好像要把我拽下去。极度恐惧中,我死死抓住身后山体上的石块,叫了半个小时,才被人听到救下。
后来,父亲知道这件事后,只问了我一句:没事吧?
父亲的严酷教育在我的成长中以一贯之。他要求我百分百服从,一旦拒绝去野外工作,就对我极尽辱骂。在其他事情上也一样。小学时,我喜欢打乒乓球,一旦考试成绩不好,父亲就直接把球拍摔了。
这类事情反反复复,让我总是怀疑自己是不是父母亲生的,多次离家出走。但必须承认,父亲的教育方式确实也教会了我独立,即便是变成没有星期五的鲁滨孙,我也能好好生活。现在,我和父母已经能心平气和地沟通了,但和解并不意味着理解,我只想远远避开他们,永远不要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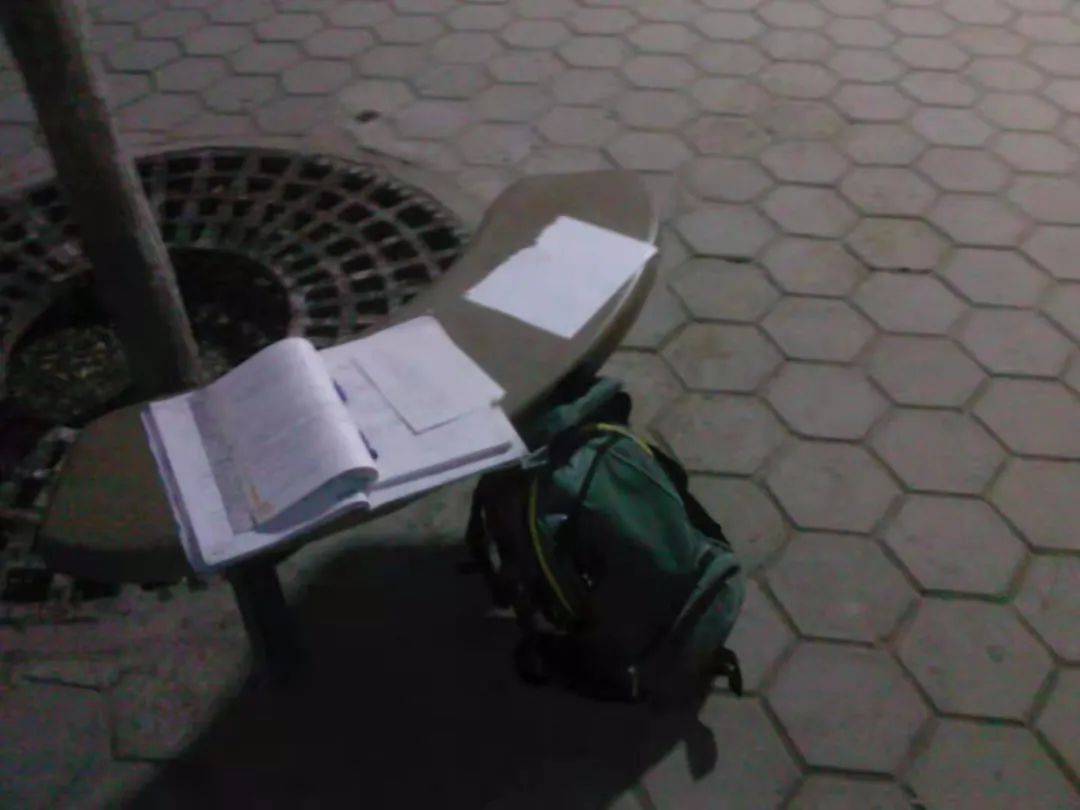
图 | 穷游时,我露宿街头
菁菁 25岁 天津
1斤草莓,换来穷养女孩的初恋
我的妈妈是否爱我,是我小时候一直纠结的“人生命题”。我好像很难找到妈妈爱我的证据。
小孩子最直接的感受是,妈妈好像从不肯在我身上浪费钱。
我的父母是公务员双职工,家里不缺钱,但他们从不给我零用钱。小朋友们在学校分享1毛钱的辣条、5毛钱的跳跳糖,5块钱的信纸,我都没有,就这样被他们起哄“你妈妈不爱你”。
我很难过,但似乎确实是这样,看看自己身上的衣服和鞋子,没有一件是妈妈给我买的,全都是亲戚们送的。有的鞋子大一码,磨脚,我告诉妈妈,她认为我是矫情,想要穿新鞋子。
初中毕业后,我和邻家姐姐都被安排去外地读寄宿高中。开学前一周,邻居阿姨来我家借钱,给女儿买新款手机和新衣服,母亲大方借给她2万块。而我,去学校报道的时候,带着充话费送的老人机,生活费每个月只有260元。周末食堂不开门,要吃饭得去外面买,可我连四块五的煎饼都不舍得买。
我试探着和妈妈说,生活费不够,她开玩笑般让我买袋榨菜凑合凑合。
我很小就渴望离开家,但离开家后,钱依旧不够用。我开始在周末兼职,白天去服装店卖衣服,晚上去超市卖牛奶、方便面。宿舍周末的活动我不参与,被大家说不合群。后来兼职早出晚归,又被同学说成不太正经。很长时间,我觉得我的生活没意思极了。
17岁时,我随口和一个男人说,好想吃草莓啊。当晚,他买了一斤给我送到宿舍。从小到大,我从没有过需求被父母认真回应的“体验”。他却这么重视我的那一句话。当时我就觉得,他对我比爸爸妈妈还好。我和他迅速相恋了。男人大我十一岁,在一起三年,他家的床单被罩,筷子碗,家具都是我打工一点点存钱买的。他在我面前说起想要什么,我就想方设法实现。我小心翼翼地对待他,直到发现他出轨,我第一反应还是原谅他,我只想和他在一起。不过,最终我们还是分手了。
分手很久,在一个聚餐场合,我们又见面了,他过来向我感慨:“将来我有了孩子一定要富养。不然别人给一块糖就被骗了”。我一怔,不知该说什么。
后来,随着年龄的慢慢增长,我已经能理解,父母总是把自己觉得最好的路安排给你。孩子要一颗桃子,他们种了一山橘子,一个觉得自己辛辛苦苦,一个觉得自己要得不多。但理解不意味着原谅。现在,我在感情上成熟多了,不会因为谁对我好,就轻易喜欢谁。不过每次想起初恋,我还是会感慨,一个女孩的真心,一斤草莓就能换来。
张云天 30岁 南京
作为大哥,我成为家中被穷养的那个
我是家里早早懂事的长子,我有个比我小7岁的弟弟。
仔细想想,我的家里不至于穷,但绝对不宽裕,父母想要同时满足两个孩子的需求,就会比较吃力。而两个孩子之间,弟弟永远是被偏爱的那一个。比如,母亲会带他去买新衣服,而我一直穿着亲戚的旧衣服,有时候太长,有时候又太短。小学四年级,我作为优秀学生上台发言,穿了一身打补丁的衣服,感觉全校都在笑话我。
仿佛一种融在骨血里的习惯,从小,我会主动压缩自己的需求,觉得不公平也从来不说。潜意识里,我相信母亲喜欢省钱的孩子,我就在学校里尽量吃白米饭,把省下来的伙食费还给母亲。那种时刻,我总是感到一种承担责任的自豪:比起弟弟,我更懂事,更努力,能够为家庭分忧。
但物质的匮乏让我整个成长都很压抑。读大学之后,我终于有了人生中第一件羽绒服,是一件很土气的红色大衣,我穿了很久。那时候我交了女朋友,跟她一起出去时撑的伞都是坏的,我很尴尬。而那件羽绒服,我一开始没觉得有问题,后来她无意之间说这件衣服像她爷爷穿的那件,我忽然就有些敏感,总觉得那意味着什么。
我有时候想,我这种沉重别扭的人,这样纠结敏感的爱,女友可能也不需要吧——这又是一种悲观的心态,就像我所有的思考方式一样,根植在童年里,沉淀在漫长的时光里,可能已经成为我的一部分了。我没办法改变自己,更无法从头再来。
撰文 | 林正茗
编辑 | 林扉
=========================================================
牙疼,要了年轻人的“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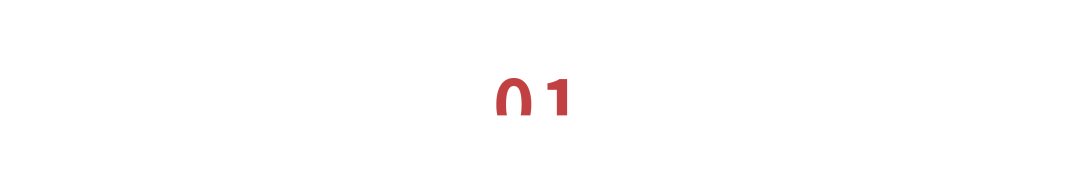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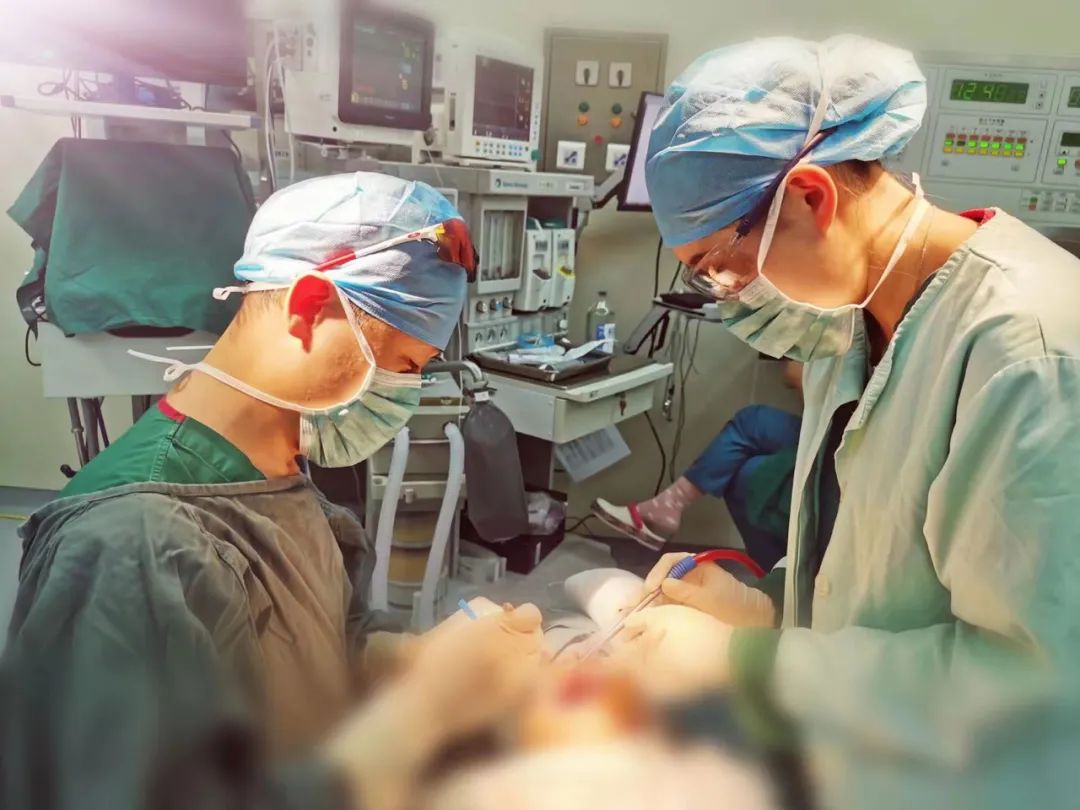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