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在除夕这天逃走

1
2

3

4
- END -
编辑 | 陈晓妍
---------------------------------------------------------------------------------------------------------------------------
助浴师,把晚年洗净

“老人味”
在拨打助浴电话之前,李琴已经为家里两个老人的洗澡问题困扰了多年。
李琴的母亲今年90岁了,父亲92岁,两位老人都是腿脚不便,无法出门,5年前她为老人请了保姆,照料三餐起居。但洗澡,她不放心交给保姆,怕弄伤老人,每周过来自己帮着洗。
只有亲身经历的家属才知道,给老人洗澡,真的是一项大工程。
李琴父母长期卧床,体重都有130多斤,仅仅把老人扶起来,迈动脚步,她就已经气喘吁吁。从客厅的凳子,到轮椅,再到浴室里的防滑凳,这样的扶持搬运,一共需要四次。还不包括洗澡、脱衣穿衣时的托举。何况,浴室环境潮湿闷热,老人无法待太久,需要速战速决,每次李琴和保姆都是手忙脚乱。
有一次,临过年没几天,母亲想好好洗个澡。那会李琴忙着置办年货,抽不出身,她让母亲再等些日子,老人一听就发了脾气。“我老了,叫不动你了是么。”保姆怕老人情绪激动,出岔子,硬着头皮一个人为老人洗了澡。第二天李琴一进门,就迎来保姆的抱怨,腰都快累断了。
李琴自己,也已经是快60岁的老人了。她有风湿病,天气转凉,两条腿都疼得难以行走。
元宵节前一天,老人又提出洗澡的要求,想起前几日在养老驿站看到的助浴服务,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她拨下了那个号码。
这绝不是个别家庭的困局。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19年末,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超过2.5亿,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约4200万人。北京一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就达300-400万人,也就是全市近四分之一的市民是老年人。
老人身上有味道,这味道甚至有一个专属标签:“老人味”。中药的味道,尿液的味道,饭菜的味道,闷在厚衣服里身体的味道……这些味道搅合在一起,就是刻在印象里那种“老人味”。人们带着某种嫌弃和无奈提起这种味道,避开它,仿佛这是老人的一部分。
这一切的原因,不过是“老人洗澡难”。这句话仿佛平常,却蕴含着太多无力解决的现实,老人的精力,子女的工作,甚至包括社会对老人的种种谨慎与忧虑,把老人牢牢按在他们的标签里。
90岁的孟爷爷几次试着去大众浴池洗澡,可一进门就被工作人员拦下了:“你这么大年纪了,也没人陪着,不安全,下次别再来了。”
这么多年,孟爷爷只成功去澡堂洗过一次澡。
孟爷爷住在北京北新桥的胡同里。那一带多是平房,无法连接天然气。浴室空间小,水压和水温也上不去,夏天还能凑合,到了冬天没法淋浴,只能用湿毛巾简单擦拭。
02
给陌生人洗澡
从预约助浴服务开始,李琴就发现,老人嘴上不多说,却在每次助浴师上门那一天,早早起床,端端正正坐在靠背的椅子上等着,好像这是一种仪式。
李琴感慨,她从前都不知道老人这么盼着洗澡。
前几次,李琴不放心,会在浴室里全程旁观。她看到助浴师先调试好水温,把老人推到浴室,抱起靠墙,快速把老人的三条裤子一口气褪到大腿处,又赶紧扶老人坐下,褪下裤脚。
然后,助浴师接一盆热水,将老人的脚泡在热水里,试试水温,把花洒的水流调小,轻轻淋在老人的后背,四肢,腿上。接着戴上搓澡巾,开始擦身。从后背,到脖子,胸前,上半身、下半身,每洗好一部分,就用水冲洗后,再擦拭一遍,反复两次。约四十分钟后,洗浴完成,再为老人抹上护肤霜,重新穿好衣服。
李琴说,刚洗完澡,冒着热气坐在椅子上的老人,“温顺的像一只洋娃娃,可爱极了”,她喜欢看着母亲那样心满意足的样子。
对助浴师来说,“让顾客心满意足”却并不是可以轻易抵达的目标。洗澡,只是助浴师们的附加服务,她们的另一个身份,是居家养老护理员。给陌生人洗澡,还是陌生的老人,对这些女孩子来讲,难处绝不仅是一系列复杂细致的规则,还要越过心里那道坎。
“助浴,这个活其实也有一套标准流程。”45岁的助浴师郝美云说,首先,助浴前要给老人测量血压,观察老人当前是否适合洗澡,确保安全,一些老人常见的基础病也要事先和家属确认,每个老人的情况都要建立档案。
正式洗澡前,助浴师要仔细观察浴室条件,将水温调试到标准的42度,嘱咐家属提前晾好温开水,以便老人洗完澡后能及时补充水分。
如何转移老人也需要技巧。“像这样把老人的脚分开,让老人的手勾住我的脖子,我两只手臂交叉抱住老人的腰,再一用力,老人就能从凳子上托站起来,这个时候在轻轻放在另一个轮椅上。”郝美云比划着说。
每一种服务业,在标准规则的壳子之下,都要满足顾客各种各样的特别需求,助浴也是如此,或者说,尤其如此。上了年纪的老人精力散漫,很多时候并非理性动物。几乎每个助浴师都能回忆起一兜子或是尴尬或是委屈的经历。
24岁的冮雪,第一次上门服务,就被家属说哭了。“为什么洗完后还是这么多干皮,你要是这样洗的话,我要你干嘛。”指着她大骂。冮雪觉得委屈,老人的皮肤失去了水皮,变得很干,洗得太用力皮肤很容易红肿,反而不好。可是对方就是不理解。
21岁的小谭印象最深的是一个“讲究奶奶”。助浴前,家属就叮嘱她,“我们家老太太要求高,喜欢搓背,你要按照她的要求来,千万别和她顶撞。” 小谭做足了心理准备,可洗澡刚没几分钟,老人就打断了,“小姑娘,你是南方人吧,你这样搓可不对。”语气里夹着火。说不清楚,索性一把夺过搓澡巾。“这个一定要拧干了,然后这么一层层的往下搓,看到了么,有东西出来这样才算搓透了,搓干净的地方水一冲是滑的,没搓干净的地方很黏。”老人像严厉的老师一样,一板一眼地和小谭说。
有那么几秒钟,小谭觉得空气都凝固了,心里一阵一阵发慌,什么也说不出来。只能一笔一划地按照“北方规矩”给老人搓。慢慢地,气氛缓和下来,“奶奶你真讲究。” 小谭忍不住说。“现在搓的好了。”“老师”终于点了头,“学生”的脸已经涨得通红。

图 | 助浴前,小谭为老人测量血压
慢慢地,随着助浴从一件尴尬的事情淡化成职业习惯,助浴师们也开始理解这些老人的处境。冮雪说,在狭小的浴室里这样密切地接触,尴尬的不是只有她,老人也会尴尬。需要陌生人给他们洗澡,对很多要强的老人来说,是一件触及自尊的行为。她试图想象在漫长的日子里渐渐衰老的自己,像她认识的一个奶奶说的那样:每天力气只够洗一条腿,第二天再洗一条腿,第三天洗胳膊……直到有一天,连这也做不到了,只能求陌生人到家里帮自己洗澡。她极力想,那时自己会是怎样的一种心情?
后来,在助浴的时候,冮雪会有意识地让老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帮着拿花洒,让老人感觉到自己也在帮忙,不是任凭摆布。她发现,这些小事,确实能够让老人松弛下来,减少助浴的尴尬与摩擦。
冮雪和小谭都谈到在这份工作中感受到的价值。只是至今,这价值仍然停留在情感层面。——“助浴师”听起来时髦,却仍是零散小众的低端服务,产业远未铺开。小谭和冮雪们一小时只挣几十块。
03
藏在浴室后的悲喜
每次洗澡,助浴师待在老人家里的时间,一般不超过两个小时,却几乎可以窥见一段家庭关系的最隐秘处。
曾经有一次,郝美云服务一位有认知障碍的老人。老人患病多年,女儿早已磨光了耐心,“让你去洗澡了!”郝美云听见女儿对着老人吼叫,老人抖了抖肩膀,两眼空洞。“慢慢说,别吓着老人。” 她连连劝说。
郝美云知道,这样的老人,任何交流都无法流到耳朵里,必须像哄小孩那样耐心,儿女长久的照顾压力巨大,在公共养老服务尚不完善的今天,这是一个难解的结。
但其实,想到为老人找助浴,已经是一个普通家庭为改善老人状况难得的努力。助浴并不是一项便宜的服务,均价在80-120元之间,专业的护理机构甚至高达400元以上。对很多家庭来说,一次助浴的价格,也许就是一个星期的生活费。
从机构数据看,在偌大的北京,每个月寻求助浴的家庭数量平均在几十个,很少上百。
“多数客户的家庭条件其实挺苦的。卫生间很小,没有任何防滑设施。” 郝美云见过仅有两平方米的卫生间,摆放着桶,盆等杂物,连一把多余的椅子都放不进,老人洗澡只好坐在马桶盖上。郝美云转个身都困难。
她看见过脏乱、刺鼻,“几乎待不下去”的房间,堆满脏衣服,酸味一阵阵飘出来。剩菜,碗,碟子就在客厅的桌子上放着,也没有洗,桌上还有乱堆一气的杂物。窗户关着,似乎老人和家人都没怎么想着通风。
这样的老人,其实是最需要助浴的那部分人,但却是服务的触角最难抵达的人群。一个助浴师记得曾接到一个年轻人的电话咨询,“他是奶奶的孙子,询问的特别仔细,尤其是价格,最终,他还是没有下单。”
只有助浴师才能真正理解,洗澡这件再普通不过的事儿,对老人有多重要。从业5年,郝美云最触目惊心的记忆,是一个70多岁的爷爷后背一道一道刮痕,那是皮肤不断发炎积下的痕迹。一年前,老人在家里洗澡时差点摔倒,从那以后就不怎么敢洗澡,更不想麻烦工作忙的冒烟的女儿,只能用毛巾擦擦身子。见到郝美云的那一刻,老人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激动。
老人说,他已经一年没洗澡了。
还有些家庭,经济状况好一点,保姆长期在家,儿女找助浴的原因是怕保姆太累了,把气撒在老人身上。一个顾客透露,她找助浴,纯粹是给保姆减轻负担,她每次来看望母亲,总是听保姆唠叨,在老人那里受了气,她一边给保姆送礼物宽慰着,另一边又哄着母亲。没办法,现在市场上保姆太难找了。
52岁的王淑玲是老年助浴点的管理员,在她的手机里,存着几十位老人子女的微信,每个家庭都有各自的故事和无奈。见的人多了,她慢慢感觉到,所有的故事,指向的都是同一个问题:照顾老人难。
曾经,有个客户忍不住和王淑玲倾诉:一边照看孙女,一边顾着住院的老公,还有家里的老母亲,真的管不过来,客户说着就哭了,她自己也已经进入老年人的行列,却要撑起更年迈的父母。

图 | 王淑玲在打扫浴室
王淑玲也跟着伤感起来,她太能体会这种感受。2012年10月27日这天,是她刻骨铭心的日子。王淑玲代表公司参加活动,出门前家里的母亲对她说,“昨天你萝卜丝可能是炒烂了,我有点不舒服。”因为有事,王淑玲没有在意,“没事没事,我不碍事,你去吧。”母亲对她说。几个小时后,母亲突发心脏病,倒在家里还来不及上救护车,人就不行了。王淑玲疼得锥心刺骨,她忍不住假设:“如果我那天不去公司,马上带母亲去看病,会不会一切都来得及。”
很多时候,王淑玲把这份工作当作是对母亲的补偿,“我觉得,我是在替那些不能陪伴老人的子女,为他们的父母做一些事。”
在那些关于助浴的故事里,有一个像曾经的王淑玲那样,无暇照顾母亲的女儿,她记着妈妈需要洗澡,定期为她叫助浴。而故事里的母亲已经80多岁了,一天大半时辰处于失智状态,大部分记忆离她而去,但死死记得自己有一个女儿。助浴时,这位母亲大喊大叫,不让任何人靠近,助浴师万般哄劝无效,只有一句话无往不利:“奶奶,是你女儿叫我们过来的。”
听到这话,这个奶奶顷刻放松下来,欢天喜地走进浴室,淡定地享受助浴师帮她搓背、掏耳朵,像收到了一件美好的礼物。
洗完澡,穿上干净蓬松的衣服,老奶奶舒服地眯起眼睛,赶紧给女儿打电话:“你给我找的这个小姑娘啊,洗的真好。”
- END -
编辑 | 林扉
-------------------------------------------------------------------------------------------------------------
我是一名在非洲安家的中国女性
白杨/口述
张尼奥/撰文
我叫白杨,今年32岁,是一名在非洲安家的中国人,过去五年一直待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我老公叫查尔斯,比我大6岁,目前在华为驻乌干达分公司工作。
我们俩是十年前在中国认识的,那时他在重庆大学留学,我在隔壁的四川美院,我们谈了三年恋爱,毕业结婚后有了一个可爱的混血宝宝。2015年,因为工作关系,我跟查尔斯回到乌干达,过上了和想象中完全不一样的非洲生活。
前年我怀上二胎后,我妈专门从国内飞来照顾我,我爸和我弟也一起到这边找了工作,现在我们一家老小都在乌干达。

2020年春节,我们一家人在乌干达南京饭店的合影,当时二女儿还在我肚子里。
尽管我自己过得还不错,但因为嫁到非洲,我听到过各种难听话,大到三观不正、人格有问题,小到人身攻击,已经懒得去解释什么。如果大家依然对我的故事感兴趣,那么请抛开偏见,听一听我的真实经历和感受。
我一直认为,婚姻是个人选择的事,冷暖自知,两个人合不合适,跟国籍、人种和肤色真的没啥关系。查尔斯如果不是足够优秀,对我足够好,我怎么可能嫁给他?更别提和他生孩子、跟他回非洲。相反,按我妈的话说,能遇见这样的老公也算是我的幸运。
查尔斯是乌干达第二大王室的后代,和他相比,我的家庭要普通很多,父母都是河南漯河的农民,经济情况在村里算中不溜,不好也不差,他们靠养猪供出了我和弟弟两个大学生。

考上大学后的我,看上去一脸稚嫩。
偏偏我学的美术专业很烧钱,号称“人民币焚烧炉”。在我2008年考上四川美院后,家里的积蓄已经花得差不多,那几年市场行情不好,爸妈靠猪挣不到啥钱,我也跟着过起了苦日子。
美术生家里条件一般都不差,舍友们每个月的生活费基本都是1500元起,爸妈却只给我600元,最困难的时候还一度缩水到300。这点钱连吃饱饭都很勉强,更别说买颜料、买画笔这些开支。所以从大一下学期开始,我就在校外兼职挣钱了。
那会儿大学生兼职最常见的选择就是去学校附近的餐馆打工,我找了一家兰州拉面馆,每天饭点过去端盘子,一个月工资150元。钱虽然少,但管饭,我主要也是看上那几顿饭了,从大一一直干到大三。拉面馆的生意很火爆,不知道是不是正对外国人口味,周边几所大学的留学生特别喜欢去,黑的白的棕的,什么肤色的人都有。

我和朋友在饭馆的合影,上大学后,我对肤色和人种完全没偏见了。
查尔斯就是这群留学生中的一个。他当时在重庆大学读硕士前的语言班,和几个留学生来吃饭的时候要了我的电话。我当时并不觉得有什么,毕竟我在学校也认识不少外国人,认识一下互相练习语言也很正常。
结果没多久,查尔斯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说他第一眼见我的时候就觉得我貌美如花、勤奋能干,将来一定要娶我。
我以为他和朋友们在恶作剧开玩笑,没当回事。我一直都不怎么瘦,单眼皮、大脸盘,除了白点没啥特别的地方,就连爸妈也曾觉得我长得丑。好笑的是,到大学之后我才发现,我这样的长相正好符合一些外国人的审美,有好几个外国男生都跟我表达过心意。
可我当时压根没想过和谁谈恋爱,人穷的时候,哪敢考虑这么奢侈的事?谈恋爱就意味着要花钱,男方再主动,也不可能一直让人家出钱吧,这样会显得女生地位低。

那时候的查尔斯,大我6岁,看上去成熟许多。
对查尔斯,我的态度也一样,纯粹当朋友处着,经常和包括他在内的一群外国朋友玩。后来查尔斯每天都来拉面馆吃饭,见面聊天的时间多了,就有了追求我的机会。
有次他约我出去吃饭,明明自己身上只剩100块钱,还花70多给我买了一个德克士的全家桶,那个月剩下的时间只能艰苦地凑活着过,当时我就觉得他对我挺真心的。
还有一次我因为肠胃炎上吐下泻,去医院输水钱不够,只能给我妈打电话求援,结果我妈在电话里撂下一句:你怎么这么多事儿?我当时伤心透了,觉得爸妈不爱我,留我一个人在重庆也不管死活。查尔斯听说后赶紧跑来替我交了药费,陪我输水。从这以后,我俩差不多就确定恋爱关系了。

我和查尔斯在一起后的合影。
大学生还是比较单纯,我谈恋爱的时候没想那么多,什么结婚生孩子啊,对方家庭怎么样啊,这些现实问题统统没考虑。我只知道能来中国公派留学的非洲学生家里都不差,有些还是酋长或者官员的儿子。
查尔斯很少跟我说他家里的情况,还是和他一起留学的非洲同学跟我说,查尔斯家的人基本都是从政的。我那时最担心的问题就是查尔斯会不会已经在非洲有家室,甚至有孩子了?后来发现是自己多虑了。
朋友和老师都知道我和查尔斯谈恋爱的事,大家平时经常在一起交流,他们对查尔斯的人品还是很放心的,没有人说闲话,更没有人劝我分手。
爸妈也都知道我谈了个非洲男朋友,是我主动告诉他们的。我妈觉得无所谓,自己的人生自己负责,跟外国人学点英语挺好的,谈恋爱又不等于结婚。
我爸是很典型的大男子主义,不到结婚谈彩礼的时候都不怎么关心这些事。何况我们在重庆,山高皇帝远的,他也管不着。

2012年5月,我和同学穿学士服拍了毕业照,查尔斯比我毕业晚。
毕业离开校园后,我和查尔斯都留在了重庆,我在一家公司当文案策划,他在培训机构当英语外教。虽然我那时候工资只有几千,但两个人一起打拼,幸福指数还是挺高的。
2013年的一天,查尔斯突然把我带到教堂,在朋友们的见证下虔诚地向我起誓求婚。我觉得也到时候了,回到家就跟爸妈商量起结婚的事。我爸不怎么同意,问我为什么要嫁给非洲人?
我没敢跟他们说,我之所以愿意嫁给查尔斯,一方面也是受他俩的影响。我奶奶和我妈经常吵得不可开交,我爸每次都不吭声,从来不去调和矛盾,我很不想自己也要面对婆媳矛盾的问题,所以既然没遇到合适的中国对象,那不如嫁给外国人。
再就是我爸从小对我关心不够,我总觉得比较缺少父爱,查尔斯的稳重成熟让我很有安全感。我知道,他就是我在可选范围内的最优解。

2014年春节,我带查尔斯回河南老家见父母,我们俩堆了个雪人。
我爸一个劲儿地劝我,说自从我大学毕业后,已经有很多人来找他说媒,我有大学文凭,在老家很抢手。但我已经毕业挣钱,经济独立了,他干预不了我的决定。我妈觉得年轻人想做啥大人们也管不了,不如在背后默默支持就行了。
于是没多久,我和查尔斯领了结婚证,在河南老家办了场婚礼。我们村里的人还是比较明事理的,没人当面说难听的话,也没人私下里问我怎么嫁给非洲人了,大家没见过外国人,都觉得稀奇,盯着查尔斯使劲看。

右上角是我和查尔斯的结婚证,后下角是当时在老家办的生育证。
2014年7月,我和查尔斯在重庆迎来了一个可爱的混血女孩,给她取名艾斯特。我妈当上奶奶高兴得不行,早早地给孩子打好了毛线棉鞋和小毛衣,还专程赶来重庆照顾我们。
她在重庆待了一年半,也和查尔斯近距离相处了一年半,对女婿的评价特别高,知道我没嫁错人。
查尔斯很细心,有一次我们去吃西餐,牛排一端上来,我和我弟就拿起刀叉只顾着自己吃。查尔斯见我妈抱着孩子不方便,很认真地把我妈那块牛肉都切成一小块一小块。我妈感动得不行,扭过头就笑话我和我弟:要恁俩有啥用?以后查尔斯就是我儿子!

2014年,我妈抱着孙女出去重庆街头遛弯。
虽然查尔斯和我们一家人都处得很愉快,但他在工作上一直不怎么开心,他硕士读的是经济学专业,一直想去银行这类金融机构工作,却因为语言和国籍问题始终没找到合适的,又不甘心一直当外教,心里不太好受。
他好几次跟我说想回乌干达发展。我这人活得比较洒脱,去哪儿都可以,反正我会英语,就在网上给自己找了一份驻乌干达的销售工作。2015年11月30日,我带着女儿艾斯特,和查尔斯一起告别了重庆。

我们一家人在去乌干达的飞机上,这是我第一次出国。
乌干达位于非洲东部,赤道正下方。飞机落地之前,我也以为非洲哪哪儿都很热,到了才发现人家这里气候好得很,就跟云南大理差不多,全年四季如春,放眼望去到处都是绿油油的,即便旱季也只是阳光辐射强,不会特别热,所以我们家至今连空调和风扇都没安。
乌干达曾被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誉为“非洲明珠”,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穷,那么脏乱差。贫富差距还是肉眼可见的,贫民区是特别小的土房子,里面可能就摆了张床,有的床都没有,人直接睡在垫子上。富人家的房子盖得很好,有的甚至像中国南方农村一样,盖了四层的小洋楼。

乌干达首都的公园,看上去不比我们国家的差,四周有很多棕榈树。
也是到了乌干达之后,我才对查尔斯的家庭情况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从家族背景来看,他属于乌干达第二大王室的后代。虽然他这一代关系已经隔得比较远,也没有王位继承权,但从姓氏“Isiko”依然可以分辨出来,只要是他们王族的人,一听这个姓就知道查尔斯是王子。
我刚到这边的时候,有人把我介绍给一位当地的老人认识,说我是Isiko夫人。那个老头已经一把年纪了,听到这个姓氏之后惊讶了一下,竟然半跪下来给我打招呼,说Isiko是他们的王室的姓,一副很尊重的样子。

因为查尔斯家的关系,我还参加过乌干达政府高层晚宴,见到了很多政要。
我公公婆婆都是大学老师,在乌干达很有人脉和资源。查尔斯在家排行老十,他的哥哥姐姐都很有才,有的是小学校长,有的是医生,有的在警察局任职,还有一个是外交官,我的本科学历在他们家基本算是垫底。
以前我也听过传言说非洲有钱人可能会三妻四妾,但这在查尔斯他们家族完全不存在。他们也讲究门当户对,但由于我是外国人,所以没那么在意这个问题。
他父母对我家情况其实也不是很了解,对中国的第一印象就是发展很快,人特别有钱。查尔斯给家里介绍我的时候说我们家有个养猪场,还有很多地,听起来很富裕的样子,就这样糊弄过去了。用我妈的话说,真按门当户对去论,我们家和他们家肯定不是一个层级的。

去查尔斯亲戚家做客,从他们穿西装带名表的打扮上也能看出来,他们属于精英阶层。
在乌干达安顿下来之后,我便开始工作,一直做了三年多的销售,后来查尔斯他姐夫从税务局退下来,他们家族做清关生意有便利,于是我就去自家的清关公司工作了。
大部分非洲人比较佛系,不像中国人做生意都想做大做强,人家觉得差不多就可以了,小富即安。所以公司基本上是由我在负责,中国业务都是我拉的,作为股东,我可以抽一半的利润。平时通过牵线介绍一些国际合作项目,还可以拿到不少提成。

这是货柜到了,我去安排工人卸货,非洲人习惯把东西顶在头上搬运。
虽然平时工作不是很忙,但因为家里有俩孩子,我还是请了一个保姆。非洲人力成本特别低,保姆一个月佣金只要300元人民币,而且对当地人来说,这个收入已经算不错的了。
我吃不惯乌干达的香蕉饭,在家还是以中餐为主,保姆不会做,所以不用管饭,只负责打扫卫生、洗衣服、看孩子。

乌干达被称为“香蕉之国”,我不吃香蕉饭,平时都是用香蕉来做沙拉。
我们家贴身衣物也不用保姆洗,都是查尔斯下班回家会主动去干的活儿。他是一个很有家庭责任感的人,认为女性在家庭分工中只是帮忙的角色,他累了我帮一下就行,平时不用承担太多。
所以懒不懒跟肤色无关,真的是分人的,查尔斯就比我勤快。我们在一起有十年了,尤其是结婚后,基本上都是他早早起床给一家人做早饭,我俩口味不一样,他就提前问我们是吃饼还是吃面包什么的,这些他都会做。

查尔斯在用擀面杖做饼,身上穿的是他在华为的文化衫。
也许是性格使然,也许是受到的家庭教育比较好,查尔斯从来没有冲我发过火,他生气的标志就是不说话,然后默默走开,最严重的情况就是瞪我。
跟他相比,我脾气比较暴躁,一生气就会拉着他狂吼。他也希望我脾气变好一点,后面发现我就这个脾气,也不说什么了。
我俩最大的分歧是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女儿原本既学英语又学中文,还短暂地学过一阵儿乌干达的斯瓦希里语,我还想让她去上法语学校,查尔斯就死活不同意。
他说孩子已经学得太多了,这么小的年纪就应该玩起来,散养,而不是我说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他学历比我高,在这个问题上,我最后还是听了他的。

除了让女儿学中文,我还会教她一些中国传统文化,这是给她买的汉服。
大部分非洲家庭现在也不会生很多孩子,那都是上一辈人的想法,查尔斯就从未计划过要二胎,后来还是架不住我爸妈的催生,把备孕计划提上了日程。
2019年上半年,我再次怀孕了。刚到八月,我妈就像当初跑去重庆一样,专程从国内飞到乌干达照顾我。知道我在这边过得挺好的,我爸一起跟着来了。我弟刚好大学毕业,他之后也来这边找了个销售经理的工作。

爸妈落地后,我和孩子带着鲜花去接机。
我爸最开始在一家农场帮忙种地,后来又去乌干达北部帮一个开民宿的老乡做饭。他说这一辈子过得最安逸的日子就是在乌干达,可是因为语言不通,现在多少还是有点想回国。
我妈是舍不得走,她在这边待得挺开心的,没事做点好吃的,带带孙女。她特别喜欢乌干达的气候,不冷不热,河南老家冬天太冷了。她也吃不惯当地饭,就在我们的院子里种了菜,刚开始只有两米长两米宽的样子,最近正在努力扩展。

我妈在院子里开辟的小菜园,葱、韭菜、小青菜都有。
我妈之前犯过脑梗,行动力记忆力各方面都大不如前。我愿意让她来不单单是为了孩子有人带,这种事保姆也可以做,大不了请两个。主要是老家没人,子女都在外面上班,必须把她带在身边我才放心。
去年出现新冠疫情后,乌干达也有风险了,我们都待在家很少出门。一个朋友看我们一家人在非洲过得挺有意思的,跟我说可以试试在西瓜视频上做个博主。我想反正疫情无聊,找个事儿干挺好的,就让我妈出镜当主人公,我负责拍摄和剪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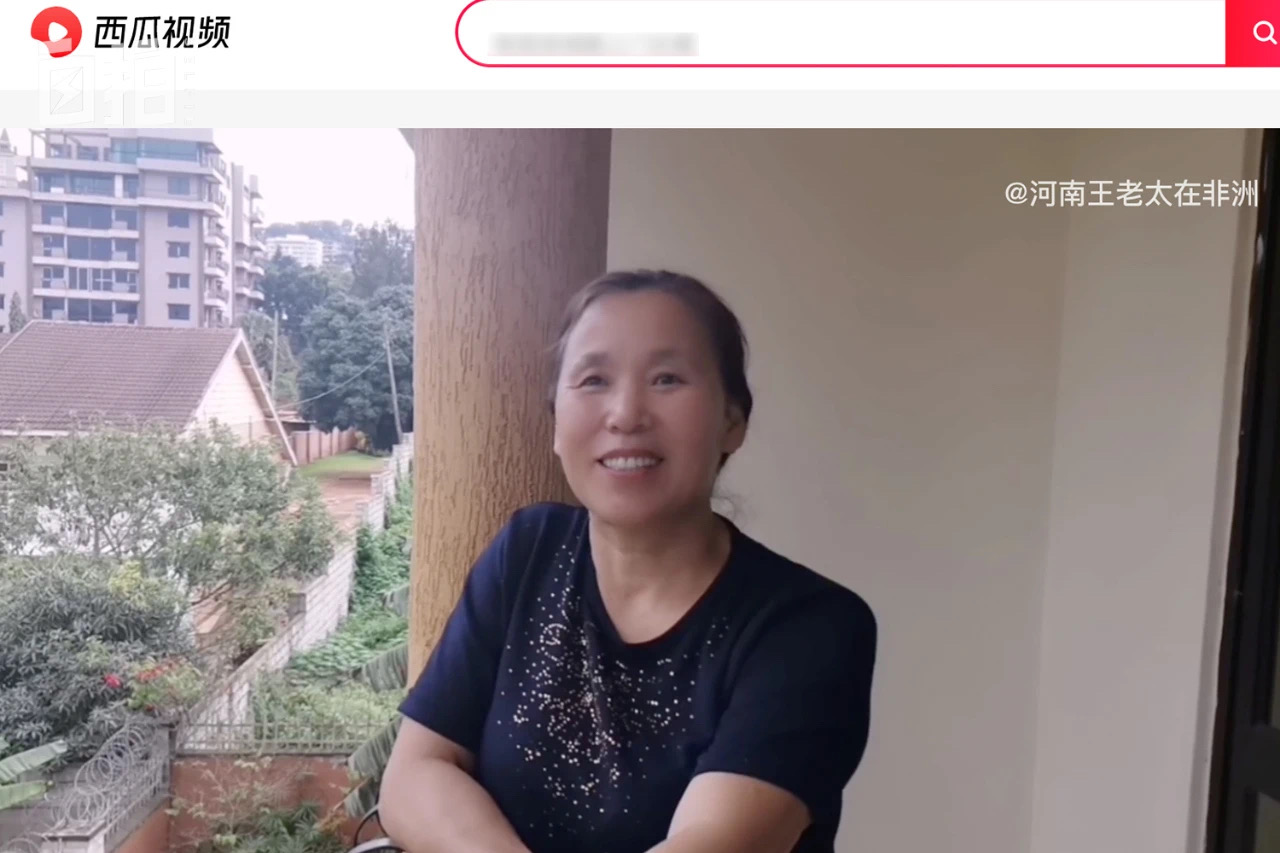
去年10月底开始拍视频,我妈从没直面镜头说过话,一开始很羞涩。
我只是拍着摸索着玩,没想过靠这个挣钱,后来流量收益一到账,我妈成就感就上来了,越拍越兴奋,每天都跟我研究拍什么话题,哄孩子一睡着就抱着手机回复网友评论。
一开始,有极个别人会说一些不好听的话,比如说不喜欢黑娃娃,嫁到非洲有罪,总之就是拿肤色说事。我记得有一条评论说的是说“如果我生了个女儿嫁到非洲,就当没有。”
我觉得这样的人真是有点不可理喻,实际上还是以自己为中心,不去考虑孩子过得到底幸不幸福。对这种不好的评论,我妈有时候会回复解释一下,有时候也怼回去。
大多数网友还是友善的,很多人留言说我们的视频改变了他对非洲和非洲人的认知,夸我妈的这个非洲女婿温文尔雅、憨厚老实,一大家子很让人羡慕。

被网友夸赞的娃他爸,抱着小女儿,大女儿喜欢骑在他头上。
看着那些评论,我有时候想想也觉得自己挺幸运的。以前我对婚姻的所有期许,现在基本都已满足——老公对家庭负责,对事业上心,挣的钱全交,把我和孩子放在第一位,遇事能第一时间护着我们,有什么好的能第一时间想着我们,我还能奢求什么呢?
当然,非洲并不是所有男人都像查尔斯这样,中国也一样。所以我不会鼓励其他人重复我的选择,但也不会刻意卖惨,非要去证明我的婚姻是场错误,因为事实并非如此。

我和俩孩子的自拍,小的刚生下来很白,现在肤色也和姐姐差不多了。
聊这么多,我并不是想说自己嫁得好或者有多成功,我只是个选择了跨国婚姻的普通人。介绍完自己的经历,我其实还想告诉更多父母:如果想让孩子幸福,那就请先做好榜样,想想你们对孩子留下了什么印象,有什么样的引导或影响。
有些年轻人不婚或丁克,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看到了太多家庭矛盾,就像我恐惧婆媳关系,更倾向于和外国人结婚一样。
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原因,生活中很多东西远比表面要深刻,要难很多。我的跨国爱情也并不浪漫,无非是在抉择和平衡之后,作出了能让生活变得更好的选择。
现在,我的家人都在乌干达,我完全没有背井离乡的感觉了,想趁年轻再好好扑腾扑腾,在非洲这片土地上好好发展。等疫情结束,我会每年回国一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