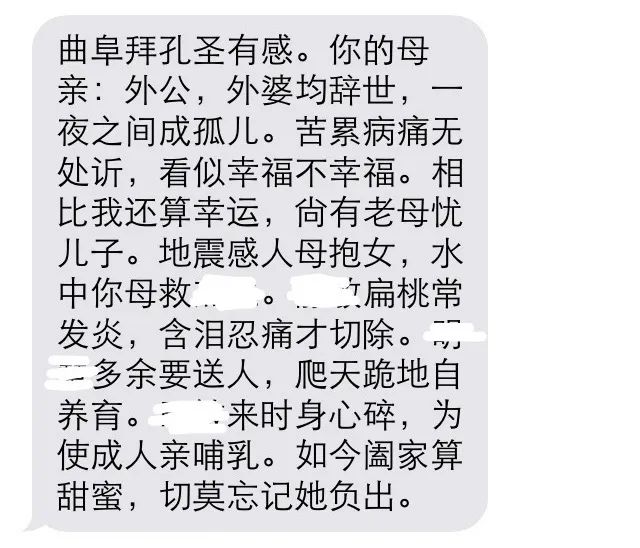她的叛逆期来得太晚,一直到更年期降临,她才从各种细节里觉察到,生活的欺骗。
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的第652个故事
2019年5月某一天的晚上8点,我接到爸爸从老家打来的电话,他问:“你妈和你联系没有?她电话一直关机。”
长时间联系不上妈妈,几乎是没有的事。她身边除了两三个至亲外,没有特别交心的朋友,更别提个人爱好。
她能去哪里呢?我们兄弟姐妹四个轮番轰炸妈妈的手机未果后,弟弟甚至问了公安局的朋友是否有接到报案,
同在老家的三姨也发动了家里人出去找。
几个小时后,我们终于等到了妈妈的电话,她的解释是:“泡澡去了。”待焦灼的心绪平复,我又回拨电话。
她这才告诉我,她是故意关机的,就想看看爸爸会不会为她着急,但没想到闹得这么大。
两个月后,妈妈第二次离家出走,吸取上次教训后,她没再关机。我姐找到妈妈的时候,她正一个人蹲坐在台阶上,身旁是一个同她一般高的买菜用的拉篮。姐姐立在远处拍了照片,发到家庭群里。清晨萧索,妈妈缩在照片上端,又瘦又小,看着有些可怜。
她并不是一位任性的母亲。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她倾力饰演“家庭补丁”一角,买房需砍价、装修得盯着,谁有需要她都能立刻顶上。或许,她曾相信过自己就该是一块“补丁”的模样。
在这两次动静较大的出走之前,妈妈已经默默地吃了三年的抗焦虑药。在那段与他们同住的日子里,她会间歇性的发脾气,毫无顾忌地表达对爸爸的不满。姐姐作为主治医生,百般嘱咐我要照顾她的情绪。但那时我年轻气盛,故而选择站在爸爸的立场上,试图用言语扭转妈妈的情绪。抗辩的结果是母女关系变得空前紧张,她甚至一度怀疑是新搬进的这座房子风水不好。
妈妈没有沾到一点儿外公的富贵气。自她出生,贫穷与成分问题便成了高悬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爸爸是自1978年恢复高考后,走出乡村的第一个大学生。聊起为什么嫁给嘴笨口拙的爸爸时,她回答:“当时觉得他有学历也有个子,其他的后面可以慢慢培养。”
可她没想到爸爸身上的诸多毛病,她倾尽半生也未能将其纠正。
生育孩子的那些年,日子陷入混乱与无序之中。好在爸爸一直是个自律且乐观的人,为了养活家庭,他拼命学习进修,连除夕夜也未曾缺勤医院。成年后的某一天,我看到爸爸中午在家边休息边输液,我在他身边坐下,想了一想,说:“我已经连续两个小时看到你了,有点意外。”
在男主外的家庭模式下,家中的琐碎便全然落在了妈妈身上。她走路带风,说话钢刀利水,没用的闲聊与闲逛于她而言,就是奢侈。她注重细节,有时严苛到看不起那些烧伤的孩子的家长,认为“我就转身去放个东西,谁知道......”这类都是无用的废话。我们兄弟姐妹四个的身上都没有留下疤痕,这在多子家庭中简直是个奇迹。
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姐姐在回家途中被胡同里停放的货车撞碎了半截门牙,她满嘴含血地跑回家。被吓坏的妈妈立即穿上鞋出门找停放货车的那家人理论,面对对方的拒不承认,她丢掉知识分子的脸面破口大骂。那家人在一周内搬离了社区。
县城不大,整个医疗行业几乎所有人都认识我的爸妈。长辈们总说:“你爸妈太不容易了,长大要好好孝敬。”我曾天真地以为所有的妈妈都是这样勤劳能干,“超人”是母性的同义词,直到我目睹她的脆弱、任性,还有消沉。
我爸妈已经结婚30多年了,有记忆以来我从未见到他们吵架。以前,他们没有时间吵架,后来我发现是爸爸根本不会吵架。
03
在辛苦奋斗的这些年,爸爸除了白发和皱纹变多外,仍沉迷于钻研医术。于他而言,家庭生活像是一束火焰,很暖很亮,但不能凑得太近。
妈妈却渐渐松了下来。“好好过你们的二十岁,想吃什么就赶紧去吃,你看我以前多傻啊,连一串葡萄也舍不得吃,现在能吃了又怕血糖高。”她意识到人终有一死,年轻时因生活所迫而放下的精神诉求,犹如老牛反刍,一阵阵刺激着她。
原来辛苦工作是迫不得已,那如今又为了什么?她无法理解。
2018年我爸正式退休,妈妈以为日子终于要正常起来。她相信只要闲下来,爸爸就会变成一个有耐心、懂生活的老伴儿。这个期望,随着我爸单方面接受省城工作而宣告结束。
她就是在那段时间感受到绝望,开始吃起抗焦虑的药。她不明白为什么爸爸从不心疼她,冷战了这么多次,为什么从来不肯改一改?在最无奈的时候,我说:“你离婚算了,去找个疼你的。”她只觉得我不愿听她诉苦。
直到有一天,她真的提出离婚。在离婚信上,她细数了30年来随爸爸一起生活的苦,指责他对她的付出不闻不问。他自己是块石头,就以为身边人同他一样不需要关爱与肯定。
我问她导火索是什么?她回答:“昨晚你大姨坐我们的车回城里,我说头疼,你大姨立刻让我住院检查,但你爸愣是一言不发。”我说:“那你自己住院检查去啊!”她反驳道:“我就是想听他说一句‘你身体重要,快去住院检查’,可他就是不说话。”我妈把爸爸的沉默理解为对住院这件事不满,回家后越想越气,纠结一番后决定和爸爸理论,而身侧已传来呼噜声。
我听完她的复述,便知她不是想离婚。她只是想激一激爸爸,执拗地想看看究竟要到什么程度,他才愿意回过头关注一下他的妻子。
我就着这事问了爸爸,他说:“我也不知道这些年辛辛苦苦到底是为了什么。”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他神情颓丧。
妈妈曾试图改造父亲,想拉他一起跳舞锻炼身体,一起外出旅游,抛开饮食顾忌吃顿大餐。可惜她的丈夫不是一个配合的人,常常无视她的请求。我不止一次听到她说:“我已经放弃你爸了,我要保全自己,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她说这话时,爸爸就坐在旁边埋头研究膏药。
我在妈妈对爸爸大段的数落中逐渐明白了他们之间的分歧,比如我爸对病人有求必应,甚至呼之即来,而我妈则认为他应该具备知识分子的清高。我爸为达目的听得了领导的冷言冷语,受得了同事的刻薄尖酸,而我妈则觉得人应该有底线,这时候就应该掀桌子来展现男子气概。这些差异大概也来源于成长环境的不同。物质的极度匮乏让我爸早早意识到金钱的力量,而一直受困于成分问题的我妈,从小就近乎偏执地注重气节和名声。
坦白说,观念的分歧在长久的相处中不算什么。她真正在意的是爸爸从未提供作为丈夫的关心。她总是想起十年前自己突然生病晕倒的场景。当时午睡起来,她头晕得厉害,坚持着到了单位后便开始呕吐。爸爸出了医嘱后就匆匆赶去省城出诊。妈妈随后查出小脑梗塞,如果当时过去了,可就真的过去了。
这么多年来,每次想到只觉心寒——作为妻子,她竟不如一个病人重要。
她后来还漫不经心地和我说过一件非常小的事。有一天早上醒来,她发现被子都被爸爸卷走了,但她记得多年前弟弟还小时,我爸会把被子盖在弟弟身上。她说这话时,有些不好意思,怕我嫌她小题大做。
我却是从这个细节中真正共情到了她的痛苦。她想说:你看,他怎么会是个榆木疙瘩呢?他分明懂得什么是本能之爱,他分明是有意将我排在了价值序列的末端。
05
2020年1月,我和先生带着各自的爸妈游玩美国的东西海岸。我以为外出散心能让妈妈开心一些,而目睹另一对同龄夫妇的亲密,却让妈妈更加感慨。她对来自丈夫的关怀与肯定的渴求从未消失。
矛盾爆发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座商场,起因是她想买一瓶保健品而我爸不耐烦地说:“这些都没用。”她突然大怒,眼神像舞台上的追光灯般,紧紧地盯着游走在身旁的爸爸。她一边无助地落泪,一边说着世上最狠的话。

我拉住爸爸,在他手里放了四瓶一样的保健品,要求他亲手放进妈妈的购物篮里,又教他怎样跟妈妈道歉。他还是犹豫了一会儿,嘴里嘟嘟囔囔地,然后把保健品一个个放进妈妈的篮子里。很快,妈妈的情绪平稳了下来。
那一刻我想起很早之前,爸爸在外游玩有感而发写的一首诗,大意是说妈妈这些年生活很辛苦,让我们好好待她。这首诗无论文采还是韵律都远不如他写的其他,但妈妈竟然感动得偷偷哭了出来。她要的实在是太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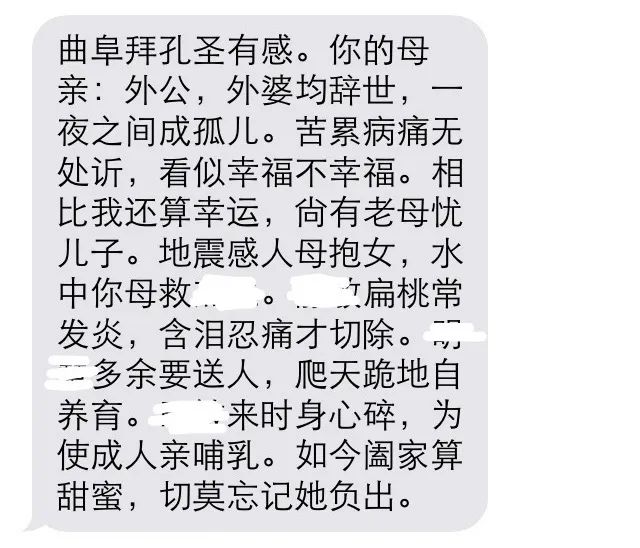
一周后他们回国,开始了居家隔离。那一个月里,妈妈终于过上了她一直想要的规律安稳、踏实平静的生活。他们大概从未如此长久地日日夜夜在一起过,这令她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
前段时间和妈妈通话,她说起爸爸现在每天早上会给她端一杯水,饭后削一个苹果给她。她在这些细节中极为努力地寻找自己想要的关爱,我笑她是在石头里找糖。尽管有时他们还是会闹别扭,但我猜她已经从内心里放过了自己。
- END -
编辑 | 金思雨
----------------------------------------------------------------------------------------------------------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极昼工作室 Author 小昼
这个世界上似乎只有猫还在乎她。最先发现异样的就是斯芬克斯,在客厅“喵呜呜”地叫。

|本文由【极昼工作室】授权转载,微信公众号:media-fox,作者 | 蔡家欣,编辑 | 王珊
红棕色的防盗门背后是一间50平米的小屋。一室一厅,老式的黄色原木家具,典型的上世纪九十年代装修风格。卫生间很小,厨房杂乱,猫爬架,猫砂盆,猫垫子,填满了客厅。一个瘦瘦的女生经常坐在角落的餐桌吃饭,一只斯芬克斯无毛猫牢牢占据另一张凳子。
这是26岁的杨琳在北京的第一个住处,距离单位不到两公里。一人一猫,在这个略显凌乱的小空间里,她享受着独居的自在和舒适。唯一的缺点是隔音不好,经常从远处传来关门的巨响,深夜楼上冲马桶的声音也听得一清二楚。
按照防疫要求,今年,杨琳留在北京过年。对她来说,除夕那天,没有特别之处,甚至工作都没停下。下班后,潦草地和朋友吃完一顿火锅,她急匆匆地往家赶。旧历年的最后一天,她想一个人待着,与远方的朋友、家人视频聊天。
电视节目自顾自播着,斯芬克斯惬意地缩在脚边。嗑着薯片,她在电话里告诉妈妈,隔天要去寺庙上香。挂断电话已经是凌晨约1点钟,杨琳拎起衣物,走进浴室,关上门。
在那个不到两平米的小空间里,她度过了人生中最漫长的30个小时。
洗完澡,杨琳用手转动那颗老式的球形门锁,球是转动了,门纹丝不动。她又找出刮眉刀,沿着门的缝隙刮擦锁舌,还是没有反应。
不到两平米的卫生间,木门上的百叶孔是唯一的通风口,室内热气氤氲,令人窒息。杨琳有点着急。她拆下花洒,用力砸门。嵌在中央的玻璃碎了,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洞,杨琳伸出细长的胳膊,用力拧动插在另一侧锁孔上的钥匙,钥匙只动了一点,门依然没什么反应。
手机放在卧室,没法与外界联系。她试图呼唤苹果手机智能系统siri,距离太远,没有反应。接着,她又想到了卧室里的智能音箱天猫精灵。她朝着外面大喊“天猫精灵,报警”,但音箱没有这个功能。它只会傻乎乎地报时:现在是凌晨3点钟。一字一顿,声音还是那么俏皮。
那是她第一次知道时间。距离她被困至少过去了一个多小时。
杨琳所在的这个小区位于北京核心商圈东三环,有14栋楼,2500多户人家。这是1990年代那种典型的塔楼,住户大多是老年人。楼道迂回环绕。每层以电梯间为居中点,南北两侧各有一个主楼道,顺着主楼道,又衍生出楼道。杨琳推测,每层至少有10户人家。
杨琳住在15层,南侧楼道的最里边,两户邻居,一户正在装修,一户是80来岁的老夫妻。作为一个外来租户,杨琳素日跟邻居来往少。交集最多的是隔壁的老太太,出门碰着会互相打个招呼。
已是深夜,屋内屋外都静悄悄的。杨琳有点疲惫,饿意隐约传来。她决定睡觉保存体力,通过语音设置,给智能音箱上好7点的闹钟,“那个时候,很多人起床买菜、运动”,她就可以求救了。坐在马桶盖上,靠着暖气片,杨琳睡着了。
大年初一早上7点,她被智能音箱喊醒,开始呼救。卫生间离入户门不远,果然有人循声围过来。杨琳焦急地说明情况。一个中年女人警惕的声音响起来,“一个人洗澡为什么锁门?”还有一个声音说,“洗澡为什么不带手机?”反复回答几遍。杨琳越来越着急,音量随之升高。门外的人问:“你说你被困,怎么声音还这么大?”
根据隐约听到的声音,杨琳判断,至少有两人围在门口。她连连哀求对方,“求你们帮忙报个警”。没人理会她的请求。不知过去多久,门外安静下来。杨琳急了,声嘶力竭地喊:“有人吗?有人吗?”
那一刻,泪在眼眶里打转,还没流下来,就被抹掉了。杨琳喝了两口自来水润嗓子,又用冷水拍拍脸。
冷静下来后,她又想起了快递。杨琳平日很宅,生活用品都是网购,房门口总是堆满各种纸盒子。她问天猫精灵,最新的快递什么时候送达?答案是今天(初一)下午。她把希望寄托在快递小哥身上。
那个下午,她伸长耳朵听电梯声。金属的摩擦声传来,电梯门开了,她扯着嗓子大喊“救命”。无人回应。电梯门开开关关了好几次,呼救都失败了。最后,连电梯也安静下来了。
她决定制造点噪音。毕竟人都是利己的,“只有他们的生活被打扰,才会意识到要上来看看。”
杨琳是四川人,2008年汶川地震以后,每个周五的自然课,她作为班长,都会上台给同学念相关知识。现在,这些防震减灾的知识都用上了。她调高天猫精灵的音量,让它每小时提醒一次:主人,要喊救命啦。时间一到,挥动花洒,用力锤击水管,先喊“救命”,再简要说情况。
卫生间的水管,房东没有做隔音层,敲击的“嗡嗡”声一阵一阵回荡,震得耳朵一阵阵发麻,她想用纸巾塞住,又怕来人听不到。有时感觉过去一小时了,询问天猫精灵,才知道不过10分钟。
不知道过了多久,一股饭香飘进来,“不知道是不是饥饿的错觉”。可能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吧,她尽量屏蔽这些干扰,继续敲击水管,那时她只有一个念头,“想出去”。
在那个逼仄的空间待得久了,杨琳胸口发闷,开始心慌。那晚洗完澡后,头发也没法吹,靠卫生间里的暖气烘干,现在头皮又油又燥。因为穿得少,到了夜里又四肢冰冷。
这个世界上似乎只有猫还在乎她。最先发现异样的就是斯芬克斯,在客厅“喵呜呜”地叫,躁动不安。似乎感知到杨琳的困境,它不断地用身子撞门,爪子“吡吡”地抓卫生间的木门。杨琳蹲在门后面,温柔地喊着斯芬克斯的名字,又从门底下的缝隙伸出手指,想安慰它。斯芬克斯舔了舔她的手指,安静下来。
隔着卫生间的门,一人一猫,就这样坐着。到后来,家里的自动喂食器,每次哗啦一声,倒出猫粮,猫都无动于衷,只守着她。喂食器储存的猫粮能吃15天,“猫咪也许会活得比我久”。想到这里,她有些绝望,如果初七上班旷工,单位才发现她失踪,那时的她“可能已经死了”。
大年初二早上约七点钟,住在14层的林健被“嗡嗡”声吵醒了。
林健的第一反应是气愤,“哪有人一大早在敲管子”。他隐约听到有个女声从楼上传来,“救命”,声音听着有点遥远。林健趴在墙上,听到一个女孩正在讲述自己的情况:15xx住户,除夕晚上洗澡,被关在浴室出不去。
“是不是恶作剧,或者家暴?”他感觉现实生活不太可能遇到这种情况。
30岁的林健,来北京打拼6年,买下了这个50平米的房子。他从事互联网相关工作,每天早上10点上班,晚上7点下班。一个人在家,啃个苹果,看电视,打游戏,有时逗弄那条棕色的小狗约克夏,一天很快就过去了。他不是一个特别需要陪伴的人,“一个人也还过得蛮好的”。
今年春节,林健也没有回老家。除夕下午,提前和家人发过年祝福,晚上吃过外卖,打了会游戏,《难忘今宵》一唱完,零点的钟声过了,他就躺上床。但那一夜,林健睡得并不安稳。事后回想,可能是隐约听到噪声。
在这里住了三年,和邻居的关系不咸不淡。出门时,会寒暄一句“上班啦”,纸盒子留给邻居收,他们偶尔帮忙接个快递。“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事,现在的人,都不太关心别人家的情况。”他说。
水管里传来的呼救声一直没有停止,持续了20来分钟。林健又细细听了一下,女生正在让智能音箱报警,机器人自顾自地说话,不理会请求,他感觉,“可能真的有问题”。
林健决定上楼看看。他在15层的楼道里绕了好几圈,才在楼道的最尽头,找到杨琳的房门。
门外的这个声音听起来有点冷漠,杨琳既激动,又有一丝担忧,不会像上次那些阿姨一样吧。为了证明真实性,杨琳迫切地跟对方说自己的被困经过。
杨琳请求帮忙报警,林健爽快地答应了。警察建议找开锁师,提供了几个认证过的开锁公司电话。因为是假期,林健连续打了三四个电话,才找到人。
担心林健失去耐心,杨琳想让他进门等待。虽然有点担心,但她还是直接告诉这个陌生人房门密码。她太害怕对方再次一走了之。
林健回忆,进到房子里面,杨琳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现在是什么时候了?”那时,距离她被困已经接近28个小时。
林健坐在拥挤的客厅。楼上楼下,彼此没见过的两个年轻人,隔着一堵门闲聊。在全国9200万独居的人中,因为一次意外,他们有了一次短暂的交集。杨琳怕他走掉,主动开启话题,讲自己工作和北漂经历,“想赢得他的信任”。林健问起斯芬克斯的体重。杨琳趁势拜托他,把卫生间门口的玻璃碎片清到垃圾桶,担心误伤了它。中间,林健又给开锁师傅打了4个电话,询问是否快到了。
杨琳终于放心,自己快要获救了,“到这一步,他不可能不管我了”。
开锁匠王师傅很快到了,不到10分钟,就打开了卫生间的门。担心女孩不方便,王师傅和林健退出房门外。
对王师傅来说,大多数锁都能在10分钟内搞定,难度大的,不超过半小时。但对普通人来说,一旦锁舌卡在门框,门基本打不开。杨琳的门朝里开,与墙的距离很窄,中间还放着一台洗衣机,更不可能踹开。
做这行不到一年,在北京,王师傅见惯了这样的情况。一个女孩,被锁在厨房,自己拆了三四个小时才打电话求救;一个80来岁的老人,被锁在卫生间,6个小时后,家人下班才发现;除夕当天,一个30多岁的独居女性,出门贴春联,就被锁在了门外;还有的年轻人,出门后发现没带钥匙,提前跟他预约下班时间开锁。杨琳的事没过多久,东三里屯又有一个女孩被锁在卫生间。每天王师傅都要接到十来个单子。他说,“一个人住,这种情况更没办法避免”。
杨琳最惨,被困30个小时。不过,王师傅记得,从卫生间出来后,杨琳的状态还算不错,声音很响亮。他对那只穿灰色衣服的猫印象深刻。拆锁时,它一动不动地蜷在桌子底下,警惕地看着四周。
锁拆完了,白色的门上留下一个黑洞。想到杨琳已经30个小时没吃没喝,王师傅想买份饺子给她。他在楼下转了一圈也没找到饺子店,最后提了袋面包和牛奶送上去。
王师傅和林健都走了,房间里又只有她和斯芬克斯。杨琳坐在餐桌前,弓着背,眼神涣散。嘴里咬着牛奶吸管,手上捧着草莓味的面包,眼泪开始无声掉落。过去三十个小时,孤独,冷漠,绝望,死亡,温情的滋味,她都尝过。
她以为会有很多人惦记自己。从浴室出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奔向手机,“应该会有很多消息”。点进微信,满屏都是小红点,但除了或许是群发的拜年信息和订阅的公众号文章,还有一条丰巢的消息,她找不到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消息。
她感到失落。在这个技术追求5G、万物互通互联,社交讲究距离感和边界感的时代,人与人的联结这么脆弱。“我们已经身在非常原子化的社会,而且习惯这种方式,朋友发消息两天没回,都不觉得奇怪”。
没有心思吃午饭,大年初二下午,杨琳点了一杯奶茶,身体像“大”字一样,瘫在床上,任眼泪流淌。
晚些时候,她收到微信,朋友约她去看《唐人街探案3》。妈妈也打来电话问,初一去寺庙玩得怎么样?那个瞬间,杨琳才感觉,自己终于回到现实世界了。杨琳没有提自己被困的事,她讲不动了,也觉得没有讲的必要。那场电影看得支离破碎,周围掀起一阵又一阵的笑声。她有点恍惚。回想那30个小时,感觉自己跟这个世界既近又远。
为了表示感谢,杨琳后来请林健吃了一顿饭。林健送给她一副对讲机。他们聊起韩国电视剧《甜蜜家园》,一群独居的人,遇到丧尸来袭,要如何应对?林健调侃说,万一哪天来了丧尸,我们就可以用对讲机呼救了。
日子又回归到以前的波澜不惊。现在,“门”变成她最大的阴影。去卫生间会特别谨慎,不敢关门。电梯门一合上,她的眼睛紧盯着跳动的楼层数字,生怕再次被关。
她在朋友圈记录下这段经历,想提醒周围人注意防范。七八年没怎么联系的高中同桌,打电话过来询问;有一回她手机没电关机,联系不上,同事到处找人寻问;阿里巴巴的商业团队也联系她,表示要给智能音箱增加报警功能。
正式上班第二天的中午。朋友发来消息,她上热搜了。有人将她的朋友圈内容传播出去。那天下班,在拥挤的电梯里,她大喊“十五楼”。电梯里的其他人,眼睛齐刷刷地朝她射来。“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他们都知道了。”
杨琳忍不住猜测,也许那30个小时里,她呼救的声音,已经传遍整栋楼,但是没人伸出援手。不过,她能理解。人对陌生的求助经常会抱有很大的不信任。当然,也可能是网上的消息传开,记者一茬一茬上门询问,才引起邻居的注意。
她无法理解的是,有网友质问她,“独居锁什么浴室门”“为什么不踹门”“洗澡为什么不带手机”。还有评论称杨琳在炒作。甚至有人问她:“为什么不找男朋友”“为什么一个人住”?
她很无奈,一个独居的女孩,到底还要承受多大的恶意。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独居也成为媒体讨论的热点。很多人分享自己独居被困的经历,也有人在房间里晕倒又醒来,整个过程没人发现。杨琳不是没考虑过独居的风险。比如,突然生病要怎么办?但念头只是一闪而过。确实也做过防范,为了安全,她在家里安装了两个摄像头。但生活总会有让人措手不及的瞬间。
幸好还有母亲安慰她,“不要因为这个事,盲目去找一个男朋友。就算以后不结婚,也没事。”
2月26日深夜,杨琳收到一个不明快递。纸条上写,“我在看着你”。她拉上窗帘,冷静地拍照、报警。
她已经决定搬离这个地方。以前图清净,现在她希望房子离电梯近点,不靠近角落。再遇到危险,至少求救的声容易被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