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姆吴阿姨的北京见闻

保姆回家过年了,我心空落落的,感觉像失恋了,偶尔扫一眼空荡荡的房子会莫名其妙觉得难受。
她才来两个月,对我也不太好。早上蒸包子,一个肉包,一个菜包,她会吃了肉包,把菜包留给我。
呼唤她抱走孩子,也老装听不见。可她走那天下午,孩子睡醒四处找她,咿咿呀呀叫了声“姨”,
我却有些泪目了。
还是第一次和一个陌生人朝夕相处了两个月。某种程度上,她算得上我的救星。
她来了以后,婆媳关系这道世纪难题,我终于可以弃考了。阿姨姓吴,是四川人。
北京找保姆,按照菜系来分。
山西阿姨、河南阿姨、东北阿姨、安徽阿姨,还有就是四川和重庆、湖南这些做辣菜的阿姨。
喜欢什么口味,就找哪的阿姨。比起北方的省份,南方阿姨更受欢迎,价格也更高。
吴阿姨在保姆界也算是形象气质十分出众了,45岁的人了,皮肤依然白皙、身段丰盈,只是头顶有些掉头发。来北京二十年了,她穿梭于各种阶层的家庭,像是折叠北京里的主角,偷窥着这座城市的秘密。
我最喜欢听她讲有钱人家怎么过日子,这也是她最为津津乐道的话题。
说来也奇怪,吴阿姨服务过的高端家庭,许多人都没有工作或者说不需要工作,是真正的北京闲人。
据她观察,绝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是躺着。
有一家太太,每天中午十二点才起床,吃了饭又睡到下午五点,晚上洗澡护肤,十点又睡了。
吴阿姨一直很好奇,“睡了那么久,背不疼吗?”据说,这位太太身体倒是没问题,只是不太爱动,
请了四个保姆,连水都是保姆倒的,水果要切成小块用牙签叉着吃。
后来老公贪污进去了,太太不得不从豪宅里搬了出来,住进了一间两居室,留下了一个最便宜的阿姨。
她老公不是政府官员,而是一家头部互联网公司的高管。根据阿姨给的名字,才发现原来是个新闻人物。
外界都在猜测这人明明年薪几百万,前途无量,为啥要贪污呢?
她刚去那家的时候,拨了一些菜出来,打算端进房间吃。
在这种家庭,阿姨的职业习惯就是在保姆房吃饭,不和主人家同桌。
那位高管突然从她身后探出了半个脑袋,“吴阿姨,你在干吗?”她吓了一哆嗦。
他重申了这家的规矩,“一般是我和宝妈先吃,你放心,我们两个人也是用公筷,没有口水的”。
这家还有个规矩,保姆不允许用热水,说是“热水洗碗会有水印子”。最让她接受不了的是不许她用卫生纸。
看到她用卫生纸包浴室地上的头发,就从垃圾桶里捡了一根棉签对她说,
“你以后就像这样,卷卷卷,把头发卷起来”。她说实在恶心,就自己买了包纸。
还有一对小夫妻,家里生了两个孩子,也不用上班。
他们家是价值两千多万的豪宅,连保姆房间里的灯,都是价值十几万的水晶灯。
住家保姆市场价是每月7000元,可是他们家就给6500元。
后来才知道孩子爷爷奶奶给的保姆费,小两口私自截留了一部分。吴阿姨很看不上他们,“就是个寄生虫”。
可和我聊起他家那辆小车,又透露出一种与有荣焉的意味,
“做阿姨那么久了,没见到过谁家的车钥匙有一斤重,他那个车说是要1100万”。
有时候路过一些高档社区,这里有哪些户型,采光如何,绿地怎么样,她都如数家珍。
魔幻的是,对于城中村也是如此。哪些楼盘过去就是城中村,哪个城中村里的房子便宜,她也都门清。
她过去住在费家村,是北京北五环外的一个城中村,住着几万名像她这样的劳工。房租已经涨了三轮。
2017年,大兴“11·18”火灾,房租翻了一番,500元变1000元。2019年,清理外地包租公,又涨了一轮。
最近又涨了一些,一间房也要1500元。
北京公布的流调中,连续工作17个小时的网约车司机、一天打三份工的夫妻,成了北京劳工的辛酸缩影。
这群人都住在顺义,比费家村还要往北。顺义是距离北边主城区最近的郊区,房租大约一千元左右,
还通了地铁,是劳工们最佳的落脚地。
吴阿姨最近也搬了过来,房租只要500元。坐车来我家要一个多小时,索性住到了我家,周末再回去。
除了给我带孩子,中午还得去一个老主顾家做饭。
这家人是老北京,拆了六套房子,靠租金过着优渥的生活,也是全职在家带娃。
吴阿姨绝对是劳工中的金领,出入都是高档社区,月收入上万,工作轻松还受人尊敬。
北京流调中的网约车司机、快递员,是劳工中的白领。
修理工、泥瓦工、洗碗工这些,拥有单个技能的劳工是工薪阶层。
上了年纪的老人们才是底层中的底层,他们只能找到捡垃圾和看大门这种工作。
我在小区常常看见上了年纪的老头、老太太穿着绿色或者橘色的背心,身上印着垃圾分类员的字样。
他们站在垃圾桶前面,徒手从垃圾箱里掏出垃圾袋,一个个撕破后,
恶臭的厨余垃圾就哗啦啦地倒进了厨余垃圾桶。
劳工的等级线,几乎与年龄平行。吴阿姨才45岁,已经有了危机感。过了50岁,工资就难突破6000元。
55岁往后,只能去收垃圾了。吴阿姨计划再干七八年,存些养老本。
她儿子已经结婚,在市区买了套上百万的房子,他们老两口拿出了90万首付,今年还计划把剩下贷款也还了。
这就算给了儿子一个交代,未来赚的钱留着自己养老。
前几天,吴阿姨老公的喉咙查出个息肉。听到别人说,可能是个癌,吓得打碎了两个玻璃杯。
她丈夫也在北京,是个泥瓦工,专门给豪宅安装大理石外墙。
她去过那些豪宅,“不是别墅,比别墅还要高级,叫公馆”,面积有几千平米,
走在里面让人有些害怕,“太大了,阴森森得像个庙”。
每天六点半,吴阿姨准点起床,夜里十二点才睡。
她自己从不花钱,连银行卡都没有,每个月工资直接打到儿子账户。
打底毛衣穿了十几年,密密麻麻起得都是球。每天夜里,我都能听到她在和家人打电话,一直聊到深夜。
过去还在心里埋怨,有些太吵了,如今总感觉家里有些过分安静了。
--------------------------------------------------------------------------------------------------
每一天,我在北京都想着如何多赚些钱|谷雨影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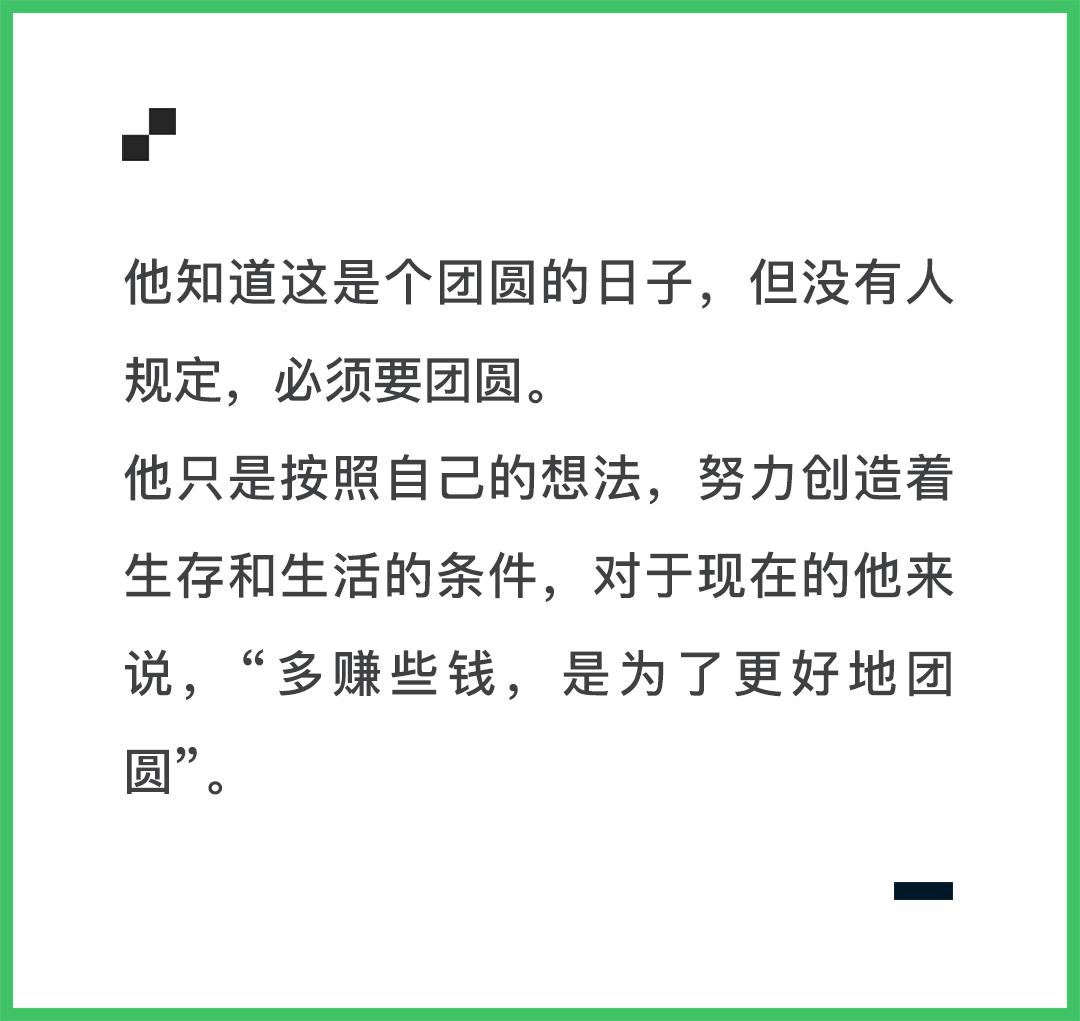
摄影&撰文|龙摄团 Fago
编辑|迦沐梓 周安
出品|腾讯新闻谷雨工作室
春节,回乡,团圆,千百年来始终是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情愫。所以,当因为疫情不得不“原地过年”时,很多人会把这看作一种无奈或者无私。
但其实,也有人并未想那么多——比如20岁的四川青年小春,数以百万计的北漂中普通的一员。他说,春节回家也没什么事可做,不如留在北京,多赚些钱。
01

除夕,小春在出租屋里准备午饭
尽管决定不回家过年,但小春的除夕,还是和平常的日子不太一样。这一天中午,他和朋友约好,在自己的租住地吃一顿老家四川的火锅。
参加聚会的人有4个:小春和表婶,同为外卖小哥的晓峰和光头强哥。
几个人说好,以吃为主,尽量少喝酒。小春还惦记着,下午能够多接几个外卖单。

“春节这几天,一单能挣12块。”小春边说,边用手机登录外卖平台。然而,毕竟是除夕,几乎没人点外卖。

小春住在丰台城中村,邻居都是北漂打工者
这是小春来北京的第三年,也是他连续在北京过的第二个春节。能和几个朋友在一起过年,他觉得很满足。“刚来北京的时候很孤独,这么大的城市,一个朋友都没有。”
在北京的每一天,小春都在想着如何多赚些钱。本是该享受青春、享受恋爱的年纪,小春无暇顾及这些。

春节假期,小春在物业公司上班
2021年的春节,小春是这样计划的:初一,物业公司白班,晚上送外卖;初二,白班夜班连轴上,24小时;初三,白天送外卖,晚上上夜班;初四休息一天,初五开始第二个循环。
小春算了算,3倍工资加上外卖赚的钱,这个春节收入还是不错的。

小春(右)和强哥(左)
按照约定,除夕晚上他们“转战”孙强在五环外金盏乡的家,参加一次更大规模的聚餐。这一餐,孙强邀请了更多同是从事外卖行业的外乡人。

北京很多城中村成为打工者租住的地点,外卖骑手尤其多。强哥租住在北京东北边金盏乡东窑村,每个月房租1000元
大家有不同的口音,也有不同的乡愁。“大家也不是忙到顾不上回家,很多是担心因为疫情,春节之后回不了北京。”孙强说。
回不了北京,意味着收入暂停,甚至重新开始。他们把和家人视频通话当做团圆,在很多人看来,“多赚些钱,是为了更好地团圆”。
02

除夕的晚上,大家喝了不少酒。临近午夜,到了最期待的放炮环节。“五环内不允许放炮,这是五环外,没事儿!”孙强说。
鞭炮是小春和晓峰在前一天,骑车来回60公里去通州买的。本来,他们计划买些烟花,约两个女骑手一起去放,“但没买到烟花,她们就懒得出来了。”小春说。

伴随着炮竹声和酒意,北京的五环外,小春这些外乡人不是没有思考过自己的未来,但他却想不出清晰的模样。正如他喜欢车水马龙的北京,他却不确定,自己的未来该如何归于此地。

年初二,小春在物业公司上白班
2018年春天,小春从高中辍学,跟着表哥跳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他的家乡在四川达州。离开老家时,小春父亲已经身患重病,几乎丧失劳动能力,母亲照顾着还在上小学的弟弟。父母靠种地勉强有些收入,一年不过5000元。
初到北京,小春和表哥租住在丰台区的城中村,不到5平米的屋子,厨房公用,一个月600元房租。继而,通过表哥的关系,小春获得了一份在王府井高档商场物业公司的工作。

小春没有什么技能。别人修空调、修管道,他就打下手,谦虚好学、嘴也甜,很快就和那些50多岁的同事打成一片。上半个月,休半个月,月薪5300元,这让他觉得很满足。“这一个月的工资,顶得上在家种一年地了。”

工作之余,小春也不愿闲着,就琢磨着去送外卖。他曾经尝试过满负荷的模式:白天上班,下班后送外卖,晚上跟表哥干装修活,凌晨回公司睡觉。铆足了劲,小春一个月挣了16000元,这是他在北京3年的最高收入。
然而,代价是睡眠严重不足,身体吃不消。
03
尽管如此,小春还是把送外卖这件事,尽力坚持了下来。一来,能有份稳定的兼职收入;二来,可以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仿佛融入了这座中国最大的都市。

初一晚上,小春下班后赶到十里堡,和晓峰交换电动车。“因为他(晓峰)的电动车跑得更快。”小春说。
不久,小春接了一单。因为对这一带不熟悉,加上导航定位不太准确,小春找了半天也没找对地方。还没吃饭的他,骑车穿过欢庆春节的人们,焦急而彷徨。

最后,他和顾客加微信发了定位,才在一番周折后把餐送到,没有超时。小春刚下楼,那位顾客给他发来一条信息:“辛苦了,感谢深夜送餐,新年快乐!”

这让小春鼻头一酸。他想起自己在北京送的第一单,也是找不到地址,也是共享了位置。那个客人同样没有埋怨,还送给他一瓶水。
在小春看来,庞大的北京,有她冷酷的一面,但更多的,是温暖。

也是缘于送外卖,小春还收获了几个年龄相仿的朋友,比如在除夕一起聚餐的晓峰和光头强哥。

除夕这天吃饭的时候,几个人聊起家乡的春节。小春说,他没什么特别的印象。也许是因为清贫,他总觉得家中缺少欢笑,即便过年也是如此。
不过,刚来北京那年,小春作为一名助唱,登上了央视《星光大道》的舞台。节目播出的时候,父亲召集了全村的人来看,小春仍记得一家人在电话中传递出的喜悦。
另一件事,就是当小春把在北京第一年赚的6万元寄回家时,父亲很欣慰。
04

这个春节,小春留在北京过年
今年春晚还没结束,社交媒体上就出现了一个个段子。其中有一个段子是这样的:“一片片地‘倪妮好白好白’‘千玺笑起来好好看’,感觉这一代青年算完了。我小时候镇上有个小伙子,因为在赵本山出场的时候放鞭炮,被邻居打成二级伤残,我怀念那个时代。”

深夜,小春从物业下班准备回家
年味越来越淡了吗?小春没有这样的愁绪,他对赵本山无感,对于春节,“也就那么回事。”他知道这是个团圆的日子,但没有人规定,必须要团圆。他只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努力创造着生存和生活的条件,对于现在的他来说,多赚钱,就是最重要的事。

变成暗夜外卖骑手的小春,穿梭于北京街头
在这个现实的世界,小春从不抱怨。不管是春节,还是平常的日子,他都不忘拧动手中的油门。
他也有自己的愿望:等疫情过去,带父母来北京看看,“他们还没看过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