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日 | 邹韬奋:办一份为大众所爱读、为大众做喉舌的刊物
编者按:邹韬奋先生对自己的定位是要做一个“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新闻记者,他一生都在追求“办一份为大众所爱读、为大众做喉舌的刊物,办一个自由的、不受检查的报纸”。他为《生活》周刊所设定的宗旨是“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1944年的今天去世,年仅48岁。
上海静安区新闸路上的沁园村是一片石库门小区,外墙被刷成黄色,窗台上摆满了鲜花,每户都有天井和阁楼。小区门口的铭牌上提示,9号楼曾是影星阮玲玉的故居。但很少有人知道,出版家邹韬奋也曾住在沁园村的22号。并且这是他生命中最后的一处居所。
房屋的主人,是生活书店浙江金华分店在上海的同事毕青的哥哥。1944年2月,韬奋先生的病情恶化,日军谍报机关已知道他在上海治病,派出特务四处打探。如果继续住在医院里,很有可能发生意外。因此,生活书店的同事们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把他转移到新闸路沁园村(现新闸路1124弄)22号隐居。
1944年,是韬奋生命的最后一年。年初,他就开始撰写自传性质的《患难余生记》。他简要回顾了《生活》周刊与生活书店的发展历程,用更多的笔墨控诉国民政府对新闻的钳制、打压,对文化事业的迫害、摧残。这本书只完成了三章五万多字,写到生活书店的“八种精神”,未及展开便无法坚持下去了。按计划,他还要写《苏北观感录》和《各国民主运动史》。
1944年7月24日,一代出版家韬奋先生终于走完了他的人生,享年49岁。临终前,他给夫人沈粹缜写下三个字——“不要怕”。为了不被敌人发现,韬奋先生的遗体仍用“季晋卿”的名字暂时存于上海殡仪馆,两年后才以真名落葬在上海虹桥公墓。

邹韬奋铜像
此前9年在鲁迅先生公祭大会上,邹韬奋曾发表最简短的演说:“今天天色不早,我愿用一句话来纪念鲁迅先生;许多人是不战而屈,鲁迅先生是战而不屈。”他当年未必意识到,他对鲁迅先生的评价对他自己也同样适用。
韬奋先生身后所获评价极高,他甚至成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典范。郭沫若的挽联即写道:“瀛谈百代传邹子,信史千秋哭贾生。”最高的评价则见于革命的名义,毛泽东对生活书店的柳湜说:“我们干革命有两支队伍,武的是八路军,文的是邹韬奋在上海办刊物,开书店。”
《生活》:特殊时代的精神食粮
1926年是邹韬奋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元旦,31岁的邹韬奋与沈粹缜完婚。婚礼就在上海南京东路永安公司楼上的大东酒家。邹韬奋为妻子买了一只镶嵌珠宝的手镯和一枝珠花,还置办了一套家具,这花去他一大笔钱,为此还借了债。沈粹缜后来回忆说:“手镯和珠花,在婚后不久当我知道韬奋为举办婚事欠了债时,就变卖了用来还了债,而债务也依靠我们撙节用度,在他每月薪水中节约一部分,很快陆续还清了。因为韬奋和我都不愿在债务的负担中去过心情不舒畅的日子。”
婚后随着孩子的相继出生,他们先后换了几处房子。吕班路万宜坊54号(现重庆南路205弄54号)是他们居住最久的地方,前后一共6年,小女儿邹嘉骊就出生在这里。新中国成立后,这套住房作为邹韬奋故居保留了下来,并在隔壁53号建立了韬奋纪念馆。

1926年邹韬奋与夫人结婚时留影

1937年12月,邹韬奋从香港、广西、湖南转赴汉口,途经长沙时留影
1926年10月,就在长子邹家华出生不久,韬奋以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的身份,接办了职教社的机关刊物《生活》周刊。当时社址在辣斐德路(现复兴中路444号)的一个小小过街楼里,三张办公桌就把小屋塞得满满的,几乎没有转身之地。编辑部、总务部、发行部、广告部、资料室、会议室,六位一体,都在这十几平方米的空间里。全编辑部只有两个半人从事实际的工作,除了韬奋以外,就是主管营业、总务和广告的徐伯昕和兼职会计孙梦旦。因此编辑部的“独角戏”就落在韬奋身上。他搜集了各种材料,分类排列,每一类编写成刊物上需要用的文章,以不同的笔名发表。如心水、思退、沈慰霞、因公、惭虚、秋月、落霞、春风、润等等,都是他接办《生活》之后,先后所用的笔名。
1921年,邹韬奋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此前他曾就读南洋公学的机电专业。毕业后他曾担任过纱布交易所的秘书与翻译,职业教育社的编辑,《时事新报》的秘书以及兼职的英文教师。做新闻记者是邹韬奋长期以来的理想,直到接手《生活》周刊,他才有了真正实践理想的机会。
《生活》周刊创办于1925年10月,由银行家王志莘主编。其内容主要是刊登有关职业教育的情况和信息,宣传资本家要开明,职工要乐业,要求相互体谅,共同把工厂、商店办好。读者对象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社员和一般职工。每期只印2000份,发行面不大。
邹韬奋接手《生活》后,最重要的改革就是加强刊物的趣味性,尽量“多登新颖有趣之文字”,“力求精警而避陈腐”,并在报头上用大字标出“有价值、有趣味的周刊”。就像他喜欢说的:“本刊的态度是好像每一星期乘读者在星期日上午的闲暇,代邀几位好友聚拢来谈谈,没有拘束,避免呆板,力求轻松生动简练雅洁而饶有趣味,读者好像在十几分至20分钟的短时间内参加一种有趣味的谈话会,大家在谈笑风生的空气中欣欣然愉快一番。”
邹韬奋能够迅速改变《生活》周刊的面貌,不仅在于他敏锐的时代嗅觉,不可忽视的还有他良好的英文水平。初期大量的文章,都先由他从国外期刊上编译,消化吸收后重新写出。随着刊物的发展,邹韬奋也在国外发展了一些作者作为通讯员,如日本的徐玉文、英国的费福熙、德国的王光祈、苏联的戈公振、美国的李公朴等。
他最重视的是《生活》周刊的一头一尾。“一头”是每期的开篇的“小言论”。这虽是仅数百字的豆腐块,却是他每周最费心血的一篇:“每次必尽我心力就一般读者所认为最该说几句话的事情,发表我的意见。”“一尾”就是每期末尾的“信箱”专栏。这里给广大群众提供了发表自己看法,提出自己建议的园地。回答读者问题的文字也是邹韬奋的精心之作。
看信、回信甚至占据了邹韬奋大部分时间。他每天要看几十封信,并安排回复,有代表性的直接发表。最长的回信,他会写到上千字。邹韬奋1937年在苏州监狱中曾回忆起这段生活:“我的妻子有一次和我说笑话,她说:‘我看你恨不得把床铺搬到办公室里面去!’其实后来纵然‘把床铺搬到办公室里面去’也是来不及的。”
三年间,《生活》周刊销数由2000份突增到4万份以上。到1932年,发行量已达15.5万份,创下了当时我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后来他主办的《大众生活》,销量高达20万份,再次开创了中国杂志发行的新纪录。在识字率只有30%左右的民国时期,这是一个出版史上的奇迹,真正称得上是一纸风行。

邹韬奋与亲友合影(左起:邹韬奋、陈德恒、郁鸿诒、邹恩泳)
民国时代著名记者赵浩生后来曾回忆说:“至今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每期《生活》周刊在学校饭厅门前的地摊上出现时,同学们都一改拥进饭厅去占座位抢馒头的活动,而如饥似渴地抢购《生活》周刊。一册到手,大家就精神物质食粮一起狼吞虎咽;而最迫不及待要看的,就是韬奋的时事评论和连载的游记。”《生活》周刊已经成了那个特殊时代的精神食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深感国难之痛,《生活》周刊的编辑方针也进一步做了与时俱进的调整。正如他自己说的“本刊最近已成为新闻评述性质的周报”,要“就民众的立场对政府对社会,都以其客观的、无所偏私的态度,作诚恳的批评或建议论事论人,以正义为依归”。于是“生活周刊已经按一般读者的要求”,“渐渐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
邹韬奋开始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并全力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生活》周刊的内容也逐渐从城市中产阶级的趣味转向宣传抗日救国,成为全国救亡运动的舆论阵地。胡愈之后来回忆说:“从这(‘九一八’)开始,《生活》周刊逐渐改变了方向,关心和议论起国家民族的大事,使刊物和全国人民反蒋抗日的愿望一致起来,刊物更受到读者的欢迎。”
借由《生活》周刊始,杂志成为邹韬奋一生的主要奋斗领域。《生活》之后有《新生》,抗战前夕有《生活星期刊》,抗战发动后有《抗战》三日刊及《全民抗战》。国内局势转变,《大众生活》又在香港复刊。一刊遭挫折,一刊又起,前仆后继,如缕不绝。这一类刊物的读者最为广泛,学生、教师、店员、学徒、农村青年、工厂职工、公务人员、自由职业者、妇女、士兵、僧道以及贩夫走卒,无不包括。
邹韬奋的伙伴徐伯昕后来在纪念文章中写道:“他不是个大思想家,也不是个文学家,在学术上亦没有太大的贡献,但就是他朴素至极的言论,却影响甚广。他的《生活》周刊和《大众生活》,被25万中国人读到。”

1934年邹韬奋与美国学生旅行团在克林姆林宫炮王前合影(第二排右二为邹韬奋)
生活书店的火种
随着《生活》周刊的影响逐渐扩大,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胡愈之便向邹韬奋建议创办生活书店。这样不仅可以出书、卖书,即使《生活》周刊被封禁了,还有书店,阵地依然存在,可以换个名字继续出版刊物。
于是《生活》周刊便先从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分离出来,于1932年7月在“书报代办处”的基础上又成立的生活书店。最初的店址设在上海环龙路80号,后几经辗转搬到了福州路384弄4号,并公开登报招考和聘用了一批批职员和练习生。邹韬奋为书店确立了经营原则,即“盈利归全体,没有剥削存在,一面为社会服务,同时也为自己工作”。
生活书店的门市布置如图书馆,各类图书按图书分类法列置在四周的书柜里。首创开架售书,任随意取阅,读者称便。在厅中的书台上,新书、新刊分台陈列,一目了然。在推荐书台上,每一种被推荐的书,都有文字说明,介绍内容特点。
门市开架售书,难免被偷。不过邹韬奋定下规矩,不可公开斥责偷书者。有一次,一青年读者在书店看书看不完,不付钱,揣着书出店门了。被书店门市工作人员发现,领到隔壁房间谈话。原来是一位爱好读书的穷大学生。书店十分同情,劝其下次不可这样干了,大学生很受感动。他回去后把过去拿走的书统统送回来了,还附一短信,表示悔改。由此,书店便在售书厅中大柱四周设置了几圈座椅,让读者站累了可以歇一歇,使门市权充流通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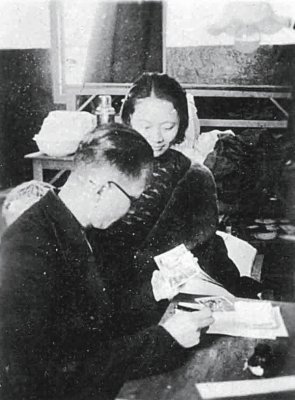
夫人沈粹缜关注邹韬奋写作(在狱中)
抗战初期是生活书店发行业务的全盛时期。在抗战大后方的大中城市中设立了56处分支店,一时超过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老牌出版单位的分支店的规模。一个分支店就是一个据点,如火种一般向四周辐射。每个分店还负有组稿的任务。
即使处于高压的舆论环境中,生活书店依旧寻求新闻与出版的自由。生活书店的《文学》、《译文》、《太白》和《世界文学》,刊载了鲁迅先生译著达到78篇;仅是1935年就发表47篇。生活书店还出版了大批所谓“禁书”,如抗战时期,被查禁的书多达200多种,作者的名单上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吴大琨、张仲实、陈伯达、徐懋庸、李公朴、章乃器、钱亦石、夏衍、端木蕻良、刘白羽、冼星海、胡绳、罗瑞卿、孙冶方、洛甫、艾思奇、欧阳山等等。有趣的是,国共合作时期,生活书店出版过一本《蒋委员长抗战言论集》,竟然也被查禁掉了,因为这本书是在共产党的支持下编写的,旨在“压蒋抗日”。
关1937年“八一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邹韬奋预见到这是一场持久的战争,绝不会在短时期内结束,就坚决果断地将几种大型的刊物,如《文学》、《中华公论》等停刊合并,集中精力,编辑出版《全民抗战》,并将书店中心先后迁往武汉和重庆。并在各地先后设立了55个分支店。同时对上海这个重要据点也没有放弃。福州路的编辑部和门市部虽然收缩,但在同一条马路上的378号,仍以“远东图书杂志公司”名义开门营业,保持了同外界的联系。当“远东图书杂志公司”因出售《日本的间谍》一书引起日寇注意时,又在一夜之间改换了招牌,用“兄弟图书公司”名义照常营业。
在1941年“一二·八”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侵入租界时,“兄弟图书公司”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光明书局及良友图书公司等八家同业同时被日军宪兵队的报道部查封。一个月后因形势变化才得启封。启封以后,由于抗日救国的书不能出版,低级庸俗的书又不愿经售,存货越来越少,营业日益清淡。为了维持职工生活,就在原址先后用“新光教育用品社”和“新光百货公司”的名称经营文具和百货。当时,尽管图书出版举步维艰,但生活书店仍通过各种外围组织与上海作家保持联系,接济生活困难的进步作家,使他们安心写稿,为今后积累稿件做准备。

1933年7月,邹韬奋出国时与毕云程等友人合影(左起:毕云程、邹恩泳、邹韬奋)
收买与压迫
毕云程先生在《邹韬奋先生五周年祭》中提到,1931~1932年,《生活》周刊发表了一篇《最近我们的思想和态度》。文中说:“我们主张生产工具公有,而以国营实业为达到生产工具公有的一种方法。”这完全是共产党的主张了,居然公开发表出来,当局自然不满。于是,“有一天,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来访问先生,亲自驾着汽车把先生接了去……约莫过了四个钟头,先生回来了”。毕先生继续转述道:“据先生自己后来对我说,他这一次和胡宗南辩论了四个钟头,主要是辩论抗日问题和《生活》周刊的主张问题。”
这是第一次国民党对于邹韬奋的“劝说”,规格很高。但显然,一个将军和一个出版家四小时的“辩论”没有形成共识。
国民党下令邮局对《生活》“禁邮”是在1932年的7月。国民党元老蔡元培两次致电蒋介石解释,均遭拒绝。邹韬奋最初认为这只是个误会,“因为《生活》自问只有在政策上批评的态度,并没有反政府的态度,所以先从解释误会下手”。但蒋介石把《生活》合订本上批评政府的地方都用红笔划了出来说:“批评政府就是反对政府,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
这年秋天,邹韬奋终于因为政治压力严重,而被迫出国考察。1933年底,邹韬奋还在出国考察期间,《生活》周刊以“言论偏激”的罪名被封禁了。邹韬奋早已预料到这个结局。最后一期《生活》发表了他早在一年多前就准备好的《与读者诸君告别》一文:“记者所始终认为绝对不容侵犯的是本刊在言论上的独立精神,也就是所谓报格。倘须屈服于干涉言论的附带条件,无论出于何种方式,记者为自己的人格计,为本刊报格计,都抱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
邹韬奋回国后,国民党又派出了要员张道藩与刘健群进行劝说,地点在邵洵美家。但是这次依然没有共识和结果。邹韬奋随后还在《大众生活》上发表了《领导权》一文,驳斥了刘健群的“领袖脑壳论”。
武将、文官轮番上阵,依旧没有效果。蒋介石决定亲自出马,约邹韬奋到南京面谈。为了免去邹韬奋对安全的担心,由杜月笙陪同往返。但当时邹韬奋已加入全国各界联合执行委员会,是执行委员之一。在和救国会同志协商后,决定不去南京。主要考虑在于,邹和蒋的身份特殊,无法迁就,如果观点僵持住,则可能影响到救亡运动的坚决态度。
于是,邹韬奋在预定前往南京的前夜把决定告诉了杜月笙。而在杜月笙看来此即是失约。在《患难余生记》中,邹韬奋饶有兴致地记述了故事的尾声,第二天戴笠仍奉蒋介石之命去南京火车站接人,接不到人,只能原车返回。不料天降大雨,道路泥泞,半路车子翻了,弄得戴笠满身污泥狼狈不堪。邹韬奋写道:“在他们看来,我大概是一个最不识抬举的人!”
邹韬奋放了蒋介石的“鸽子”,随后1936年底苏州法院便以“危害民国”罪拘捕了救国会领袖邹韬奋、王造时、沙千里、沈钧儒等七人,被称为“七君子案”。直到1937年7月才获自由。
抗战开始后,邹韬奋的思想越发“左”倾,国民党当局对言论的压制也更加严厉。1938年颁布的《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和《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要求所有出版物须重新送“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发给审查证,印在封底上,才能出版。

1939年10月,邹韬奋(中)与夫人沈粹缜(右)参加在重庆举行的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大会
而针对生活书店的打压也逐步加强。1939年4月西安生活书店被封闭,此后,各地生活书店遭搜捕的事故不断发生。到最后,全国50余处分支店除了重庆、桂林、贵阳三处分店,其余均遭封闭。1940年6月,国民党派出几个会计专家突然来书店总管理处查账,检查是否领取共产党津贴,结果也毫无所获。
手段用尽后,由国民党主管文化出版的刘百闵出面再与邹韬奋做最后的谈判。刘百闵提出生活书店与国民党办的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联合”或“合并”,成立总管理处,请邹韬奋主持,管理所属三个出版机构,各店对外的名称保持不变。但邹韬奋表示,所谓联合与合并,不过是消灭与吞并的别名罢了,绝对不能接受。
刘百闵又提出另一个方案,即政府给生活书店注资成为股东,派两个人挂个空职“监督”,让政府放心。邹韬奋又严词拒绝,理由是:民办事业是国家法律所允许,生活书店一向遵守法令,已经接受法律监督,不能再受派人“监督”。刘百闵最后摊牌说,这是蒋总裁本人的主意,不能违反。邹韬奋则回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谈判宣告破裂。
接下来,生活书店各地分店相继被查封,只留下重庆等几处权当做“言论自由”的装饰。邹韬奋最终对于国民政府彻底失望了。“皖南事变”后,他辞去国民参政会议员,秘密离开了重庆,前往香港寻找较为自由的言论空间,继续他的出版事业。然而不久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他的理想再次被击碎。时逢乱世,不仅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连一个编辑部一部印刷机都无处藏身。邹韬奋在东江游击队的保护下,混在汹涌的难民人潮中离开香港。在广东隐藏了几个月后,国民党的通缉令便已下达,他便动身前往新四军的苏北抗日根据地。
出版家的理想
1933年,邹韬奋第一次流亡海外前曾写下一段话:“我常勉励我们的兄弟姐妹们,我们是在一个血腥的黑暗时代,如不为整个社会的前途努力,一个机关的内部如何充实,如何合理化,终不免要受黑暗势力的压迫摧残的。我们这班傻子把自己看做一个准备为文化事业冲锋陷阵的一个小小军队,我们愿以至诚的热血,追随社会大众向着光明的前途迈进。”
生活书店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韬奋先生的预言。然而不管时代如何不堪,他始终保持了那种“傻子”一般的热忱,从没有放弃努力,始终怀有理想。如茅盾所言,这便是“永远年轻的韬奋先生”,“由此可以想象到:要他在一个恶浊的社会中装聋作哑,会比要了他的生命还难过。他需要自由空气,要痛快的笑,痛快的哭,痛快的做事,痛快的说话。他这样做了,直到躺下,像马革裹尸的战士”。
早在主编《生活》周刊期间,邹韬奋便严守着自己的“报格”,坚持言论自由和精神独立,使《生活》周刊真正成为“民众的喉舌”。无论受到了怎样的外界压力,邹韬奋始终坚持编辑与媒体的独立性。他说:“我的态度是头可杀,而我的良心主张,我的言论自由,我的编辑主权,是断然不受任何方面任何个人所屈服的。”他在《生活》周刊上写文章说:“所要保全的是本刊在言论上的独立精神——本刊的生命所靠托的唯一的要素。倘本刊在言论上的独立精神无法维持,那末生不如死,不如听其关门大吉,无丝毫保全的价值,在记者亦不再作丝毫的留恋。”
邹韬奋终生不愿当官,只愿当编辑、做记者开书店。1937年时,他曾写道:“时光过得真快,我这后生小子,不自觉地干了15年的编辑。为着做了编辑,曾经亡命过;为着做了编辑,曾经坐过牢;为着做了编辑,始终不外是个穷光蛋,被靠我过活的家族埋怨得要命。但是我至今‘乐此不疲’,自愿‘老死此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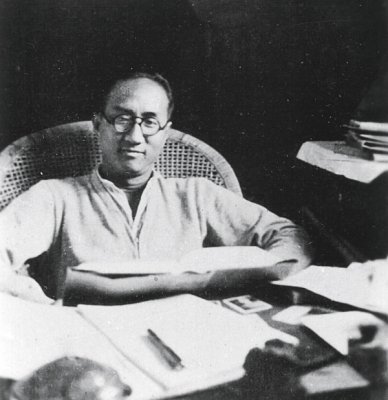
在狱中阅读写作的邹韬奋
在重庆期间,生活书店负责发行和邮购的许觉民收到一封读者来信,问“抗战胜利后,中国会成为什么样的中国?”年轻的许觉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他拿着这封信去向邹韬奋请教。“我记得,他当时说,将来的中国,要成为一个人人有书读,人人有饭吃,人人都有民主权利的社会。他还说,这些要经过很大的努力,不是马上就能实现的。”许觉民后来回忆说。
但韬奋先生的生命终究太过短暂,如果从1926年主持《生活》周刊算起,他才只有19年的出版生涯,他不仅没有看到他所期望的社会到来,甚至没有等到抗战胜利。
在生命最后时刻,他曾对身边人说:“如时局好转,首先恢复书店,继办图书馆与日报,愿始终为进步文化事业努力,再与诸同志继续奋斗二三十年!”“对政治主张,始终不变,完全以一纯粹爱国者之立场,拥护政府,坚持团结,抗战到底,能真正实行民主政治。”
本文有所删减,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如需转载,请务必注明。
mp.weixin.qq.co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