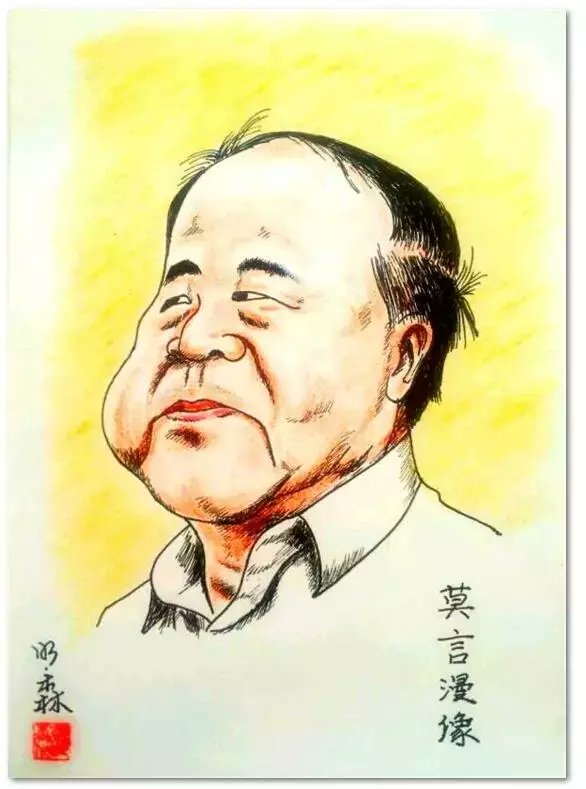莫言: 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
那时候我们这些孩子的思想非常单纯,每天想的就是食物和如何才能搞到食物。
我们就像一群饥饿的小狗,在村子中的大街小巷裡嗅来嗅去,寻找可以果腹的食物。
许多在今天看来根本不能入口的东西,在当时却成了我们的美味。
我们吃树上的叶子,树上的叶子吃光后,我们就吃树的皮,树皮吃光后,我们就啃树干 。
那时候我们村的树是地球上最倒楣的树,它们被我们啃得遍体鳞伤。
1961年的春天,我们村子裡的小学校里拉来了一车亮晶晶的煤块,我们孤陋寡闻,不知道这是什麼东西。
一个聪明的孩子拿起一块煤,咯嘣咯嘣地吃起来,看他吃得香甜的样子,味道肯定很好,於是我们一拥而上,每人抢了一块煤,咯嘣咯嘣吃起来。
我感到那煤块愈嚼愈香,味道的确是好极了。
看到我们吃得香甜,村子裡的大人们也扑上来吃,学校裡的校长出来阻止,於是人们就开始哄抢。
至於煤块吃到肚子裡的感觉,我已经忘记了,但吃煤时口腔裡的感觉和煤的味道,至今还牢记在心。
不要以為那时候我们就没有欢乐,其实那时候我们仍有许多欢乐,我们為发现了一种可以食用的物品而欢欣鼓舞。
这样的饥饿岁月大概延续了两年多,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我们的生活好了起来,虽然还是吃不饱,但每人每年可以分到两百斤粮食,再加上到田野裡去挖一点野菜,基本上可以维持人的生命,饿死人的事愈来愈少了。
当然,仅仅有饥饿的体验,并不一定就能成為作家,但饥饿使我成為一个对生命的体验特别深刻的作家。长期的饥饿使我知道,食物对於人是多麼的重要。
什麼光荣、事业、理想、爱情,都是吃饱肚子之后才有的事情。
因為吃我曾经丧失过自尊,因為吃我曾经被人像狗一样地凌辱,因為吃我才发奋走上了创作之路。
20世纪的60年代初期,正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古怪而狂热的时期。那时候一方面是物质极度贫乏,人民吃不饱穿不暖,几乎可以说是在死亡线上挣扎;但另一方面却是人民有高度的政治热情,饥饿的人民勒紧腰带跟着共产党进行共产主义实验。
那时候我们虽然饿得半死,但我们却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而 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包括美国人――都还生活在“水 深火热”的苦难生活之中。
而我们这些饿得半死的人还肩负着把你们从苦海里拯救出来的神圣责任。
当然,到了八十年代,中国对外敞开了大门之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如梦初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