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匹大音乐系的学业,一定要介绍我的导师荣鸿曾(Bell Yung)教授。我能到此自费留学,是经过荣老师的不断努力才实现的;在音乐系的读研以及做研究助理和助教的工作,特别是硕士和博士论文的写作,都始终是在荣老师的悉心指导下进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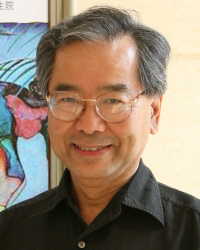
荣鸿曾教授(照片来自网络)。
根据相关的正式介绍,荣鸿曾教授“原籍江苏无锡,生在上海,长于香港”。曾有一位说话靠谱的朋友告诉我,荣鸿曾教授是中国民族资本“荣氏家族”的成员。当时正值荣毅仁先生担任国家的重要职务,然而荣老师对这些从来没有提起过(至少对我以及在我知道的场合)。
荣老师的求学经历很独特,他是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理论物理的博士学位以后,又到哈佛大学随著名学者赵如兰教授学习中国音乐,并在那里成为音乐学博士。随后他在学术和教学上表现优秀,著述甚丰,获奖无数,还曾担任海外中国音乐研究会的会长多年。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他钢琴弹得非常好。记得有一次部分教授和同学在他家聚会,有人请他弹奏钢琴。他没有做任何“热身”,直接就弹了一首非常华丽动听的乐曲,令人赞叹不已!在场的一位钢琴行家低声告诉我,那是一首勃拉姆斯的作品,难度很高。
回想在匹大音乐系读研,我永远感激荣老师对我的教导!我从匹大毕业以后,听说荣老师除偶有兼职以外,一直在匹大音乐系任教,直到2012年退休,现在仍是匹大的荣休教授(Professor,Emeritus)。退休后,荣老师移居西雅图,并担任那里华盛顿大学音乐学院的兼职教授(Affiliate Professor)。今年(2021年)适逢荣老师八十寿辰,祝荣老师健康长寿,工作顺利,生活幸福!

上图是1993年秋我入学不久,荣老师过生日,在家招待他的学生,我也有幸在场。左二是荣老师。
下面转发一篇荣老师的访谈录。这虽不是我初到匹兹堡时参与完成的,却是介绍荣老师很全面的资料。1998年,我受国内《中国音乐年鉴》编辑部的委托,对荣老师进行了采访,谈了约两个半小时。在采访中,荣老师介绍了自己的求学经历和多年的研究工作,以及他对“民族音乐学”,“音乐学”等学科的见解。我根据录音整理成访谈录,经荣老师审阅后,发表在《中国音乐年鉴 1997》(实际是1999年出版的,所以收录了1998年的访谈录)。以下是这篇访谈录的全文:
中国音乐年鉴 1997
人物专访
著名中国音乐学者荣鸿曾教授访谈录
特约记者 吴犇
荣鸿曾(Bell Yung)现任匹兹堡大学音乐系教授,香港大学音乐系教授。祖籍江苏无锡,1941年生于上海。五六岁时开始学习钢琴。1948年至1960年在香港上小学、中学。1960年到美国加州的圣 克拉拉大学学习。一年后转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主修物理。1964年毕业并获学士学位后,到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深造,于1969年毕业并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9月成为哈佛大学音乐学系的研究生,一年后决定专业方向为音乐学[那时该系尚无专门的Ethnomusicology(以下译为“民族音乐学”)专业]。除研习西方音乐学的各种课程以外,开始从赵如兰教授学习中国音乐。博士论文的课题为“广东粤剧音乐研究”,曾到香港做多次实地考查。1976年论文完成并获得音乐学博士学位。1976年至1978年在康奈尔大学做博士后,边教学边研究,并从那时开始学习古琴。1978年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两年半后,于1980年12月到美国匹兹堡大学音乐系任教至今。在此期间曾于1990年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任访问教授一个学期。自1996年开始兼任香港大学音乐系教授。
荣鸿曾教授是海内外知名的音乐学者,在中国音乐研究与“民族音乐学”领域著述甚丰。同时他还为推动海外的中国音乐研究事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与重要的贡献。他是海外“中国音乐研究会”(Association for Chinese Music Research,简称 ACMR,1986年成立)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并担任该会会长兼会刊主编多年。他还积极参与海外另一学术团体“中国演唱文艺学会”(The Conference On Chinese Oral and Performing Literature,简称 Chinoperl)的活动,并于1996年起任该学会会长至今。
受《中国音乐年鉴》编辑部的委托,吴犇对荣鸿曾教授进行了采访,时间是1998年8月6日下午,地点在美国匹兹堡荣教授的寓所。采访进行了约两个半小时,其主要内容整理如下(已经被采访者本人审阅)。
记者:
荣老师,您的经历与多数音乐学者不大一样,特别是您获得物理学博士以后又开始念音乐的研究生。能否请您谈谈您改学音乐前后的情况?
荣鸿曾:
其实我一直都想学音乐。我从小开始学习钢琴,后来一直坚持练习。大学毕业后,本想开始念音乐的研究生,但麻省理工学院给了奖学金,是很难得的。后来在该院学习期间,曾跟一位有名的钢琴教师凯莉阿娜•西洛蒂(Kyriena Siloti)继续学琴。她的父亲亚历山大•西洛蒂(Alexander Siloti)是李斯特的学生。她是朱莉亚特音乐院的钢琴教授,利用每个周末的时间在波士顿教学生。另外我还参加了“波士顿中华合唱团”,担任钢琴伴奏。这个合唱团是1967年成立的,绝大多数成员是华人学生,主要演唱中国歌曲。当时由于中国和日本在钓鱼岛的领土之争,合唱团曾演唱了不少抗战歌曲,同时也演唱一些艺术歌曲。在这个合唱团,我认识了赵如兰教授,她当时担任合唱团的顾问。这些都使我学习音乐的愿望更加强烈。所以从麻省理工学院一毕业,就开始到哈佛去念音乐的研究生了。一开始是什么课都学,包括钢琴、作曲、西方音乐史等。一年以后发现自己最喜欢的还是音乐学,同时希望做中国音乐的研究。当时系里并没有“民族音乐学”的课程,所以主要向赵如兰教授学习中国音乐。我的学习与研究受赵教授的影响很大。她的研究大体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中国音乐史,以她有关宋代音乐史的博士论文及专著为代表,主要以各种史料研究为基础; 另一个方面是对京剧及说唱音乐的研究,包括她发表的有关专著与文章,主要以她本人的实地考察为基础。我更多地受到她后一方面的影响,所以选择了广东粤剧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并特别注重实地考察。
记者:
能否再谈谈您本人的研究工作,包括以前的成果,现在进行的项目及将来的计划?
荣鸿曾:
我的研究工作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对广东粤剧音乐的全面研究,其成果发表在我的博士论文及后来出版的英文专著中(Cantonese Opera:Performance as Creative Proces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第二个方面是对古琴音乐的研究。我是在1977至1978年期间开始向张世彬先生学习古琴的。他当时在哈佛大学做一年的访问学者。后来我于1978年至1980年在香港工作期间,向蔡德允先生学琴。在那两年半的时间学了不少琴曲。另外在1979年至1981年的三个夏天,曾到上海向姚丙炎先生学琴。我最近出版的关于古琴的专著(Celestial Airs of Antiquity,Madison:A – R Editions,Inc. 1997),主要就是根据向姚丙炎先生学习的六首《神奇秘谱》中的琴曲。另外也先后发表了一些关于古琴音乐的文章。最近在考察蔡德允先生的生平及古琴艺术。他今年92岁了,是浙派沈草农的学生。
第三个方面是对一些广东说唱音乐曲种的研究,也是主要建立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已经发表了一些有关文章,主要是在《中国演唱文艺学会会刊》(CHINOPEAL PAPERS)上。近两年在香港教学期间 ,还在继续这方面的考察,希望将来能完成一部有关的专著。
第四个方面是对查尔斯·西格的研究。西格是美国“音乐学学会”与“民族音乐学学会” 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对美国音乐理论界有很大影响。他的一些学说具有很深的历史与现实意义。西格晚年曾到波士顿讲学。我曾多次听过他的演讲并与他讨论过一些有关音乐研究的问题。后来我在匹兹堡开设了有关西格的研究生讨论课。以后在一些研究生论文的基础上编辑了一本关于西格及其音乐理论的书。我自己写了其中一章,是受西格一些思想的启发,第一次结合物理学的方法谈音乐学的一些间题。这本书已定稿,将于明年(1999年)出版。另外我还想继续做一些结合物理学的方法去看音乐现象的研究。物理现象是大自然的现象; 而音乐现象则是一种人为的结果。人的创造与选择与自然规律不同;但另一方面,音乐现象也与自然现象有某些相似之处,因此可以结合物理学的方法,对一些音乐现象进行研究。这也是我今后想做的一个课题。
此外还有一个方面是对中国仪式音乐的研究。1993年在匹兹堡主持了一个关于中国仪式音乐的研讨会。后来在会议论文的基础上,与历史和人类学的另外两位教授(Evelyn S. Rawski,Rubie S. Watson)一起编辑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仪式音乐的书(Harmony and Counterpoint:Ritual Music in Chinese Contex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我写了其中一章,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仪式音乐研究的模式。这个方面的研究也将要继续下去。
记者:
您有这样多方面的研究成果,真令人敬佩! 您的绝大部分研究与中国音乐有关,相对中国本土而言,这些研究是在海外完成,出版的。您多年来一直在为推动海外的中国音乐研究事业做不懈的努力。能否请您谈谈海外中国音乐研究的特点及一般状况,特别是与国内的研究有哪些不同?
荣鸿曾:
首先,在海外搞中国音乐研究,由于研究对象在中国,所以一定要回国去做实地考察,收集资料。这一点很重要。当然国外有些方面的书面资料也不少,如一些历史文献及用外文发表的有关材料与成果等,有些还是国内所没有的。所以对某些研究课题来说,最好是国内国外的资料都能占有。
在实地考察和收集资料之后,往往是回到国外写出论文或专著。这时有一个很大的不方便,就是在书写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现在实地考察时,有些情况还了解得不够。这时再通过写信等方式了解就很不方便,有时不得不等到下一年再回国时弥补。但另一方面,我觉得在国外写也有一定优点,那就是离开了实地环境后,可以比较清静地分析和总结研究对象在一定时间内的状况。因为对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地变化,我们做为研究者对它的看法也会不断有所变化。如果在分析和写作时离对象太近,就会不断受其变化的影响,反而可能写不好了。
另一点不同之处是国内的研究人员多,在一个工作单位内往往有人可以互相交流、讨论、商量,因为大家都是做中国音乐研究的,有共同的兴趣。在海外就不同了。做中国音乐研究的人分散在不同的学校和单位,没有人能够随时交流和讨论,同时又要教一些其它的非中国音乐的课,看一些其它领域的书,不能把全部精力都用来做中国音乐的研究,这是不如国内的地方。但另一方面,在国外的优点是能及时了解到国际上的有关新的理论与方法,并学习和运用其中合理的成分。例如国外的中国音乐研究受“民族音乐学”的影响要比国内大。
记者:
据我所知,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对“民族音乐学”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您在美国教“民族音乐学”的各种课程已有多年,请谈谈您对这一学科的大致看法。
荣鸿曾:
这一学科虽比较年轻,但对研究世界上的非西方音乐和把音乐做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等方面,它无疑是做出了很大贡献。它的很多理论和方法是值得很好地学习并加以运用的。但另一方面,它也存在一些阿题,人们对它的确有很多不同看法。首先它的名称“Ethnomusicology”本身就很有问题。因为英语“ethno”或“ethnic”原本具有“非主流”或“非自身”文化的含义。在历史上,它甚至还有贬义。虽然一些“民族音乐学家”认为这个词的词义已有所转化,但对普通读者来说,它的以上含义仍是明显的,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名称应该改。今年两位“民族音乐学”学会会长候选人朱迪丝·贝克(Judith Becker)教授和邦尼·韦德(Bonnie Weide)教授都认为学科名称应该更改,说明这个间题确实是该解决了。
再有,这个学科究竟是怎样一个学科? 它的主要方向与方法是什么? 对此仍有不同看法。从理论上,很多人认为它是包括用各种不同方法,从各种不同角度研究音乐的学科。但在实际上,又有很多人认为它与人类学关系密切(这与“民族音乐学”的历史有关,在五六十年代,很多这个学科的人都是人类学家或有人类学背景),主要是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音乐的学科,是人类学与音乐研究的交叉领域,并不是一个界定非常广阔的学科。这些不同看法与做法目前仍然存在,使得这一学科在这些关键问题上并不明确。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研究对象。从理论上讲,很多人认为这个学科研究世界上所有的音乐; 但在实际上,绝大多数“民族音乐学”学者在做非西方艺术音乐的研究,即西方以外世界各地的音乐以及西方的民间与当代流行音乐。有人认为不应该如此,但却又不能不面对现实。这也与刚才谈的学科名称的问题有关,因为“Ethnomusicology”给人的印象就是研究非主流文化的音乐。所以有人建议,不管是研究西方音乐还是非西方音乐的学科都统称“音乐学”。这样最公平,是很理想的,但在实际中又会有新的问题。按目前这样把“民族音乐学”与研究西方艺术音乐的“音乐学”分开,在管理上与财务上会对“民族音乐学”有一些好处。因为现在有一些资助或职位是明确要授给“民族音乐学”学者的。如果大家都混在一起叫作“音乐学”的话,原来做非主流音乐研究的人就很可能被挤掉或丧失很多机会。因为在美国或其它西方国家,搞主流音乐的人比搞非主流音乐的人多得多。所以按目前这样分开,在实际上对“民族音乐学”是有些好处的。这个名称问题很复杂,不是轻而易举就能解决好的。
记者:
您对“民族音乐学”的这些看法真是言简意赅,我想对国内关心这一学科的同行们也一定会很有启发。您刚才谈了在海外中国音乐研究的一些特点,能否再请您谈谈对国内中国音乐研究的看法及希望?
荣鸿曾:
国内的资料丰富,对自身音乐研究的历史长,研究人员的数量大,多年来发表的研究成果也多,这些都是海外所不能相比的。总的来看,国内有很多高质量的研究。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研究虽包含很丰富的资料,但理论显得不够。这一点与海外的情况正相反。在海外,由于受西方各学科理论的影响,音乐研究也往往非常注重理论,这是好的一面; 但另一方面,有时忽视了实际的资料。有的研究甚至就是从理论到理论,没有一点实际的资料或音乐,这就太极端了。而国内的一些研究往往是资料多,描述多,理论研讨不够。再有,国外现在一般承认音乐是社会的一部分,音乐不能与人分开。但在国内,有些研究似乎还不是这样,即对音乐本身的描述多,但联系社会与人还不够。总之,希望国内的研究在资料丰富,描述具体的基础上,多一些理论的探讨与规律的总结,同时多一些音乐与社会及音乐与人的联系。
国内的中国音乐研究有一个优点是西方“民族音乐学”所没有的。由于实际上多数西方“民族音乐学”学者是在研究“非我”音乐或西方社会的非主流音乐,他们往往强调对研究对象的客观态度,即对音乐作品不作主观评价,特别是美学与艺术方面的评价。这一点与研究西方艺术音乐的“音乐学”不同。“音乐学”的一个前提就是音乐有价值,有好坏高低之分。他们的研究就是讲在西方艺术音乐领域中“好的”音乐是如何产生的(音乐史),“好的”音乐为什么好(音乐作品分析),以及如何创作出“好的”音乐(作曲法)。这些工作是必要的,因为这是建立西方主流文化价值观的一部分。而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往往不谈(非西方)音乐的美学与艺术价值。这虽然与研究者大都是“局外人”有关,但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因为这实际是否认了非西方音乐的美学与艺术价值。而中国国内的研究就不存在这个间题,往往是两个方面的工作都在做:既有客观的描述与分析,又有艺术方面的评价。这也是建立主流文化价值观的一部分,是很重要的工作。当然也有很多困难,比如如何评价西方文化对中国音乐的各种影响,如何使少数民族的音乐精华成为中国主流文化的组成部分等方面,都还有很多工作需要下功夫去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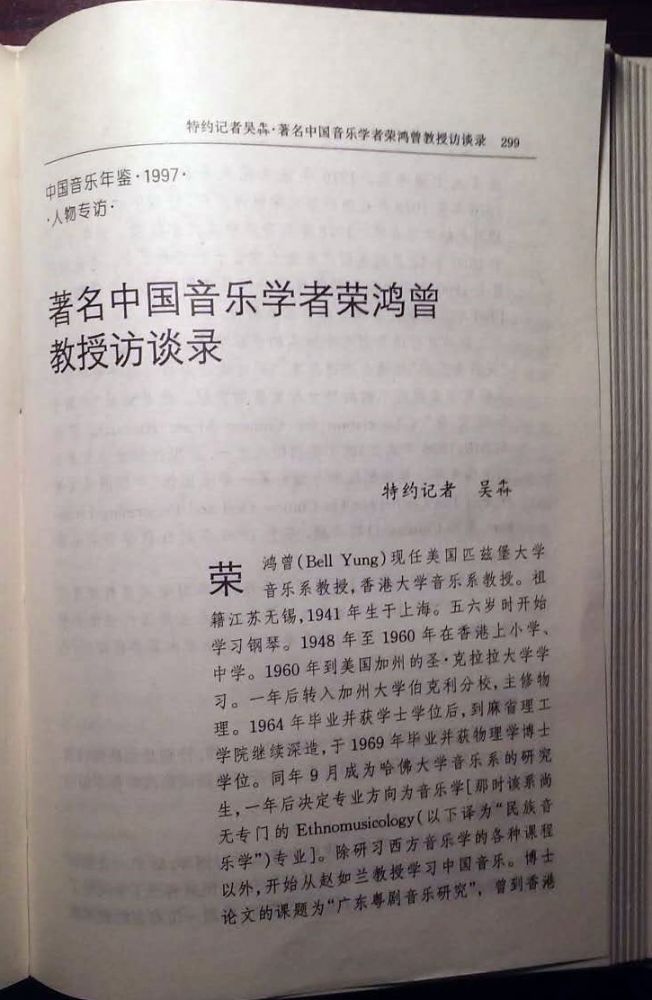
上图是《中国音乐年鉴 1997》上发表荣老师访谈录的第一页(全书第299页)。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