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独立日
如果赋予夏天以更为宽泛的定义,那么1776年的夏天可以说正是美国历史即将展开的时刻。在那一年5月到10月这段时间里,人们达成了对于北美独立的一致意见:美国的独立是以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为标志,随后在1783年9月3日英美双方签署的《巴黎条约》中,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的独立。
我常常在想,要是我没有在这种形势下临危受命,我准会快乐得多,我将扛起我的步枪,参军入伍,或者……隐居于荒村山野之中,求庇于兽皮棚屋之下。
——乔治·华盛顿1776年1月14日写给约瑟夫·里德(JosephReed)的信
尽管在1776年的暮春之前,北美独立一直没有得到正式的宣布,但是它已经拥有了自己的英雄。它的英雄就是乔治·华盛顿,一支由不同民兵部队拼凑而成的队伍(现在被称作“大陆军”)的最高统帅。华盛顿身高6英尺多,体重超过200磅,以18世纪的眼光来看就是标准的彪形大汉(关于华盛顿的身高学术界一直有争议。在他提供给裁缝的说明中,他说自己有6英尺高。在法印战争与他共事的军官们说他有6英尺2英寸。为他的遗体入棺而进行的测量数据则显示他有6英尺3英寸半)。亚当斯在1775年6月提名他当军事统帅,并且后来解释说,他是最合适的人选,部分是因为他是弗吉尼亚人,而弗吉尼亚对这场未来不宣而战的战争的支持相当重要;部分原因则是他比房间里的任何人都高了整整一头。

波士顿围城实在不像是一场战斗,倒更像是一场战术意义上的持久的小步舞曲。北美军队在人数上有着三倍于对方的优势,而英军最终撤离以图日后再战这一事实被北美新闻界看作是一场重大胜利。这场胜利的明显象征就是华盛顿。不仅哈佛大学授予了他荣誉学位,而且马萨诸塞议会(the Massachusetts General Court)也发表了声明,预言人们将会建起以他名字命名的纪念碑。大陆会议也颁发了一枚金质奖章以纪念他取得的胜利。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解释了这枚奖章被用来纪念什么:“美国历史的这一篇章将会把您的头衔放在名誉殿堂中醒目的位置,以告诉子孙后人,在您的带领下,一支散漫的平民部队,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变成了真正的战士,[并打败了]一支由最老练的将军所率领的历经百战的军队。”
事实就是如此。“英军不可战胜”这一广为流传的观念已经被打破。不仅英国舰队在失败和耻辱中黯然离去,而且人们也得以发现北美军事胜利的法则。对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有着坚定信念的业余士兵能够打败为酬劳而战的英国职业军人——也就是说,指挥北美军队的是这样一位自然产生的领袖,他证明了自己有能力激发麾下那批出身市民的士兵心中源源不绝的爱国热情。华盛顿明显就是那个角色,而现在他一个人就成了“这项事业”的体现。

当华盛顿带领着近万人的军队从波士顿向南奔赴纽约以抵抗英军可能发起的进攻时,他受到人们的夹道欢迎,人们纷纷向“将军阁下”敬酒,并自发地在公开场合赞颂他,这样的待遇也成为华盛顿日后人生中的家常便饭。如果说所有成功的革命都需要有英雄,并且它们最后确实也会有,那么美国革命已经找到了它的这个中流砥柱般的传奇人物。
华盛顿不仅在外形上很符合这一角色的要求,而且在心理上差不多也算得上是完美人选。他对于自己的优越如此满意,以至于他觉得对此已无须赘言(他在青年时代参加法印战争,那时的他曾经比现在更坦率健谈,但历经世事后,他学会了用气场去说明一切)。那些不自信的人仍然在侃侃而谈,他却保持着沉默,这让他成为众多拥护者最诚挚信念的寄托对象,成为一种容器般的存在,可以让众多的抱负志向神奇地聚集于一人之身。在他出现的场合,所有关于“独立代表着什么”的争论都将停止。就像人们向华盛顿敬酒时所说的,他“凝聚起了所有人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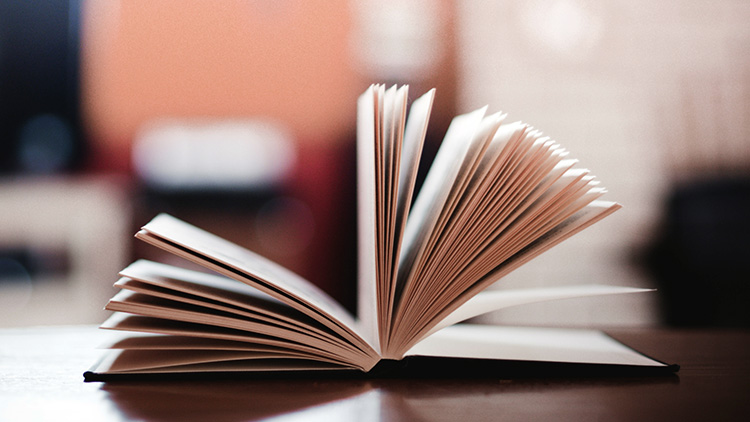
然而,在威严的外表之下,华盛顿自己对于汉考克激励人心的评判所暗含的假设(主要是他对这支业余军队的作战能力的信心)抱有深深的疑虑。在波士顿围城期间,他曾多次表露出自己的这种疑虑。“期待毫无作战经验、缺乏纪律的新兵能够有和老兵一样的表现,”他警告说,“那就是在期待从未发生过也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毫无疑问,爱国主义是(革命)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它不能替代军事纪律和经验。没有人注意到的是,波士顿围城的胜利并不是通过什么重大的战斗得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大陆军还没有经历过什么考验。华盛顿也并不清楚这支军队在纽约面对全力作战的英国军队时能否同样取胜。如果他那时知道了英军打算在纽约怎样进攻他们,他的疑虑将会更重。
有一个潜在的矛盾在这里第一次显露出来,实际上这个矛盾从未得到彻底解决(在华盛顿的观念里,它有着撒旦般的幽灵的样子)。这就是,北美爱国者宣称为之而战的那些价值观与职业军队所要求的纪律文化互不相容。共和制支持者信奉“民意赞同”这一核心原则,而军队则是不容商讨的服从精神和常规化的压迫思想的制度化体现。正是“常备军队”这一观念让大陆会议的大多数成员以及各州议会深感震惊,他们认为这是对共和制原则异常严重的威胁。然而,至少像华盛顿所认识到的那样,只有采用英军模式的职业军队才能赢得战争,而只有赢得战争才能让这些共和制原则维持下去。至少从逻辑上讲,这一困境是无法解决的,它是最戏剧化的“手段-目的”之争。甚至我们可以打个比方说,只要它还被华盛顿神秘的个人光辉所掩盖,它就永远无法得到解决。因为他是北美走向共和制的象征,那么就定义而言,他指挥下的任何军队在特征上都是共和制的。托马斯·杰斐逊本来要宣布一些他自己认为相当重要的、不言自明的真理,但是现在——实际上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是这样——华盛顿就是那马背上不言自明的高大真理,他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他让所有的争论都显得不必要。
在持续九个月的波士顿围城中,华盛顿一次又一次地认识到,由他领导着沿海岸穿越罗得岛和康涅狄格抵达纽约的这支大陆军,既没有在特征上体现出大陆性,也没有任何严格意义上的职业军队的样子。
在第一点上,他的军队中90%以上的人是新英格兰人。考虑到最初在波士顿发生的所有军事行动,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由“这项事业”召集起来的民兵部队几乎全部是来自马萨诸塞、新罕布什尔和康涅狄格的志愿者。更重要的是,如果爱国主义能用温度衡量的话,那么北美殖民地中最狂热的地区就是新英格兰,在那里,对政治的漠不关心在许多乡镇和村庄会被贬斥为叛国行为。如果你公开表明对英国国王的忠诚,那么你将会受到严厉惩罚,人们会在市政广场往你身上浇柏油、撒羽毛,暴徒们将会拆毁并烧掉你的房屋,公众将密切关注你即将到来的死期。正是因为这样,英国内阁才将新英格兰视为叛乱的摇篮。
但是,如果军队是北美的抵抗和爱国主义最清晰有力的表达,那么新英格兰人在其中的霸权性的存在就对中部和南部殖民地的政治忠诚度提出了严肃的质疑。华盛顿行动的思想基础是,他率领着北美人民坚定地要脱离大英帝国的统治,但是大陆会议还没有发表过宣称要达到该目的的政治声明。尽管华盛顿在骑马穿越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新伦敦(New London)和纽黑文(New Haven)时表现得十分自信,但是人们仍然不清楚哈德逊河南面和西面的那些殖民地是否会像新英格兰人那样聚集在“这项事业”的旗帜周围。

在华盛顿身后行进的那支军队或许会被仁慈地叫作“一件有待完成的作品”。它代表着民兵部队的长久残留,这些民兵部队前一个夏天在波士顿周围出现,后来则被陆续编入了现在被人们称为“大陆军”的军事组织之中。实际上,大部分拥有自己的农场和家庭的人,以及那些自耕农,都已经回家耕种,并继续担任所在殖民地的民兵的角色。留下的士兵则代表了社会等级的最低阶层——前契约制佣人,最近来到美洲的爱尔兰移民,失业的工匠、铁匠和木匠——他们留下是因为他们没有地方可去。华盛顿所说的大陆军中的“军人”只是由一群社会的边缘人和不适应者组成的杂牌部队,他们大多数人身上所穿的是猎装而非军人制服,每走十来步就有人啐吐烟叶,并且所有人都对对手心存蔑视,对于自己刚刚在波士顿让英军精锐部队蒙受耻辱这件事显得自信满满,认为他们不久在纽约也一样能够获得胜利。自由奔放、言行粗野、精力旺盛,这群人不会让你想要与之为邻。
在过去九个月里,他们曾将华盛顿逼到愤怒的边缘,他们违抗几乎所有形式的军事纪律,不分时间地点,随心所欲地放下自己的职责,并且嘲弄他们部队里的下级军官。在许多时候,他们选出这些军官,只是将他们当作自己的代表而非上级。“我常常在想,”华盛顿曾经向一个心腹随从坦白道,“要是我没有在这种形势下临危受命,我准会快乐得多,我将扛起我的步枪,参军入伍,或者……隐居于荒村山野之中,求庇于兽皮棚屋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