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364)
在银行催债,我见过一万种悲惨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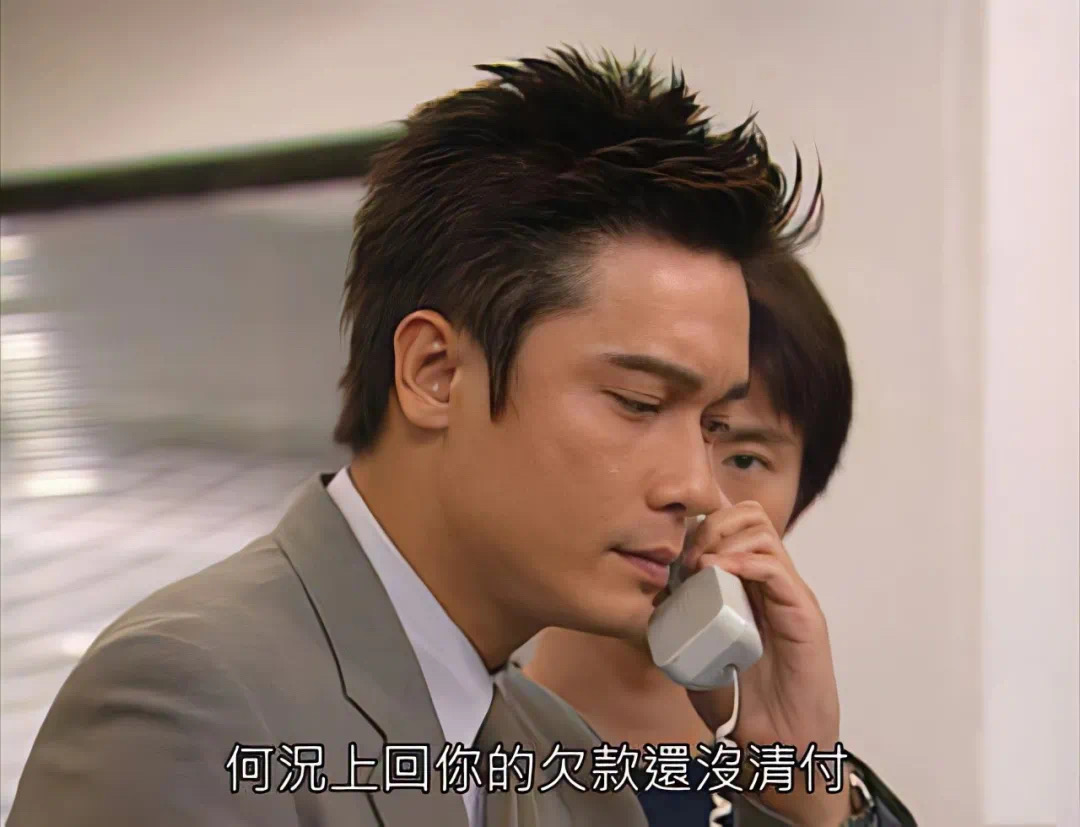
一通电话3分钟,所有电话拼凑起来就有种众生皆苦的感觉。一开始我还会感慨,怎么这个人能这么惨,到后来会发现,5个人里面5个人都这么惨。这份职业打碎了我所有过往的职场想象,把各种人赤裸地塞进我的生活,然后又让他们离开。
文 | 邬宇琛
编辑 | 赵磊
运营 | 绘萤
突然消失的男人和所有的朋友都断了联系,大家知道他生意不好做,但是却不知道他的心结是一大叠撑爆钱包的信用卡。孩子的母亲对着空气发呆,这个月的债要借谁的钱来还,借来的钱又要再借谁的补。路口的小店或者厂子突然关门了,疫情来后,这只是无数惨淡里的冰山一角。
某种意义上,债务是一个人最隐秘的部分,即便是一个看似风光的人,身上也可能背着巨额负债。根据央行发布的《2021年第二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截至2021年二季度末,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818.04亿元。
即便欠债者对债务秘而不宣,但最终瞒不住催收员。催收员的全称是“资产管理专员”,作为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重要职位,负责催缴那些逾期的债务。债务逾期背后是催收员和持卡人的纠缠,打电话的短暂交集中,有时候托出的是一大串争吵和粗言秽语,有时候则是不小心窥见手握信用卡滑入无兜底的的人生。
2020年夏天起,陈辉进入了长辈们青睐的银行做信用卡催收员的工作,缺乏社会经验的他被电话那头荒诞却真实的世界所震撼。疫情仍在持续,行业频繁变动的一年里,面对滑头、欺骗、消极、愤怒,陈辉通过这份职业的一个剖面,对世界有了更深的认识。
以下是他的自述——
这不是一个听故事的工作。
前年夏天临近毕业,我找了几份工作,面试都没过,整个人都很迷茫。毕业之后做什么?我心里没底。这时候我父母的一个朋友推荐了份工作,还是在银行,岗位是“资产管理专员”。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职业,面试之前,我在百度上搜了很多资料,了解到这个岗位简单说就是追债,让逾期不还款的信用卡用户还款。我看到印象最深的描述就是“赚快钱可以,不要企图做这个职业挣一辈子钱,会很压抑”,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哭诉指责,“催收员害得我家破人亡”之类的。
我不想做这个职业,但父母说银行好,何况还有机会再调岗,先去试试看,我就去了。
我还记得面试时面试官问了个问题:这个岗位业绩压力非常大,有没有考虑过去行政岗位?我心里窃喜,说“尊重公司安排”。但面试官马上告诉我,这个岗位需要“坚定”、“强势”的人,我不是他想要的人。
“我们这一行需要的是社会阅历,面对全国这么多客户,追不同人的债要有不同的方法。我举个例子,如果持卡客户是男的,某些南方地区的,一般都有姐姐或者妹妹。这种时候,可以跟他姐姐或者妹妹施压,她们不帮忙还,持卡人的父母也会逼姐妹帮着这个男性持卡人还债,这就是地区的特色。”他说。
我听完非常震惊,如果不做这个职业我都不敢相信还有这种事,有一点不择手段。但我想了想我接触过的那个地方的人,好像确实是这样。
最后我还是被录取了,在入职之前的培训里,类似的催收技巧还有很多,那段时间每天都在听各种各样的通话录音,教我们怎么攻破客户的心理防线让他们还钱,此外就是反复强调:尽量不要同情客户。
那时候我很喜欢听有投诉案例的课,课上会有通话录音,客户各种飙脏话激怒催收员,催收员也受不了就骂回去,听着很好笑,很提精神。但按规定,催收员不能对持卡人恶语相向,只要说粗口骂人,催收员就可能会被投诉,而投诉的代价据说是取消晋升评选的资格。
培训结束后我就正式开始工作了。办公场所是银行大楼,看上去富丽堂皇,我们的部门占了银行几层楼,一层楼坐了一百来号人。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走进去的场景,同事们对着电话说话、嘶吼,特别吵。上一分钟一个同事还警告电话那头的人“你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下一分钟又开始友好交流,“大哥,你早这么说话,我们就把事情解决了”。
和其他工作一样,我们的竞争也很激烈。基本工作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每天打固定的几十通电话,并且要求一定要打通才能作数,打不通就不停地打,所以“回访”在我们这儿是理所当然的,100%永远不够,工作量要超出100%才有优势。我们的业绩每一天都会有排名,而且每个月都会有回款任务,回款多的人,提成才多,只靠打电话赚不了多少钱。
其实刚上班时,我更多的感受是新奇。我有点害怕和客户沟通,每一通电话都像是在开盲盒。催收电话的接通率其实是很低的,打20-30通电话接1通,这是常态,但每次打之前都很忐忑,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完全不知道,也无法预料我将面临什么。

坦白说,我这个人缺乏大的认知,对宏观的就业情况、行业状况、经济情况什么都不关心,我从来没有赚过钱,也不知道钱有多难赚。但这份工作真的让我对这些东西一下子有了概念。
我的这些客户基本都很“惨”,不管是他们自己立了个很惨的人设还是说真的这么惨,但从他们的描述看,就是一塌糊涂。被疫情压垮是大多数逾期客户的共同点,被问到欠钱的原因时,所有客户第一时间都会说“疫情害的”:店开着开着就突然就开不下去了,工作好好的突然没了,紧接着就是源源不断、还不完的债务。
我催过最多的应该是餐饮行业的人,最惨的也是搞餐饮的,实在是太多了。印象里有一个中年客户,他欠了我们2万多,这不算大数目。我打电话去问,他告诉我,自己疫情前是开饭店的,疫情之后没多久后饭店就倒闭了。他的债主包括多个银行,共债很高。因为负债太高,老婆和他离婚了,这期间他父亲腿摔断了,有心脏病和高血压需要住院,弟弟股骨头坏死了需要靠低保生活。他借钱带孩子在外面租房子住,现在找到一份后厨的工作,每个月收入3000-4000元,房租1500元。
这个事情一听就没办法处理,他每个月还是套现去还债的,借了这家还那家。每个月都如此,万一其中一家降额了,其他家就都还不上了。遇上这种情况我只能用很官方的话术告诉他,“我个人非常理解您这个情况,但是欠钱总是要还的”。他都那么惨了,只能和他谈解决方案,但我知道,他可能一两百还能处理,让他处理1000元以上就已经很困难。
这种属于很极端的状况,家里多灾多病,碰上生意破败。我还记得一个类似的饭店老板也是总负债五六十万,饭店倒闭之后跑美团外卖,一个月挣四五千元,这是餐饮生意失败的很正常的案例。

除了餐饮,逾期最多的就是工地上的人,农民工和搞工程的都有。农民工欠的比较少,搞工程的客户欠的却很多,8万-10万都有。最近一个搞工程的客户给某个企业做劳务分包,工人工资和用工材料的钱都是他从银行借的,但是企业到现在还没结尾款,有100多万。要是结款了当然能够轻松还掉我们这边的债务,但这种事情不靠谱,结不结款,什么时候结款,大家都不知道。
逾期的人形形色色,很多人都学历不高,做体力劳动工作,法律意识淡薄。我遇到一个99年的妹妹,她是西南地区的人,初中毕业就没再读书了,看照片特别小,欠的钱不多,只有几千元。但你跟她说起诉,她会理直气壮地告诉我,“就算我上了法院,法官也会酌情考虑”。
刚入行的时候我经常难受,打电话的时候听到对面不经意的一句话心就会猛颤,我清楚他们是欠钱不还的人,在被催收的情况下会很暴躁,但现实里未必是坏人。
有一个客户在广东做服装厂,他在传统制造业最发达的时候来到广东起家,所在的那个村全是服装厂。我第一次打电话过去的时候用常规的话术说明了他的帐单情况,然后告诉他我们会走法律流程,他静静听我说完,然后用一种很低沉的语气告诉我,夏天的时候厂子已经做不下去倒闭了,没有收入之外,他还要给他已经患癌10年的爸爸治病。
“今天早上大夫让我接他回老家休养。”他停顿了下然后又说:“那个大夫让我爸等死。”我也不好说什么,对着“台词本”念了几句挂断了。过了两天我又打了一通电话过去催,问他在哪儿,他说他已经回到老家了,父亲今天去世了。我什么话都说不下去了。我能怎么办?只好再次挂掉电话。
一位客户比那个开服装厂的还消极。那个大叔五十多岁了,没有老婆也没有小孩,开了一家教育培训机构,不久前倒闭了,他在我们这边欠了两三万,还欠了其他银行共债二三十万元,加上房贷,全面逾期了。我问他问题的时候他基本就不搭理我了,知道还不上了所以也不挣扎了,“再坏能坏到哪里去,更狠的话我听其他银行说过了”。
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压力很大,每天都想哭。催收员面对的有滑落的人,也有一些蛮横的人,欠了钱还觉得自己很有道理。我记得有客户跟我说,“你们给我这个钱,那不就是给我用了?用了还要还?”遇到赖皮的真的忍不住想要吵架,但有些人就是没办法还钱了,所以就会反问我:“这个钱我去偷,去抢给你好不好?”
655,我至今记得这个数字。一个很忙的女人欠了655元,40多天一直不还,我打电话过去,她就很急躁地告诉我:“我很忙!我要开会!你别催我了!”还有另外一个人在东北洗浴场的生意失败后,欠了3000多元一直没还,她在父亲开的菜鸟驿站打工,当我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把电话给了她的父亲,她父亲说,“我不认识她”。
以死相逼的人也有很多,在欠债的情况下持卡人很容易说出“这么难,我都想跳楼了”“我现在在开车,我一头撞死好了”之类的话,像口头禅一样,最开始我会很害怕,真出事了怎么办?到现在我也会用一些话尽量去说服,如果是男的,我就跟他说,“先生,生命诚可贵啊!”如果是女的,我会跟她说“女士,你还有孩子,替他想想!”
很多事情都是碎片,不完整,很短暂,一通电话3分钟,所有电话拼凑起来就有种众生皆苦的感觉。一开始我还会感慨,怎么这个人能这么惨,到后来会发现,5个人里面5个人都这么惨,这个人讲了一个自己倒闭、失业、妻离子散的故事,下一个人就会讲一个类似的故事。但故事是没用的,起初我还会听,到后来我会打断他们,“但这不是逾期的理由”。
我察觉到我自己的心态在慢慢转变,每次打完电话都会在电话外摔鼠标或叹口气。谁的生活容易呢?
我入行不算是赶上最好的时候。催收员这一行也有它的转折点。首先是去年11月《个人信息法》施行对这个行业的打击很大。一个持卡人办信用卡会留直属家属的联系方式,过往我们会联系家里人,让家里人帮持卡人想办法。但现在我们已经没办法打电话给第三方了,这无疑让回款变难了。
更重要的还是大环境变差了。一个经历更长的同事告诉我,疫情之前,2019年底到2020年初的时候,回款特别快。大家手里都有些存款,一催客户就还款了,那是催收行业景气的时候,大家都没有预料到后面会这么糟糕。那时催收员一个月也能稳定拿一万多元的工资,但现在大部分人都只能拿五六千元,差的可能只有三四千元。
这里人员流动也很快,当初和我一起进来的员工里有八成都离开了,有人去了别的银行,有人备考公务员。业绩压力太大了,每个月几十万回款的指标,达标的次数很少。由于很难追回款,大家只能不断地加班打电话,希望提高一点概率,才能赚更多的钱。
这个行业已经是夕阳行业了,监管越来越严,而且逐渐能被AI代替,或许以后债务通过诉讼回收会比较多。加上业绩压力大,有合适的机会我就会选择调岗或者换行。毕竟是个职业,同情啊、伤心啊,没必要,大家都是普通人,各有各的难处。只是有时候走在路上我看到一些中年人会想,这个人在电话里说话会像我的客户那样吗?
前段时间催到了一个女客户头上,她告诉我她丈夫入狱了,自己带着孩子,正在努力赚钱还债,话说到一半哽咽了。我只能安慰她说,“希望你乐观一点”,但挂电话前还是加上一句,“努力赚钱把债还上吧”。
如果一定要说这行给我带来了什么,那就是教会我,不要搞什么创业,我要打一辈子工,而且要在大公司或者事业单位。
(陈辉为化名)

▲ 图 / 电视剧《Hush》截图
=========================================================================
============================================================
春节失眠第三天,我选择说给一个淘宝药师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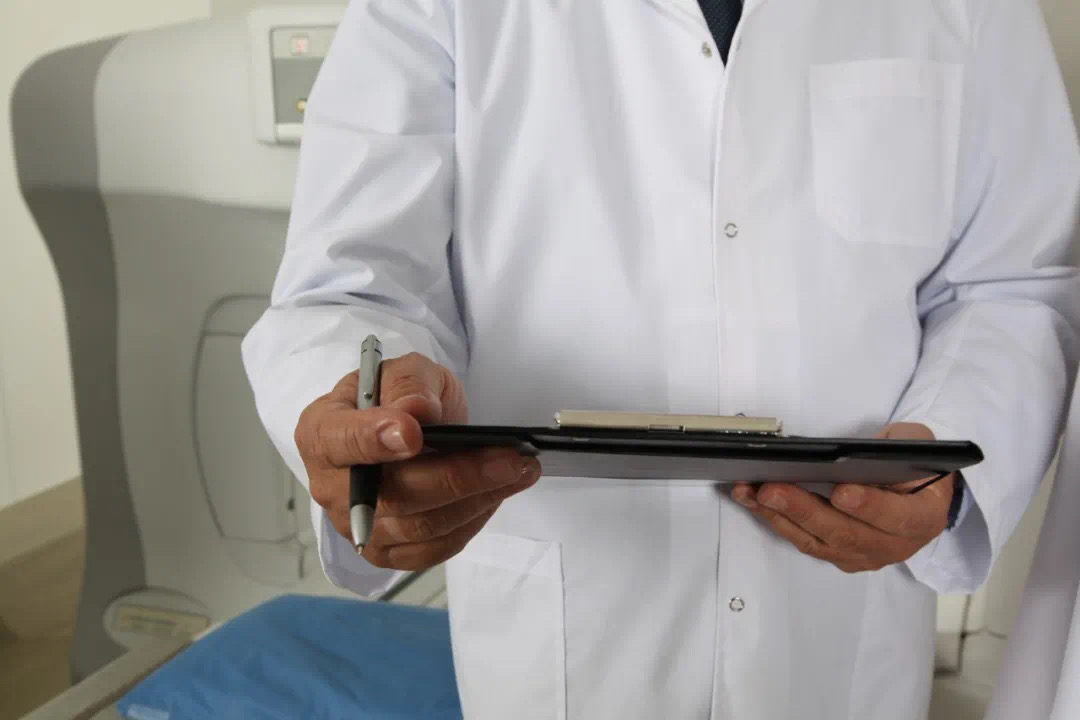
每一个人,
都可以成为别人迷惘时的借力点
万物皆可互联的时代,在网络上寻医问药,成了不少人的一种路径依赖。
网络药师,却是一个不常被关注的群体。有些时候,他们像客服一样,承担着最基础的药品解疑。有些时候,他们又被普通人视为“医生”,为生命保驾护航。
春节期间,总有一些人仍在岗位上维持着社会的运转。线上药师,和警察、医生、环卫工人、公交车司机等一同构成了贺岁光景的底色,将我们的生活兜住。
王敬和李翠哲是两名普通的淘宝药师,入行以来,他们在阿里健康上陪伴无数人迎接新年,用药方抚平病痛。今年春节,他们依旧如每个工作日一样,接待着客户的咨询。
一
救急如救火
春节,是聚会的高峰期,也是线上药师的工作高峰期。
“我从晚上开始就一直拉肚子,是不是吃坏东西了?” 这是值班药师李翠哲今天接待的第5位吃坏肚子的客户。
“今天吃了什么?”、“排便是什么样的?”、”有呕吐症状吗?”例行询问了这些状况后,她判断是因为春节饮食杂乱导致的急性腹泻,向客户推荐了蒙脱石散。
对方道,“那我就直接在淘宝下单了,你发我个链接呗。”
“现在下单,最快也要明天送到了。虽然不是大毛病,但腹泻次数太多会导致脱水。您的情况不好拖的。”
“不好拖”是李翠哲的口头禅。丈夫有时调侃她,别人是“急人之所急”,你是 “比人更急”。不过李翠哲向来觉得,治病如救火,用药如用兵。
据《2021年夜间用药行业研究报告》显示,近九成受访者近一年内有过夜间生病或家人需要用药的经历,而其中61%的人选择了忍耐。在用药这件事上,李翠哲最大的希望就是患者“不忍”、“不拖”。
在得知这位客户住在城区后,李翠哲建议对方直接从外卖平台上下单,以便尽快收到药物。并将如何用药,多久恢复,如何配合调理等细则一一叮嘱。
对方听了很是感动, “你可真是个良心的大夫。”
对李翠哲来说,“大夫”是一个甜蜜的误会。
药师不同于医生,并不负责开方问诊。“同样是白大褂,医生天然更被关注,药师就像是一个背景板。”
李翠哲曾经在线下药店做过15年的“背景板”。不过相比药师,李翠哲认为那时的自己更接近于一个 “销售”,每天的工作围绕着推销药品打转。
16年,偶然看到了阿里健康招聘线上药师,她投递简历,面试录取,不久后从兼职云药师成为了全职。
从线下到线上,李翠哲有了更多“被需要”的实感,也经常被客户叫做 “医生”,虽然她清楚那只是一种口头称呼的惯性。现在她平均每天服务100-120个人,服务半径触达到西藏、新疆等偏远地区的用户。“越是线下医疗资源匮乏的地方,越是需要我们这样的专业药师。”

李翠哲
李翠哲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天生敬业心很重的人,但这五年多里,她生出了一些“杞人忧天”式的责任感。
“以前在线下药店的时候,我加班也不积极,总觉得我在或不在一个样,但现在会担心病人没遇上像我一样能提供专业指导的药师怎么办。”作为本地人,她总是主动担下逢年过节值班的任务。
春节期间,常有急性病的患者找上门来。除了推荐合适的药物,李翠哲还花了不少精力帮客户查找当地方便外送的药店。平台上的药,有时反倒成了第二选择。
“我都没从你家购买,你还给我讲得这么详细,真是太谢谢了。”李翠哲经常接收到此类感谢。
石家庄的王敬是另一名在春节值班的阿里健康执业药师。
除夕夜,儿子发来拜年视频的时候,她正在处理一位上海宝爸的连环消息——孩子屁股起了一大片红斑和水泡,大哭个不停,老婆又堵奶。
同样是妈妈的王敬,对这种第一次为人父母的慌张,很能感同身受。她一步一步指导着这个新手爸爸如何处理红屁股,如何给人类幼崽做物理按摩,媳妇坐月子有哪些注意事项。
渐渐地,对方敞开了心扉,说起家常。王敬得知了他的境况,男人一边照顾媳妇和孩子,一边工作,恰逢家里老人生了病,媳妇又老是跟他吵架,特别焦头烂额,每天都掉一大把头发。“再掉下去,都快被小毛头的发量给赶上了。”
“做父母的难免都有这个阶段,你媳妇可能承受着更难以想象的压力,只要熬过宝宝一岁就会好很多的。”王敬用过来人的经历安慰他。她还开始了 “授人以渔” ,把自己关注的几个育儿账号和APP推荐给了对方。
聊到最后,这位爸爸执意要让王敬留个给联系方式给他。王敬告诉他,“我的工号是119,下次如果有事,可以直接报这个工号。”出于数据安全和用户隐私的考虑,药师并不被允许和客户交换私人联系方式。
追问几次未果后,男人最后留下了一串自己的手机号,希望王敬能来联系他。
王敬很能理解这种“想要紧紧抓住什么”的心情,也很庆幸,自己可以成为别人迷惘时的一个借力点。

王敬
因为专业过硬,态度亲切,王敬经常遇上“回头客”。“119号在吗?”是她和老客户的赛博约定。“被人期盼着,真的是一种很好的体验。”
凌晨1点40分,王敬脱下工作服,裹着一身寒气回到家里,丈夫和孩子已经入睡。但客厅的小灯还亮着,年夜饭被妥帖地放在桌上的保温盒里,边上搁着一副筷子。那是另一方天地对她的期盼。
二
说出来本身,很重要
李翠哲做过统计,每年春节,因为失眠、焦虑而来咨询的比例高于平时。
推开房门,大家扮演着情绪稳定,说吉祥话的成年人。关上房门,生活工作的失意、亲密关系的受挫......挨个在夜晚报到。
山东临沂的庄涵就是其中之一。春节回家第三天,也是她难以合眼的第三个夜晚。她感觉身体里仿佛内置了一个时钟,嘀嗒嘀嗒地作响,大脑清醒无比。天色一点点亮起来,白天和父母的争吵,学生时代老友的聚会,都在脑中自行生成蒙太奇闪回。
“有没有失眠的特效药?我真的很想好好睡一觉”。抱着“反正也睡不着”的心态,庄涵摸到手机,点开淘宝,向随机分配到的药师李翠哲发出询问。
李翠哲大概能猜出庄涵的潜台词——她想要买安眠药。
这类处方药,并不在淘宝上售卖。李翠哲推荐了一款褪黑素给她,顺便介绍了用药细则,要避免饮酒、喝茶、喝咖啡和含咖啡因的物质。
可能是一时兴起,李翠哲加了一句,“不要跟《开端》里的男主角一样,用白酒配褪黑素。”
“哈,你也在看《开端》呀!”那头的庄涵来了劲。
或许是这一点点“遥远的相似性”,在这个难熬的夜晚,激起了庄涵的倾诉欲。
她跟李翠哲分享起了自己的故事。毕业四年,在北京做广告行业,公司里常年放着折叠床和牙杯,以备通宵之需。在体制内呆了一辈子的父母并不能理解她的工作,过年照例又是一次劝她回家考公的动员大会。
庄涵不是没想过辞职回家,朝九晚五。年前赶项目,一位同事突然昏倒,进了ICU,她心有戚戚。
但在老家,好像哪里都是一眼望到头的人生。而在北京,落户买房,又像是一个奢侈的白日梦。
躺在床上,她感觉自己在被两股力量拉扯,“但好像两边都没有我的归属。”
“你已经很优秀了,不靠爸妈的支持,自己在大城市立足,等你再大一点,你会发现,长辈的认可是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自己认可自己。”
“不过经常加班这点,确实要注意。有房有钱是很好,但无病无灾不是更重要嘛。老家也好,北京也好,说到底是两个选择,但只有身体健康才能去做选择。”
李翠哲的开导,总是用一些最朴实的话语,讲最普世的道理。
“姐你可真温柔呀”,庄涵回复道。
在李翠哲经手的近几千例失眠咨询中,除了少部分需要服药的重度患者,更多的人是心结难解。
虽然没有专业的心理咨询背景,但李翠哲觉得自己可以胜任一个树洞,她愿意倾听这些故事。
她相信,虽然很多时候“说出来也没有用”,但是“说出来”本身,很重要。
李翠哲遇到过一年体重猛增60斤的996社会人,被班级同学边缘化不愿再去上学的少年,女儿突然查出胰腺癌的中年父亲。
在药石难解的人生课题前,李翠哲试着去成为一剂名为“陪伴”的强心针。
“网络上茫茫多人,但我恰好收到了TA的消息,可能是冥冥之中要我做点什么吧。”
正月初四,庄涵又一次找到了李翠哲,“我今天早上去公园散了步,还自制了一个年宵花福桶,虽然还是没睡多久,但心情一下子好多啦,谢谢你那天晚上陪我聊了那么久。”还附了一张新出炉的年宵花。
李翠哲长按图片,存进了相册。

庄涵发来的年宵花福桶
她知道,自己的宽慰,并不足以拯救这些身处难关的人们,但或许能给以他们几分向前走的勇气。
在名为“生活”的旷野奔跑中,总有人因为一个突然的土坡而跌倒,也总有人因为一句平凡的鼓励,而打起精神,漂亮活着。
三
隐秘的伤痛
“万一真检查出来我有什么绝症呢?”已经结束10多分钟的对话框里,突然又弹出了一条新信息。
“没有这种万一。” 王敬回道。
半个小时前,王敬接到了一个阴道出血的病例。“我没来例假,但一直在出血是怎么回事?”
王敬询问了对方的用药史,了解到女生有在服用一款激素药。这款药品需要根据个人的激素水平来决定用量,但女生全靠网上的资料,自行摸索用药。
王敬判断她是“撤退性出血”,由于服用激素药物过量所致。
“不用进行治疗,停药就行,一般四天左右会好转。”王敬也建议她,最好还是要去医院做个全面检查。
“可是我好害怕去医院,春节在老家也不方便,我们这儿特小,怕遇到熟人。”
对药师来说,“害怕去医院”是太过普遍的情况。王敬试着用浅显的语言和女生解释撤退性出血,一点点打消她的顾虑,直到女孩还开起了玩笑“如果检查出来没问题,我就给你寄一面锦旗。”
王敬觉得,某种意义上,药师就像是病人和医院之间的一个缓冲带。“很多客户的恐惧,是因为信息的不对称”。王敬总是尽可能地告诉患者一些病理药理,让他们知其然,也知其所然,从而消除一些莫须有的想象,正视去医院这件事。
而身处妇科的缘故,王敬遇到的患者,也会更多一层惧意。
长久以来,在我们的社会认知中,妇科疾病是和“性”挂钩的,带着浓浓的审视意味。反射到个体身上,是众多女性的身体羞耻。从藏在衣袖里的卫生巾,到面对妇科病时“先忍忍再说”的直觉反应。

电影《月事革命》
王敬见过太多受困于“羞耻感”的女性。
有年轻女生染上妇科病,不敢拍照,发来一段长长的文字描述。也有中年女性忍受着生理不适多年,直到“实在受不住”才发来求助,却已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
每当这种时候,王敬都特别难受。
在被社会定义为“私密”的话题上,“很多女生,不敢去和家里人说,不敢和医生说,不敢去和朋友说,只敢跟我们说。”
这种“敢”可能只是出于“对方看不见我”的原始安全感,但王敬想回馈给对方更多的安全感。
“很多女孩子喜欢叫我们小姐姐,”既然作为一个“姐姐”,王敬便想承担起一些关于“教育”的责任,去引导她们建立科学的认知,爱护自己,及时就医。
王敬希望有一天,所有女性,都可以告别身体羞耻,坦然地面对自己的病症。
这注定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但王敬希望自己每一句对女性客户的劝慰和支持,都可以让这条路再往前铺开一厘米。

陶勇医生在《目光》中写道:希望是唯一廉价而又有效的可以对抗人间疾苦的方法,它是俘虏的自由,病人的健康,乞丐的财富,极寒中的暖阳。我坚持医学,不仅源于热爱,更是想给更多的病人希望 ,让那些对我心怀期待的人看到——有人在为Ta们而努力。
淘宝上这些“不打烊”的药师们,就像是一张张具像化的敬业福,带给人一份坚实和希望。
急人之所急,尽力所能及,或许就是平凡人在平凡岗位的英雄主义。
网络药师身上的簇簇微光,点亮着每个普通人对健康的期许。
作者 郭芙蓉 | 内容编辑 程渔亮 | 微信编辑 冻杨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