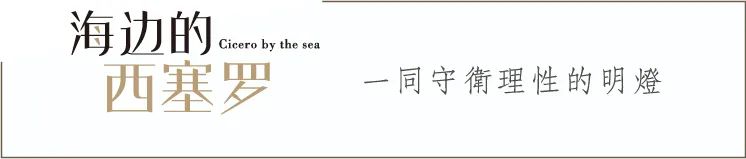
最近文章写多了,总有朋友调侃,说:小西,你天天说今天休更,结果哪天也没休。
其实我也是无意的,你就比方过年这几天,好不容易回了趟家,想着怎么着也得休更几天,陪家人娱乐娱乐。
第二天年初一我又陪他们看了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打越南的那场比赛……
…… ……
…… 原来,我一直以为,说相声应该是搞笑的,踢球应该是不搞笑的。
但今年的春节颠覆了我的认知,是我浅薄了,原来,相声也可以如此不搞笑,足球也可以如此搞笑。
原来,我一直以为,说相声应该是搞笑的,踢球应该是不搞笑的。
但今年的春节颠覆了我的认知,是我浅薄了,原来,相声也可以如此不搞笑,足球也可以如此搞笑。
前天,姜昆的节目播完之后,有人说,如果这个节目能逗乐一个人,那一定是郭德纲——他以前暗讽姜昆说相声的“慷慨激昂,催人尿下”,本来是损人,没想到居然成了现实。
估计有不少观众都把他那个节目当成了“尿点”,上完厕所后看这节目还没完,就掏出手机回复亲友、同事拜年短信,即保障了群众的身体健康,又促进了社会关系的融洽。姜昆老师功莫大焉。
那按照这个思路来推论,昨天,如果说有人看完中国队1:3输给越南,也给一部分人传递了正能量,比如缅甸球迷。因为范志毅老师早几年就继承球王贝利的衣钵做出神预言:
按照凯尔特故事的套路,一个预言如果要实现,那多半会实现三次,估计缅甸人民现在在等着中国队上门,给他们国家的足球事业打上一针强心剂。
让我们为这些在大年里重新定义相声与足球的人们,送上一点理解与掌声,并提一点合理化建议,希望双方彼此换换行当:
姜昆老师可以去踢足球,多“教育”一下国足,传递正能量;
插科打诨的话不多说了,我想重点谈谈到底为啥这样:为什么主流相声不好笑了,中国足球却越来越搞笑了。
作为一个小学二年级就挂靴的人,我绝对我其实没有资格谈太多。但我又认为我的足球生涯过早夭折的责任也不全在我。我的小学今天想来其实也蛮奇怪的——学校明明有一个很大的操场,两头还装模来做样的立了俩球门,但老师却反复警告过我们:不允许带足球到学校来,活动课、体育课上组织球赛更是严重的违纪行为。带球到学校的组织者要被“请家长”。
这个规矩没有被明文写到校规里,但各班班主任都会在班会上反复申明,堪称小学版的《第22条军规》。
它怎么来的没人知道,直到我离开那学校很久以后,才隐约听说一点传说:
原来那俩球门当中有一个正对着校长办公室的窗户,本来也挺远的。但在某个遥远的、学校还让踢足球的时代的某一天、某位天赋异禀的同学起脚远射,较劲儿大了一点,居然踢出了一记青春mini版的世界波,正砸中校长办公室的窗户……
不,和你想的不一样。窗户没碎,校长也没生气。就是把几个肇事者叫过来说了两句,不置可否,只是临了随口又一问“你们哪个班的?”
但就这句话,就把该班的班主任老师给吓怕了,开了个班会,此后严禁该班男生再踢足球:活动课,你们可以干点别的么!跟女生一样,丢沙包,跳皮绳,多好,还安全。
这个规矩后来陆续传染给了其他各班、各年级。从那以后,我们学校的球场就彻底摆设化了。
时间过去这么多年了,我觉得我也能理解我的老师们,她们都是兢兢业业的一线教育工作者,领着并不算多丰厚的工资,管着一帮熊孩子,既要对家长负责,把孩子管好,又要对校长负责,年末评个先进,多发点奖金什么的。
而在那个体系内,想评先进,最重要的要求就是“不能出乱子”,在这种视角下,足球这种激烈的身体对抗项目,天生就是乱源所在,把校长窗户踢碎了,可能还是小事,万一要是把哪个孩子踢坏了踢伤了——当时城市的独生子女政策下,这些孩子可都是家里的独苗,家长要是找上门来,学校可就没有安生日子过了。
这样的事情其实在我人生中还真就发生过;我的高中设施条件原本更好,操场中央居然原本是一片足球草坪。可是就在我升学入校的那一年,学校紧急把草坪铲了,浇上水泥,改成了篮球场。
为啥呢?原来那一年暑假有学生在草坪上踢球,一个不小心,足球打到了一个学生眼睛上,送到医院一查,视网膜脱落了,孩子一只眼瞎了。
学校吃一堑长一智,赶紧把草坪给铲了,之前一直拿来标榜的“足球传统”也不敢要了。
上大学后,我上经济学课,发现这其实是个再简单不过的博弈论问题:
对于校方而言,他们可以选择鼓励学生踢球或者禁止学生踢球,可是鼓励学生踢球,这对老师和校长们其实没有任何好处。因为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就算学生里真能出一个梅西或者C罗,那是十几年以后的事儿,现任校长甚至教委主任都估计早就调走了,给学校长了脸也跟他们没关系。
但与之相反的,如果学生因为踢球出了差池,麻烦马上就会找上门,老师的工资,学校的声誉,领导的仕途,都会受极大地影响。
收益全无,而风险极高,换你是校长,掌握了在学校内说一不二的权力,你怎么选?
当然是教育孩子们都别踢球了,有时间还不赶紧多做两套《五年高考三年模拟》,考个好大学,学生有前途,家长能放心,老师得奖金,校长有面子,四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我一直觉得有人一输球就抱怨“中国十四亿人,还挑不出十一个踢足球的?”这话很不负责任。在足球这事儿上,我们真有十四亿人么?至少我们这一代,多少足球少年在小学时候就被老师的说服教育和邻桌的小报告下,早早挂靴了。
那会儿,踢足球跟课间追逐打闹、揪女孩辫子、丢石子砸老师玻璃一样是违纪行为,要扣小红花的。
我们大多数学校的文化氛围,就是教育孩子别添乱,别惹事儿,严守校规校纪,让胸前的红领巾更鲜艳一点。
你可以想一下,如果让乌姆里奇当霍格沃茨的校长,我觉得英格兰魁地奇球队一定能打出国足的风采。
很难说,听说前几年在上级的命令下,一些城市和学校开始搞起了“足球试点”,让孩子加强足球培训也纳入了校长和老师们的KPI了,可是这种手段真的会有效吗?
网上传过这样一张图:《一图看懂中国足球为啥搞不好》。
不,你别觉得学校把足球搞成了“足球操”很奇葩,用“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去考虑,这是校方最合理的选择——是的,开展“足球培训”是他们接到的上级的指示,可是“别出事儿”依然也是他们对学校管理的刚性要求啊!
既然踢足球担心出事儿,“足球培训”又不能不搞,那怎么办呢?搞个“足球操”么!你不能说它不算足球培训吧,孩子,户外活动,足球,啥都有,完全足够拿来交差了,还能保证花费最低管理成本的安全、不出事故。
唯一的问题,是这么“练”足球,对我国足球事业的发展,似乎是屁用都没有。
其实你仔细想一下,类似“足球操”这种求稳而应付差事的劳什子,在我们身边还有很多——比如,前天晚上姜昆老师讲的那个相声,严格说就是相声界的“足球操”。
这个相声的其他的问题,这两天网上吐槽的人太多,我就不说了。
单说一点,这个相声的定名。姜昆老师虽然总说他要讲“新相声”,但从这个相声的框架结构来说,看得出他走还是传统相声《学聋哑》《学叫卖》《学小曲》《学方言》那种“学xx”那个套路。
那么按照传统定名思路,这个相声显然应该叫《学方言》或者《学粤语》。
可是姜昆老师偏偏不这么起名,他管这个相声叫——《欢乐方言》。虽然全程听下来,这相声一点都没让人觉得欢乐。
但这个改名是很精明的。因为传统的《学xx》,这个“学”字就是有一种淡淡的嘲讽在里面,好似阿Q回了未庄,跟王胡等人学城里人管板凳叫条凳,煎鱼里放葱丝。老相声的《学xx》,其实用的是老北京、老天津们那种淡淡的地域优越感,把包袱抖响。
姜昆老师其实是明白人,他知道这其中的嘲讽意味有“地域歧视”之嫌,所以他果断把名字给改了。
当然,虽然名字改了,说粤语的人听了这种相声还是会觉得受了冒犯。有广东朋友那天就直接私信我,说“小西,我们广东人压根不是那样说话的!”
这当然是对的,如果这个相声的本意就是为了不带偏见的介绍方言,为什么不找一个正宗广东人,直接上台去介绍呢?中国这么大,能讲流利普通话,又把这事儿深入浅出说明白的广东人,我相信一定是有的。
只能说,“学xx”这个题材,本来就是为了揶揄而生的,任姜老师自带一身绿坝娘般的“净化”神功,也改不了其根性。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佩服姜昆老师的这个能耐。他敏锐的把握了“晚会相声”最需要把握的的哪个点——别惹麻烦。
现在有人说,姜昆这个相声,其实2008年的时候就在曲苑杂坛说过了,2019年,加拿大人大山还改编又说了一遍。
在相声界,冷饭热炒本来倒也没啥,但如果你真去找来之前两个版本看,会发现2022年这一版中,姜昆把这个相声里所有暗含嘲讽、揶揄的小段落,都挑走了,挑的都像国宴厨师给外宾挑鱼刺一样仔细。这导致这个相声味道全无。
是的,晚会相声和正经相声最大的不同,就是其实你不用在乎包袱响不响——那个现场效果的是可以请观众配合出来的。
可是你若为了抖包袱讽刺了张、揶揄了李,得罪了王二麻子,揭批了某种丑恶现象。那造成的麻烦可能是不可控的。
所以在一个好笑但得罪人的相声和一个不好笑但安全的相声之间,导演一定会选择后者——就像中小学的校长们,不允许孩子踢足球,却让他们去跳足球操一样。
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足球与相声,这俩事儿其实是很相似的。他们本质上都是野性、自由、但也是容易惹麻烦。
在现代足球的发源地英国,足球最早就是一帮荷尔蒙过剩、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轻人,在狭窄的中世纪街巷里追着皮球踢起来(听说现在拉美、非洲还是这么踢),两帮人打着打着踢起来、或者踢着踢着打起来的情况都很常见。
从12世纪到16世纪,光英格兰国王就先后四次发布过“足球禁令”,指责足球是“乱源”,有伤风化、毁坏公物,严厉禁止伦敦市民再踢。
但后来英国王权衰落,老百姓越来越不把“王法”当盘菜了,足球这才发展起来。
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足球在近代英国的兴盛,其实是国家“城市治理”失败的一个产物。如果英王或者伦敦市长有我们小学班主任对我们的那种管束力,这个运动是压根不会兴起。
而这个出身,决定了足球的那种独特的气质,足球比赛的规则特别类似英国的习惯法,它是后天的、累加的、法无禁止即许可的。
一个天才的球员可以在球场上、在既有规则允许范围内任意的发挥自己想象力——就俩球门,双方十一个人,你凭本事踢吧,踢进去就算你赢。不问你到底是绅士还是流氓。
甚至正经赢不了的美国人,还一度抱起足球往对方球门里冲,发明了他们的“美式足球”(橄榄球)。因为当时的足球规则,好像确实没规定有人可以这样打破规矩。
从某种意义上说,橄榄球其实就是对足球的另一种理解——把人体体能自由的发挥到极致就行,你(当时)没说非得用脚踢啊。
所以,若说足球比赛最排斥哪种思维,那一定是“管束思维”,管理者怕出乱子,干脆把球场铲掉;孩子们踢球时害怕砸了张家的窗户,撞坏了李家的公子;选进国家队以后,球员们想的还是:这场球是热身赛,对付对付得了;那场球领导很重视,“打平即可出线”……
这规矩就太多,第一个国家如果要带着这么多条条框框去踢足球,那铁定是踢不好的——因为从文化气质上说,以“不惹事儿”为最高信条的咱,与自由奔放的它,本来就是“八字不合”的。
相声其实也是一样的,它也是一种野性、自由的运动——只不过是口腔运动。
相声诞生于清末,那段日子兵荒马乱,对穷苦人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可能就是官府的管束不那么严厉了。所以他们走街头卖艺,靠拿自己或别人开开涮逗大家乐一乐。
“台上无大小,台下立规矩”,几千年来只要你不落草为寇就无时无刻不讲规矩、明尊卑、分大小的中国人,总算在相声这点方寸天地里获得一时“没大没小”的解脱与释放。所以相声才能在半个多世纪里迅速受到民众的喜爱。
可是,如果你硬要在相声里也弄些条条框框,这也不敢讲、那也不能说……那这个相声也就不用听了。
就像若想强身健体,直接做体操、跑步不行吗?干嘛非踢足球呢?
自由是人的天性,如果没有对自由奔跑、追逐的肯定与热爱,那么踢足球就成了一种容易砸人窗户的劳什子运动。
如果没有对自由嘲讽、戏谑的肯定与热爱,那么说相声也就成了一种容易祸从口出的废话文艺。
所以,这其实无非是个选择问题,你到底是要在绿茵场和戏台上,少一点规则的管束,挥洒野性与自由的热情?还是只要在这这里也追寻极致的安全、不惹事?
如果我们的选择是后者,那我觉得,我们也不必再琢磨强扭足球和相声的颓势,因为它们的价值观与我们就是相互抵触的:
何况这说白了就是两个文体活动而已么,就像“工业党”说的“足球兴盛与否,与中国国力崛起相比不值一提”。
也像郭德纲说的:“那能咋办呢?元杂剧不就没了吗?没了就没了呗。”
只不过,足球和相声,之所以受人喜爱,是他们是响应了人们心底的那种欲望与冲动——自由奔跑,追逐的欲望,让我们想踢球;自由嘲讽、解构的冲动,让我们想听相声。
少了这两种东西的陪伴,我们的生活会不会因为少了点什么,而感到一丝丝不快呢?会不会让我们的族群,更缺少了某种幸福生活所必须的气质呢?
这,可能就是选择的代价吧——每种极致的选择,总会有极致的代价。

==========================================================
去年12月,国家对《妇女权益保障法》做了第三次修订。增加了当下热议的话题,如性骚扰、家务补偿。当时,网上吵成一片。很多男人说,不是男女平等吗,平等就不要再额外有保护女性的“法律”了。大家一视同仁。
这个社会,真的男女平等吗?在精英阶层或许是,但在底层肯定不是。
以我眼见的生活和阅历,看到的是,即使是社会最底层的男人,他尚有机会和能力,去盘剥或奴役一个比他更弱的女人。而这个加害的过程,整个社会经常不自知的,为他助力,成全他的作恶。
1991年,初中毕业的曹小青,和父母赌气,独自乘火车去找姐姐。火车站没出,就被人贩子下了迷药,拐卖到内蒙徐家窑村。从此,这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就成了村里老光棍泄欲和繁衍的工具。两年后,曹小青的家人,辗转找到内蒙古。此时,曹小青已经身怀六甲。他们没有带走曹小青。而是买了一点生活用品做嫁妆,然后就走了。
一年后,生完孩子的曹小青再次被转卖。从1991到2008年,17年转卖4道,被数不清的男人强暴、共妻、殴打、虐待。从一个伶俐的小姑娘,到一个丧失语言和自理能力的疯女人。2008年,记者和公安找到曹小青的时候,她衣不蔽体被囚禁于一个破窑洞。墙面上被她写满了字,记者用四川话问候她,她没反应。
送到医院没几天,这个疯女人开口的第一句话是:“怎么不早来一天呢?”
徐州丰县,一个来历不明的“疯女人”,囚于铁链,暴产八子。
最大的儿子23岁,最小的1岁半。从十三四岁,一直生到现在。
这个女人是男人的父亲路边“捡来”的。1998年6月捡来,8月,就被带去民政局登记结婚了。男人还为她取了个新名字:杨某侠。整个经过,没人报警,没人疑义,没人觉得这不合法理。大家习以为常。
1986-1989年,徐州六个县有48100名被拐来的妇女,其中最小的才13岁。有个叫牛楼村的,全村已婚青年妇女中,有2/3是被拐卖来的。也就是说,村里男人娶老婆,基本靠从人贩子手里买。在这样一个村子里,逃是逃不走的。即使家属和公安寻来了,大概率也没法当场带人走。这是一种悠久的传统,有坚硬的民风,这里的人,他们是穷凶极恶的,自成体系的。
不要以为这是久远的“旧事”。你们可以用“农村 捡媳妇”、“光棍 女人 神志不清”等关键词,去搜这十年的社会新闻。出来的结果是这样的:农村的男光棍们,遍地在“捡”精神失常的女性。甚至还有70岁老光棍“捡”十几岁少女,还生下好几个孩子的。
2021年10月14日,有个湖南人在湖南郴州日报第四版登了一则公告,说他1989年6月,在东莞捡到一个神智不清的女人,遂将其带回湖南老家。公告后90天,若没人来认领,这女人就落户他家,是他的人了。
从底层的个体,到乡间的风俗,甚至到基层政府组织、媒体,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从上至下,没有人觉得,这是犯罪。
杨某侠的事情在网上发酵,作为基层政府的丰县政府,连续发布的两份官方公告。第一份只说,不是拐卖。第二份说,人是捡来的。
路上的人,是可以随便“捡”回家养的吗?带未成年且患有精神疾病的女性,去领结婚证,这是犯法的呀。
为什么他们都“捡到”了?这里有多少女人是“虐待致疯”而后被转卖,有多少是因精神疾病被亲属卖掉或遗弃,又有多少是从精神病院秘密流入社会?
知道吗?在杨某侠被舆论关注前,她居住的那间破屋,已是DOU音很多网红博主的打卡地。这些人跑去拍她、拍董某民,那时宣传的基调是董某民如何“父爱如山”,含辛茹苦养育8个孩子,当地政府是如何精准扶贫,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这些人觉得,一个老光棍用一条铁链拴住一个来历不明的疯女人,让她生下八个孩子,是一种社会正能量,应该弘扬。
后续这件事发酵到了微博,舆论才从“父爱如山”转为人间悲剧。
可即便如此。在事件被广泛关注和谴责后,现在DOU音最火的视频,是采访董某民连续生七胎儿子的秘诀。而董某民,真的在侃侃而谈。
在DOU音,还有个很出名的视频,一个傻X网红博主问杨某侠:那你咋不走呢?
这个脖子拴着铁链的女人说:这个世界不要俺了,不要了。
一个女人,八个孩子,24年,今天终于发现违法了,连夜成立的派出所吗?
买一只鹦鹉判5年,买一只大熊猫是10年以上。但买一个妇女,最多被判三年!一个女人的价值,不如一只鹦鹉。
你有妻子、女儿、姐妹。关注弱势群体,就是关注你自己。有法不依,没有反思,没有系统立法的改变,没有后续的严厉追责,下一个不被保护的人,可能就是你。
最后想说,无论是扶贫,还是新农村建设,比经济上脱贫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祛愚昧祛落后啊。
看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看它如何对待女人和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