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329)
房企爆雷,那些收不到房子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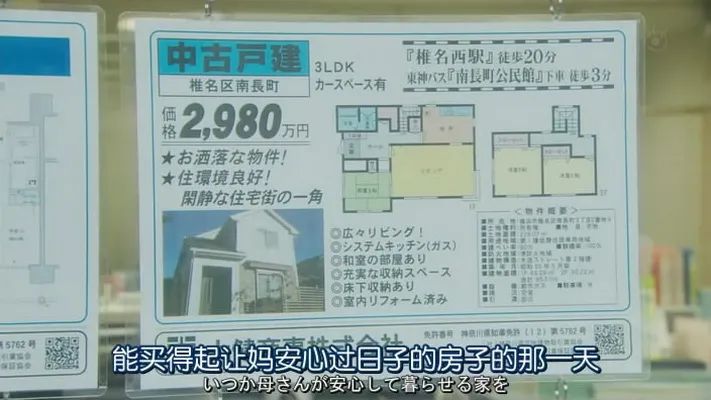
这里是每日人物专栏“千万间”。
过去一年,房地产行业经历动荡、调整,一些巨头房企也陷入泥潭。我们关注过房企爆雷、员工被裁,记录下行业从烈火烹油到冷冻萧瑟的过程。回过头来看看,变动之下,最脆弱、最扛不住损失的还是那些普通的买房者。
文 | 高越
编辑 | 楚明
运营 | 月弥
售楼大厅内,两个人背朝镜头站立,衣服上印着“烂尾佳兆业”“我要收房”等字样。更多的人聚集在电梯门口,待目标人物出现后一拥而上,围个水泄不通。
这些人是广州佳兆业的购房业主,他们5年前在此买房,但收房之日却被一推再推,验收期限早已过去,工地却连主体都未建完。这些年轻业主的共同心声是:我只想有个家,为什么这么难?
有人在社交平台上提问:现在买新房最大的风险是什么?一个热赞回答是,买到烂尾房。如今,对于购房者来说,买房逻辑已然发生变化,升值多少、地段如何被延后考量,最先关心的是能不能按时交房。
去年以来,房地产行业有些动荡。泰禾、华夏幸福、佳兆业等百强房企爆雷,就连昔日地产冠军恒大集团这艘巨轮也岌岌可危。
大房企陷入泥潭的背后,那些普通人买的房子还好吗?毕竟,对于大多人来说,房子是一生当中买过的最贵的东西,也是生活里最大的希冀之一。
1
工地上的一粒灰,吹落在普通家庭身上,就成了压在肩膀上的一座山。
宋世杰一年来几乎没有睡过安稳觉。他原本一直期待2020年最后一天的到来,因为按照开发商承诺,这是收房的日子。
停工的风声突然传来,刚开始他不相信,可没几天的功夫,工地变得空无一人。眼看房子出现问题,宋世杰踏上维权之路。他一边查资料、关注新闻,一边联合其他业主,找律师帮助。但人多事杂、力量有限,时间过了1年多,房子仍然立在坑里,并无进展。
为了房子的事,宋世杰和妻子没少吵架。他今年35岁,毕业后一直从事出版工作,北漂十多年,两年前与妻子终于决定在北京落地。选择买什么房子,两人曾有过分歧:妻子想买二手房,买完就能入住。但宋世杰对家仍充满浪漫的幻想,“在大城市买房,一辈子就这一次”,他想买新房。
宋世说服妻子,他们将新房、交通便利、五环之内作为挑选房源的三大标准。
挑了几套,宋世杰和妻子都不是十分满意,直到他们终于被带到了现在这套房子面前。在销售口中,这套房子机不可失。当时工地只打了地基,是在预阶段售的期房。他们走了“内部认购”,每平米7.5万元。
对交付时间,宋世杰有过犹疑,但销售拍着胸脯保证“绝对没问题”。
宋世杰咬咬牙,一鼓作气选了一个120平米的新房,首付50%,整整450万元。
为了支持儿女在北京安家,一套房子掏空了3个家庭的积蓄,双方父母贡献攒了一辈子的钱,宋世杰和妻子拿出10年的全部存款。
房产,是无数人一生中购买的最大宗消费商品,是为之奋斗一辈子的动力来源与寄托。为了做出最优选,他们小心翼翼地挑到房企巨人,但致使他们“跌落摔伤”的不确定因素,有时恰恰就是“巨人”本身。
2019年,王雨竹跟男友决定从上海回到西安老家,买婚房准备结婚。她选了租房小区附近的一个楼盘下了定金,在她眼中自己做了充足的准备,不但事先在网上查询确认该房企资金流充足,而且上下班还能经常路过工地,随时监督进展。
购买时,一期已经交付,买的是二期的房子,90平米的小三居,首付交了45万。五证齐全、备案摇号、资金监管,一套流程走得顺风顺水。在王雨竹看来,这些都是按时交房的保障,可以稳稳放心。
付款的那一刻,王雨竹跟男友产生了“我们终于有家了”的感觉,开始提前规划起新房的装修,每次路过家具店都会进去逛一下,添置的一件件小玩意渐渐堆满了出租屋。
王雨竹更新着楼盘的进度,修到第几层、准备封顶了……如果跟朋友一起路过,她还会把位置指给朋友看,“最高的那层楼就是我们的”,“距离中心商圈只需要10分钟”。
但是她没想到的是,封顶竟然就是进度条的终点了。
后来这家房企被曝资金链断裂,今年初的3个月一直停工,后来断断续续开工,但每次王雨竹都只能看到十几个工人。直到7月份,工地二次烂尾,至今再也没有复开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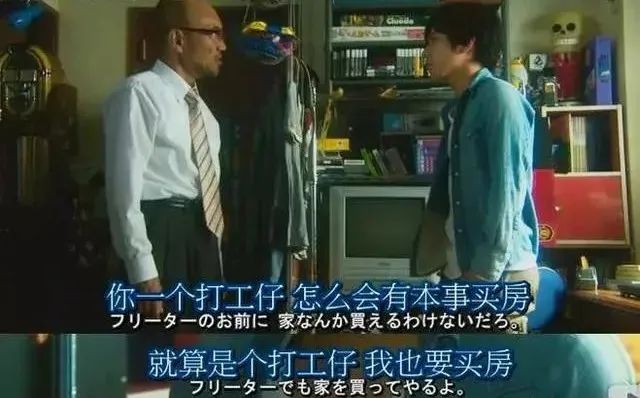
▲ 图 /《打工仔的梦想房》截图
2
买新房,就像是“抽盲盒”,抽好、抽坏全凭运气。在陈燃看来,自己的运气“臭到家了”。
3年前,步入30岁的陈燃选择在郑州安家。她选定了一个小两居的公寓,户型方方正正,一梯两户。运气臭在于,房屋中途有过两次断工,拖延一年才交上房。同一期中一共有五六栋高层,之前几栋成功交付,唯独她这一栋“卡在了正中间”。
为了等房,陈燃多交了一年房租。面对新毛坯房,她早已丧失好好装修一番的兴趣,只简单安了门窗、刷了油漆,囫囵收拾了一番就搬了进去。
有房总比烂尾强,陈燃曾如此安慰自己。但直到住进去,陈燃才发现自己有些天真。这种几度停工、开工的楼盘在质量上早已打折扣,毛病逐渐显露。
曾经说好的绿化面积、水池喷泉没了踪影,连基本的车位都没有兑现。小区里没有安快递柜,陈燃每次只能将快递寄到公司,刚搬家的时候,天天捧着大箱子坐地铁。
不仅如此,陈燃还要应对源源不断的新状况。水电常常停供,电梯也时时罢工。一看到楼栋群里又传来停水或停电的消息,陈燃就会自动加班。先在公司附近搞定晚餐,晚上再用留在工位上的日用品卸妆、洗漱。到后来,陈燃甚至养成了储存生活用水的习惯。
电梯出故障是常态,休息日的时候陈燃宁可宅家一天不出门。最不方便的要属工作日的早晨,为了上班打卡,陈燃不得不走楼梯下14楼。楼梯间没有扶手,台阶既陡又窄,每次走过一半就会开始腿软,不得不脱下高跟鞋,扶着墙才能慢慢走。但上楼比下楼更难,有过几次晚上爬楼梯的经历后,陈燃觉得自己可以不再报健身房了。
11月中旬之后,郑州开始供暖,但陈燃家却迟迟没有跟上大部队的节奏。她自己放过两次水,但暖气摸起来还是温的,没有一点烫手的感觉。她向小区物业反映,但一直没有得到任何有效回复。在朋友感叹室内温暖的时候,陈燃只能裹紧自己的珊瑚绒睡衣。
甚至后来,客厅天花板的角落还出现渗水,一大片墙面都受到波及。陈燃怀疑,是楼上住户的暖气管漏水,渗到了楼下。
陈燃不愿意邀请朋友们到家里做客,因为这和她畅想的“小窝”截然不同。
有许多人面对着比陈燃更糟糕的情况。他们无力承担房租,也无家可归,只能选择搬进烂尾房。
这些烂尾房曾登上热搜。但这不是一段段故事,而是购房者真实承受的打击与困难。那里没有高楼绿荫,只有一片废墟和被施工队遗弃的水泥搅拌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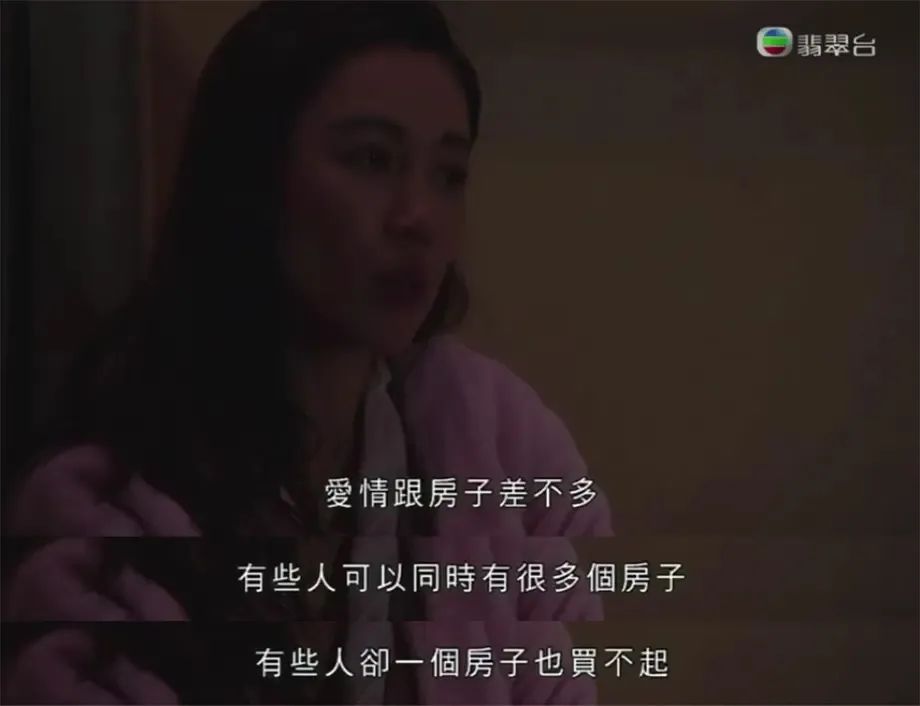
▲ 图 / 《金宵大厦》截图
3
盲盒抽得不好,可以“再来一次”,但买房却很难有重头来过的机会。
房子迟迟未交,买房的人只能继续租房。现在,宋世杰和妻子一边每月花6000多元在公司附近租房。另一边房虽没住,但房贷还是要还,1万多元月供照出不误。光是房子几乎就掏出了宋世杰夫妻俩一大半的工资,再加上车贷和生活支出,他越来越觉得,“怎么房子、车子都有了,反而过得不如以前了呢”。
花销一涨,家里的消费水平立马降级,妻子很久没买过新衣服,宋世杰也不敢提想换个新手机。夫妻俩曾商议,房子买完之后准备生孩子,但如今计划不得不搁置。
步入35岁之后,宋世杰本来想将生活节奏缓下来,但如今不仅不能慢,反而还要更加拼命。有时下班后,宋世杰还会再接几个打车单子,“反正在家也没事做”。妻子本来打算调岗的想法,也只能不了了之。
为了让双方老人放心,宋世杰不敢告诉家里房子的真实情况,只能不停用“因为疫情,工期耽误了”“快了,年初可以交房了”“正在找朋友设计,明年预备装修了”来善意地隐瞒父母。但他也会担心,如果理由用光了还未交房的话,自己应该怎么办。如果父母提出来北京小住一段时间,自己又该如何回复。
年轻的王雨竹有着别样的焦虑。她和男友的婚期定在2022年,本打算坐在新房里接亲,但如今房子未收,一系列规划都要随之调整。
婚宴需要提前一年预订,她既不敢确定日子,又担心被抢了合适的时间,只能时时盯着,以防万一。为了婚礼效果,王雨竹做了近视激光手术,还一直在坚持减肥,好不容易瘦了20斤。但节食过程很辛苦,她担心一直拖下去自己会复胖,塞不进买好的婚纱。
父母与她在这方面也有着分歧。父母希望二人能够先领证,租房住,新房慢慢等。如果房子明年初能下,就赶赶时间先简单装修,日后再慢慢打算。但王雨竹并不这么想,房子、结婚都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她一个都不想敷衍凑合。
一边是老业主的抵抗与妥协,但另一边却是新业主的热闹入场。宋世杰在维权过程中了解到,他购买房屋的所属房企,有多个楼盘存在停工现象。但在收了他们这一期业主上千万的预付款后,另一个更早停工的项目竟然重新开工了。
甚至与此同时,房企仍然在搞全城大卖,高价返佣,疯狂拉人。宋世杰渐渐明白了房企间的套路:他们是在拆了东墙补西墙,一手疯狂促销吸引新业主交纳定金,另一手就用卖掉一期几百套期房获得的资金,来继续开工其他耽搁的房产。
“三道红线”拉住了大小的房企扩张的步伐,“借新债还旧债”的游戏渐渐玩不下去了。在激烈洗牌下,卖房回流资金成为了高负债房企们的首要之路。
也有购房者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荀莉莉在成都老家工作,母亲退休后打算把家里住了快二十年的老房子卖掉,跟女儿一起付首付换一套面积大些的新房一起住。她看了几个楼盘,其中一个是期房,总价140多万元,如果当月能付全款,不到100万元就能拿下。
咨询意见时,荀莉莉表示反对,房企有钱没钱就是一瞬间的事,卖掉老房子的钱是母亲唯一的积蓄,万一烂尾怎么办?于是,荀莉莉和母亲还是决定买二手房,看得见摸得着,内心更踏实。
面对还没等到的房子,王雨竹至今没有想清楚自己走错了哪一步,只能将原因归结为“运气不好”。宋世杰准备跟妻子对好“口供”,今年过年回老家,面对父母和亲戚关于房子的询问,二人要如何过关。
(应受访者需求,文中宋世杰、王雨竹、陈燃、荀莉莉为化名)

▲ 图 /《花束般的恋爱》截图
=========================================
一群想推倒孤塔的人

在我国,像石城川这样的听障人士有近3000万名,像周彤这样的视障人士有1700多万名。科技浪潮汹涌而来,诞生了人工耳蜗、避障眼镜、震动手环等产品,但想推翻孤塔,让他们能像普通人一样无障碍沟通,仍有很多屏障要突破。
文 | 盐里
编辑 | 周维
运营 | 橞楹
11岁那年,一场脑膜炎之后,石城川的世界变成了一片静默。
孩子们叽叽喳喳聊得火热,石城川只能用文字加入,大多时候跟不上大家。原本活泼好动的小男孩,进入了一段漫长的孤塔时光。
“失聪这个事对我来说,并没有造成很强烈的不适感,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办法跟其他小伙伴无障碍地交流。”石城川回忆道。
失聪后的日子,像是被封在了高墙垒砌的孤塔中。他的很多表达欲望,最终都消散在无声的静默里。他深刻体会到了海伦凯勒所说的“视力障碍隔绝的是人与物,但听力障碍隔绝的是人与人”。那时候,石城川最大的愿望,是为像自己这样的听障群体做一些事。11岁的他还没有具体的梦想,内心却有一股强烈的渴望。
后来,石城川像大多数人一样,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毕业,然后进入一家软件公司上班。他甚至属于优秀的那一类人,高考考上了重点大学,入职第一年就被评为了公司优秀员工。
但是,那座隔离外界的孤塔一直存在,因为听不见,他变得内向,极少说话。内心的愿望也一直在,他曾向就职的公司提过,能否从事与听障群体相关的工作,可公司没有这样的业务。他又写信给谷歌、腾讯等公司,却没有收到回复。
在互联网时代,大部分公司都在殚精竭虑想着如何掀起流量大浪,鲜有公司关注到那些海浪无法抵达的孤塔。
90后女生周彤也经历过孤塔时光。她先天失明,对世界的感知更多地来自倾听和触摸。她能够像正常人一样自己上下班,自由穿行在工位间,也能独立完成工作。读屏软件可以帮助她听取很多信息,但是,屏障仍然随时出现。
比如点外卖时,她可以利用读屏软件,打开外卖页面,找到商家,点击一下屏幕,手机会发出声响:“XXX麻辣烫”;再点一下屏幕,声音传来“评分4.5”;再点,“月售25单”;再点,“商品信息:白菜”;再点,“商品添加”……按这个流程成功点上一道麻辣烫,周彤得花上一二十分钟。
周彤也爱“听”电视,最近她在追的是《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可是,找到它并不容易。当周彤打开视频软件,普通人可以看到分类栏里写着“电影、电视、综艺”,但通过读屏,她耳朵里听到的却是“按钮、按钮、按钮”——读屏软件不是万能的,很多科技产品的信息至今仍难以读取。
在我国,像石城川这样的听障人士有近3000万名,像周彤这样的视障人士有1700多万名。科技浪潮汹涌而来,诞生了人工耳蜗、避障眼镜、震动手环等产品,但想推翻孤塔,让他们能像普通人一样无障碍沟通,仍有很多屏障要突破。


然而,推翻高墙不是容易的事。
很少有项目像“声音识别”一样,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从策划到测试,流程走了10多遍,更别提私下的修改,次数多到李天鹏都记不清了。改进,不停地改进,最终目标是AI算法不止要在安静的环境里捕捉声音,在大千世界复杂的背景音里,也要精准识别到婴儿哭声。
改进一直在持续。功能正式上线的45天前,团队决定增加“视频通话”这一功能。时间像一只不断追上来的猛兽,七位开发者不断地修改、测试、更新。测试时,有用户提出,希望拥有聊天记录的“一键删除信息”功能,于是团队就开始了改良。有用户表示,声音识别功能里的手表震感不强,项目团队又与vivo智能手表团队沟通,特意为“哭声识别”设置更强的震动感、更快的震动频率……
更早一些,石城川也经历了重大改变。他理想中的智能眼镜做成了,但却过于笨重,市场也反应平平。到2017年,公司成立一年了,没有任何营收。他想,要不改做软件吧。
音书App就此诞生。这是一款结合语音识别、语音评测等AI技术,将语音和文字相互转换的软件。四年时间里,这款软件积累了近百万用户,也经历了十次左右的迭代。

石城川听说,有听障用户使用这款软件的语音转换功能,进行说话训练,于是就在音书里加入了语音训练功能。有用户提出,希望语音转文字的翻译窗口可以接入更多的软件,但这不只是技术的问题。悬浮翻译窗口想接入各个App,需要和各家运营商沟通,问题至今仍在解决中。
然而,最大的挑战是孤塔里正在消解的表达欲。石城川的公司有个听障女员工,有阵子,他发现这名员工的眼睛一直是红的,便提醒她去就医。对方表示,症状已经出现三年了,就这样吧。石城川把劝说的话说了一周、两周,拖到第三周,他亲自领着女生去了医院。医生确诊为睑缘炎,但是拖的时间太久,已经变成了慢性疾病,无法治愈。后来,他问那个女生为什么不去看病,女生回答,因为不会说话,一直觉得看病太麻烦,所以就拖着了。
不过,也有美好的故事。科技改变了沟通方式,也一点点唤起孤塔里的人。
蔷薇曾对一通客服电话印象深刻。听筒那边是一位湖北中年视障人士,40多年时间里,他几乎很少出门,从未离开过自己住的村子。他对外界信息的了解全部来自一台收音机、一部老式按键功能机,还有一部不知如何使用的智能手机。
某一天,他在收音机的电台里听到了心智无障碍助手App的存在,也想安装一个,就拨通了客服的电话。二十多个电话沟通后,他学会了如何一步一步地安装、使用这款软件。那天以后,在遥远的湖北村落一角,一位视障人士开始与外界连通。
如今,石城川仍记得他的孤塔倒塌的时刻。
那是新产品上市不久,很多场合需要创始人上台演讲。过去,合伙人彭驷庆一直担任这个角色。但彭驷庆提出,希望石城川成为那个演讲的人。于是,每天下班后,他们就花上两个小时,进行特训。石城川一遍遍地尝试,两名合伙人一遍遍地纠正他的发音。路演时的主角,也从彭驷庆变成了彭驷庆、石城川——特训初期,因为石城川时常咬字不清,两人决定各讲一半。后来,就变成了石城川一个人。他独自站在台上,孤塔轰然倒塌。他逐渐恢复了自信、开朗,像11岁前那样。
现在,石城川的团队正在为学校、银行、医院等各类公共服务机构提供标准化无障碍沟通解决方案,助力更多机构为听障群体推倒孤塔。

李天鹏也清晰记得vivo听说功能Demo测试的那一天。测试手机交到了十几岁的聋哑女孩芊芊手中,她封闭多年的表达欲,在那一天被完全释放。
测试时,芊芊不停地抛出问题。她在vivo手机里输入文字,迅速地转成语音,vivo团队的回答又转为文字呈现在屏幕上。他们聊手机使用相关的问题,也聊团队开发的相关经历。
“你就能感觉到她在不断地找话题。”李天鹏回忆。聊到后来,团队和芊芊的父母聊起她的小时候。李天鹏注意到,芊芊一直捧着手机,把父母的每句话都转行成了文字,整个人看起来很兴奋。她后来用手机“说”,那是她十多年来第一次直接地了解到父母的表达。
徐超一家也拿到了vivo的测试手机,夫妇俩第一次和大儿子没有用手语进行视频交流。儿子的话语,在屏幕上的透明悬浮窗口中转成了文字;徐超则在窗口打下文字,转换成声音传递过去。声音和文字,穿越1800多公里的距离来来回回,一家人挤在手机屏幕前,笑容在脸上绽放。
做了半年的项目,李天鹏发现自己有了一些变化。过去,他看待产品的思维,是贴近大多数人。但如今,他看到了人的更多维度,边缘人群的需求已经刻入他的思维。
李天鹏表示,未来团队会考虑加入更多的声音识别,比如汽车鸣笛声、烟雾报警器的蜂鸣声、防盗器的警报声等,同时,也会针对老年人等群体继续开展信息无障碍建设。
这也是vivo与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联合发布信息无障碍“声声有息”公益计划的一部分。像李天鹏这样的故事仍会继续,vivo将通过联合调研、系统升级、公益帮扶等形式,缩小听障群体与普通人间的信息“沟通差”,让更多的孤塔被推倒,让更多的人与外界连通。
“推动行业信息无障碍的技术升级,关注与帮扶更多有需要的人,改善他们的生活。”vivo高级副总裁施玉坚在昨天召开的2021vivo开发者大会上表示。vivo的应用商店也投入了较大的推广资源,服务于信息无障碍的开发者。他希望通过vivo的一些努力,可以让这些群体不再被数字鸿沟隔绝在外。

一群想要推倒孤塔的人,把信息化的浪潮带到了塔中。一座座与世隔绝的孤塔正轰然倒下,塔里的人走了出来,他们被看见、被听见,被同时代的科技洪流簇拥着向前。
(文中芊芊、徐超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