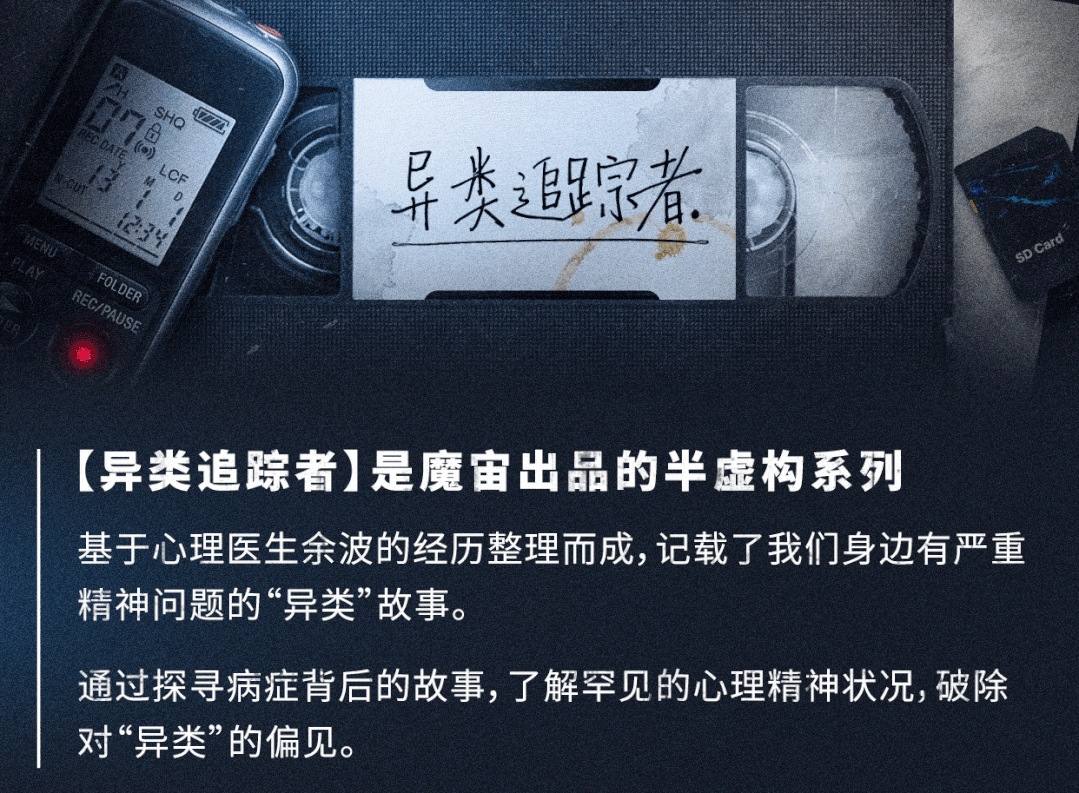
大家好,我是掘坟仔。
后台有读者问我,为什么这个系列叫“异类追踪者”?
实际起名的时候,我、徐浪、朱富贵想了很久,简单妥帖地描述需要心理治疗的人,其实不容易。
人是社会动物,想合群是天性,排斥异类也是天性。
因为任何人被归为“异类“”,都意味跟他做切割,剥夺他的某一重身份和权力。
即使如此,还有一些人,蔑视主流价值,选择成为异类。
今天的故事就是一个“异类”的故事,我相信你看完,肯定有话想说。


林文祥是个爱穿女装的小伙子,在我做过的咨询里,他算是个挺特别的人。
岁数不大,胆子不小。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一次,他父亲老林大晚上来咨询室找我,带我去找他儿子,劝他回家。
那天北京下着雪,大街上行人稀少,一路上老林用责备和怨恨的语气冲我发着邪火,他觉得是我把他儿子带坏了。
老林把我带到东交民巷的一座天主教堂附近的街上。

东交民巷天主教堂
我看到一个年轻人,穿着连衣裙和高跟鞋,在寒冷的街上,跳着不知道叫啥的舞蹈。
那个就是林文祥,要是我没见过他,可能只会把他当做是一个遇到开心事的姑娘。
我有点惊讶于自己的第一反应,居然是他看上去还挺漂亮。
老林上去就是一巴掌,小林差点摔倒,我赶忙上去拦住老林。
我知道他把我拉过来,就是想让我看看,小林的行为是有多么的不合理。
路上几个为数不多的行人停住脚步,站在路边看戏。
我拽住老林,让小林赶紧上车,因为只穿着一件单裙,他的小腿已经冻得通红。
小林踩着四五公分高的高跟鞋,愤怒地看着老林,然后转身沿着东交民巷,朝地铁口走去。
老林指着我鼻子,训斥我在对小林的咨询不负责任,让他越来越极端。
然后他愤怒地坐上自己的车,开车去追他儿子,把我晾在马路上。
我想起第一次见林文祥的场面,也是这么火爆。
是在他高三的时候,他爸爸把他揪到咨询室来,说他有毛病。
我看到的是一个白胖白胖的高中生,很腼腆,不爱说话。我问啥基本都是他爸老林代劳。
我问到因为啥来做咨询,老林抢着回答,说小林思想有问题,让我矫正一下。
林文祥憋得脸通红,半天憋出一句,我不用矫正。
他爸一听这话,站起来就准备抽他。林文祥是一副宁死不屈的样子,梗着个脖子,让他爸打,跟英勇就义似的。
我赶忙拉住,劝了半天才把他爹劝住,这还是第一次见到来访者家属这么激动的。
问儿子啥也问不出来,我只能转过头去问老爹。
老林长叹一口气,说他儿子穿女人衣服。
我一听,想乐,但忍住了,不是因为这件事,而是老林表达的状态。
我认同儿子的看法,我也不认为这需要矫正。
很多类似的癖好,只要不对其他人造成影响和伤害,不对自己精神造成伤害,我们也不会去矫正。
但是当爹的反应很大,跟我控诉了很多儿子“荒唐”的举动。
我接下这个活,随后的几次咨询,我单独跟林文祥聊,评估了一下,他没有什么心理问题。
如果说有问题,那只能说青春期的少年和家长会遇到的普遍问题,就是家长和孩子的关系问题。
这种问题会以很多种形式爆发,叛逆算是其中一种。
孩子需要反抗大人,大人需要接受孩子的反抗。当然很多时候,大人是不能容忍和接受的。
林文祥挺勇敢,他对自己穿女装的爱好也不藏着掖着,时不常挑战一下他老爹的权威。
他特别愿意展现自己,即便这样会让他老爹愤怒,甚至招致他爸的毒打。
基本上每次他这么做,他爸都得给我打电话,然后让我去劝他放弃这个爱好。
说实话,我挺羡慕他,有胆量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毫无顾虑。

余波寄给我的来访者登记表,为方便阅读,内容整理在下面表格里
|
|
|
|
|
|
|
|
|
|
|
|
诉求:改变异装癖,顺利参加高考(该诉求主要是家长的诉求,个人无此诉求,也不认为自己的异装行为对自己的生活有影响)
|
|
|
|
备注:来访者自己并不认为自己的异装癖好对自己的生活有影响,但来访者父亲对这件事情非常在意,前来咨询的主要动力也是他的父亲。
来访者对自我的性别认同没有问题,他并没有对此感到困惑或者焦虑。主要的问题来自于他的父亲,他对自己儿子现在的做法意见非常大,与儿子之间的关系也很紧张。
来访者母亲态度较为温和,对儿子的选择不支持也不反对,只是希望儿子能够快乐。
来访者父亲来做咨询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认为高考临近,他认为儿子这样的精神状态会影响到高考发挥。
|
|
余:我也希望是这样,不过咱们似乎得把你爸这关混过去。
余:让我先评估一下你现在的情况,我虽然不认为你有病,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的父亲对你的这种对立态度继续下去的话,对你的生活还是会有一定影响的。
林:能有啥影响,高考完了我就离开家,跟他就没关系了。
余:这也是种办法,有的时候父母的想法真的很难改变。
林:解决不了问题就回避,这种做法是不是有些不成熟。
余:也不能这么说,回避也是一种面对问题的方式,有能力解决就解决,没能力解决还要硬着头皮去面对,会给生活带来很大困惑的。
林:如果我爸能像我妈那样就好了,我不指望他能支持我,他不管我我就烧高香了。
余:你离开家他就管不着你了,不过你得先确定,你能离开这个家。什么时候高考?
余:那这样好不好,在你高考之前,先把你异装的爱好放一放,这么做的目的是避免和你的父亲发生正面冲突,也算是给你自己营造一个良好的备考环境,怎么样?
林:我试试吧,但是这也是我的一种减压方式啊,高考的压力太大了。
余:那你要想穿就得想办法瞒着你爸妈了,不能像上次那样那么明目张胆,咱们尽量避免和父母的冲突,全力备战高考。
余:我还是要提醒你,你和你父亲的关系,可能是你今后生活需要解决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离开家,暂时的逃避是一种办法。但你要知道,他永远都是你的父亲,这一点没办法改变,以后如果有机会,或者说你有能力了,我还是希望你能够面对你和父亲的关系。
|
|
林文祥的咨询由于父亲的反对而中断,父亲认为儿子并没有在这几次咨询中“解决问题”,拒绝再支付咨询费用。
林文祥在最后一次咨询时给我一个手链,他说这是感谢。
|
 他还觉得他儿子从我这里得到认同之后,跟老子对着干的底气似乎更足了,于是果断结束了咨询。
小林临走的时候,送给我一个根手链,他说那是之前去西藏的时候买的,觉得很好看,一直带着。
本以为小林的事儿就到此为止了,其实大多数来访者都会想他这样,咨询的关系因为种种原因戛然而止。
小林再次回到咨询室的时候,正是我焦头烂额的时候,我家被人盗了。
那天徐晓在咨询室为第二天的团体咨询做准备,我跟周老为了帮她整理档案,忙了一宿,最后直接在咨询室打了个地铺。
更要命的是我的工作笔记,里面有来访者的录音,咨询笔记,还有我私自跟踪他们时做的记录和照片。
然后就在家里失窃的这个礼拜六,林文祥回到了我的咨询室,这回是他妈妈带他来的。
陈妈妈在带小林来之前,提前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跟我说了小林的近况。
寒假回到家,让父母吓了一大跳,原本一百四五十斤的小林,一下子瘦到不到一百斤。
老林刚开始看到还挺高兴,觉得儿子上了大学,变精神了。
没想到到家第二天,小林就换上带回来的裙子,美美地出去逛街去了。
趁小林不在家,老林冲进小林屋里,把小林的衣服全烧了。
小林一回家,炸锅了,爷俩结结实实干了一仗,小林一气之下,连年都没过,跑回学校住去了。
这一走,大学四年没再回过家,只是偶尔打个电话报平安。
大四毕业,在妈妈一再央求下,小林老大不情愿地回来了。
但是他没住在家里,在网上租了个短租的loft,跟女朋友出去住。
她顿了一会和我说,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小林和这个女孩在一起之后不大对劲。
我印象中的小林,还是那个在雪中展现自我的漂亮小伙。不是现在这个呆若木鸡,一棍子敲不出个响屁的无聊大学生。
我甚至有点怀念老林了,要是他来,场面肯定不至于这么沉闷。
他这次穿着挺简单的,一顶斜扣的画家帽,白色衬衫和一条棕色的七分裤,厚底鞋。
除了妆容衣着精致以外,他最大的变化就是失去了点朝气。
虽然体重减轻了很多,但他的动作和身态显得更笨重,像个树懒,从前饱满的脸上出现两道很深的法令纹,像鲶鱼的泪槽。
但这些都不重要,我看到小林的手上戴着几年前送给我的银手链。我记起来当时把手链放进了档案袋,档案袋随着几十个人的咨询笔记档案,被偷了。
我指着他别着的银手链,问他不是已经送给我了吗,怎么自己还留着一个。
他难得笑了,说这是女朋友送的,恰好跟送给我的款式一样。
想想也是,他刚刚毕业,之前一直在学校忙着毕业论文的事儿,不可能分身回到北京来跟踪我。
我询问了一下小林的私生活,他的性取向等等类似的问题,这些问题是除了那枚银手链之外,我可能最感兴趣的问题。
小林简略地说了一下自己的大学生活,还提到了自己带回来的女孩。
在我的评估里,我最早把林文祥的这种异装行为定义为GD(Gender dysphoria),也就是“性别烦躁”,这是DSM-5新描绘的一种障碍。
简单说就是一个成年人对自己的天生性别感到不适,不认同,甚至厌恶,他们希望用另一个性别生活。
为此有些人会选择使用药物、手术来改变自己的身份,当然也会有像小林这样的人,用异装的方式生活。
但在与小林的交流中我得知,他并没有对自己的男性身份感到特别不适与厌恶。
这次回北京带回来的女孩,确实是他的女朋友,他们是在一个叫“第四爱”的贴吧上认识的。
林文祥并不属于传统的异性恋,当然他更不是同性恋,他形容自己和女朋友的感情是“第四爱”。
“第四爱”是个民间词汇,学术上更倾向于划分到跨性别恋爱。
第四爱指的就是除了异性恋、同性恋、无性恋之外的第四种恋爱方式。
这种恋爱方式的主旨就是性别互换,两人的生理和心理性别的互换,在生理上,女性会使用假阴茎完成性交行为。
小林话很少,只是简单跟我解释了一下“第四爱”,他不愿意在咨询里讲太多。
对于病人回避的事情,我通常不会多聊。就转到了减肥的事情上,问他是怎么瘦的,想取取经。
小林说都是女朋友在帮助他。小林给我看了他和女朋友发在朋友圈里的照片,两个人都很高兴。
女孩齐耳短发,带着一个黑框眼镜,是大学校园里经常能见到的文静女生长相。
他们带着银色的情侣手链,与一般情侣唯一不同的是,小林的脑袋依偎在女孩的肩膀上。
小林对我说,没有女朋友他不可能活到今天,他的命都是女朋友给的。
我从咨询的只言片语里知道一个事儿,林文祥和他的女友是在大四的时候才认识。
他们认识没多长时间,我收到了那条短信,然后我的来访者一个接一个的出事儿。
我本能的把这两件事通过时间线联系在一起,为啥这么做,我也不知道。
那段时间正好有个朋友在gay吧当主持,让我过去捧场。
第一眼我没认出来,她一身男士着装,光着脚在舞台上和反串演出的drag queen围着一根钢管热舞,没戴眼镜,画了一点烟熏妆,跟之前反差很大。
伴随lady gaga 的歌声,她妖娆的和变装演员在灯光下缠绵,一曲结束他们在舞台上拥吻,台下口哨声连连。
我看着眼前的场景,几近幻影,很难想象这是照片里和林文祥依偎在一起的女孩。
演出结束后,她牵着变装演员往外走。我立刻凑上去,自我介绍是林文祥的医生,想和她聊聊。
女孩倒是和气,让男友在门口等一会,和我坐回吧台喝酒。她叫宋菲,是个插画师。
宋菲说不是她脚踏两只船,只是因为她特殊的癖好,她真正的性取向是喜欢同性恋的男生。
“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穿了一双白色长筒袜,非常喜欢,当时还磕了一阵子他和班上男生的cp,谁能想到他竟然只喜欢女生。”
“发现他是直男后就下头了。但当时,我们的关系在圈子里已经传开,他对我挺依赖的,没有办法直接说分手。我就各种挑他毛病,让他减肥,不减40斤就分手。其实分手我也提过,他寻死觅活,什么办法都用,我担心他出事也不敢再提,医生……”
“其实我挺怕他出事的,他为了减肥去切了胃,他爸他妈都不知道,前阵子他一直在住院。”
这时候,刚刚在台上和宋菲拥吻的变装演员冲进来,牵起宋菲的手着急去下一场派对。他们像烟花一样消失了。
离开酒吧,今天的天气好像被烟雾掩埋。酒吧门口熙熙攘攘的路灯下,全是年轻快乐的男女,我走在他们中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狼狈。
我总觉得在这些快乐的人群后面,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
回去路上我的腿一直打晃,想起来几年前在大雪里跳舞的林文祥。
我忽然意识到,那时候的确是忽略了林文祥的问题,他的心理是健康的,但他同时也在面临一种危机。
他的性别认同在成长中得不到肯定,在之后的亲密关系中非常容易衍生出补偿心理,也许宋菲最初的爱给了他从来没有过的认同感。
我想到陈凡对我的忠告,我从来没有像那一刻怀疑自己。
更糟心的是,那天以后,我就不能专心工作了,每当来访者坐在对面的那把椅子上,我会怀疑坐在对面的每一个人真正的面目,我又能为他们解决什么。
我甚至会产生幻觉,常常看见另一个人,那个人没有面目,只有一张黑漆漆的影子,冷气森森。
我认定,我和我的患者们身上发生的所有的事,都跟他有关,包括小林。
小林说,宋菲恰巧给他买了同款的银链,我不信,肯定有人捣鬼。
小林也许不过是又一个被他盯上的来访者,我不知道他的计划,但我不想让小林陷入到危险中。
我觉得要找我现在的状态,继续给小林做咨询很可能会伤害到他,我决定把他转诊给徐晓。
我在箱子里翻了半天,把剩下没看的笔记都翻了一遍,没有林文祥的名字。
余波的笔记上说,小林被转给给了他的同事徐晓,我跟她有几面之缘。
酒馆不大,消费不低,我请的客,毕竟是我求人办事儿。
徐晓进来的时候,两手空空,我心里一沉,显然她没带来关于林文祥的记录。
徐晓告诉我,余波还有一些笔记放在办公室,之前她也不知道。
徐晓看过了这些笔记,都是余波离开前记录下来的一些来访者,其中也包括林文祥。
余波丢失的文档,其实不止我这里有,她也有,甚至他们的老板周德松那里也有。
可以合理推测,收到余波的文档的人不在少数,这些资料流出,对于一个心理咨询师几乎是毁灭性的,甚至包括他服务的治疗所。
我又点了一轮酒,又问徐晓,知不知道陈凡这么一个人,她点了点头。
我说我分析过余波档案里的案子,余波的事,可能跟这个陈凡有关系。
没搭理陈凡这岔,徐晓抿了一口酒:“后面来找我的不是林文祥。”
老林之前无论来诊所,还是收拾儿子,都精神抖擞,气势汹汹,但这次来连胡子都没刮,从上到下没一点精神。
老林来这里,是因为小林垮了。宋菲突然失联了,而且拉黑了林文祥的社交平台,从前的朋友圈子也都联系不上。
林文祥因为承受不了打击,情况越来越糟糕,他觉得是因为自己减肥不成功造成宋菲的离开,得了神经性厌食症,进了医院。
小林倒下之后,妻子跟老林大吵一架,认为儿子变成现在的模样,都是老林逼的,等儿子出院就要跟老林离婚。
老林愁容满面,但说话支支吾吾,还一直绕圈子。徐晓知道,这次咨询大概率会无疾而终,要一个中年男人对陌生人敞开心扉,难度太高了。
老林说的颠三倒四,徐晓不断引导,花了一整个下午,才终于搞明白了。
老林千方百计阻拦小林穿女人衣服,甚至对小林拳打脚踢,是因为恐惧,他害怕小林步了自己的后尘。
“我一开始也不信,但中年男人不会拿这个开玩笑。忽然之间,我就全能理解老林了。”徐晓说。
老林是个极为传统的人,多年以来一直否定自己,尽好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但他的内心很煎熬,而在看到儿子的样子后,怕得不行。
老林说他过了一辈子苦日子,没人知道。不想小林跟他一样,所以要趁小林还没定型,让人给矫正过来。
他还觉得他儿子从我这里得到认同之后,跟老子对着干的底气似乎更足了,于是果断结束了咨询。
小林临走的时候,送给我一个根手链,他说那是之前去西藏的时候买的,觉得很好看,一直带着。
本以为小林的事儿就到此为止了,其实大多数来访者都会想他这样,咨询的关系因为种种原因戛然而止。
小林再次回到咨询室的时候,正是我焦头烂额的时候,我家被人盗了。
那天徐晓在咨询室为第二天的团体咨询做准备,我跟周老为了帮她整理档案,忙了一宿,最后直接在咨询室打了个地铺。
更要命的是我的工作笔记,里面有来访者的录音,咨询笔记,还有我私自跟踪他们时做的记录和照片。
然后就在家里失窃的这个礼拜六,林文祥回到了我的咨询室,这回是他妈妈带他来的。
陈妈妈在带小林来之前,提前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跟我说了小林的近况。
寒假回到家,让父母吓了一大跳,原本一百四五十斤的小林,一下子瘦到不到一百斤。
老林刚开始看到还挺高兴,觉得儿子上了大学,变精神了。
没想到到家第二天,小林就换上带回来的裙子,美美地出去逛街去了。
趁小林不在家,老林冲进小林屋里,把小林的衣服全烧了。
小林一回家,炸锅了,爷俩结结实实干了一仗,小林一气之下,连年都没过,跑回学校住去了。
这一走,大学四年没再回过家,只是偶尔打个电话报平安。
大四毕业,在妈妈一再央求下,小林老大不情愿地回来了。
但是他没住在家里,在网上租了个短租的loft,跟女朋友出去住。
她顿了一会和我说,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小林和这个女孩在一起之后不大对劲。
我印象中的小林,还是那个在雪中展现自我的漂亮小伙。不是现在这个呆若木鸡,一棍子敲不出个响屁的无聊大学生。
我甚至有点怀念老林了,要是他来,场面肯定不至于这么沉闷。
他这次穿着挺简单的,一顶斜扣的画家帽,白色衬衫和一条棕色的七分裤,厚底鞋。
除了妆容衣着精致以外,他最大的变化就是失去了点朝气。
虽然体重减轻了很多,但他的动作和身态显得更笨重,像个树懒,从前饱满的脸上出现两道很深的法令纹,像鲶鱼的泪槽。
但这些都不重要,我看到小林的手上戴着几年前送给我的银手链。我记起来当时把手链放进了档案袋,档案袋随着几十个人的咨询笔记档案,被偷了。
我指着他别着的银手链,问他不是已经送给我了吗,怎么自己还留着一个。
他难得笑了,说这是女朋友送的,恰好跟送给我的款式一样。
想想也是,他刚刚毕业,之前一直在学校忙着毕业论文的事儿,不可能分身回到北京来跟踪我。
我询问了一下小林的私生活,他的性取向等等类似的问题,这些问题是除了那枚银手链之外,我可能最感兴趣的问题。
小林简略地说了一下自己的大学生活,还提到了自己带回来的女孩。
在我的评估里,我最早把林文祥的这种异装行为定义为GD(Gender dysphoria),也就是“性别烦躁”,这是DSM-5新描绘的一种障碍。
简单说就是一个成年人对自己的天生性别感到不适,不认同,甚至厌恶,他们希望用另一个性别生活。
为此有些人会选择使用药物、手术来改变自己的身份,当然也会有像小林这样的人,用异装的方式生活。
但在与小林的交流中我得知,他并没有对自己的男性身份感到特别不适与厌恶。
这次回北京带回来的女孩,确实是他的女朋友,他们是在一个叫“第四爱”的贴吧上认识的。
林文祥并不属于传统的异性恋,当然他更不是同性恋,他形容自己和女朋友的感情是“第四爱”。
“第四爱”是个民间词汇,学术上更倾向于划分到跨性别恋爱。
第四爱指的就是除了异性恋、同性恋、无性恋之外的第四种恋爱方式。
这种恋爱方式的主旨就是性别互换,两人的生理和心理性别的互换,在生理上,女性会使用假阴茎完成性交行为。
小林话很少,只是简单跟我解释了一下“第四爱”,他不愿意在咨询里讲太多。
对于病人回避的事情,我通常不会多聊。就转到了减肥的事情上,问他是怎么瘦的,想取取经。
小林说都是女朋友在帮助他。小林给我看了他和女朋友发在朋友圈里的照片,两个人都很高兴。
女孩齐耳短发,带着一个黑框眼镜,是大学校园里经常能见到的文静女生长相。
他们带着银色的情侣手链,与一般情侣唯一不同的是,小林的脑袋依偎在女孩的肩膀上。
小林对我说,没有女朋友他不可能活到今天,他的命都是女朋友给的。
我从咨询的只言片语里知道一个事儿,林文祥和他的女友是在大四的时候才认识。
他们认识没多长时间,我收到了那条短信,然后我的来访者一个接一个的出事儿。
我本能的把这两件事通过时间线联系在一起,为啥这么做,我也不知道。
那段时间正好有个朋友在gay吧当主持,让我过去捧场。
第一眼我没认出来,她一身男士着装,光着脚在舞台上和反串演出的drag queen围着一根钢管热舞,没戴眼镜,画了一点烟熏妆,跟之前反差很大。
伴随lady gaga 的歌声,她妖娆的和变装演员在灯光下缠绵,一曲结束他们在舞台上拥吻,台下口哨声连连。
我看着眼前的场景,几近幻影,很难想象这是照片里和林文祥依偎在一起的女孩。
演出结束后,她牵着变装演员往外走。我立刻凑上去,自我介绍是林文祥的医生,想和她聊聊。
女孩倒是和气,让男友在门口等一会,和我坐回吧台喝酒。她叫宋菲,是个插画师。
宋菲说不是她脚踏两只船,只是因为她特殊的癖好,她真正的性取向是喜欢同性恋的男生。
“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穿了一双白色长筒袜,非常喜欢,当时还磕了一阵子他和班上男生的cp,谁能想到他竟然只喜欢女生。”
“发现他是直男后就下头了。但当时,我们的关系在圈子里已经传开,他对我挺依赖的,没有办法直接说分手。我就各种挑他毛病,让他减肥,不减40斤就分手。其实分手我也提过,他寻死觅活,什么办法都用,我担心他出事也不敢再提,医生……”
“其实我挺怕他出事的,他为了减肥去切了胃,他爸他妈都不知道,前阵子他一直在住院。”
这时候,刚刚在台上和宋菲拥吻的变装演员冲进来,牵起宋菲的手着急去下一场派对。他们像烟花一样消失了。
离开酒吧,今天的天气好像被烟雾掩埋。酒吧门口熙熙攘攘的路灯下,全是年轻快乐的男女,我走在他们中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狼狈。
我总觉得在这些快乐的人群后面,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
回去路上我的腿一直打晃,想起来几年前在大雪里跳舞的林文祥。
我忽然意识到,那时候的确是忽略了林文祥的问题,他的心理是健康的,但他同时也在面临一种危机。
他的性别认同在成长中得不到肯定,在之后的亲密关系中非常容易衍生出补偿心理,也许宋菲最初的爱给了他从来没有过的认同感。
我想到陈凡对我的忠告,我从来没有像那一刻怀疑自己。
更糟心的是,那天以后,我就不能专心工作了,每当来访者坐在对面的那把椅子上,我会怀疑坐在对面的每一个人真正的面目,我又能为他们解决什么。
我甚至会产生幻觉,常常看见另一个人,那个人没有面目,只有一张黑漆漆的影子,冷气森森。
我认定,我和我的患者们身上发生的所有的事,都跟他有关,包括小林。
小林说,宋菲恰巧给他买了同款的银链,我不信,肯定有人捣鬼。
小林也许不过是又一个被他盯上的来访者,我不知道他的计划,但我不想让小林陷入到危险中。
我觉得要找我现在的状态,继续给小林做咨询很可能会伤害到他,我决定把他转诊给徐晓。
我在箱子里翻了半天,把剩下没看的笔记都翻了一遍,没有林文祥的名字。
余波的笔记上说,小林被转给给了他的同事徐晓,我跟她有几面之缘。
酒馆不大,消费不低,我请的客,毕竟是我求人办事儿。
徐晓进来的时候,两手空空,我心里一沉,显然她没带来关于林文祥的记录。
徐晓告诉我,余波还有一些笔记放在办公室,之前她也不知道。
徐晓看过了这些笔记,都是余波离开前记录下来的一些来访者,其中也包括林文祥。
余波丢失的文档,其实不止我这里有,她也有,甚至他们的老板周德松那里也有。
可以合理推测,收到余波的文档的人不在少数,这些资料流出,对于一个心理咨询师几乎是毁灭性的,甚至包括他服务的治疗所。
我又点了一轮酒,又问徐晓,知不知道陈凡这么一个人,她点了点头。
我说我分析过余波档案里的案子,余波的事,可能跟这个陈凡有关系。
没搭理陈凡这岔,徐晓抿了一口酒:“后面来找我的不是林文祥。”
老林之前无论来诊所,还是收拾儿子,都精神抖擞,气势汹汹,但这次来连胡子都没刮,从上到下没一点精神。
老林来这里,是因为小林垮了。宋菲突然失联了,而且拉黑了林文祥的社交平台,从前的朋友圈子也都联系不上。
林文祥因为承受不了打击,情况越来越糟糕,他觉得是因为自己减肥不成功造成宋菲的离开,得了神经性厌食症,进了医院。
小林倒下之后,妻子跟老林大吵一架,认为儿子变成现在的模样,都是老林逼的,等儿子出院就要跟老林离婚。
老林愁容满面,但说话支支吾吾,还一直绕圈子。徐晓知道,这次咨询大概率会无疾而终,要一个中年男人对陌生人敞开心扉,难度太高了。
老林说的颠三倒四,徐晓不断引导,花了一整个下午,才终于搞明白了。
老林千方百计阻拦小林穿女人衣服,甚至对小林拳打脚踢,是因为恐惧,他害怕小林步了自己的后尘。
“我一开始也不信,但中年男人不会拿这个开玩笑。忽然之间,我就全能理解老林了。”徐晓说。
老林是个极为传统的人,多年以来一直否定自己,尽好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但他的内心很煎熬,而在看到儿子的样子后,怕得不行。
老林说他过了一辈子苦日子,没人知道。不想小林跟他一样,所以要趁小林还没定型,让人给矫正过来。

咨询完之后,老林心情好了一些,还跟徐晓约定后面做咨询的日程。
徐晓咂摸一口酒,摇了摇头,说不知道,老林再没来过。
跟徐晓的聊天的时候,我没感觉到,回过神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我忽然有一种感觉——天永远不会亮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这代表了一些人的生活。他们笑着跟你挥手道别,然后潜回永恒的黑暗。
徐晓思考了一会儿,“没听他说过,他不愿意说,不过他好像对潮湿土地的味道挺敏感,阴天下雨可要了他亲命了。
有一次,因为一个来访者,我俩进过一次防空洞,出来之后他好几天打不起精神,还过敏了,脸上身上一个劲儿起疹子,那是最严重的一次。”
看着徐晓的车拐过路口,我决定,该去好好找找余波了。
推送故事的时候,我爸正好喝醉酒刚睡醒。他摇摇晃晃的从卧室里走出来,准备去卫生间。
我问我爸,如果我有一天喜欢上穿女装你会是什么反应。
不过,我还想到汉娜阿伦特的一句话:“恶是不曾思考过的东西”。
如果有一种观念是以伤害你爱的人为前提的,那么无论它多么根深蒂固,都得谨慎决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