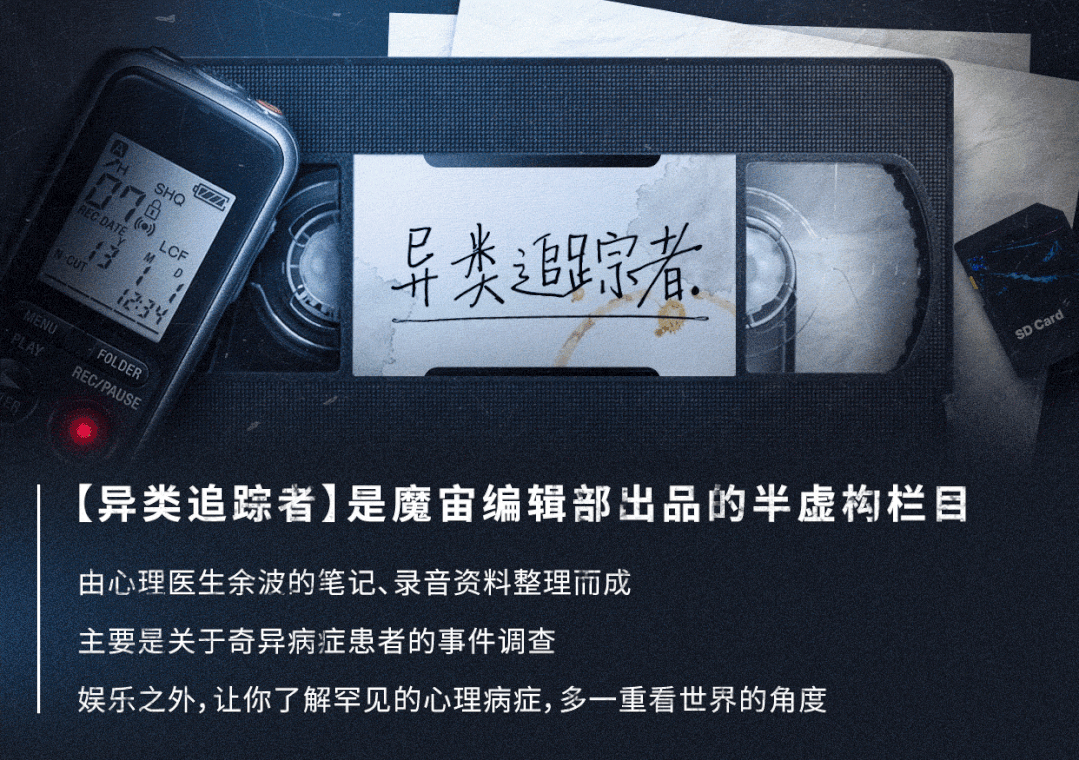
大家好,我是掘坟仔。
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还活着吗?
这不是废话吗。
绝大部分时候,确实是废话,但在某些情况下,生与死的界线,可并不如想象中那么明显。
人死后,真会意识到自己死了吗?
电影《第六感》里,布鲁斯·威利斯扮演的心理医生,试图帮助一个心理有问题的小孩走出困境。
心理医生很快就发现,小孩其实没有心理疾病。他的麻烦来自于他的特异功能——阴阳眼,能看到那些不肯离去的灵魂。
这些灵魂也会来找小孩,求他帮它们解决一些放不下的问题。
故事的最后,医生成功帮助小孩走出困境,但却发现一个事实——他自己在一年前就已经死了。
极度强烈的执念,会扰乱人的心智,甚至让人分不清生死。
今天故事里的人,就有这样一个搞不清生死的人,而他的经历,可能比电影更离奇。
2017年刚一过完年,我收到一件快递,用塑料泡沫做的箱子邮过来,箱子上写的生鲜,寄过来的时候用胶带裹得严严实实。
 收到的快递箱子
我打开箱子,一股臭味儿往鼻子里钻,站在旁边的徐晓熏得直干呕。
我拿着根铅笔在箱子里扒拉,里面是颗腰子,旁边放着几个冰镇用的冰袋,有俩已经破了。
这个快递看样子已经发出来挺长时间,冰都化了,腰子泡在已经有点温热的血水里。
我第一反应是前段时间给一个淘宝卖家差评,遭报复了。我把箱子里的血水倒进洗手池,准备拿着箱子直接扔到外面垃圾箱。
血水倒了一半,我看见其中一个冰袋上粘着一张纸条,上面有一行打印出来的字:
“你总说这种腐烂的味道是我幻想出来的,现在闻到了没?”
他是我的一个来访者,本应该在上个礼拜六来做咨询,结果没来,也没打任何招呼。
最近的几次咨询,刘文涛都反复说,觉得自己快要死了,觉得自己身上老有股臭肉味儿,洗也洗不掉,要花上大半的时间来跟我形容,他身上又有哪个器官腐烂了,哪个器官没了。
我停下手,看了看箱子里的这颗肾脏,后腰眼一股凉意。我赶忙把干呕的徐晓拉过来,让她看看这腰子到底是人的还是别的什么牲口的。
警察通知我们的时候,还有点不耐烦,埋怨我们应该去找菜市场卖肉的鉴定。
徐晓骂咧咧地问我,哪个缺德玩意儿邮来的,搞得她现在鼻子闻什么都是臭的。
我告诉她,我大概猜到是谁,下礼拜他来做咨询,你可以让他当面向你道歉。
等了一个礼拜,刘文涛没来,他老婆来了。他老婆跟我说,刘文涛失踪了。
收到的快递箱子
我打开箱子,一股臭味儿往鼻子里钻,站在旁边的徐晓熏得直干呕。
我拿着根铅笔在箱子里扒拉,里面是颗腰子,旁边放着几个冰镇用的冰袋,有俩已经破了。
这个快递看样子已经发出来挺长时间,冰都化了,腰子泡在已经有点温热的血水里。
我第一反应是前段时间给一个淘宝卖家差评,遭报复了。我把箱子里的血水倒进洗手池,准备拿着箱子直接扔到外面垃圾箱。
血水倒了一半,我看见其中一个冰袋上粘着一张纸条,上面有一行打印出来的字:
“你总说这种腐烂的味道是我幻想出来的,现在闻到了没?”
他是我的一个来访者,本应该在上个礼拜六来做咨询,结果没来,也没打任何招呼。
最近的几次咨询,刘文涛都反复说,觉得自己快要死了,觉得自己身上老有股臭肉味儿,洗也洗不掉,要花上大半的时间来跟我形容,他身上又有哪个器官腐烂了,哪个器官没了。
我停下手,看了看箱子里的这颗肾脏,后腰眼一股凉意。我赶忙把干呕的徐晓拉过来,让她看看这腰子到底是人的还是别的什么牲口的。
警察通知我们的时候,还有点不耐烦,埋怨我们应该去找菜市场卖肉的鉴定。
徐晓骂咧咧地问我,哪个缺德玩意儿邮来的,搞得她现在鼻子闻什么都是臭的。
我告诉她,我大概猜到是谁,下礼拜他来做咨询,你可以让他当面向你道歉。
等了一个礼拜,刘文涛没来,他老婆来了。他老婆跟我说,刘文涛失踪了。
|
|
|
|
|
|
|
|
|
|
|
|
诉求:2011年7月在回龙观医院确诊抑郁症,接受了两年的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此后症状好转。2016年由于工作和生活压力,抑郁症症状加重,伴有一些妄想症状。来访者希望能够减轻抑郁状态和妄想症状。
|
|
|
|
备注:来访者在咨询过程中,表现出一些特别的幻想症状,比如认为自己要死了,感觉自己身体里的器官消失,或者根本不存在。这些幻想症状是在2011年刚确诊抑郁症所没有的,2016年第二次抑郁症发作后出现。
2016年的抑郁症发作,据来访者说,部分原因是父亲的病逝带来的生活变化。来访者所产生的一些幻想也多发生在父亲遗体告别仪式之后。
|
|
刘文涛(以下简称刘):我有时候都不认识镜子里的自己了,余老师,你有过这种感觉吗?
余波(以下简称余):时常会有,有的时候盯着镜子时间长了,就会感觉不认识镜子里的自己了。
刘:余老师,这么说可能会吓着你,但我还得说,我觉得最让我安心的地方不是你们活人待着的地方,而是我们死人待着的地方,我知道有一个地方,你从来没去过,你也不可能去过。
余:“我们”死人待的地方,你认为你现在的状态并不是活着?
刘:余老师,我知道有个地儿,那里都是和我一样的人,都是死人。这地儿有个老头,可有意思了,他也不喜欢活人,他也喜欢死人,我就喜欢去他那儿。
刘:嗐,咋说呢,也不是啥神秘的地方,但是我跟你说了你可别跟别人说。
余:嗯,我们有保密原则,咨询室内的信息,不会对外透露的,不过我先问一下,你说的地方不是什么违法乱纪的地方吧。
刘:余老师你想啥呢,我不是那样式儿的人。原先在昌平住的时候,我参加过一个户外俱乐部,认识了一个老头,家是十三陵村里的,老头是个老人院的护工。老人院么,都有个停尸房,他就是个看停尸房的。
刘:开始我跟朱老头不熟,嗐,说是老头,也就五十出头,有一次也是显摆,他带我去过一趟他工作的地儿。一到那儿,我感觉就跟回家了似的。
余:不,我只是确认一下,毕竟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并不会觉得停尸房会给人带来“回家”一样的感觉。
刘:你们是活人,你们当然体会不到。我喜欢待在那个房间里。
|
 当刘文涛一脸陶醉地说起他躲在停尸房里的场景,我就知道这事儿要坏。
2017年2月18日,元宵节后的第一个礼拜六,从来都是准时参加咨询的刘文涛爽约了,他没有提前打电话取消咨询,也没有通知我要推迟。
礼拜二,我正在咨询室整理资料,一个女人闯进来找我,她说自己是刘文涛的妻子,叫李华,她告诉我,刘文涛失踪了。
“他开车从家出来,说来这里做咨询,本来是应该下午四点多就回家的,等到晚上都没信儿,给他打电话不在服务区。”
李华在家等了一天,礼拜一一大早跑去派出所去报了案。
我告诉她,她丈夫礼拜六并没来做咨询,他那天出家门之后应该就失踪了。
李华觉得我应该知道她丈夫去了哪儿,碍于保密原则不愿说,一个劲儿求我。
李华有点激动,“他跟我说过,他会跟你说他的秘密,我听他说过,有个地方能给他减轻压力,他一定告诉过你。”
我只好安慰她,让她相信警察,回家等信儿,我这边也帮她,从咨询录音里找找刘文涛提到的这个地方到底是哪儿。
李华正跟我这儿求情,手机叮的响了一声,她看了眼手机,眼睛瞪得贼大。
我问她什么情况,她把手机递给我,手机上微信的一个停车小程序显示一条信息,她家的车停进了昌平的一个停车场。
李华哀求地看着我,我也想知道刘文涛开车去昌平到底干啥。就直接拽上李华,开车上路。
沿着京藏高速开了一个多小时,开到了这个停车场,在昌平一中对面,一个住宅楼底下。
我开进停车场,路过一辆白车,李华在副驾上指着这车吱哇乱叫,我踩了脚刹车,车没停稳,她就窜出车,从包里掏出车钥匙,打开车门一通看。
我在旁边停好车,围着这辆飞度转了一圈,没发现啥问题。
李华打开车门看了半天,也没查出什么异常,我让她赶紧报警。
警察来了之后,搜查半天,最后让李华开着车跟去交警队调监控。
交警队调出的监控看,车子是最有可能从东关方向进入的昌平城区,在进入昌平城区之前,一直遮挡着号牌,所以警察在调查时没有在第一时间发现车子的行踪。
我跟着李华一直跑到晚上,从交警队出来,我俩在昌平政府街上的一家麦当劳随便吃了个晚饭。
吃饭的时候,李华跟我说了个细节,她在交警队看到了行车记录仪里的录像,刘文涛下车后过了马路,往西走了。
“警察说从记录仪上看,刘文涛也没有被人挟持,也没收到什么伤害,所以没法立案,他们只能配合帮忙寻找,他们说准备调取附近店铺的监控看看,不过得需要点时间。”
从麦当劳出来,我跟李华道了别,她开着自己的车回了市里,我拐了个弯,又来到昌平一中门口的那条路上。
从昌平一中门口往西,直到十字路口,都是昌平一中的院墙。
我开着车向北拐,路边是几个小卖铺,天晚了,有几家都已经关门,单有一间还开着,我进去问了问,没啥收获。
再往前走,路边的公交车站,站牌上一共七八趟公交车,有八方达的长途公交,还有“昌”字头的区内公交车。
我对这些车的线路也不熟悉,就用手机照了张照片,回去方便查。
李华之前的话提醒了我,刘文涛在咨询的过程中,的确提到了一个人,据说是昌平一家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就是那个看死尸的。
我翻出了和刘文涛谈话的录音,找到一个人名,叫朱春平。
刘文涛没跟我说这家养老院的具体位置,只说离长陵镇不远。
我找到拍的公交车站牌,有一路昌55路车,沿着这路公交车的线路,还真在长陵镇附近找到一个养老院。
这天晚上,我来回听了好几遍刘文涛的录音,想从他说的话里再找出点什么线索。
其实在咨询过程中我已经察觉出刘文涛的异样,我一直犹豫要不要建议他到更专业的精神卫生治疗机构去就诊,没等我拿定主意,他就失踪不见了。
刘文涛的异样在于他的妄想,他的抑郁症其实已经很严重,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死人,是一具已经腐烂发臭的尸体。
“我觉得我的内脏已经烂掉了,你能闻到我身上的臭味吗?”
刘文涛的这些幻想与一种称作科塔尔的妄想症十分相似,科塔尔综合征又被称为活死人综合症。
它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当事人认为自己已经死了,其中一种行为就是喜欢待在存放死人的场所,比如太平间或墓地。
我在录音里听到了一个事儿,刘文涛经常独自潜入到敬老院的太平间里,按他的说法是“回家”,自打他跟朱师傅到过太平间之后,他待在“家”的时间越来越长。
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接待了我,我谎称给家里老人看养老院。
接待姓林,我就叫她林姐,她领着我在院子里参观,从宿舍绕到食堂,又绕到一个有凉亭的花园。我看到在花园西北角沿着后墙根有一排平房,没有标识。
我夸了几句环境不错,又问了问老人衣食起居啥的,顺便问道,“咱这儿离城区也不近,那要是老人过身了,咱们这儿是怎么一个流程?”
林姐笑了笑,跟我解释他们的流程,她说我们这里也有太平间,可以暂存老人的遗体,院方和地方民政也有便捷通道。养老院跟附近的墓园也有合作,价格上也有些优惠。
看我一直盯着那排平房,林姐告诉我,那边最里面的几间屋子是太平间。
林姐答应说有,说完就朝站在平房边的一个人喊了声朱师傅,那人转过头。
这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板寸头,身材又高又瘦,长得有点像马三立。
我跟他打了个招呼,说是我一个朋友认识您,也是我朋友介绍我到这儿来的。
我说是刘文涛,听说他这几天到附近的一个山庄来玩,我还没去找他。
“朱师傅,之前不是有个叫刘文涛的来找过你,是不是他啊。”
没等朱师傅开口,林姐就跟朱师傅聊起了院里工作的事儿,托付了两件工作上的事情后,就带着我往医务所走。
我跟林姐又在院子里走了一会儿,跟他说我想独自转转,顺便去找朱师傅聊聊天。
朱春平见到我,一脸不乐意,我问他刘文涛,他言简意赅,回了一个不知道。
我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的联系方式,我跟他说你要是想起刘文涛的事儿,联系我,现在刘文涛联系不上了,家里人都在找他。
还没说完,朱春平的同事进来问事儿,我转身离开办公室,余光看见他顺手把我的联系方式扔进了垃圾桶。
朱春平知道点东西,只是不愿意告诉我,来来往往有同事,我也不好问。
我离开了养老院,回到车里,把车停在能看到养老院大门的路旁,蹲朱春平的点。
这天早上朱春平开了辆面包车上班,下午三点多就下班离开了养老院。
他开着车来到了昌平城区北面的北山公园,面包车沿着一条土路向山脚下开。
我开车跟了一段,把车停在了路边,这附近没有汽车,跟得近了太显眼。
面包车开到了一个土堆边上,朱春平下了车,翻过了土堆,不见了。
我快跑两步,走近了才发现,土堆的后面有个混凝土山洞,是个废弃的人防工事。
这是一股熟悉的气味,我能感觉到我的心跳速度直线上升。
我贴着洞壁慢慢坐下,用深呼吸平复心情,看着朱春平手电筒的光亮一点点变弱,最后还是决定进洞。
进洞之前,我掏出手机,给徐晓发了个定位,然后给她打了个电话,让她来接我。
洞里漆黑一片,我只能看到前面极其微弱的一点光亮,那是朱春平的手电筒发出的光,光亮在前面一暗,然后又亮了起来。
我不敢用照明的东西,一直摸着水泥墙壁往前蹭,离光源近了,才发现在大洞的侧面,有个房间,光从这个房间里照出来。
我没等他把裤子提起来,一脚踹过去,一着急,砖头也捎带手扔出去。
板砖没砸中,这一脚踹的挺结实,直接把朱春平踹进了房间里的一个大坑里。
这个坑就好像一个墓穴一样,朱春平脸朝下趴在了坑里,想站起来,被没提起来的裤子绊了一跤,脑门直接磕在坑沿儿上,磕懵了。
我站起来揉了揉屁股,跳进坑里,抽下他裤子上的尼龙裤带,把他手反绑住,连拖带拽,把他拖出了坑。
到这会儿,我才腾出功夫,捡起地上的手电,照向地上那个穿着破烂的人。
这人穿着一件已经看不出是什么颜色的军大衣,头发胡子老长。
我推了推他,这人没反应,身后朱春平说话,“别杵了,死人。”
朱春平摇头,他也不知道这人是谁,只知道这人是个流浪汉。
我问他知不知道刘文涛去哪儿了,他瞪着个眼睛,不吱声。
我告诉他,你跟我说刘文涛在哪儿,警察调查完证明人不是你杀的,你冲着死尸撸管这事儿,我就当没看见。
朱春平考虑了一会儿说,你别把我今天的事儿说出来,我说行。
朱春平挺点儿背的,今天让我看见的事,前几天也让刘文涛给看见了。
据他说,刘文涛前几天偷偷溜进自己看着的停尸房,在里面躺了不知道多长时间,谁也没发现。
朱春平有个癖好,恋尸。也是因为朱春平对着停尸房的死尸打飞机打得太投入,让刘文涛好奇他在干嘛,起身看了一眼。
哥俩一个恋尸,一个认为自己是尸,俩人推心置腹谈了一宿,朱春平同意让刘文涛待在太平间。
老朱认识一个姓王的人,一直就管他叫大老王,经常一块喝酒,在酒桌上,老朱把刘文涛的事儿当玩笑说了。
老朱说太平间有时候会有尸体没人认领,大老王有卖给医学院的路子,就都处理给大老王。
大老王跟老朱说,你把这人介绍给我,我给你点钱,转天老朱就把刘文涛介绍给大老王。
我问这俩人去哪儿了,朱春平说不知道,可能是回大老王老家了,在张北小二台,昨天刚走。
说到这儿,远处走过来一个人,拎着个棒球棍,是徐晓。
她说我怕你有危险,过来帮你,拿棒子主要是给自己壮胆。
我又嘱咐徐晓跟警察说,赶紧到张家口市张北县小二台镇去抓人,我先走一步,晚了刘文涛可能就梦想成真了。
朱春平一提到大老王,我大概就猜到大老王在吹牛,无人认领的尸体想进医学院,得有公安机关的证明,程序很不简单。
但他“拐”刘文涛是啥意思,我没想明白,我只是觉得,大老王没把刘文涛当活人看。
我顺着朱春平告诉我的地址,我连打听带问,找到大老王的住处,一个农家院子,里面是二层小楼。
我敲了半天门,才出来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圆脸盘,一脸胡子,问我找谁。
我在他身上闻到了一股淡淡的甜味,是乙醚,一种麻醉药。
男人感觉我有点不对劲,手往门背后摸,我让他别动,说我已经报警了。
男人有点懵,喊了一声,屋里跑出来几个男人,都在四十岁以上,岁数最大那个就是大老王。
几个人显然没经过这事,都有点慌,想看我是不是诈他们,又犹豫要不要跑,没讨论个结果,警笛就响了。
我跟警察一起进了屋里,在二楼的木板床上发现刘文涛,已经让人麻翻了,像一具尸体。
刘文涛被拉到张北县医院去洗胃,我跟着警察回公安局做了笔录。
一个多月以后,在我的推荐下,刘文涛住到了我老师周德松的病房里,接受专业治疗。 半年后,他回到我的咨询室,跟我聊了聊这事儿。
大老王确实是倒卖尸体的,他活动的范围就是在冀北京北一带,除了给人配阴婚,他还帮想要土葬的本家寻觅代替火化的尸体。
这个活比配阴婚挣钱,所以有时候,大老王实在找不到尸源,就会找一些流浪汉代替。
经过后来警方调查,在昌平北山公园防空洞里发现的流浪汉,就是大老王所为,他原本算好时间,想把流浪汉诓骗回老家再杀害,没想到流浪汉不配合,大老王失手杀死了流浪汉。
大老王急于找到新的尸源,这时养老院的老朱给他讲了刘文涛的事儿,大老王把目标转向了刘文涛。
挣钱心急,大老王就没想过,刘文涛不像那些流浪汉,他有家有业,有人惦念着他。
这事儿过去不到一个礼拜,有一天徐晓跟我在酒馆喝酒,问我一个事儿。
她说那天我在防空洞洞口跟她碰面,我脸色惨白,两只手不由自主地颤抖,感觉随时都要昏倒,她觉得我这是恐惧症的表现。
她说怪不得你下雨天要戴口罩呢,是因为和以前经历的场景有关吗?
我一想到了9岁那年那个暴雨夜的防空洞,就感觉有股寒意顺着脖梗子往上窜,我喝了一大口酒,都没暖和过来。
我忽然想到刘文涛跟我说过,遮挡车牌开车到昌平的主意,是一个男人给他出的,那人跟他一起到了昌平,然后就不见了。
我问刘文涛那人长啥样。刘文涛说没啥特点,就是个普通人。
徐晓看了看我,什么也没问,可能是看到我脸色又慢慢变白了。
余波又遇见这个神秘的男人,他介入余波患者的生活,引诱他们做一些本不可能做的事。
我知道他躲在暗处,猎手一样静静观察一切,在某些关键时候,又变成毒蛇,给出致命一击。
接下去会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也许下周六10:00,会有答案。
当刘文涛一脸陶醉地说起他躲在停尸房里的场景,我就知道这事儿要坏。
2017年2月18日,元宵节后的第一个礼拜六,从来都是准时参加咨询的刘文涛爽约了,他没有提前打电话取消咨询,也没有通知我要推迟。
礼拜二,我正在咨询室整理资料,一个女人闯进来找我,她说自己是刘文涛的妻子,叫李华,她告诉我,刘文涛失踪了。
“他开车从家出来,说来这里做咨询,本来是应该下午四点多就回家的,等到晚上都没信儿,给他打电话不在服务区。”
李华在家等了一天,礼拜一一大早跑去派出所去报了案。
我告诉她,她丈夫礼拜六并没来做咨询,他那天出家门之后应该就失踪了。
李华觉得我应该知道她丈夫去了哪儿,碍于保密原则不愿说,一个劲儿求我。
李华有点激动,“他跟我说过,他会跟你说他的秘密,我听他说过,有个地方能给他减轻压力,他一定告诉过你。”
我只好安慰她,让她相信警察,回家等信儿,我这边也帮她,从咨询录音里找找刘文涛提到的这个地方到底是哪儿。
李华正跟我这儿求情,手机叮的响了一声,她看了眼手机,眼睛瞪得贼大。
我问她什么情况,她把手机递给我,手机上微信的一个停车小程序显示一条信息,她家的车停进了昌平的一个停车场。
李华哀求地看着我,我也想知道刘文涛开车去昌平到底干啥。就直接拽上李华,开车上路。
沿着京藏高速开了一个多小时,开到了这个停车场,在昌平一中对面,一个住宅楼底下。
我开进停车场,路过一辆白车,李华在副驾上指着这车吱哇乱叫,我踩了脚刹车,车没停稳,她就窜出车,从包里掏出车钥匙,打开车门一通看。
我在旁边停好车,围着这辆飞度转了一圈,没发现啥问题。
李华打开车门看了半天,也没查出什么异常,我让她赶紧报警。
警察来了之后,搜查半天,最后让李华开着车跟去交警队调监控。
交警队调出的监控看,车子是最有可能从东关方向进入的昌平城区,在进入昌平城区之前,一直遮挡着号牌,所以警察在调查时没有在第一时间发现车子的行踪。
我跟着李华一直跑到晚上,从交警队出来,我俩在昌平政府街上的一家麦当劳随便吃了个晚饭。
吃饭的时候,李华跟我说了个细节,她在交警队看到了行车记录仪里的录像,刘文涛下车后过了马路,往西走了。
“警察说从记录仪上看,刘文涛也没有被人挟持,也没收到什么伤害,所以没法立案,他们只能配合帮忙寻找,他们说准备调取附近店铺的监控看看,不过得需要点时间。”
从麦当劳出来,我跟李华道了别,她开着自己的车回了市里,我拐了个弯,又来到昌平一中门口的那条路上。
从昌平一中门口往西,直到十字路口,都是昌平一中的院墙。
我开着车向北拐,路边是几个小卖铺,天晚了,有几家都已经关门,单有一间还开着,我进去问了问,没啥收获。
再往前走,路边的公交车站,站牌上一共七八趟公交车,有八方达的长途公交,还有“昌”字头的区内公交车。
我对这些车的线路也不熟悉,就用手机照了张照片,回去方便查。
李华之前的话提醒了我,刘文涛在咨询的过程中,的确提到了一个人,据说是昌平一家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就是那个看死尸的。
我翻出了和刘文涛谈话的录音,找到一个人名,叫朱春平。
刘文涛没跟我说这家养老院的具体位置,只说离长陵镇不远。
我找到拍的公交车站牌,有一路昌55路车,沿着这路公交车的线路,还真在长陵镇附近找到一个养老院。
这天晚上,我来回听了好几遍刘文涛的录音,想从他说的话里再找出点什么线索。
其实在咨询过程中我已经察觉出刘文涛的异样,我一直犹豫要不要建议他到更专业的精神卫生治疗机构去就诊,没等我拿定主意,他就失踪不见了。
刘文涛的异样在于他的妄想,他的抑郁症其实已经很严重,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死人,是一具已经腐烂发臭的尸体。
“我觉得我的内脏已经烂掉了,你能闻到我身上的臭味吗?”
刘文涛的这些幻想与一种称作科塔尔的妄想症十分相似,科塔尔综合征又被称为活死人综合症。
它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当事人认为自己已经死了,其中一种行为就是喜欢待在存放死人的场所,比如太平间或墓地。
我在录音里听到了一个事儿,刘文涛经常独自潜入到敬老院的太平间里,按他的说法是“回家”,自打他跟朱师傅到过太平间之后,他待在“家”的时间越来越长。
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接待了我,我谎称给家里老人看养老院。
接待姓林,我就叫她林姐,她领着我在院子里参观,从宿舍绕到食堂,又绕到一个有凉亭的花园。我看到在花园西北角沿着后墙根有一排平房,没有标识。
我夸了几句环境不错,又问了问老人衣食起居啥的,顺便问道,“咱这儿离城区也不近,那要是老人过身了,咱们这儿是怎么一个流程?”
林姐笑了笑,跟我解释他们的流程,她说我们这里也有太平间,可以暂存老人的遗体,院方和地方民政也有便捷通道。养老院跟附近的墓园也有合作,价格上也有些优惠。
看我一直盯着那排平房,林姐告诉我,那边最里面的几间屋子是太平间。
林姐答应说有,说完就朝站在平房边的一个人喊了声朱师傅,那人转过头。
这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板寸头,身材又高又瘦,长得有点像马三立。
我跟他打了个招呼,说是我一个朋友认识您,也是我朋友介绍我到这儿来的。
我说是刘文涛,听说他这几天到附近的一个山庄来玩,我还没去找他。
“朱师傅,之前不是有个叫刘文涛的来找过你,是不是他啊。”
没等朱师傅开口,林姐就跟朱师傅聊起了院里工作的事儿,托付了两件工作上的事情后,就带着我往医务所走。
我跟林姐又在院子里走了一会儿,跟他说我想独自转转,顺便去找朱师傅聊聊天。
朱春平见到我,一脸不乐意,我问他刘文涛,他言简意赅,回了一个不知道。
我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的联系方式,我跟他说你要是想起刘文涛的事儿,联系我,现在刘文涛联系不上了,家里人都在找他。
还没说完,朱春平的同事进来问事儿,我转身离开办公室,余光看见他顺手把我的联系方式扔进了垃圾桶。
朱春平知道点东西,只是不愿意告诉我,来来往往有同事,我也不好问。
我离开了养老院,回到车里,把车停在能看到养老院大门的路旁,蹲朱春平的点。
这天早上朱春平开了辆面包车上班,下午三点多就下班离开了养老院。
他开着车来到了昌平城区北面的北山公园,面包车沿着一条土路向山脚下开。
我开车跟了一段,把车停在了路边,这附近没有汽车,跟得近了太显眼。
面包车开到了一个土堆边上,朱春平下了车,翻过了土堆,不见了。
我快跑两步,走近了才发现,土堆的后面有个混凝土山洞,是个废弃的人防工事。
这是一股熟悉的气味,我能感觉到我的心跳速度直线上升。
我贴着洞壁慢慢坐下,用深呼吸平复心情,看着朱春平手电筒的光亮一点点变弱,最后还是决定进洞。
进洞之前,我掏出手机,给徐晓发了个定位,然后给她打了个电话,让她来接我。
洞里漆黑一片,我只能看到前面极其微弱的一点光亮,那是朱春平的手电筒发出的光,光亮在前面一暗,然后又亮了起来。
我不敢用照明的东西,一直摸着水泥墙壁往前蹭,离光源近了,才发现在大洞的侧面,有个房间,光从这个房间里照出来。
我没等他把裤子提起来,一脚踹过去,一着急,砖头也捎带手扔出去。
板砖没砸中,这一脚踹的挺结实,直接把朱春平踹进了房间里的一个大坑里。
这个坑就好像一个墓穴一样,朱春平脸朝下趴在了坑里,想站起来,被没提起来的裤子绊了一跤,脑门直接磕在坑沿儿上,磕懵了。
我站起来揉了揉屁股,跳进坑里,抽下他裤子上的尼龙裤带,把他手反绑住,连拖带拽,把他拖出了坑。
到这会儿,我才腾出功夫,捡起地上的手电,照向地上那个穿着破烂的人。
这人穿着一件已经看不出是什么颜色的军大衣,头发胡子老长。
我推了推他,这人没反应,身后朱春平说话,“别杵了,死人。”
朱春平摇头,他也不知道这人是谁,只知道这人是个流浪汉。
我问他知不知道刘文涛去哪儿了,他瞪着个眼睛,不吱声。
我告诉他,你跟我说刘文涛在哪儿,警察调查完证明人不是你杀的,你冲着死尸撸管这事儿,我就当没看见。
朱春平考虑了一会儿说,你别把我今天的事儿说出来,我说行。
朱春平挺点儿背的,今天让我看见的事,前几天也让刘文涛给看见了。
据他说,刘文涛前几天偷偷溜进自己看着的停尸房,在里面躺了不知道多长时间,谁也没发现。
朱春平有个癖好,恋尸。也是因为朱春平对着停尸房的死尸打飞机打得太投入,让刘文涛好奇他在干嘛,起身看了一眼。
哥俩一个恋尸,一个认为自己是尸,俩人推心置腹谈了一宿,朱春平同意让刘文涛待在太平间。
老朱认识一个姓王的人,一直就管他叫大老王,经常一块喝酒,在酒桌上,老朱把刘文涛的事儿当玩笑说了。
老朱说太平间有时候会有尸体没人认领,大老王有卖给医学院的路子,就都处理给大老王。
大老王跟老朱说,你把这人介绍给我,我给你点钱,转天老朱就把刘文涛介绍给大老王。
我问这俩人去哪儿了,朱春平说不知道,可能是回大老王老家了,在张北小二台,昨天刚走。
说到这儿,远处走过来一个人,拎着个棒球棍,是徐晓。
她说我怕你有危险,过来帮你,拿棒子主要是给自己壮胆。
我又嘱咐徐晓跟警察说,赶紧到张家口市张北县小二台镇去抓人,我先走一步,晚了刘文涛可能就梦想成真了。
朱春平一提到大老王,我大概就猜到大老王在吹牛,无人认领的尸体想进医学院,得有公安机关的证明,程序很不简单。
但他“拐”刘文涛是啥意思,我没想明白,我只是觉得,大老王没把刘文涛当活人看。
我顺着朱春平告诉我的地址,我连打听带问,找到大老王的住处,一个农家院子,里面是二层小楼。
我敲了半天门,才出来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圆脸盘,一脸胡子,问我找谁。
我在他身上闻到了一股淡淡的甜味,是乙醚,一种麻醉药。
男人感觉我有点不对劲,手往门背后摸,我让他别动,说我已经报警了。
男人有点懵,喊了一声,屋里跑出来几个男人,都在四十岁以上,岁数最大那个就是大老王。
几个人显然没经过这事,都有点慌,想看我是不是诈他们,又犹豫要不要跑,没讨论个结果,警笛就响了。
我跟警察一起进了屋里,在二楼的木板床上发现刘文涛,已经让人麻翻了,像一具尸体。
刘文涛被拉到张北县医院去洗胃,我跟着警察回公安局做了笔录。
一个多月以后,在我的推荐下,刘文涛住到了我老师周德松的病房里,接受专业治疗。 半年后,他回到我的咨询室,跟我聊了聊这事儿。
大老王确实是倒卖尸体的,他活动的范围就是在冀北京北一带,除了给人配阴婚,他还帮想要土葬的本家寻觅代替火化的尸体。
这个活比配阴婚挣钱,所以有时候,大老王实在找不到尸源,就会找一些流浪汉代替。
经过后来警方调查,在昌平北山公园防空洞里发现的流浪汉,就是大老王所为,他原本算好时间,想把流浪汉诓骗回老家再杀害,没想到流浪汉不配合,大老王失手杀死了流浪汉。
大老王急于找到新的尸源,这时养老院的老朱给他讲了刘文涛的事儿,大老王把目标转向了刘文涛。
挣钱心急,大老王就没想过,刘文涛不像那些流浪汉,他有家有业,有人惦念着他。
这事儿过去不到一个礼拜,有一天徐晓跟我在酒馆喝酒,问我一个事儿。
她说那天我在防空洞洞口跟她碰面,我脸色惨白,两只手不由自主地颤抖,感觉随时都要昏倒,她觉得我这是恐惧症的表现。
她说怪不得你下雨天要戴口罩呢,是因为和以前经历的场景有关吗?
我一想到了9岁那年那个暴雨夜的防空洞,就感觉有股寒意顺着脖梗子往上窜,我喝了一大口酒,都没暖和过来。
我忽然想到刘文涛跟我说过,遮挡车牌开车到昌平的主意,是一个男人给他出的,那人跟他一起到了昌平,然后就不见了。
我问刘文涛那人长啥样。刘文涛说没啥特点,就是个普通人。
徐晓看了看我,什么也没问,可能是看到我脸色又慢慢变白了。
余波又遇见这个神秘的男人,他介入余波患者的生活,引诱他们做一些本不可能做的事。
我知道他躲在暗处,猎手一样静静观察一切,在某些关键时候,又变成毒蛇,给出致命一击。
接下去会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也许下周六10:00,会有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