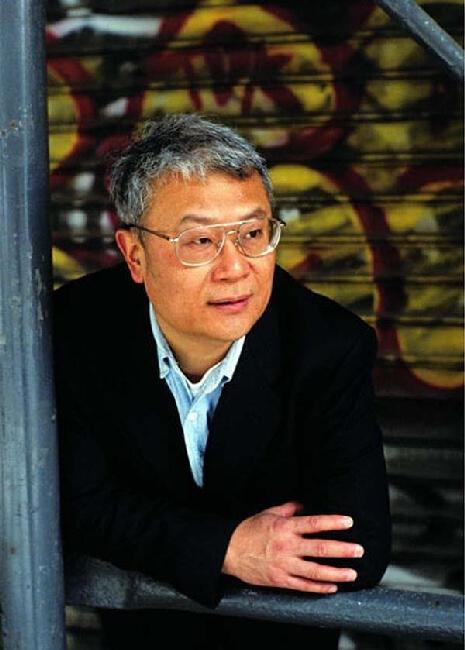博士和民工
2021年06月04日 17:59 分类:生活 阅读:573
某跨国公司发现,肥皂生产线上存在有包装时可能漏包肥皂的问题。
于是该公司总裁命令某个博士组建团队对这个问题攻关。
该研发团队使用了世界上最高精尖的技术(如红外探测、激光照射等),
在花费了几十万美金和半年时间后开发了一套肥皂盒检测系统,问题终于解决了。
有意思的是,某个乡镇肥皂企业也遇到类似问题。老板命令初中毕业的流水线工头想办法解决。
经过半天的思考,工头扛了一台电扇到生产线的末端吹风,那些没有装填肥皂的空盒子都被风吹下去了。
问题也解决了,而且不花一分钱!
【此处应有今日头条、天涯论坛等网民或反智人士的无数唾沫喷给博士,掌声送给民工......】
且慢高兴,故事并没有结束。
后续故事1:
针对吹风扇的“高招”,有高人问了几个问题:
1、在空盒子被吹掉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盒子的翻滚、相互碰撞等不可预料的情况,
可能致使非空的盒子移位或者同样被撞掉。
这会给生产线上后续的步骤带来一定的干扰(比如影响后面的自动装箱),
严重时可能会导致整个生产线停顿。
而以跨国公司的出货速度,一旦某个空盒子乱飞乱撞导致生产线停顿的事故,
每秒钟都可能会引起成千上万元的经济损失,这是公司所不能接受的。
2、检测精度难以控制,无法保证100%的空盒子全部被检出,并且装了香皂的盒子也有可能被误吹掉。
漏检和误检给跨国公司带来的损失也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
3、被吹掉的盒子跌落在地上,需要专人人工去处理,而且有可能因为跌落的缘故,
或者处理不当等原因造成香皂盒的破损。
4、跨国公司对香皂质量要求很高,有可能要求生产现场是无尘、无菌车间。
因此采用电风扇吹的方式他们肯定无法接受。
后续故事2:
小工立了一功,老板很高兴,给了1000块奖金,皆大欢喜。
“走,哥们几个喝酒去”。可是在经济危机的海啸中,公司要裁员,小工要被砍。
小工说:“我立过功啊。”
老板说:“立个毛啊,屁大点事情,小聪明!”
那个博士呢?他研究出机械抓臂,发表了论文,申请了专利,开了个公司,将这项技术大规模推广。
跨国公司在肥皂生产线安装空盒识别器之后,忽然有一天发现,有的肥皂盒内虽然有肥皂,
但是只有半块,有得也有瑕疵,怎么办呢?
还好博士就是厉害,一个机械抓臂够“模块化”,咱就把“红外线识别”模块改成“瑕疵肥皂识别”模块,
真省事。而此时可怜的乡镇企业的大工(小工被裁了)伤透了脑筋。
电风扇只能吹走空盒啊,怎么办?几年后,小工还是小工,博士变成了百万富翁。
如果我们把博士和民工看做是两种文化(高科技vs.小聪明)、
两类国家(技术创新vs.山寨)、两套思路(系统解决vs.头痛医头),是不是也很贴切?
(说明:本文素材来自网络,出处不详。)
============================================================
李银河:做一个世俗的出离之人
2021年06月04日 17:45 分类:生活 阅读:127
在信息爆炸时代,一瞥之下,只觉周围世事喧闹,如波涛汹涌,心境竟是只想远离,出世,躲进精神的桃花源。
人到了可以不问世事的年龄和位置,真是一件惬意的事。从此可以摆脱所有的纠结与烦恼,回归存在本身。
在年轻时,为生存,为奉献社会,人不得不辛劳忙碌,至少要挣钱谋生,好些的要在本行中出类拔萃,
最好的还要能够产生些社会的影响,推动社会的改良。
但是到了可以颐养天年的岁数,人终于获得了自由,物质的自由和精神的自由,
可以随心所欲不逾矩,可以从尘世出离。
然而,这出离之心并不是出家人的出离,而是世俗之人的出离。
远离所有的诱惑,所有的热闹,所有的虚荣,来到那个最纯粹最洁净最愉悦的世界。
这两种出离最大的区别是,出家人的修行旨在消弭人身固有的各类欲望,即使不能修炼到欲望全无的程度,
也要竭尽全力把欲望压制到最低,只保持生存的最低条件,温饱而已,
其余的生命全部用来修炼到无色界31天。
而世俗凡人的出离只是摆脱世间烦恼之事,满足各类身心欲望,以愉悦自身身心的态度度过人生。
做一个世俗的出离之人,让生命活在多彩多姿的精神世界。
=============================================================
远离中国的哈金让我读到了切肤之痛的中国故事
余华
我很欣赏美国笔会在授予《等待》二000年福克纳小说奖时,对哈金的赞誉:“在疏离的后现代时期,仍然坚持写实派路线的伟大作家之一。”
二00三年初春的时候,我在北京国林风书店买到了《等待》,然后又见了几个朋友,回家时已是凌晨。我翻开了这部著名的小说,打算读上一两页,了解一下哈金的叙述风格就睡觉。没想到我一口气读完了这部书。当我翻过最后一页时,已经是晨光初现,然后我陷入到冥思苦想之中。我惊讶哈金推土机似的叙述方式,笨拙并且轰然作响。哈金的写作是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段叙述都是扎扎实实的。在他的小说里,我们读不到那些聪明作家惯用的回避和跳跃,这种无力的写作至今风行,被推崇为写作的灵气。作为同行,我知道迎面而上的写作是最困难的,也是最需要力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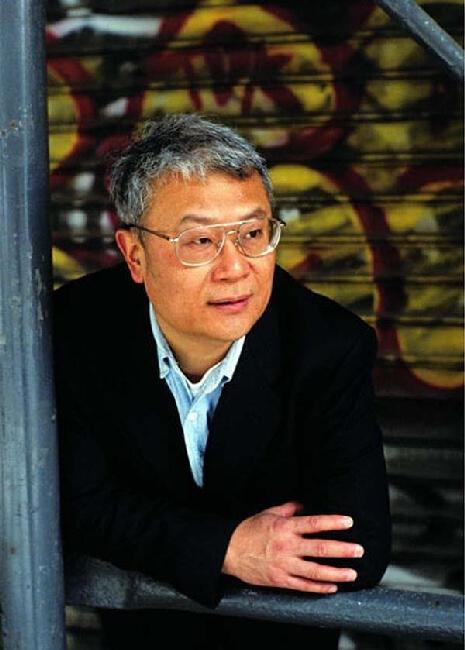
哈金
这个一九五六年出生的中国人,当过兵,念过大学,二十九岁时漂洋过海去了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任教于美国的大学。这是那个时代很多年轻中国人选择的康庄大道。可是用英语写作后,哈金奇特的人生之路开始了。毕竟哈金去美国时已经不是一个孩子,而是一个成年人了。一个带着深深的中国现实和中国历史烙印的成年人,用异国他乡的语言来表达自己故乡的悲喜交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可是哈金做到了。他的每一部英语小说都要修改二十多遍,并不是为了对人物和故事细节上的把握,而是对英语用词分寸的把握。美国是一个在很多方面十分规矩的国家。作为著名的波士顿大学英语文学写作的教授,哈金不能向他的同事请教,更不能向他的学生请教。哈金的太太是一位地道的中国人,她的英语表达能力远远不如哈金。哈金在用英语写作时可以说是举目无亲,只能自己苦苦摸索。
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写出来的英语让一些纯种美国人都赞叹不已。而我,一个中国人,读到自己同胞的小说时,却是一部翻译小说。可是这部名叫《等待》的翻译小说,让我如此接近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近到几乎贴在一起了。很多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甚至从未离开过中国的作家写出来的小说,为什么总让我觉得远离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我读到了太多隔靴搔痒的中国故事,可是远离中国的哈金让我读到了切肤之痛的中国故事。
我想这就是一个作家的力量—无论他身在何处,他的写作永远从根部开始。哈金小说所叙述的就是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根部。那些紧紧抓住泥土的有力的根,当它们隆出地面时,我们看到了密集的关节,这些老骥伏枥的关节讲述的就是生存的力量。
《等待》之后,我又读了哈金的《疯狂》,以及零星发表在中国杂志上的一些短篇小说。现在铁葫芦图书即将推出哈金的代表作,这对于国内的读者认识哈金作品的全貌是件好事。这位美国的少数民族作家,在享誉国际文坛之后,以这样的方式回来,令人欣喜。在我眼中,哈金永远是一位中国作家,因为他写下了地道的和有力的中国故事,虽然他使用了我所不懂的语言。
我难忘第一次在波士顿见到哈金的情景:那天晚上大雨滂沱,哈金带着我们一家三口在哈佛广场寻找酒吧,所有的酒吧都拒绝我十岁的儿子进入,最后我们四个人在大雨中灰溜溜地来到了旅馆,在房间里开始了我们的长谈。那是二00三年十一月的某一天。
文章来源:
https://www.zgnfys.com/a/nfwx-5893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