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138)
农村老人自杀:隐忍晚年的最后一声呼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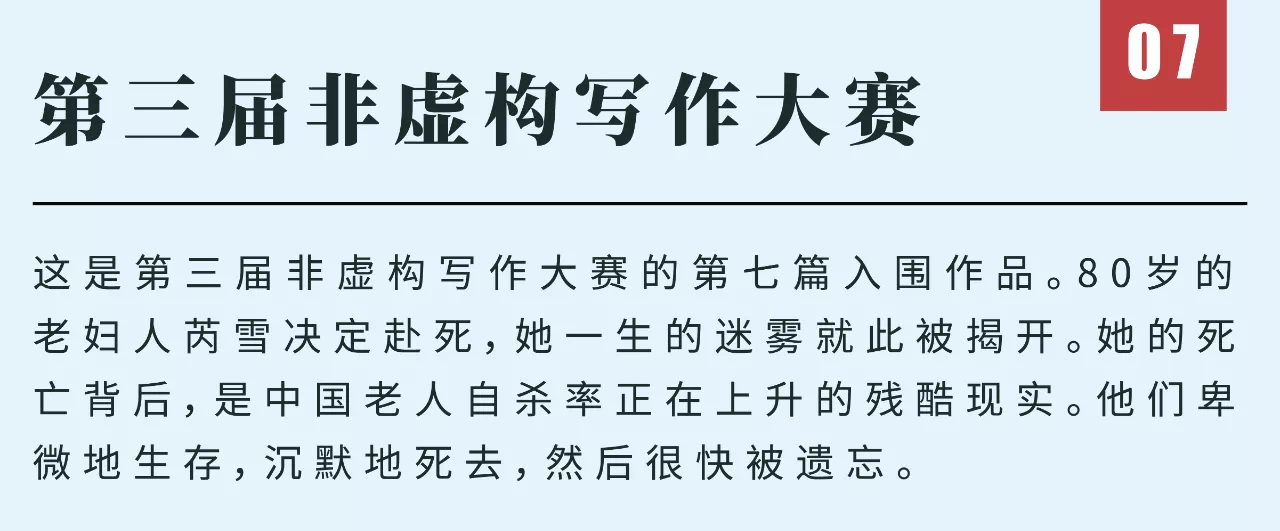
庆功酒

图 | 丁湖村主路
2

图 | 升金湖

图 | 芮雪的葫芦
================================================================
家,无法告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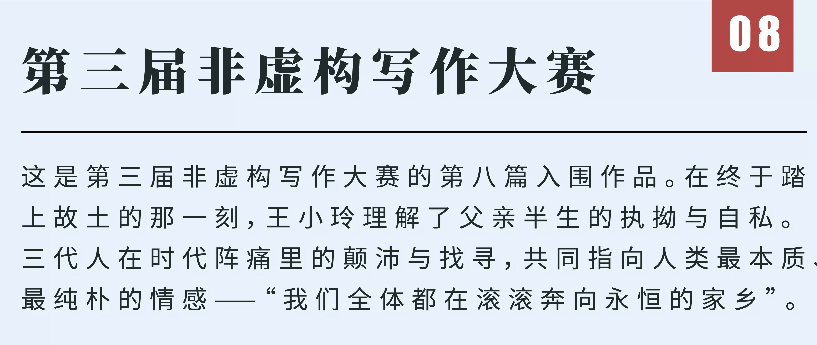
对父亲来说,青海巴仓农场有种种不详的征兆。
1958年,父亲在大跃进期间获罪,和其他犯人一道,被押在闷罐车里,颠簸了十几天,最后被扔在青海省贵南县的巴仓农场,获释后在此定居。
我们兄妹三人,原本安稳生长于兹。但大哥20岁那年,去场部的文化室看电视,在向管理员要钥匙的时候,好好的一个人,突然倒地去世。
一年之中,跟大哥一样突然死亡的年轻人有好几个。有人说,前些年这里死了很多犯人,邪气重,专克年轻人。
大哥的离世,让父亲对这里产生了深深的恐惧和怨恨。

我们一家五口就住在这间低矮破旧的房子里。靠着父亲修拖拉机那点儿工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那时,一家人的主食通常是洋芋和青稞面,一个月定量供应的15斤白面根本不够吃。
即使如此,作为高原孩子的我,对巴仓农场的记忆依然是温柔的。走出农场,是一片不见天际的原野,我喜欢跟农场的子弟们一起,在原野上无忧无虑地玩耍。
农忙时节,父亲经常要加夜班,农场提供夜宵,有馒头、烙饼、炒饭,父亲舍不得独自享用,会用茶缸装回来给我们吃。母亲虽然目不识丁,但勤劳、贤惠,用最大的爱呵护着这个家。
农场里有一台淘汰下来的磨浆机,父亲求了好多人,才以废铁的价钱买下。父亲小时候看过村里人做过豆腐,凭着记忆开始尝试。
他自己打土坯,在原来房子的外面搭了一间房子,开起了一家小吃店,经营豆腐、豆浆、油条和面食,我们的课余时间经常在小吃店里帮忙,生活因此有了很大的改善。

但父亲的悲伤始终蛰伏在他心底,有时候溜出来,在他最柔软的地方咬上一口。
冬日的巴仓农场,天寒地冻,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每逢除夕夜,父亲讲的全是他小时候的事情。说着说着,父亲眼圈就红了——他想念老家。
父亲的故乡位于浙江省常山县白石镇的蒋村,那是与西北高寒农场相去甚远的江南小县:
祖母是小脚,针线活是村里的一绝;村口的小溪,有成群的石斑鱼,用网捕上来,裹上面粉油炸,是下酒的好菜;后山有成片的毛竹,春天,竹笋两天不拔就长到半人高;家门口的那棵柿子树是祖辈就种下的,结出的柿子又红又甜,吃不完,就做成柿饼,留着过年吃。
2
刚开始,父亲只是试探母亲:“要不,我们一家人迁回我老家生活吧?”母亲坚决不同意,说:“孩子们在这里都习惯了,再说,转学过去,会影响成绩。”父亲轻声嘀咕道:“人年纪一大,就更想老家了。”
1989年年初,父亲预订了车票,准备春节期间带全家人回老家探亲,但出发的前一天下起大雪,道路封闭,车辆不通。那个春节,父亲过得闷闷不乐。
大哥离世之后,父亲离开的决心更甚。有时候喝了酒,就冲母亲吼:“要是当时听我的回老家,儿子就不会死,这里不能呆了。”
尽管心脏病、类风湿、高血压等疾病缠身,也没能动摇父亲。上高中时,父亲决定先把我送回蒋村。一直以来,父亲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回老家的行李是父亲帮我收拾整齐的,一条被褥,被绳子紧紧地捆扎成一团。
独自去往陌生异乡,让我无比惶恐。那天晚饭后,我独自出了家门,原野已经被帷幕一样的暮色包围,让我有些透不过气。
回到屋已很晚,父母都已经睡下,我偷偷地把捆紧的被褥松开。第二天起床时,被褥又被捆好了。父亲看我一眼说:“我送你上车站。”我眼泪就刷地流下。
我转入蒋村的一所学校,寄住在大伯的家里。父亲自己也在到处送礼托关系,要办理病退,尽快回到老家。
蒋村的一切都那么陌生,让我最不适应的是气候,潮湿、闷热,夏天的时候,身上被蚊子咬得全是包,还流着脓水。
一天晚上,我特别想念远在几千公里之外的父母,独自一人坐在村口的大石头上流眼泪。有一位村干部路过时看到我,担心我出事,把大伯一家人都叫来了。

图|浙江省常山县蒋村外境
一直在高寒的青海生活,我脸上有高原红,很多同学私下里都叫我青海妹子,我总是融入不到他们中去。
那时候还没有移动电话,我用攒下的零花钱,在学校旁的公用电话亭拨通了巴仓农场的长途电话,一听到父亲的声音,我就哭了:“爸爸,我要回家。”父亲说:“那里就是家啊,是爸爸的家,也是你的家。”
1997年3月份,56岁的父亲终于办妥病退手续,快速将农场的房子和家具以最便宜的价钱处理掉,带着母亲回到老家蒋村。后来,大学毕业的二哥也留在浙江省杭州市工作。我们一家彻底与青海断绝了关系。
父亲拿出多年积蓄,在老屋边上盖了一座砖混结构的二层房子。在外漂泊大半生的父亲,带着一身的病痛,终于回到故乡,落叶归根了。
代价是,我们家其余的人都被迫远离故乡。父亲是自私的,他似乎从未顾及我们的感受。
母亲也曾提过,想回青海看看亲人,或者住上一段时间。但那时候,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经受不起长途车旅劳顿。何况,在巴仓农场早逝的大哥,是父亲心口永远结痂不了的伤,大家都不愿去触碰。
也许是被压抑了太久,也许是出于对父亲的埋怨,我开始故意叛逆,与父亲作对。高考那年,我落榜了,这让父亲非常失望。
第二年,我认识了我的前夫。他是蒋村人,为人本分,对我也非常照顾。但父母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认为他是农村户口,不能给我一个幸福的未来。
我当时执拗,偷偷从家里拿出户口本,跟前夫登记结婚。
回到故乡的父亲并不开心,蒋村早已不是他年轻时的样子。在巴仓农场度过了近40年,而故乡,不过占据了他前17年的时间。哪里才是故乡?他开始摇摆。
母亲同样不快乐,我经常看到两个老人默默地坐在门口,父亲看着门口的那棵柿子树发呆,而母亲,则望着通往外面的那条村道出神。
2006年,父亲得了重病,从检查出来到去世,不到半年时间。
父亲去世后,以前常念叨要回青海的母亲,倒是再也没有提起这个话题。母亲在浙江生活,语言不通,除我之外,几乎没有一个亲人,她内心的那种孤独和寂寞,别人是体会不到的。
在母亲面前,我变得更加小心翼翼,从不跟她谈论有关青海的话题,怕触动她的思乡之情。
一天晚上,母亲和我正吃着饭,她说:“我以后死了,你把我跟你爸爸葬在一起,我陪着他,你爸爸,可怜。你大哥,更可怜,青海那么远那么冷,没人陪他。”
我听后泪水直流,又怕她看见,就偷偷地抹去,心里说:“妈妈,你也可怜。”
我经常会在睡梦中回到巴仓农场。2005年7月的一天,我像被什么东西牵引着一样,鬼使神差,独自一人坐上去西宁的火车。但下了火车,我没敢坐上开往巴仓农场的汽车。
我怕到了那里,看到那些熟悉的景和人,再也不肯离开,于是立即买下一张返程的火车票。
猛然间,我在自己身上看见父亲的影子。渐渐的,对他的怨气变成了理解。
父亲离乡时才17岁,跟我离开青海时的年龄相仿。父亲是家里唯一一个上初中的孩子。1958年,“大跃进”运动期间,父亲告发占有集体物资的生产队蒋队长,举报不成,反而因此获罪。
那年的10月初,家门口那棵柿子树上的柿子红如烈焰。父亲被判了15年,被带走时,没有告知家人一声,也不允许捎带换洗衣服。
父亲被送往西北劳改农场,从事种地、喂猪、牧马、赶车、制坯、烧窖、修渠等劳动。父亲拼命干活,希望能减刑,早一天回到老家。1971年10月中旬,获得两年减刑的父亲刑满释放。那年,他30岁。
一位姓区的管教干部找父亲谈话,建议他留在农场:“回老家种地,生产队记的是工分,年底才分红。倒不如在农场就业,每个月有48到52元,发的还是现钱。”
父亲说:“我还是想回家。”
那天,巴仓农场下起那年的第一场雪。父亲走出劳改农场大门时,仰起头,让漫天飞舞的雪花落在脸上,平复自己激动的心情。往前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整整呆了13年的地方,然后一转身,踏上了回乡的路途。

与当初被带走时一样,回到蒋村时,门口的柿子树上正红得耀眼。当父亲出现在大伯和大姑的面前,他们几乎不敢相认,眼前的这个人,苍老、黑瘦、拘谨,根本找不着以前的影子。
大伯已经成家,生养了两子一女;大姑嫁在邻村,也有一儿一女,日子过得贫困。而当年陷害父亲的蒋队长,3年前生了一场病,已经去世。
大伯整理出一个房间,让父亲安顿下来,随后带着他去生产队参加劳动。父亲干活舍得下力气,但别人总是有意无意地躲着他,就连以前的玩伴也不愿意同他来往。
一次,生产队长指派两名社员跟父亲一起挖畦,其中一人说:“队长,你派别人去吧,我不愿跟犯人一起干活。”
大伯的房子本就不宽敞,父亲住进来后更加拥挤。伯母的脸色慢慢地不好看起来,时不时要甩几句风凉话。
父亲在青海呆了13年,老家的气候一时未能适应,感冒发烧全身打摆子。他独自一人躺在床上,突然有了物是人非的感觉——这还是自己日思夜想,竭尽全力想要回到的故乡吗?
父亲想起了区管教的话,决定回青海的巴仓农场。
1971年12月,与巴仓农场分开50多天后,父亲重新回到了这里,他找到区管教,张口就说:“我回来了,再也不走了。”
区管教点点头说:“哪里的黄土不养人,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像你们这些人,留场就业是最好的选择。”
在巴仓农场,刑满之后留场就业的人占了五成,有的是习惯了农场的生活,有的是家乡已经无房无地无亲人,也有一些像父亲一样,感觉到故乡已物是人非,又再度折返。
和大多数人一样,父亲也想在高寒的西北农场有个家。1974年5月,在别人的介绍下,他认识了另一个村庄的母亲。随着我们兄妹三人陆续出生,父亲终于过上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

图|王小玲
生活在浙江的女儿,是我最大的牵挂。工作和生活都稳定下来以后,我希望女儿也能走进青海,毕竟这里,是她外婆的故乡,是她外公工作和生活过几十年的地方,也是她妈妈难以割舍的家园。
2016年的暑假,我把13岁的女儿带到了巴仓农场。
我陪她去了我们曾经的土坯房和小吃店,带着她去原野上采摘狼毒花,带着她去见识在高寒地带顽强生存的牦牛,也给她讲了许多往事。
但到了第4天,女儿的新鲜感过去,变得沉闷起来。那天正吃着晚饭,女儿说:“妈妈,我想回家了。”
我听后,心往下一沉。我知道,在女儿的心里,她的家,在浙江常山那个名叫蒋村的地方,不是青海的巴仓农场。
父亲的故乡,是我的他乡;父亲的他乡,成了我的故乡;我的故乡,又成了女儿的他乡。
人生可以去的地方很多,可以回的地方却很少。可以回的地方,是家,是故乡。然而,对于我们一家三代人来说,哪里才是真正的故乡?
*以上为王小玲口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