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史记(二十一)
「虎妈」影响了晚清的历史走向 | 短史记
问:请编辑谈下光绪与慈禧的真实关系。看到有学者说他们是平常母子,不是亲生胜似亲生,史料可以证明他们母慈子孝。
这大概是一种所谓的“翻案太过,反失其真”。其实,略读一下帝师翁同龢的日记,便能知道这种说法难以成立。
作为一位“虎妈”,慈禧在教育子嗣方面,可谓极其失败。
亲生儿子载淳,也就是同治皇帝,六岁即位后便长期处于慈禧的严密保护与管控之下,极少能随心所欲。甚至于在载淳大婚之后,慈禧仍“阴使内监时时监视之”。她还给帝师李鸿藻等人颁布懿旨,要他们在同治皇帝亲政后“照常入直,尽心讲贯”[1],也就是继续按以前的办法给皇帝上课。慈禧的本意,是为了将儿子培养成一代贤主,所以经常告诫他“毋辄至宫中,致妨政务”,不许他将精力耗在后宫。但同治皇帝血气方刚,又不敢违忤母亲,对策便是表面上“终岁独宿乾清宫”[2];暗地里偷偷潜出紫禁城,去各种不便描述之地“微行”。
到了后来,同治皇帝喜欢“微行”眠花宿柳,已是朝臣中不公开的秘密。1874年10月31日,帝师翁同龢在日记中含蓄地记载说:皇帝昨天又悄悄出宫去了,回宫时太监所乘马车出了意外,驾车的马受惊,马车从神武门一直飞驰到景运门,万幸皇帝坐的是轿子,安然无恙[3]。翁日记里还说,这天之前的10天里,皇帝都没到书房读书,这天之后也是如此。身为帝师,翁居然有整整一个月没机会去给皇帝上课[4]。原因不言自明:“为什么皇帝懒于读书?说白了就是经常夜间外出,弄得筋疲力尽,第二天哪有精神读书。学生放老师的假,老师无可奈何,只能干着急。”[5]
同治皇帝后来被传死于梅毒——较大的可能是天花与梅毒同时病发[6],便与这种长期被“虎妈”管控而生出的“微行”癖好有关。

♦ 同治皇帝,引自故宫博物院网站
载淳死后,慈禧选定胞妹之子、年仅四岁的载湉继承帝位。教训在前,慈禧对载湉的教育格外慎重。她先是将曾与同治一起“微服冶游”的侍讲王庆祺革职,永不叙用;又将新皇帝身边的服侍者,全部换成“老成质朴”的中老年人,理由是青年人“年少轻佻”会带坏皇帝;同时还整顿了太监系统,将一大批服侍过同治的太监或发往黑龙江为奴,或送去宫外铡草。对帝师的选择与学业监管,更是严之又严[7]。这当中唯一未改的,便是慈禧自己的“虎妈”本色。
所以,对载湉及其身边人等更加严厉的管控,并没有能够让光绪对慈禧产生真正的母子之情,反而在他们之间,造就了一道无法逾越的感情裂缝。在情感与心理上,载湉毕生都无法真正地信任慈禧。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便是1887年奕譞(光绪生父)病重时,光绪曾怀疑慈禧有意操纵医疗要害死奕譞。据翁同龢日记1887年12月29日记载,皇帝曾问他:“徐某方有效,而因用鹿茸冲酒,不令诊脉矣,此何也?”[8]——醇王府延请的医生徐某诊治之后,醇亲王的病情大有转机,为何宫中却传旨不许徐某继续给醇亲王诊治?皇帝的怀疑让翁同龢无论怎么回应都不合适,所以只好“未对”,不做任何回应。
其实,慈禧当时并无谋害醇亲王的心思。醇亲王也曾委托翁同龢,要他好好开导皇帝,说徐某的药方其实并不见效,要皇帝“勿惦记,好读书”[9];翁同龢则赞叹醇亲王这些话“实有深心”[9],是在竭力弥合光绪和慈禧之间的感情。
在同一个“虎妈”的教育下,光绪皇帝与与同治皇帝的最大不同,是他受到的管控更严,拥有的自由度更小。所以,他无法获得任何出宫“微行”的机会。但这并不代表光绪不会反抗。1889年,19岁的光绪皇帝大婚——清朝皇帝一般多在14-16岁间成婚,光绪之所以拖到这么晚成婚,是因为大婚意味着皇帝彻底成年,意味着必须启动亲政。有了同治皇帝亲政后便迅速沦于放纵的教训在前,慈禧遂不愿让光绪过早成婚。
“虎妈”的良苦用心,在光绪皇帝那里,却转化成了积怨。于是,就有了下面这一幕:婚后第四天,1889年3月5日,光绪便借口有病,说自己“早间吐水头晕”,喝了药后必须避风,将原定在太和殿宴请“国丈”和整个皇后家族,以及在京满汉大员的筵宴礼给撤销了,结果引起外间许多议论[10]。两天后,3月7日,他又在下旨分送宴桌给在京王公大臣时,“未提后父后族”[11]。
光绪的大婚,包括他的结婚对象,是由慈禧一手操办的。如此刻意冷落皇后家族,醉翁之意不在酒,显然是在发泄对慈禧太后的不满。翁同龢觉察到了这些行为背后的深意,遂将之载入了日记。

♦ 光绪皇帝,引自故宫博物院网站
总体而言,戊戌年之前,光绪与慈禧,大致处于一种“不亲密、缺信任的母子关系”之中。戊戌年后,这种原本就很脆弱的母子关系急骤恶化,终于变成了政敌关系。
这一点,由慈禧筹划另立新君一事,便能看出。她先是以光绪的名义下诏求医,营造出一种皇帝病重的假象。然后又封溥儁为“大阿哥”,试图推动“己亥立储”,继而以溥儁取代光绪。不过,她废黜光绪的计划,遭遇了朝廷内外重臣的集体抵制。地方督抚中,刘坤一、李鸿章、张之洞等,均明确表态反对废黜光绪。李鸿章甚至通过慈禧宠臣荣禄警告道:
慈禧没能在戊戌政变后成功废黜光绪,主要是“为重臣疆吏所阻”[13],得不到这些地方督抚们的支持。

到了1900年,“己亥立储”问题又与“义和团事件”纠缠在了一起。洋人对光绪的友好立场开始让慈禧感到不安,决策信息多来自亲信耳旁风而非专业智囊团队的慈禧,相信了一封假照会[14]。假照会的内容之一“列强勒令太后归政”,给了慈禧巨大刺激,使她做出了暴走式决策,最终落得一个京城被攻陷,自己挟皇帝仓皇西逃的结局。
1900年11月,为求重回紫禁城且不被列强追究,慈禧终于彻底打消了废黜光绪的念头。她颁下懿旨,拿掉了溥儁“大阿哥”的名号。但光绪皇帝被软禁的傀儡命运,却未得到任何改变。故宫有许多慈禧的照片存世,却偏偏没有一张光绪皇帝的照片留存,便是这种被软禁的傀儡命运的一个具象写照[15]。
庚子年后,朝臣疆吏们觐见慈禧与光绪,最常见的记载便是慈禧各种指示而“皇上默无一语”[16]。徐珂《清稗类钞》中记载的一段逸史,也颇有助于管窥光绪皇帝的真实处境:
大意是:戊戌年慈禧重启训政后,二人并坐接见朝臣疆吏,光绪的常规表现是默无一语。即便慈禧戳他让他说话,也只说个一两句就作罢。再后来被软禁到瀛台,那地方三面环水。隆冬时节,皇帝与小宦官踏冰而出,被守卫阻止。于是太后命人凿冰破湖。皇帝读《三国演义》,读了几行字,便把书扔了,长叹说自己连汉献帝都不如。
假如慈禧不是一位“虎妈”,假如她在养育和教导后嗣的时候多一些温情,不那般极力追求控制和鞭策,同治皇帝和光绪皇帝的命运大概会很不一样。尤其是她与光绪皇帝之间,如果能够建立起真正的情感纽带,母子关系也许就不致于那么紧张,晚清历史的走向,也会有另一番不同的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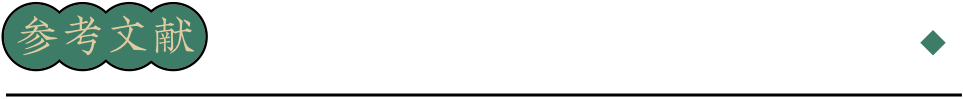
[17]徐珂:《清稗类钞》。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3页。
====================================================================
没人知道《西游记》的作者是谁 | 短史记
问:缪可馨在作文里把《西游记》的作者写成了罗贯中。希望说一说《西游记》的作者问题。
“《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这是每个中国人在他的初高中阶段,必须掌握的一种“文化常识”。遗憾的是,这个常识并没有坚实的史料依据作为支撑。
百回本神魔小说《西游记》,成书于明朝中后期。今天可知的百回足本最早刊本,是明代万历二十年由“金陵世德堂”刊印。上面的署名是“华阳洞天主人校”,开篇有陈元之的序,里面说:
也就是说,在这个刻本之前,神魔小说《西游记》已经有刻本了(但没有流传至今),世德堂的刻本,就是依据旧刻本而来。陈元之读过旧刻本上的序言,里面没有写作者姓甚名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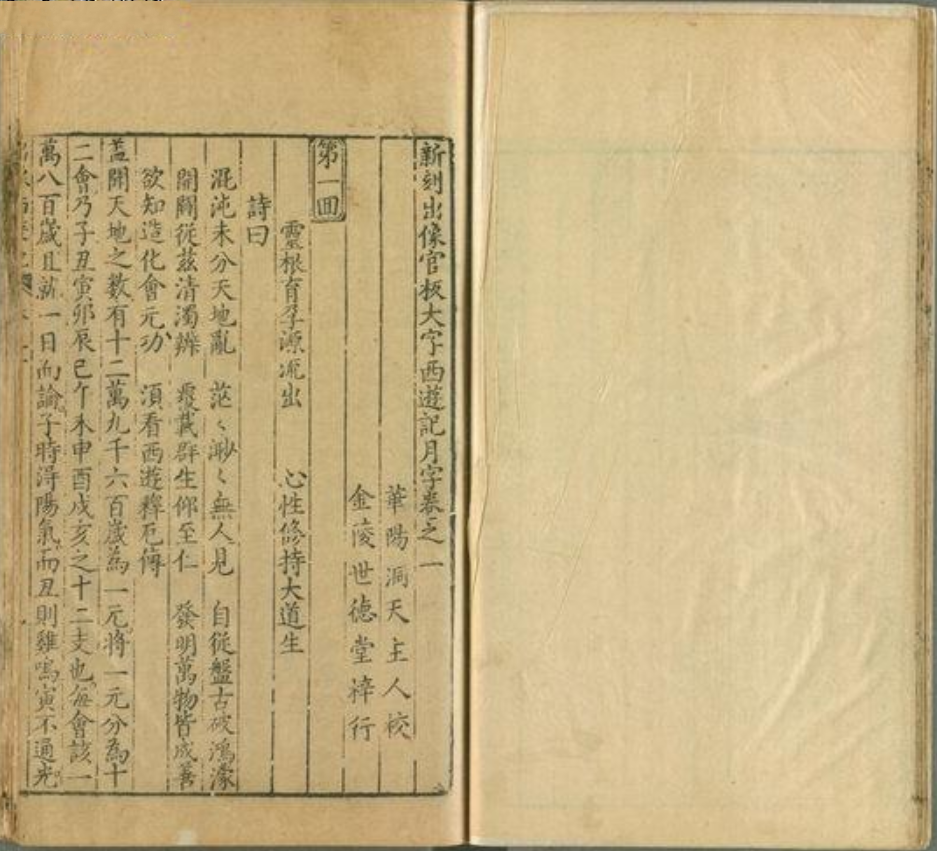
图:世德堂刻本《西游记》
其他传世的明本,还有署名为“朱鼎臣编辑”者。到了清代,则有人依据《长春真人西游记》,想当然地将神魔小说《西游记》的作者认定为元代道士丘处机——这种想当然,无法解释书中的“锦衣卫”“司礼监”这些名词的由来,除非丘处机可以坐时光机从自己生活的元代,穿越到未来的明代。
《西游记》被署名为“吴承恩著”,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才发生的事情。
最早考证认为百回本《西游记》整理者为吴承恩的人,是鲁迅和胡适。他们的主要依据,是天启版《淮安府志.艺文志》。该书“淮贤文目”中写有这样一句话:
鲁迅、胡适还找到了一些其他的“旁证”,如清人吴玉搢的《山阳志遗》、阮葵生的《茶余客话》。但是,这些“旁证”说吴承恩写了《西游记》,其依据也是《淮安府志》。比如吴玉搢说:
也就是说,这些“旁证”不过是在重复《淮安府志》中是说法,无法构成独立的史料来源。《淮安府志》说吴承恩写了《西游记》,只是一条孤证。
对于这条孤证,俞平伯在1933年曾提出过质疑:
俞平伯如此说,是因为历史上有许多叫做《西游记》的著作:

图:淮安吴承恩故居
另一位学者沈伯俊也认为,仅凭《淮安府志》里的“西游记”三个字,就认定吴承恩是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作者,是一种“想当然”的思路:
有些学界中人反击称,质疑者需要拿出确切的证据来证明《淮贤文目》中记载的吴承恩《西游记》不是神魔小说。沈伯俊认为,这种反击“是把本应由自己证明的问题推给了别人,恰恰是倒因为果,颠倒了考证的逻辑”。
在沈伯俊看来,吴承恩《西游记》不是长篇神魔小说的可能性非常大。理由如下:
另一位学者章培恒,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也于上世纪80年代撰文指出,在清初黄虞稷所著《千顷堂书目》的史部“舆地类”中,“吴承恩《西游记》”,是与“唐鹤征《南游记》三卷”、“沈明臣《四明山游籍》一卷”,并列在一起的。黄虞稷父子是清代江南屈指可数的大藏书家,其千顷堂藏书达八万余卷,依据这些藏书编纂的《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收录了明代人所写的著述一万二千余种。《千顷堂书目》将吴承恩的《西游记》收在“舆地类”,可知据黄虞稷所见(或所考据),它应该是一篇文人游记——有学者认为,吴承恩的《西游记》,所记内容乃是他晚年西行,前往湖北蕲州荆王府担任“纪善”(王府里的教师)职务时的所见所闻。这也与“天启旧志”将吴承恩的著作定性为“杂记”颇为吻合。
在方言问题上,章培恒的意见与沈伯俊相同,认为神魔小说《西游记》中出现的方言,大部分属于吴语,而非淮安方言。以方言佐证《西游记》作者是淮安人吴承恩,是难以成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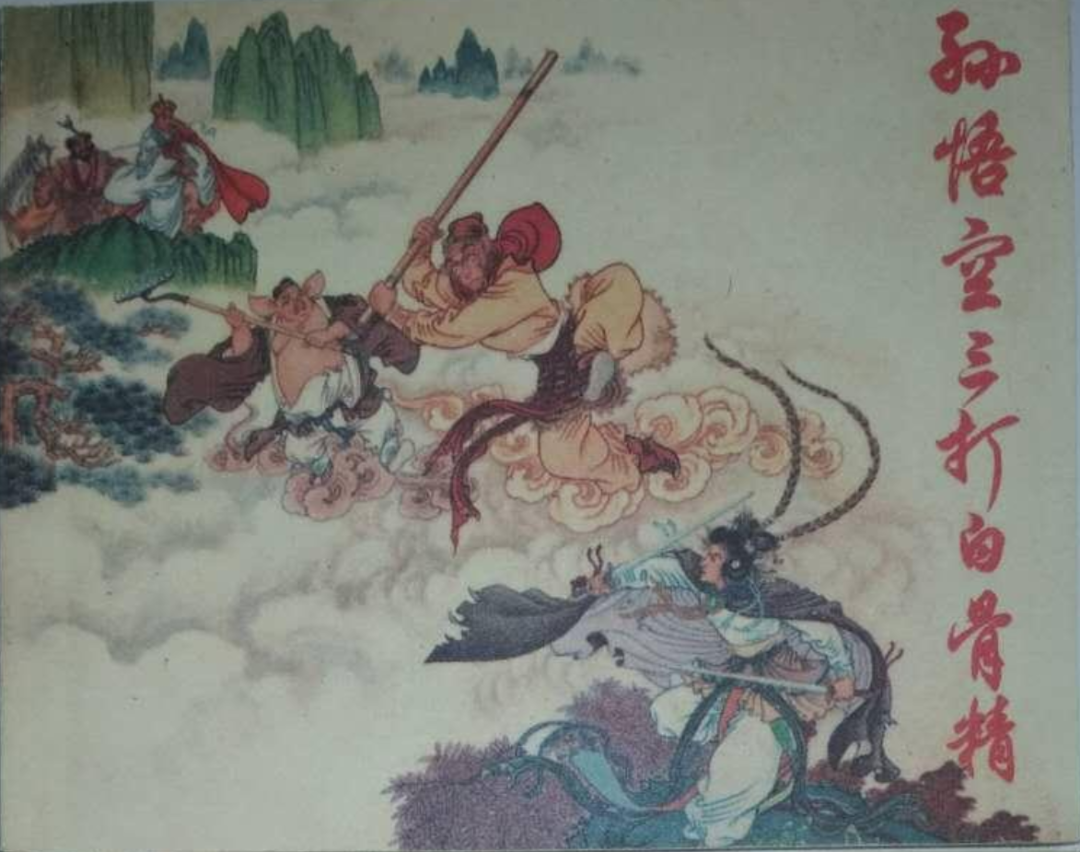
图:连环画《孙悟空三大白骨精》封面
此外,日本学者小川环树、太田辰夫,英国学者杜德桥(Glen Dudbridge),美国学者余国藩(Anthony C. Yu)等,均对“神魔小说《西游记》作者为吴承恩”之说表示怀疑。
中华书局版《西游记》的校注者李天飞,对于封面上“(明)吴承恩著”的说法,也持保留立场。他曾对记者说,
简言之,因史料有限,目前没人知道神魔小说《西游记》的作者是谁。
参考资料
①章培恒:《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
②苏兴:《也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
③单颖文:《<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文汇报》2017年7月21日。
④沈伯俊,《「西游记」作者补论》,《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