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差别
当一群高收入者决定不花钱:住公司、吃剩菜,前所未有的快乐
过去一年催生了很多新词汇:
内卷,996,尾款人,鸡娃......
为了摆脱这种焦虑的循环,

他们有的不消费,吃剩菜,住公司,
甚至毕业后压根不去上班。
有的离开都市到三亚后海村,
白天出海找浪、晒太阳、玩躲避球,
晚上听音乐、喝酒、蹦迪。
有的小夫妻,放弃几千万的公司股票,
改造房车,从此过上四海为家的生活。

假期最后一天,
我们精选了过去一年报道过的3种新生活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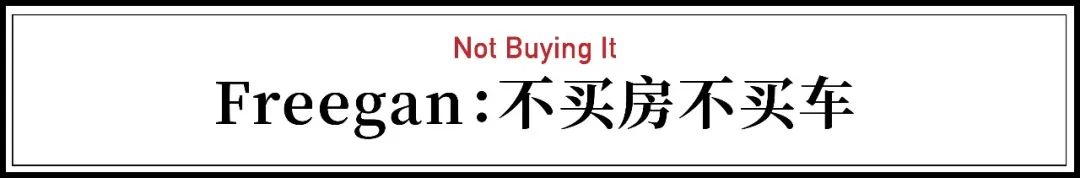

与这些年纪轻轻的负债一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群Freegan,意为“不消费主义者”,住公司,吃剩菜,翻垃圾箱,不购物,凭借社会生产的剩余物满足吃穿住行基本需求。有的甚至不上班,将积蓄赠予他人,拒绝被纳入现代货币体系。



因为支出极少,对钱的敏感度也逐渐降低,某天去查银行卡时,丁红猛然发现自己居然存下了很多钱。她热爱旅行,以极低的费用横穿美国、徒步珠峰大本营、逛遍东南亚、考到潜水证书……
35岁那年,她决定用手上的钱去新西兰学习动画,一年学费8万块,果断出手。她的第一部独立动画作品《疯狂的司机》,拿到了维塔工作室的杰出动画奖,之后留在了当地工作。


在新西兰做Freegan的好处是,这里有着数量庞大的野生食材。丁红学会了在森林里辨识数十种蘑菇,掌握潮汐的规律下海摸海鲜。吃不完的牛肝菌、海虹、巴掌大的鲍鱼、鲜嫩的海带、野韭菜、水芹菜……
为了避免成为一个“因乱吃而被毒死的吃货”,开始翻找各种英文动植物学术材料,她笑谈自己一个学渣因此掌握了大量高级英文单词。抛弃消费欲望后,她更深度地参与这个世界。

杨宗翰毕业于台湾成功大学环境工程专业,按家人原本的计划,他该朝向年薪百万的工程师迈进。然而如今30岁的他,没上过一天班。

被空屋占领的屠宰场名叫Klaonica
屠宰场位于市中心,废弃20多年,2年前被一群人进行了“空屋占领”。没电,没自来水,也没暖气,零下20度的深冬天气里,他们烧木柴取暖,回收蜡烛用于夜晚照明,收集雪化成水,生火做饭……
每到晚上九、十点钟,这群人会架着手推车上街,沿街问面包店和披萨店有无剩下要丢掉或者过期的食物。令杨宗翰大为震惊的是,这个在全欧经济排名垫底的国家,浪费程度超出想象。单单某一家面包品牌的总工厂,每天要被扔掉的面包多达一吨重!

杨宗翰的Freegan生活为他带来形形色色的朋友,以及不错的收入。他的讲座邀约不断,从中收取一些费用后,因为花得极少,每年至少能存下30万台币,比一些城市白领的积蓄还要多。
他本可以挣得更多,但也仅此为止了,杨宗翰表示要减少讲座的数量,他不想挣那么多钱,想安心当个悠哉的树懒。
不过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近距离地照顾家人。几年前他的父亲被确诊阿尔兹海默症,并出现暴力倾向,母亲也病倒了,他很自然地分担起照顾的责任。父母头一次发现,原来儿子不用上班就能养活自己,还是一件蛮不错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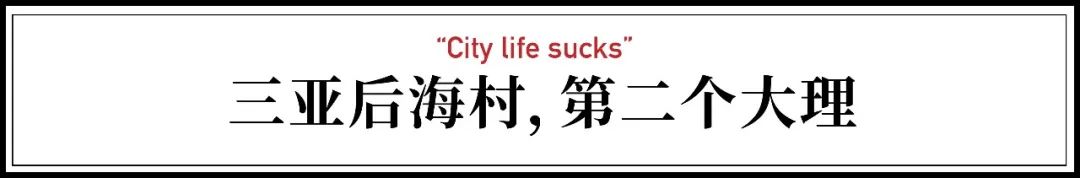


脏辫女孩大星

宝妈CC、手作人代代和数字游民Josh成为了后海村的新村民,他们在这里拥有了新的社交圈并探索出了别样的生活节奏。
CC是儿女双全、大宝8岁的宝妈。她师范大学毕业后就结婚生子,在长沙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美容院,时间自由,一有空就全国各地跑、做义工,尝试新鲜事物。



CC在后海村的日常

手作人代代

代代去过上海的club,觉得人们都端着,坐下来一块聊天,聊的都是我们家有几套房子、要不你带我做点事,而在后海村,大家对城市那一套没兴趣,“你要是说我今天冲到一道浪,太牛逼了,还有兴趣听听。”

数字游民Josh
Josh是一名程序员,公司总部在瑞典,允许线上办公。来后海村之前他先去深圳待了一个半月。



荷包蛋和哈里,是一对80后情侣,2017年开始,已经在房车上生活了3年多。两人都在风口上的互联网公司工作,自嘲“产品狗和设计丝”,加班严重,日常是“给自己打鸡血,和隔壁部门撕逼,以及等公司上市”。于是一有周末就拼命逃离,开车去城郊野外溜达,远离工作和客户,住两天再回来。


房车改造前

房车改造后



荷包蛋在老挝游泳


如今他们通过帮人改造房车获得一定的收入,却又给他们自由游荡的生活带来了限制。未来的路怎么走,他们还在探索之中。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不愿意回到城市里朝九晚五地上班了。
死亡拆船工

工人们花了好几天时间切割“利昂娜一世”号的甲板,这时一大截船体突然断落,碎钢片纷纷向经营者们飞去。这艘货轮是在克罗地亚的斯普利特建造,在海上航行了30年,大约是轮船的平均寿命。
坐标孟加拉湾,
孟加拉国第二大城市吉大港,
80余个拆船厂矗立海边,
横跨13公里海岸,
世界上最大的轮船在孟加拉国的海滩上解体,
而拆解巨轮的繁重工作由拆船工徒手完成。
这是苦难而豁命的工作,
每天却只能得到不足1美元的薪水。

几年前,一场爆炸致使多名工人丧生,
此地由旅游景点转变为对外禁地,
高网林立,戒备森严,
但巨大船体掉落的轰鸣声显示,
拆船厂仍在正常工作。

退潮时,拆船工们将一根5000公斤重的线缆拖到一条搁浅的船上,以便在拆船时用作运输绞索。
世界上大多数的轮船拆卸都是在南亚各国进行,因为劳动力价格低廉,且监管松弛。在防护条件极低的情况下,孟加拉拆船工们切割巨大的船体,与有毒物质近距离接触,工人身上遍布伤疤,常见童工与年轻的寡妇,当地几个家族控制这个暴利的行业。孟加拉国拆船厂,绝望的男人们从事着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之一。
摄影:PETER GWIN
撰文:MIKE HETTWER

有些船仍然完整,看起来是刚来到这里。其他船则被肢解得只剩一副骨架,钢铁表皮被揭下,露出里面巨穴般黑洞洞的空间。
远洋航船按理是不应当拆卸的。
发达国家报废轮船的过程,
受到严格监督且代价高昂。
而南亚则不然,
贫民区的工人工作极其艰苦,
拆船厂是获取巨额利润的捷径。

远洋航船的设计可以抵御世界上最凶险的自然环境中的极端破坏力,而且通常是用有毒材料建造,比如石棉和铅。
在孟加拉国,
500万美元的投入,
三到四个月的期限,
就能收回大约100万的回报。
相比而言,
巴基斯坦的利润不足20万。
孟加拉国拆船协会前主席说
利润率受钢材价格等多种因素影响。

工人们顾不上罹患肺癌的风险,把可能含有石棉的管道接头垫圈点燃,以驱散夜晚的寒气。
但无论如何,
一艘轮船超过90%的部分,
都能用来拆解回收进而获利。

搬运工们整日在泥浆里滚打,泥浆被船上冲下来的重金属和有毒涂料所污染。
拆船商从专门经手报废船舶的国际中间人那里购得轮船,然后雇用一名专门从事大船搁浅的船长把船开到拆船场地,也就是几乎不足百米宽的一条狭窄海滩,拆解作业开始了。

轮船嵌入泥地后,里面的液体马上被抽出,包括残余的柴油、机油和消防药剂,然后转卖出去。

之后拆除机械和配件,所有物品都被拆卸出售给废料回收商——从巨大的引擎、电池、发电机、几千米长的铜线,到船员床铺、舷窗、救生艇以及驾驶台上的电子仪表。

手持焊炬的切割工在助手的协助下,先拆除船内设施,然后有条不紊地切割层层甲板。拆卸过程持续三到六个月,取决于船的大小。

轮船被拆成一个钢铁躯壳之后,一群群来自孟加拉国各贫困地区的工人用焊炬把船骸切割成块,这些钢板被装载机运离海滩,然后制成钢筋用在建筑中。

船被拆成一块块钢板,每块钢板重量达500公斤甚至更多。运用蛮力和简易滚轴,一群群搬运工把钢板运到卡车上,卡车再把它们运到轧钢厂,制成钢筋用于建筑。
“如果你不去考虑
渗入土地的有害物质,
也没有听到寡妇们的哭声,
这听起来就像笔好生意。”
非政府组织拆船平台的活跃分子
Muhammed Ali Shahin说。
Shahin不是要求停止拆船创造,
而是改善工人们的生存处境。

当地年轻的寡妇,她们的丈夫有的是被掉落钢铁碎片压死,有的被困在船里窒息而死。
在院子周围的棚户区里,
住着沙欣最关心的数十名工人。
许多人身上带有深深的锯齿状伤疤,
有的人缺了手指,
还有几个人单眼失明。

有个人把工人们身上的伤疤称作“吉大港纹身”。
其中一个家庭有四兄弟。
40岁的Mahabub年纪最大,他做过两个星期切割工的帮工,亲眼目睹一个男人的火把不小心点燃了一小块船舱的汽油,被活活烧死。这件事发生后他就辞职了,因为害怕老板不放他走,连工资都没敢要。

老板们会威胁这里的工人,
让他们对发生的事故装聋作哑。

Mahabub指给我们看老二Jahangir的一张照片。他们的父亲死后,15岁的Jahangir就去做了切割工,Jahangir和工人们对一块巨大的船体进行切割,连续三天都没断裂。暴风雨骤至,他们在下面搭了棚子,不料船体猝然垮塌,他在2008年的这场事故中受伤去世。

喜马拉雅山脚下丘陵地带的杜诺特村中,大约三百人参加了拉纳·巴布的葬礼。22岁的拉纳·巴布是个拆船工,死于焊炬点燃瓦斯引发的爆炸。

“他还是个孩子,”一名哀悼者说道,“为什么这种事件一直在发生?”
老三Alamgir,22岁,他曾经摔进一个27米深的大洞里,所幸洞里渗入了足量的水,工友冒着生命危险把他救了上来。第二天Alamgir就辞职了,现在在做为经理们端茶倒水的工作。

最小的弟弟Amir只有18岁,是切割工的助手,身材瘦小,皮肤上还没有疤痕,笑起来很腼腆。被问到是否对他的兄弟们的经历感到害怕时,他有些不知该说什么,局促地回答:“害怕。”

这些拆船工说自己已满14岁,也就是能够在拆船厂工作的最低合法年龄。经营者喜欢年纪小的工人,因为他们价格低廉,又不清楚工作的风险,而且他们小小的身体可以钻进轮船最狭窄的角落。
雷鸣般的响声震动铁皮屋顶,
但非孟加拉国著名的暴雨将袭,
外面还是大太阳。
男孩说:“是大块船体掉落的声音,
我们每天都能听见这种声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