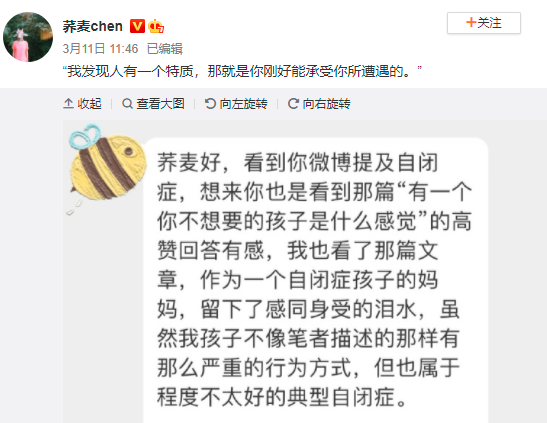去年春天,因为一条讨论婚姻的微博,作家荞麦收到了一位陌生网友的私信。这封像日本短篇小说一样的信,描述了一段「非典型」婚姻生活——一位女性,在婚姻里没那么投入,有一天发现丈夫出轨,她抓住机会果断离婚。被背叛后,她没想着变美或者变强大,还是像原来那样生活,只是快乐了一些。
这是一种很少被谈及、但确实存在的婚姻状态,荞麦决定把这封信公开。这之后,越来越多的人给她写私信,话题从婚姻开始,慢慢延展。这一年,荞麦一共发表了数百封网友来信。
在如今的中文互联网上,你很难找到这么丰富、细腻且集中的个人书写。投稿人中,很多都是年轻女性,她们谈论自己的爱情、亲密关系、工作和原生家庭、女性友谊,以及余下的全部生活。
一些来信会描述当事人两难的处境:当你遇到合拍的男孩子,但他却有一对没有边界感的父母;当一个女性婚后开始想独立,要离家工作,这是否意味着自私和伤害他人;追求自由的小城女孩,和传统的小城男孩,是否还能继续爱情。这是女性觉醒与父权传统之间,每天都在发生的故事。
这些私信也给荞麦的生活造成巨变。原来,她是一个追求文艺生活的作家,写的是一些轻盈的故事,与现实刻意保持距离。她也一直在较为顺利的性别环境里长大,在性别相对平等的行业里工作,晚婚晚育,丈夫承担了许多育儿的工作,是一位不那么典型的妻子和母亲。
但在这一年,她每天做着一些具体的工作:阅读私信、筛选、分类、打码,同时主持评论。在海量的来信中,她逐渐理解了那些在性别夹缝中挣扎的人,理解了「普通人」和「不那么先进」的人的生活,并真正地成为了一位女性主义者。这也影响了她的创作和看待世界的视角。在原来,她可能好奇的是:为什么不能每个女性都尽量成为一个先进女性?但现在她更想问:为什么这个社会,不能让不先进的女性也能好好生活下去?
以下是荞麦的讲述——
我刚刚重新翻了翻我的微博,想找到我发的第一封信。很奇怪,竟然是2020年4月发的,原来这么晚。我一直以为那应该是2019年的事情。
当时,我在微博讨论一个话题,就是女性在婚姻里,可能并不都是祈求者的角色。人们总是认为,在婚姻中,女性特别想要丈夫的专一和爱,好像这就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很多女性结婚之后,也没有那么在乎这件事,不会整天谈论老公、小孩和家庭。当时也有人出来反驳我,但就在那时候,我收到了这封私信,我可以读给你听。
我的婚姻不能说有什么不好,至少如果明确地让我抱怨,我其实也说不出一二三,但是就是长期有一种被催促着、被勉强着的感觉,一个妻子应该这样做吧,那就做吧,但内心是有点不情愿的。这种心态可以说是我婚姻的底色了。
后来发现老公出轨了,真的有一种松了口气的感觉。伤心当然是有,毕竟是在一起十多年的伴侣,但是更多的是一种「你要抓住这个机会,这可是一个名正言顺的离婚理由,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的心态,于是就离婚了。
一个女人被出轨之后,路人总是有戏剧化的期待。觉得她要变得更漂亮、更成功,找到更好的男人。但是其实我都没有,我还是老样子,如果说状态更好了,也是因为离婚之后心情好了很多,就像你说的,这件事跟性别无关,就是有的人不适合婚姻吧。
我当时看完就觉得,这封信写得很好。首先这个人应该受过不错的教育,是一位知识女性,她能够认识到婚姻中的一些问题,包括她是被催促着做一个妻子,被妻子这个身份限制着。而且丈夫出轨之后,她也没有想变得更强大,没有想扳回一城。她不是那种传统叙事中的妻子。于是我就把这封信发出来了。它也奠定了我整个私信的基础。
发出来之后,又收到了很多类似的信,写的都是非典型的婚姻状态。这批信其实是在反对大家对婚姻的刻板印象,所以我就给这些来信打了一个标签,叫#非典型来信#。
早期那些私信,尺度比现在大很多。投稿人基本都是结了婚的女性,讨论的也都是一些在世俗和道德上不太能公开谈论的东西,比如出轨。她们的处境可能和很多原因都有关系,比如婚姻的不如意,但是因为孩子或者什么别的原因,家庭又无法拆开,但还是想在夹缝里获得一点点喘息的空间,还是希望有哪怕来自陌生人的一点点理解。
再到后来,关于婚姻的各个方面都谈过了,我自己也觉得有点疲惫了,就开始开启一些新的话题。现在我每天大概要收到一百多封私信,一般会在中午或者晚上集中处理一两个小时。中午我会发一封,晚上有时候会再发一封。
这一年谈过职场、原生家庭,还谈过好几次关于性骚扰、幼年性侵和家暴相关的话题。以前我对社会热点的反应是输出观点,但现在基本就是会拿一个私信出来,大家一起来讲自己的经历,然后一起讨论。
也是因为收了这么多私信,最近这段时间,其实我就不断在想:爱情,到底是什么?
这一年,我经常收到这样的私信:一个女孩子想要离开现在的男友,但她害怕再也没有人爱自己,或者没有人像他这样爱自己、和自己契合、对自己这么好。
被爱,对女孩来说好像特别重要,但这到底是女性的真实情感需求,还是被建构出来的?这种一旦失去就可能再也遇不到的紧迫感,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怀疑过「爱情」这个词,但现在我会从各个角度怀疑它。
像我之前提到的一个例子,有个女孩被熟人诱奸了,却跟对方谈起了恋爱,后来她发现自己还是第三者的身份。我跟她说让她离开,但她还是一次次回到那个男人身边,哪怕一次次被冷酷地对待。她一定是特别特别缺爱的女孩子,哪怕在那样一个男人身上,她都想证明和索求一点点爱的迹象。
还有一个观察是,女孩子们的心态,会明显分为两个阶段。19岁到23岁,是大学时期。以及23岁到30岁,大学毕业工作后进入真正的亲密关系。女孩子们处在完全不一样的情感状态。
还在上学的女孩子,有的攻击性特别强,她们已经接受了女性主义的教育,但因为缺乏实际生活经验,看问题简单得不得了。一旦有一个女生发私信,没完没了倾诉,说自己被家暴,或者被出轨,在糟糕的关系里走不掉,评论者只会骂她:「为什么不离开?」有的女孩的想象轻松到,就是说——谁要是敢哪怕只是推了我一下,我立刻就拎起行李离开他。她可能还没有建立那种特别深入的亲密关系,觉得这很简单,其实这是非常难的。
还有一种典型的想法就是,不婚不育保平安,我要搞钱搞事业。她们经常评论说:「姐妹,走出来啊,搞钱最快乐,搞事业最重要。」这些言论刚出现的时候,我不会干预。但后面这种声音特别多了,我也不得不站出来告诉她们:不是的,这不是一个万能答案。钱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更何况你挣不到那么多钱。你为什么会觉得自己能挣到能解决所有问题的钱呢?等你马上毕业找工作,可能就会被社会鞭打。而且不婚不育不是答案,甚至是种特权。很多年轻女孩子说,说这有什么特权,为什么就那么难?她自己还没有进入那种关系里面,根本意识不到那有多难做到。
但是我也是因为收私信才发现,现在很多人结婚是很早的。以前我们大学都不太允许谈恋爱,但现在在大学,很多人已经在考虑结婚了。很多跟我咨询结婚烦恼的,都是年纪很小的小女孩。
包括彩礼,它早就在我的生活里消失了,我周围的同龄人里几乎没有听说过要彩礼的。当这个词被频繁提及的时候,我也以为是一种遥远的、落后的东西。但现在收到很多信,受过教育的年轻女孩子对此理直气壮。不管理由多充分,我真的从里面感觉到了一种婚恋的后退,我们80后体会的那种两个人作为独立的人结婚的状态,已经不存在了。
这一代年轻女孩,按道理其实是在更优越的家庭里长大的,但是家长对你的期待还是有个人爱你,对你负责,照顾你,他们愿意为此付出经济上的代价。他们可能有钱,但不一定愿意给女儿,可能宁愿补贴一个男孩,让他来照顾她。至于这个照顾是什么照顾,他们也没想好。比如说有人保护她,但真的能保护她吗?这个世界对女性来说那么不公平,又那么危险。你觉得女孩子需要男性的保护,但有时候身边的男性也很危险,这是一些非常复杂的状况。
所以「爱」这个词,里面有大量大量的问题,包括从小的教育和灌输,把爱作为女性一个非常大的标准诉求。我们说男性的时候,就说女人如衣服。但对女孩来说,好像如果不被爱,那你这个人就太失败了。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对爱情这个词进行重新的理解和认识,可能世界会更不一样。
作为一个树洞,到底要不要管理自己的评论区,我是有过纠结的。
之前我特别羡慕燕公子(注:一位微博博主),她好像从来不管自己的评论区,别人骂她,或者说一些不怎么好听的话,她也不在乎。我一度想模仿她,也不要管评论区,别人想说什么说就是了。
但是后来开始发私信了,我发现不行。因为现在在网上,大家还是习惯于评判别人的生活,甚至是无意识就开始释放恶意,如果不干预评论区,很快就会失控。
我会观察到,评论区有一些很熟悉的ID,他们在一件事上表现得非常理性、冷静、温柔,但可能在另一件事情上,他们也会说出那种伤害别人的、不自觉的、高高在上的话。而且好像只要有机会去评判别人,审视别人的生活,这种审视也能够抵消掉一些自己生活中的挫败感,这很容易变成一种集体反应。有时候我自己也不能幸免有这种心态,所以更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去矫正它。
还有些时候,有些评论,好像是说了一个道理,被赞得很高,但实际上是一种陈词滥调。比如有一条高赞评论说,「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人在面对欲望和诱惑时,会有理智去克制」,很多人都觉得好有道理,特别能说服人。但不是这样的,不是说不需要克制,而是人类的情欲是很复杂的,我就在下面回复了一条说:「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人有更复杂的情感世界。」
我还经常遇到一种情况,就是会有人持续给我发私信,但前后几封信展现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比如有个女孩子之前一直跟我讲工作的事情,后来突然又跟我说,她的小孩是自闭症,那封信写得特别好,在微博被转了上万次。还有人可能前面在讲自己的恋情多么好,过几天突然告诉我,这个恋情其实不是正常的关系。有人前面讲自己生活多么开心自在,后面又写一封很长的信,讲原生家庭的痛苦。还有人写过一封移民的信,说的是一对夫妻齐心协力移民的故事,后来这个人又问我,你要不要听故事的B面,B面就是一个出轨的故事。
这些故事完全可以连接在一起,都是真实的,但又是不同面的故事。有些人是有这个意识的,知道自己的生活有水上和水下两个部分,但有的人其实没有这个意识。而且有人可能此刻幸福,但过段时间不幸福。有人在这方面幸福,在另一方面不幸福。他们的信就像他们生活中的一段段足迹,有时候他们可能都忘记了上一封信给我写了什么,前后对照,是非常荒谬的,我常常被这种生活的多面震惊,这使我感觉到人、生活和关系都真的太复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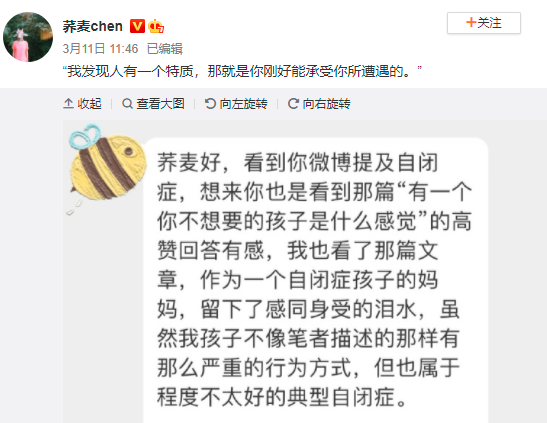
荞麦收到的一封关于自闭症的私信
我自己是在一个较为平等的性别环境下长大的。
我出生在农村,但同龄的一群小伙伴都是男孩,我们从小一起玩,甚至没有在乎过生理上的区分。我也算是聪明,在轮流当领袖的过程中,我也可以当领袖。到了小学初中,我成绩也很好,个性也很像男孩,每天打闹,甚至以自己像男孩而骄傲。而且我的朋友们大多都是独生子女,女孩子们跟男孩一样,都是被寄予厚望的,焕发着风采的,我们都觉得以后自己是要成才的。
大学之后就更是了,跟文艺青年们一起玩,也碰见很多厉害的女性偶像。我们看《欲望都市》,一开头都是对各种类型男人的评价,这个男的不行,那个男的幼稚。我们完全在这种氛围里面,忽略了结构的不平等,而以为自己是万能的。甚至哪怕有天被伤害了,还觉得自己非常强大,可以化解,很多东西是可以去战胜的。
甚至是,当某个知识女性过于情感化,受伤了,也会觉得是她的问题:「你怎么这么脆弱?你为什么不看看身边这些聪明的、强悍的女人?」这种对弱者的轻视,其实是在不知不觉中养成的。一直生活在一种较为优秀的女性集体里面,没有看到特别苦难的一面,才会产生那种幻觉。
我的恋情也是这个样子。我没有喜欢过任何传统意义上的成功男性,我喜欢在这个社会里不属于主流成功人群的男孩子,一直都是这样。那种主流男性,他们一坐下来就要教训你,你也不想听他们教训,很可能就吵起来,怎么可能产生情感。原来有时候我甚至会想说,有些人会受到压迫,不就是因为慕强吗?所以在早期,我其实是有一种旁观者心态,有优越感,没有办法共情到一些人的痛苦。
其实就是到开始收私信之后,我看到那些非常具体的人,被父权控制,被夫权控制,被家庭、父母控制,在社会上也被整个社会体制控制,在缝隙中苦苦挣扎的时候,我才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幸运,然后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女性主义者。
这中间也有认识的变化。在最开始,我对女性离开、寻找自我、搞事业、搞钱等等说法特别鼓励,对传统叙事下的女性是没有耐心的。我会怒其不争,觉得你怎么这么落后?你先进一点,不就会摆脱这些落后的痛苦吗?我早期还说过,你如果不去鞭策落在后面的人,怎么鼓励已经走在前面的人?
但是我收了这么多私信,才发现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不先进的女性,你让她完全离开这个传统叙事或者传统生活结构,她真的就幸福吗?你能保证她的幸福吗?有些女性她就是希望建立亲密关系,就是想生两个小孩。追求事业不是唯一的答案。即使是先进的、正确的观念,也是没办法覆盖到每个个体的,是不能指引每个人获得幸福的。
我现在会认为,我们鼓励她们去做一个先进女性,但是也包容她们去做一个不那么先进的女性——因为我们的社会没有那么先进。如果原来我问的是:为什么不能每个女性都尽量成为一个先进女性呢?但我现在想问的应该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不能让不先进的女性也好好生活下去呢?比如公平的婚姻制度、社会抚养制度的支持。
之前我还会在微博里发书或者电影,发一些文艺晦涩的东西,包括对生活的哀叹,现在也发得很少了。一方面是因为新粉丝里,普通人要更多一些,有很多生活上处于困境或痛苦的人,另一方面我觉得有些观点必须要从最直白的地方慢慢开始讲,要用大量的时间来讨论问题。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我自己也被影响了,被社会化的目光改造了。现在看书和电影,没有办法欣赏里面不那么社会的一部分了,没有那么多浪漫情怀了。比如之前看一部电影,那种男性视角下的家庭故事,有些人还能用艺术的眼光看,但我已经看不了了,觉得非常厌烦这种男性叙事,我都不太明白这是好是坏。
在收私信的前半年,我同时在修改我的小说《普通婚姻》,我改了很多,其中是有私信的一些些作用的,它们给我提供了对社会和世界的一些认识。想起以前,我老是被批评写东西无病呻吟、脱离生活、矫情,以前我不服气,我想去你妈的,为什么我一定要写那些。现在我理解了以前别人对我的评价。为什么我认为的正常生活,是他们觉得非常矫情的、理想主义的生活?原来我们生活在不同的语境当中。
以前我的偶像是村上春树,想写他那样的作品,写一些非现实、轻盈的东西,也一直在竭力避免自己的小说里出现社会议题,因为我觉得它不美。但现在当我开始构思下一部小说的时候,我的脑海中已经没有文艺青年了,我打算写一个普通女性。那些私信可能没办法直接用到小说里,但它们给我展示了一种崭新的生活图景。社会议题与文学性,到底怎么处理,可能这真的变成了一个问题。
至于微博私信,我还是会一直更新下去。我还是倾向于展现一些非传统的生活形态,给大家扩大一下想象力。
就像上次有一个女性投稿,说她忽然卖了房子,带着全家去芬兰读书。当时很多人骂,有人说是假的,有人说是移民广告,还有人抱着看笑话的心态。但后续她就是去了呀。她只是读书,也谈不上移民,移民也没那么容易。但我收到信,觉得非常好啊,去试试。可是很多人就觉得好好笑,居然这个年龄跑到那么远的地方,你能得到什么?
我自己是一个80后的乡下小孩儿,小时候都没有自己的房间,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上大学之前,我都是没有吃过肯德基和麦当劳的。直到工作好几年,我才第一次坐飞机。几年前才第一次出国,对很多人来说已经很晚很晚了。但就是我这样一个出身的人,对世界是有认识的,对远方是有想象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造成的,可能跟阅读或时代有关系,我们的时代就是要往外看的。
但我在私信里看到的,那些在网络时代长大、吸收着最丰富资讯,从小就玩手机、买国际品牌、甚至出国留学的小孩,对世界和生活方式没有任何想象力。这让我非常震惊,我以为他们眼里有很大的世界。
我总是说起一对意象——桃花源和旷野。在我们的传统教育里,中国人对人生的想象永远是桃花源,是寻求一个稳定的封闭的地方,安放自己,过着幸福又重复的生活。但西方人对人生的认识是一片旷野,他们从小读冒险小说,人就是要去人生中冒险的。
因此我们现在的小孩,很早很早就想找到一个自己的桃花源。我收到的私信,大部分就是一个意思——他们的桃花源建立不久就破灭了。不管桃花源建立的时候条件多么充分,这个男人也很好,家里也有钱,价值观也非常对,但这样的生活过几年之后,就动荡了,破灭了。
就像我在小说里写的那样,人有没有可能在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就获得一种确切的幸福,从此他们的问题,就是要抵抗这个幸福的乏味,是不是有这样的人生?其实是不可能的,人生是那么漫长,是充满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