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捕手计划(5)
年轻男子捡到一张黄色光盘,三年后因此毙命|群山之罪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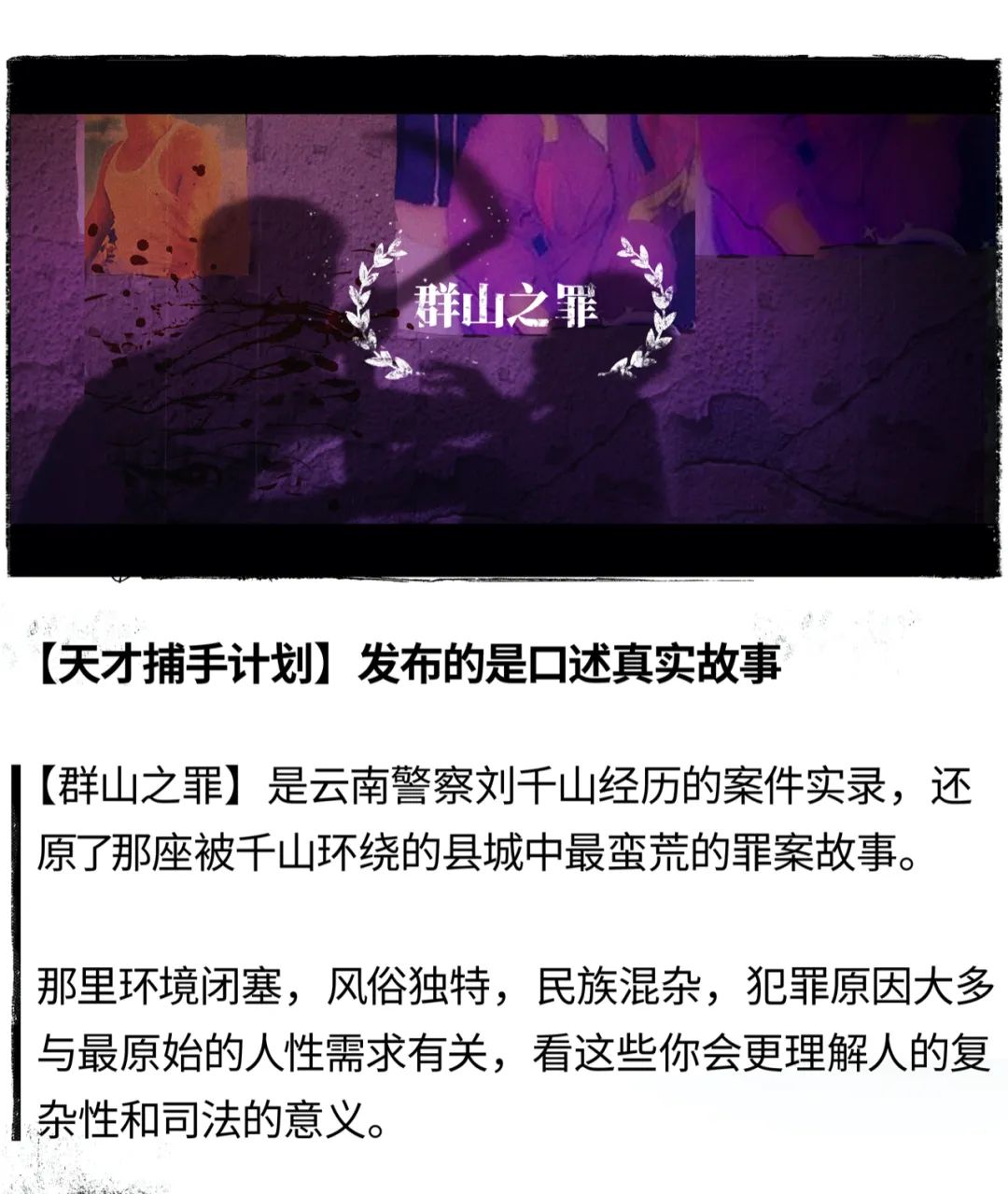
大家好,我是陈拙。
今天讲点刺激的:看黄片、被人发现看黄片。
说它刺激不是因为内容,而是说这种事儿真的很危险。
只要你上网搜搜,就会发现如下新闻:老师偷看黄片,结果忘了电脑连接的是学校主干道上的电子屏;学生偷看黄片,因为教导员闯入心脏病突发;小偷在作案现场看黄片,因为太入迷,被失主直接给逮了。
这些事儿不是最狠的,最狠的是这个新闻:

这一次整出来之后,两个人被拘禁16天,在全国闻名。经过新闻报道,成为著名的”黄碟“事件,工作被开除,还被邻居围观:到底是谁看黄片!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和这对夫妻一样惨。
有个农村老头就爱看黄片,直到有次碟片丢在了路上,恰好被自己的亲侄子捡到了。
当晚,他侄子就拿着碟片,敲响了他的房门。

南方地区常年高温,村里日子平淡,电视里日复一日地放着女特务杀鬼子的桥段。家里能有台电扇吱吱悠悠地转着、吹着、送点凉,就是好消遣。
陶安家的日子确实也是这么过的。
58岁那年,庄稼人陶安的女儿出了嫁,老婆尽职听话,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也能挪着步子,在院子根底下一坐就是一下午。
可他知道,平静的生活之下,一切都不大对劲。
近些年,陶安常感觉到一阵地喉头发紧、嘴唇发干,他知道这是自己的身体在释放一种信号。
借着村里安排他管理抽水房的机会,陶安在狭小的抽水房用几块木板搭了个简易小床,有时他会24小时待在抽水房也不回家。陪着他的还有一台村里淘汰下来的旧电视,和一台影碟机。
这样下来,背阴潮湿的抽水房,就成了陶安完美、私密的避暑胜地。
每次来到抽水房,陶安都会迫不及待地接上影碟机,把碟片推入,碟片里的内容陶安倒背如流,可是每一次看到都还是心跳气喘。
画面里两个男人纠缠在一起的画面就像一剂猛药,专灭他胸口的火,治他心里的病。这是陶安不敢对人言说的秘密。
如果不是自己丢了其中一张碟片,又恰好被自己的侄儿沈天刚捡到的话。

那天下午,陶安刚刚放完碟片,心绪略平静下来。他拉开抽水房的门,却看到沈天刚站在门外。
沈天刚是村里的后生,之前当过兵,退伍后不久,正值壮年。按辈分沈天刚得叫他一声表舅。
四目相对,气氛有点尴尬,陶安讪讪一笑,把怀里的影碟机抱紧了些,搪塞了几句后便扭头就走。
沈天刚看着陶安的背影,也暗自松了一口气。他来这边,是为了玩自己私自改造的射钉枪,怕被陶安注意到。
沈天刚刚要往回走,旁边的草丛里却突然有一道光晃了他的眼。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张光碟跌落在草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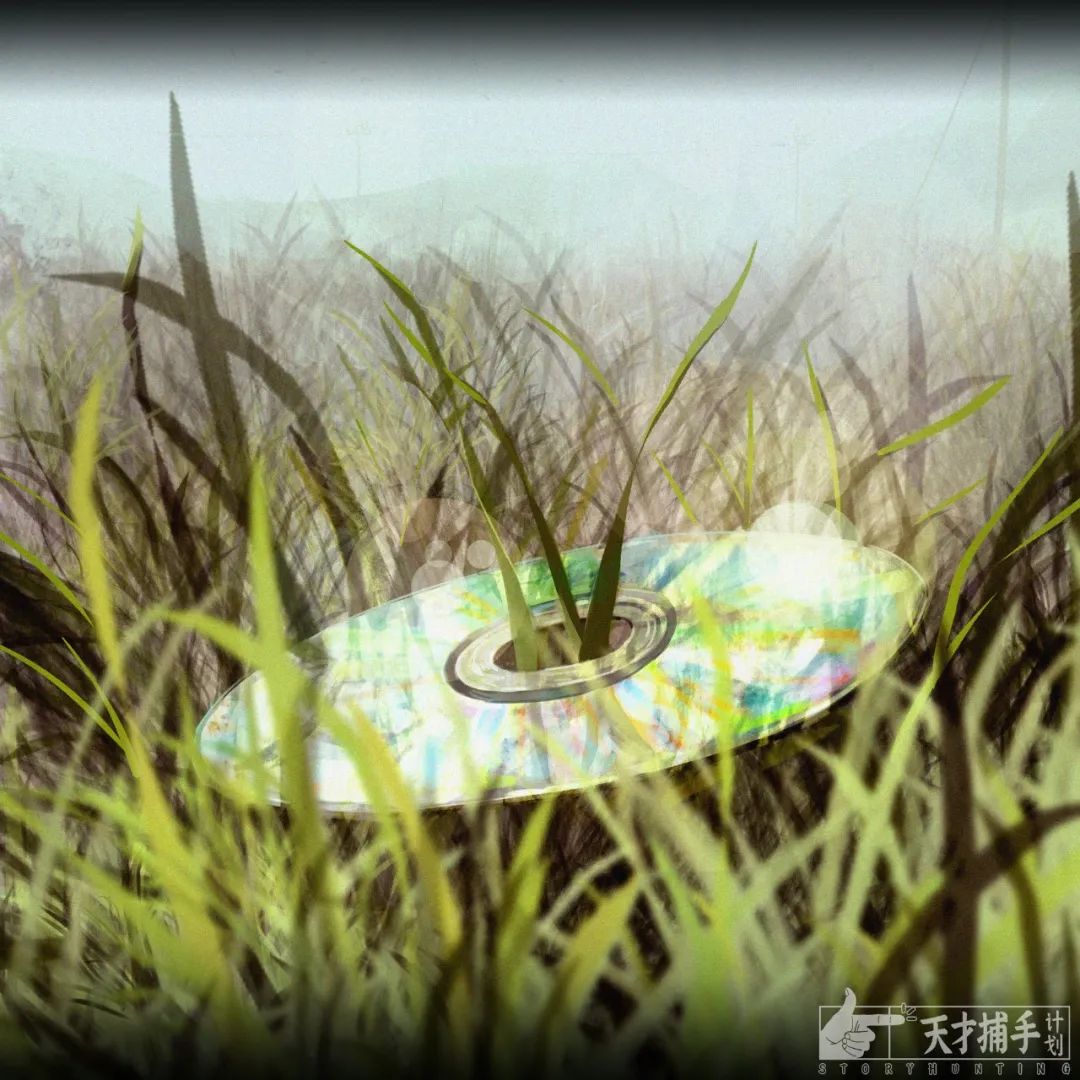
“哦哟,还看点外国片。”想到刚才抱着影碟机急匆匆离去的陶安,沈天刚吹了吹落在上面的灰,把光碟装进口袋。
陶安回到家,进到自己卧室,小心翼翼把影碟机放回置物架上。从兜里掏出碟片时,他心里一惊。碟片少了一张,翻遍全身,依旧不见。
他赶紧沿着回来的路仔细搜索。这会儿村邻基本都在家生火做饭,沿路走来倒是没遇见几个人,但是一路走完,不管路旁沟边、房前屋后,甚至把抽水房也翻了个底掉,都没有看到碟片的影子。
到了晚上,丢了碟片的陶安心有忿忿,晚饭时喝了两杯酒,早早把妻子骂去睡觉,自己躺在客厅看起了电视。
不一会儿,陶安便迷迷糊糊地在沙发打起了盹,突然一阵敲门声把陶安从梦中敲醒。
他有些烦躁,躺着没动,扯着嗓子问:“哪个?”
“叔,是我,开下门。”大门外的声音有些耳熟。
拉亮厦坎上的灯,陶安打开门——原来是白天刚见过的侄子沈天刚。
平时不怎么走动的沈天刚主动扬了扬手中的两瓶小青稞:“叔,还没睡的嘛,过来你家玩下。”
虽然诧异,但陶安还是客气地把他迎进了门,两人坐在客厅,你一杯我一杯地喝着,沈天刚就是不提为何而来。
酒至半酣,酒精的作用加上炎热的天气,沈天刚干脆脱去了身上的汗衫,赤膊上阵。陶安看向他:“侄儿子这个身体可以啊。”
沈天刚把酒杯往桌上一顿,指了指陶安卷起半截上衣露出的肚皮:“表舅你保持得好的嘛,根本看不出来你都是当老爹的人了,皮肤还白,不像天天干活的人。”
陶安直摆手敷衍说老了,身体不行了,沈天刚却似笑非笑,“身体么你怕好的。”
“表舅,今天回来时候我在水塘边上捡着一张碟子。”沈天刚说得漫不经心,陶安心里却咯噔一下。
陶安不知道沈天刚什么意思,说那是别个拿的新碟子,还没看。
沈天刚笑了,那张碟片满是划痕和指印,显然是经常播放的样子,“我倒是拿回去放了看了,好瞧得很。”
沈天刚不知从哪里把那张碟片摸了出来,放在陶安手边,说:“表舅,其实这个类型的东西我也还是喜欢的,有空么你可以约我一起瞧。”

陶安闻言愣了愣,实在拿不准沈天刚说的是真是假:“你说你喜欢看这个?”
沈天刚点点头:“百分之一百嘛,不信我两个再看一遍。”
年近六十的陶安一辈子都没下过这么大的决心。不知道是出于酒精的作用,还是多年来胸口压抑的冲动,他决定相信沈天刚。
他抱起电视机,带着沈天刚走进进卧室。
卧室里一片漆黑,陶安率先踏了进去。
“侄儿子,今天的事我两个晓得就行,外面说不得噶。”陶安再三嘱咐,沈天刚笑着答应。
陶安接上电视,放入碟片。雪花闪烁过后的荧幕里,是两个肌肉健硕的欧美男人抱在一起,赤身裸体。
陶安和沈天刚坐在床沿,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沈天刚紧盯屏幕,陶安侧眼偷看。他的喉咙在动,手在摩擦,陶安知道,沈天刚没有骗他。他现在这个样子,和以前的自己一模一样。
陶安第一次发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就是在初中时候。
有一天晚上宿舍的瓦房漏雨,陶安和自己要好的同学挤到了一张床上。两人身子贴近的时候,陶安明显感觉到自下而上的一股热气,他把那位同学抱得很紧,说是怕冷。
男同学并没有在意。
随后的一年,和陶安玩得好的同学基本都被他亲近过,有时是睡在一起,有时是一起洗澡时故意贴近。所有人都以为这是同学间的玩闹,只有陶安自己知道是什么。
在那个全国上下都充满困惑的年代,陶安升学无望,只能回家种地,然后娶妻生子,表面上与常人无异。
和一辈子没走出过大山的陶安不同,年轻的沈天刚脑子里很早就有同性恋的概念,虽然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同性恋,他喜欢女人,并不妨碍他能接受男人。
自己似乎也喜欢男人,是他近几年才发现的事。
偶然一次,沈天刚看到网站中有一个同性的分类,点进去之后算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他也说不上来那些片子里肌肉横生看上去硬邦邦的肉体为什么会给他带来如此的视觉冲击和精神向往。
从一开始的偶尔一次浏览一两部,到后来专门找着去看,这些片子让他对这个领域充满了探索欲。
后来,沈天刚结了婚,但和妻子的身体对话总让他觉得意犹未尽,不是对妻子,而是脑子里另一半干涸的自己。
那一半的自己把根扎得很深,等待着一个释放天性的机会。等待的时间越久,想冒头的欲望就越强烈。

沈天刚和陶安迅速熟络了起来。他们一起玩枪、一起喝酒、一起看碟。
陶安买碟的途径是普遍撒网,从小贩手里买回一大批碟片来,有没有他想要的纯看运气,小贩都不知到这些连壳子都没有的碟片具体都是什么内容。
而沈天刚在镇上的黑网吧停业之后,也是求片无门,在翻过去倒过来的看了几遍陶安手里的存货后,沈天刚没了兴致,他不再满足于此。
陶安倒是享受其中,可很快,沈天刚就感受不到任何的新意。
他决定寻求更强烈的刺激,他想学着片子里的样子,和陶安试一试。
陶安始终没能进一步突破,主要是因为农村的生活环境决定了他可接受程度的上限。在这里,他没有表达的对象,没有宣泄的窗口,更没有实际操作的可能。
这么些年来,陶安都只是满足于看片后的长舒一口气。此刻对于沈天刚提出的想法,他一下失了主意。
年轻力壮的沈天刚不断要求占据主动,陶安一咬牙,“来吧。”
在此之前,沈天刚用片子里的方法和自己道听途说的手段帮两个人都做了准备,但艰难的过程和剧烈的疼痛还是让陶安非常不适应。逼仄的抽水房一时间像是他的刑场。
在阴暗潮湿的环境下,第一次体验对于陶安来说实在难忍,可沈天刚却非常满足,有些不管不顾的架势。
很快,沈天刚就说了服陶安,半是强迫地来了第二次尝试。
自此,两人时常在村后的抽水房中见面,各取所需。年轻的沈天刚沉迷于肉体,而陶安需要的不是这种满足。
陶安真正在意的是——自己隐藏了一生的身份,守了一生的秘密,终于在快要60岁年纪,遇到一个可以放下所有包袱,做回真正自己的机会。
即使两人的关系只能隐藏在最隐蔽的角落,无法言说。

我第一次见到陶安的时候,他已经坐在了审讯椅上,全身都是血,眯着眼睛,皱着眉头,浑身上下散发着疲惫的气息。
我问搭档大林:“什么案子?”
“杀人。”大林言简意赅。
我有些懵圈,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小老头竟然会杀人,我赶紧拿起笔录。
“陶安,61岁了噶…”我刚看到嫌疑人基本信息这一行,门外就有人喊道:“大林,刑警队的来了,你们哪个带他们去下现场。”
“好。”大林应了一声,转过头拍拍我,“栗树村你认得的嘛,没看过凶杀案现场么你带他们去,也见见世面。”
在路上我听刚哥把案情讲了个大概:案子发生在凌晨,报警电话是陶安的母亲请隔壁邻居人打的,死者是同村村民。
“我来到的时候他家大门是开着的,整个院子里面只有一格房间亮着灯,走过去是一屋子都是血。房间里面有张床,一个人在床边跪着,衣裳也不穿,另外一个在床上躺着,也是不穿衣裳。哦哟,吓到我了,我以为一下干死两个。”
同事走近一看,发现床上那个人肚皮还会动,在那里呼哧呼哧地喘气。警察拿枪指着他,叫他出来,叫了好几声他才听见,慢慢走了出来。
那人就是陶安。
他没什么抵抗,直接承认死者是他杀害的。凶器有两样,一个是在卧室门口发现的一把菜刀,还有一个是在里面货架上挂着的一把镰刀。问到为什么起冲突,只说是一起看碟片的时候吵了架。
我找到了昨晚出警的相机,里面的照片里,死者跪在床边,耷拉着脑袋伏在床上,后背有个清晰的伤口,还能看见顺着伤口流出的血迹。
这个造型着实有点诡异。
“诶,对了,死者是什么人?”法医脱下手套,转头问我。
“也是这个村的,叫沈天刚。”

回到所里,对陶安的第二次讯问还在继续。
另一边,刚哥和兄弟们在会议室讨论案情。虽然陶安承认自己动手杀了沈天刚,但是对于杀人动机却依然语焉不详。
所长主张赶紧移送嫌疑人,便于做死者家属的安抚工作,刚哥却认为杀人动机太过牵强,一定要搞清楚两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矛盾以至于拔刀相向。
正在两人僵持不下的过程中,刚哥接到法医打来的电话。会场没有外人,刚哥打开了免提。
“大队长,跟你报告一下,我在尸体上提着点奇怪的东西。这个我也拿不准,所以想赶紧跟你探讨下。”法医吞吞吐吐。
“什么东西,你说嘛。”刚哥扫了众人一眼,把免提切换成听筒,转身出了会议室。
约莫有二十来分钟,刚哥走了进来,脸上的表情捉摸不定。他开口就问起了陶安的身体情况,还说要去讯问室再看看。
大家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一行人跟着他。进屋后,刚哥让同事把陶安手铐揭开,让他贴墙站着,说要再进行一次人身安全检查——说白了就是让他脱裤子衣服。
陶安看了看四周,显得有些犹豫。
“不用看了,都是男人,要不要我帮你?”刚哥提高音量。
陶安只能照做,最后脱得只剩下内裤。
我快速扫视了一遍,看不出什么异常,刚哥却让他继续。
在场所有人都很诧异,一般我们在对当事人进行人身安全检查,脱到这样已经是极限了。刚哥究竟要干什么?
陶安也显得很无奈,但还是把内裤脱了下来,捏在手中,挡在两腿中间。
“汗裤拿来我瞧。”刚哥伸出手。
刚哥这顿操作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陶安也用不可思议的眼神望着他。
刚哥失去耐性,一把扯过陶安的内裤,里里外外,前前后后翻看了一遍。
没一会,像是有了什么重大发现,停顿了几秒。
正当大家屏息以待,刚哥突然把内裤塞到我手里:“行了,回会议室,你们要看就看看,看完还他。”
内裤上的污渍,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回头看向陶安,他只低着头,一动不动。

回到会议室,所长按捺不住,开口问刚哥:“搞什么名堂,你也不跟我们解释一下。”
刚哥点燃一支烟,猛吸一口,说刚才法医给他打了电话,在死者生殖器前端提取到了疑似精液的物质,陶安的内裤上也有,“看什么碟会是这种情况?”
见我们都不说话,刚哥像是看透了我们的想法。
“你们以为他们两个是在自慰就错了。法医专门检查了死者的手,双手都没有发现精液,而且,我看了陶安的短裤发现,他短裤上的精液位置很奇怪,不在前面,而是在后面。这说明什么?”刚哥又丢出一个问题。
“诶,这个老倌短裤穿反了?”同事从旁抢答。
刚哥的一串问题信息量颇大,我心中却隐隐有了答案,所长也是眉头紧锁,想必和我考虑的一样。
这个答案,太过玄幻。
“他两个是同性恋,草包。”所长表示无奈。
死者手上没有任何痕迹,但是生殖器上不止有精液,还有擦破皮的地方。
怀揣这样的猜测,刚哥亲自上阵,审讯持续了三个小时,到了饭点,所长让我进去换刚哥出来吃饭,顺便送饭给陶安。
看到刚哥的精神奕奕和陶安的神情委顿形成鲜明对比,我猜刚哥已经得到了想要的答案。
我把饭端给陶安,翻看起了刚才刚哥所做的笔录。
陶安和沈天刚在一起了三年,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关系,两人在外是朋友,背着人就在一起。
陶安常年游离在家庭之外,妻子不过是自己妥协于时代和环境的牺牲品,他明白自己给不了她正常的夫妻关系。
为了弥补这种感情上的缺失,陶安选择用经济作为补偿,年轻时他吃苦耐劳,挣的钱统统交给妻子保管开销。
就像花钱买个安心,让自己心安理得地不爱她。
家里无法言语,在外难以声张。陶安只能借着一个正常家庭的外衣把真实的自己藏匿。
常年无人可以交谈,认识沈天刚,让他无法言说的一切有了出口。一起看碟的日子,也成了他多年压抑后的一点慰藉。
但他简单地以为,同好即是同类。
沈天刚狂躁张扬,强势主动,让陶安潜意识里认为这样的关系,就应该是这样。毕竟,被动接受的人生,自己过了一辈子。
可他始终没能明白,解放束缚的情欲,和找到契合的伴侣本就不是一回事。
沈天刚驾驭自己的喜好似乎全凭心情,火着枪响,想来就来。
可陶安毕竟年纪不小,沈天刚才三十出头。他渐渐有些倦意,一方面是年纪渐长,身体有恙,另一方面是沈天刚每次都把自己搞得一身伤痛。
他开始拒绝沈天刚,起了离开的念头,但总是拗不过力壮的沈天刚。
直到那一次彻底的爆发。

我看着审讯室的陶安,他的情绪还算平静。若不是我们点破了他和沈天刚的身份,看样子他会一直隐瞒下去。
被揭穿一切的陶安缓缓开口交代。动手的那天晚上,两人在沈天刚家喝完酒,沈天刚把陶安送回家。到了卧室沈天刚提议看会儿碟片再回去,陶安拿他没办法,只能如他所愿。
碟片看得沈天刚兴致高昂,他不顾陶安的反抗,也不管两人没做任何事前准备,一定要当场和陶安发生关系。
他把陶安反身扭住,扒去他的裤子就往他身上蹭。陶安又疼又气,一边挣扎,一边大骂沈天刚。
可他越反抗,沈天刚越兴奋,陶安的叫骂在他耳中成了鼓劲加油,他下手更重了。
疼痛一阵接着一阵,沈天刚却没有停下的意思。
就在他准备与从前一样放弃抵抗,缴械投降的时候,沈天刚突然掐住他的脖子,“骂嘛!咋个不骂了!”
手劲渐重,陶安几近窒息。
挣扎间,陶安猛地瞥见货架上的菜刀,借着酒意抓起菜刀就朝沈天刚挥了两下。
沈天刚仗着年轻力壮,一把就抢过菜刀,刀锋一带,划破了陶安的手。他把菜刀丢在一旁,反手给了陶安一耳光:“老*****,你疯了噶?”
骂完伸手过去拉住陶安,想继续侵犯他。
原本只是想吓吓沈天刚让他停止对自己的侵犯,可现在陶安现在却又羞又怒,脑子里闪回着这些年被沈天刚收拾的画面,不自觉地咬紧了后槽牙。
他顺手拿起货架上的镰刀对着沈天刚一阵乱挖。
“毛驴子!烂*****!”

沈天刚这才意识到陶安是真正动了杀心,两人扭打在一起,可没几下沈天刚就不动了。
空气一下子停住,只留下陶安一人握着镰刀呼哧带喘。
看着沈天刚趴在床边一动不动,背上血如泉涌,陶安意识到,沈天刚死了。他抹了一把脸,使劲让自己清醒。
余光所及,老母亲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卧室门外。
“他跟我板命,被我舞翻了,咋整?”陶安张口就问。
“那么大的事,我去喊人来瞧。”母亲颤颤巍巍地走出家门。
陶安的母亲晃到隔壁,请邻居报了警。而满身疲惫的陶安躺回了床上,直到他被民警逮捕,又对我们说出了这些不可告人的隐秘。
同事看他的样子,顺口问了一句:“你是怎么喜欢上那个沈天刚的?”
陶安开口,有头无尾几个字:“不算喜欢嘛。”
我们一时不知怎么回复。
对于陶安来说,如果不是和沈天刚,他还能和谁呢,难道又要过回被时代隐身,被社会排除的日子?
三年里,陶安都在疼痛中这么安慰着自己。他以为自己找到了一条窄路,却不知道自己走上的是一条绝路。

陶安杀人的始末很快就在所里传开了,有人当成闹剧,有人当做谈资,而我却觉得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在这段畸形的关系里,他卑微且无力。
期待了60年的解脱,最终也没有换来解脱。
事情虽然水落石出,但是案件移交却犯了难,该如何去写杀人动机呢?最终刚哥同意了所长的意见,含糊地描述成因琐事引发纠纷。
在闭塞的农村,这是对两个家庭负责任的做法。
陶安最终因为过失杀人,被判处了死缓。
和陶安短暂的接触过程中,他全程没怎么提及死亡的沈天刚,可是送押前,他主动问了我一个问题:“同志,同性恋给犯法?”
当同志和同性恋两个词同时出现在耳朵里时,我顿了几秒,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现在想想,他临死前的心愿只是想知道这样到底犯不犯法。看了陶安一眼,我回答他:“不犯法嘛。”
陶安没有说话,又把头低下。
“我大学时候住一个宿舍的就有一个是同性恋,学习好,人也好,跟大家都玩得拢。”为了引陶安说话,我继续说道。
“其实这些年么正常了,大城市里面多得很,人家外国还可以同性结婚。”不知不觉间,我竟然萌生出了对这个杀人凶手的同情。
过了许久,陶安幽幽回我一句:“可惜我又不在外国。”
陶安的选择根本没有那么多。某种意义上,他没有选择。多数时候,和沈天刚在一起,只是一种被动的配合,这种配合能延续属于真正自己的生命。
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张五彩斑斓的碟片,本来是他暮年的一个出口,却因为无法拒绝、无法诉说、无法停止,变成了人生末路的单程票。
两年后,我已经从派出所到了刑警队,一天,整理卷宗时偶然发现一份刑事裁定。
由于表现良好,陶安由死缓减成无期。
陶安短暂地活成了自己想成为的模样,代价是对方当场横死,自己终身监禁。可对于他来说,有没有遇到沈天刚,难道人生不都是一场终身监禁吗?

生活在闭塞的环境里,到底会被改变什么?
很多书里都说,环境会改变人的思维、选择、眼界、处事方式。但少有像刘千山这样的记录,将真实的案例呈现出来,告诉每个人,这种影响有多残酷。
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刘千山说,案件结束时,整座山区都认为陶安只是个单纯的杀人犯。
三年里,陶安无论被强迫多少次,也从不敢告诉别人,更别说报警。被定案时,他只承认自己杀人,其余闭口不言,直到最后除了警察外,也没人知道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
因为种种“难以启齿”,陶安的反抗成了一次彻底的、不被理解的爆发。
这世上,没有太多突破逆境的故事。就像更多人也只是抱着无望的内心,走向注定的归宿。
看完这篇故事,我老在想,自己是否也陷入过因为环境而导致的困局。不被理解,只能自己试着去突破。
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就来留言区里跟我聊一聊。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大棒骨
插图:大五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