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54)
带妈妈去取节育环

嵌进肉里的节育装置
医生推开手术室的门,递给22岁的语童一个小玻璃瓶:“拿去病理科。”那时候,语童的母亲躺在手术室里,由医生继续帮她完成取节育环的手术。
从妇产科手术室去病理科的路上,语童端详那小玻璃瓶里装着的东西。瓶底浅浅铺了层白色药水,里面浸泡着的,看起来像是一团带着血丝的息肉。语童猛然领会了那是什么:“这团息肉是从妈妈子宫里刮出来的。”
2021年1月,正值农历腊月,甘肃省天水市处在隆冬之中。家属不被允许进入手术室。隔着手术室的白墙,语童看不到手术的过程。母亲后来对她讲述了在手术室中感受到的一切。
先是做了消毒,之后,医护人员把阴道扩开,伸进探针确认节育环位置。之后,医生取出了一个20多厘米长的取环钩,深入她的宫腔。能感受到医生应该小心地尝试变换了几次角度,之后,节育环被取环钩顶部的长圆形卡住,钩离了她的身体。
那是一个两侧带着小巧钩状结构的节育环。因为在语童母亲体内放置超过18年,节育环的一端已经勾进周围的肌肉组织,与子宫内壁粘连。避无可避,医生只能硬生生往外拽,那团息肉就是过程中节育环从母亲的子宫里勾下来的。
有调研标明,佩戴节育环的女性绝经超过两年之后,节育环取出时出现困难情况的比例达43.9%,而接受调研的女性中,绝经不满两年的有96.1%顺利完成了节育环取出手术。若节育环长到肉里,发生“嵌顿”,取出时还有大出血的风险。节育环需要定期更换,一般是3年或者5年,最长11年,必须从身体里取出来。而多数女性,直至子宫内的金属制品造成更大的安全隐患后,才明白节育环需要及时取出。
术后,语童陪伴妈妈在休息室小憩。母亲脸上血色尽褪,语童问:“妈,疼吗?”
母亲声音细微,“疼。”
她虚弱得没有力气说话,轻轻握着语童的手,良久后又说,“跟生你的时候差不多疼。”
从医院出来时,天已经全黑了。医院外人群散去,风在空旷里横冲直撞,母亲裹着帽子手套,在语童的搀扶下小步挪动着。麻药反应太大,马路边,语童母亲又弯着腰吐了好几次。路灯昏黄,语童看着二人颤巍的影子,头一次冒出“母亲竟然这么瘦小”的想法。22岁的自己,已经比母亲高很多了。
从医院步行回家,平时不过6分钟路程,母女俩走了20多分钟。吃过药后,母亲很早就睡了。她拒绝语童一起睡的建议,语童猜,可能是母亲怕忍痛时发出嘤咛打扰到自己休息。那一晚,语童特意打开母亲和自己的房门,留意着母亲那边的声响。第二天一早,她去买鸡给母亲炖了红枣鸡汤。再后一天是排骨。手术后整整四天,除了吃饭上厕所,语童母亲几乎没有下过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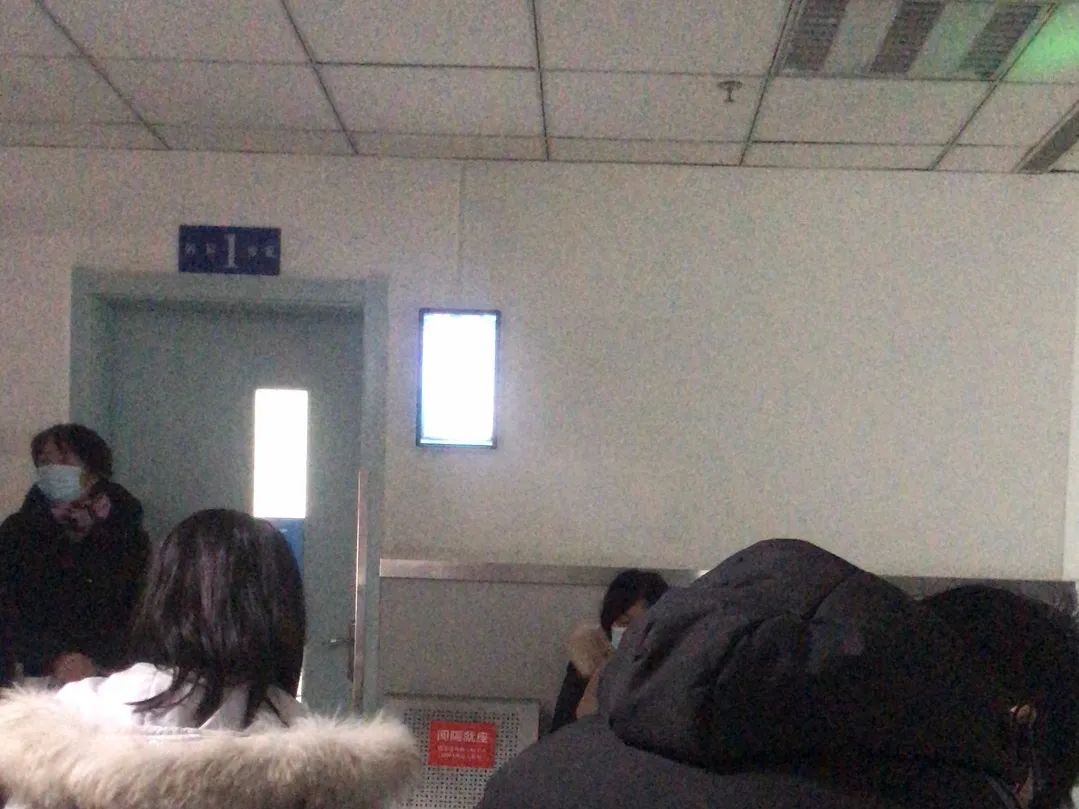
图 | 语童在手术室外等待着母亲
“节育环”这三个字,以一种更激烈的方式,时隔七年后再次闯入小贞一家的生活。
2020年9月10日,江苏宿迁市,在一所幼儿园任园长的小贞母亲,在去教育局送材料的路上出了车祸。她被一辆高速行驶的电动车撞倒在路旁,当时,只发现擦伤了小腿肚和手臂外侧。小贞母亲爱美,车祸发生后,她最担心身上的擦伤会不会留疤,为了安慰母亲,小贞还特地买了祛疤产品送给母亲。
一家人都没有料到,这场小小的车祸翻起了一个意外余浪。车祸后连着好几晚,母亲总觉得腹痛,一直发展到无法忍受的地步。一家人开始担心是撞车伤及了内脏,于是,母亲特地去了趟医院,拍片检查。
诊断结果是“肾盂积水”,专家医生看了片子,告诉母亲,引发肾盂积水的原因还需继续探查,但治疗方案“很可能要把肾摘除一个”。
现在想来,小贞觉得母亲把恐惧和崩溃藏得很深。回到家后,母亲只是淡淡说了一句:“我不想治了。”但母亲的面容憔悴了下去,第三天,她告诉小贞:“我又是一晚上没睡着。”
两天内做了三次检查,医生问小贞母亲,“你有没有戴过环?”得到肯定的答案后,医生确认,是节育环穿破子宫腔移位到腹腔,划伤了肾脏,造成肾盂积水。
2020年9月30日,小贞母亲右侧腹部开了一道5厘米切口,之后,游走在母亲腹腔内的节育环被医生取出。
小贞母亲术后两天瘦了6斤。麻药过去后,伤口开始撕裂地疼,小贞母亲常常背对着女儿,侧卧着蜷缩在病床上缓解疼痛。看着母亲的背影,小贞好几次难受得有想哭的冲动。以前爱运动、每天出门前会细致打扮自己的母亲,如今反差巨大,她脸色灰黄,在忍受疼痛中艰难康复。
02
上辈女性的生育记忆
术后,医生向语童母亲展示了那个放置在她体内近19年的节育环。那是第一次,语童母亲看到它的样式:一枚缠着铜丝的T型节育环,从体内取出后没有经过清洗,上面还勾连着血丝和肉,静静躺在医生摊开戴着医用手套的手掌上。
1998年,诞下语童三个月之后,母亲到医院“上环”,领取上环证明。“所有人都这样,因为生育后要上班必须有上环证,”母亲告诉语童,“所有人都戴,你不戴,才是奇怪的那个人。”
语童母亲有过反复戴、摘节育环的经历。
第一次上环后,由于宫颈形态与节育环形状不适配,造成语童母亲非经期大量出血,腹痛腰痛,母亲不得已取掉了环。之后,她经历了意外怀孕和强制流产,2002年第二次戴上了节育环。
语童的母亲是一名医护人员,知道节育环的病理基础,虽然没有亲眼见到手术过程,也大致知道节育环放置进体内之后发生了什么。更多女性记忆中,自己当年懵懵懂懂地,就“上环”了。
52岁的敏英就是其中的一员。
敏英自小生长在广西桂林市周边的一个瑶族自治县。1998年11月,她诞下女儿麦琪,不久后她独身一人搭汽车从镇上去了县城“上环”。
在县城,定居在那里的长姐陪同敏英到妇产科医院,戴上了一枚“Y”形节育环。
“一间很小的手术室,有张床。整个过程很快,大概只有两分钟。”这是敏英全部的记忆。在她所处的时代,医生一般会用消毒好的扩阴器打开阴道,用环钳夹着节育环,把“Y”形节育环送进子宫深处的中央位置。
“不用担心什么,”敏英记得医生一开始这么跟她说,而后补充道,“也看体质,刚上完可能会发炎。”
就这样,不消5分钟,敏英做完了手术,取了一张盖章的上环证,离开了医院。
“作为一个女人,难免有这样那样的小病小痛,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敏英说。
在旁人眼中,敏英做事利索,许多人形容她行事“风风火火”。作为小学语文教师,敏英每天七点半就到学校,上课、处理班级各种杂事,有时几乎一整天都站着。
诞生在双职工家庭,麦琪上幼儿园前没有长辈能留在家带她,敏英就带着她一起去学校上班。敏英上课时,麦琪就在教室门口听着母亲的声音独自玩耍。中午休息,敏英还要带着女儿赶回家,给孩子和丈夫做饭。“妈妈没有应付过任何一顿饭。我们家每一餐基本都是三、四盘菜。”麦琪说。

图 | 年轻时的敏英与幼年时的麦琪
但女儿麦琪知道,母亲每天都不舒服。记忆中,家里的药箱里数量最多的是各类治疗妇科病的药。“好像一直是这样。”麦琪说。金刚藤,英花片,桂枝茯苓丸,这些药名麦琪早已无比熟悉,戴节育环的副反应像一条尾巴跟在母亲的身后,让她拧着眉头,让她疲惫疼痛。
“以前那个时候,上环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敏英说。遗憾的是,在当时,这类手术的术后随访也很少得到应有的重视。很少有医生会直接指导这类手术的术后随访。许多警告信号,需要女人们通过身体的痛感去琢磨,一些妇女由于没有被告知相关知识,因而被妇科病缠身,却从未察觉与节育环有关。
术后,敏英开始感到小腹坠痛,随之而来,她发现没有来月经的时候下体也会出血,有时渗出几滴血后就停止了,有时这种不规律的出血则像真正的经血一样多。腰酸背痛日渐严重,到最后只要凳子稍微硬一些,她坐上去都十分煎熬。
22年来,敏英常常因为这些异常而去医院检查,得到的诊断结果是各种各样的“炎症”,盆腔炎,阴道炎,宫颈炎,医生开的,也都是各种各样的消炎药。
敏英从没想过,伴随自己20余年的妇科病可能与节育环有关。作为一种置入子宫腔内的避孕装置,节育环通过造成子宫的无菌性炎症,使胚胎无法正常着床受孕达到避孕目的。节育器时刻刺激着子宫内膜,女人们完全适应炎性反应,大约需要三个月。
多次寻医未果后,就连敏英自己,都遗忘了身体里那个小小的金属圈。
这始终是一种无法被说出口的病痛。丈夫无法理解,又不至于向孩子诉苦,一些女性就这样硬捱着。身为一名护士,语童母亲说,同科室的同事们聚在一起也少聊起节育环。关于节育环的全部知识,她是偷偷问妇产科的同事才了解的。
“即使是医生护士,也不是那么重视节育环。有的人是下意识逃避,有的人是真的忘记了。”母亲告诉语童。
03
理解了母亲的不适
听母亲描述的取环过程,语童脑中冒出了“可怖”二字。
她小的时候听说过“节育环”。“既然是按要求大部分女人生育后要戴的东西,那它肯定不会对女性身体造成伤害。” 那时候,语童离生育这件事还很远,没有动机深入理解它的原理和作用机制,合情理地笃定这种被批准大范围使用的器械一定不会带来痛苦。
直到2020年,她在网上偶然刷到一位女性健康博主发微博提及:“有的节育环会移位造成子宫穿孔,有的环深嵌进子宫腔……”语童第一次领会到,在确保基本安全性之外,节育环原来还带给了佩戴它的女性带来了疼痛。
同年,语童从网络上看到了艺术家周雯静的展览《女人系列·节育环》。展览收集了300个现实生活中被使用过的铜质节育环,把它们整齐排列,嵌在一块蓝丝绒墙面上展出。乍看之下,它们精致美丽,在灯光下熠熠闪光,但知道它们的作用后,这些展品就透出残忍的意味。“形态各异的节育环背后,是一个个真实具体的女人。”语童说,她想到自己的妈妈,只觉心疼。

图 | 周雯静作品《女人系列·节育环》
语童的经历,代表了许多生于90年代末的女孩认识节育环的过程。她们的生活中原本不存在与“节育环”强相关的语境,通过科普或《女人系列·节育环》这类艺术展览,她们得知了母亲与一枚小小的节育装置的渊源。其中一部分人和语童一样,鼓励并陪伴母亲到医院取出超期使用的金属节育器,一些节育环放置时间甚至超过了使用年限十多年。
母亲渐渐恢复的过程中,小贞第一次与母亲正式地聊起“节育环”。
2008年,小贞母亲在家附近小区的简易小诊所,偷偷取掉了节育环。那是一间藏在住宅区车库角落里的诊所,狭小的空间塞满了各种医用器械。
“有阿姨们进进出出,她们脸上都是不开心的样子。”小贞这样描述那时候看到的诊所。
那时候,小贞问过母亲什么是“环”。母亲含含糊糊地回答:“它在妈妈肚子里。肚子里有环就不能给你生弟弟妹妹啦。”这构成了小贞对“环”的最初印象:“肚子里有个小圆环,听起来很好玩。像是妈妈的玩具。”
麦琪也是通过互联网上的讨论,知道了母亲与节育环的关联。2020年11月5日,麦琪无意中看到一位女性健康博主开的一个话题,“带妈妈取环”。
“我妈妈以前就取出来过,听说直接从肉里往出拽。妈妈肚子难受了好久。”“我让我妈妈去取,她特别生气,说当时所有人带了,别在这吓人。她和我大吵了一架。”“妈妈子宫肌瘤,子宫都割了。”
这条微博下有八百多条评论,麦琪一条一条翻看。“原来有那么多女性上了节育环,原来节育环超过使用年限会有这么大的伤害,原来有很多病都是因为节育环。”回忆当时,她连用了几个“原来”。
一个个“原来如此”,拼凑出麦琪这些年来困惑的答案。麦琪母亲经常做家务做到一半,就放下手头的活躺在床上休息;每个星期五学校大扫除结束后,母亲通常都草草吃几口就回卧室躺下了;母亲常年眉毛都拧着,每次问她怎么了,母亲的回答总是“肚子有点不舒服”。

图 | 麦琪看到的微博
麦琪回忆着,母亲多年的疼痛找到了缘由,她替敏英感到心疼。
整理好情绪后,麦琪给敏英转发了这条微博,本以为母亲会回避或者不当一回事,没想到她立刻打来电话。
那通电话里,麦琪和母亲就节育环的问题聊了很久。“我们以科普为目的在聊天,我能感觉到她的信任。”麦琪说,那是第一次,母亲对自己说出“节育环”这三个字。麦琪心想,母亲或许多年来也期待能抛开“这种病不能对别人说”的羞耻感,认真、正式地对人谈论自己的身体疼痛。
一个星期后,11月13日,敏英在县城的妇产科医院,取出了与自己共同生活了22年的节育环。
女性身体经验:从私领域到公共情感
- END -
编辑 | 温丽虹
===============================================================================
北漂5年,我租房遇到的那些坑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冰点周刊 Author 中国青年报

|本文转载自冰点周刊,公众号ID:bingdianweekly,作者 | 陈轶男,编辑 | 从玉华
搬家期限的最后一天,北京降温到了零摄氏度以下。
我裹着羽绒服站在楼下守摊儿,搬家师傅用小拖车把我的家当陆续运下来。有七八个用胶带封好的纸箱,还有一把白色的办公椅,两个自己组装的置物架,一架电钢琴,一张折叠椰棕床垫。我的穿衣镜先被留在了楼道口。“这风一刮,挣你的钱都得赔镜子。”师傅跟我解释。
这是我在北京第七次搬家。5年前刚来北京工作的时候,我身边只有两个行李箱。在那之前我在国外上学,在8平方米的宿舍住出了坐牢的感觉。
在离单位不远的地方租下一间宽敞的卧室,我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安顿下来。
“北漂的第一个落脚点。”我在房间里拍了几张照片发到朋友圈,写下,“希望拖着箱子四处漂泊的日子从此告一段落。”
这份希望显然破灭了。几年过去,我辗转租过8个住处,跨越北京的3个区。
同事说我是他们见过的租房运气最差的人。我也想不明白,我一个勤恳打工人,从未拖欠房租,为什么租个安稳的房子就这么难?
我本来以为,只要避开黑中介,租房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作为一个新入职的记者,我的收入没多少,租房要求却有点高。我需要靠近地铁站,方便我出门采访说走就走。因为经常要在家写稿,室内环境也不能太差。坐着“看房管家”的电动车跑了几处之后,我通过长租公寓租下了北二环外一套三居室里的主卧,18平方米,朝南,带独立阳台,和舍友共用厨房和卫生间。房子是一家事业单位的家属房。
签长租公寓的好处就是方便省心。房间被装修得很新,家具家电都齐全,公共区域有每月两次的上门保洁,哪里坏了还可以免费维修。通过网站或App,客服和“生活管家”随时为我们服务。唯一的缺点就是贵。加上服务费,我的房租一个月将近3000元。
我的舍友是两个姑娘,一个在准备考研,一个在楼下的银行上班。我跟她们加了微信拉了群,在群里分摊水电费。我们就像住在同一层酒店的客人,除了在厨房碰见时会聊聊天,平时几乎不打照面。
我开始舒坦地生活,摸清了附近最新鲜的菜市,不出差的日子在家学着做减肥餐。两个月后的一个周末下午,我突然听到大门传来“咣咣咣”的砸门声。一个愤怒的中年女人在外头喊,自己住楼下,我们房里的人在她家门口吐痰,让我们出来“把痰舔回去”。
我和室友缩在屋里一动也不敢动。等她走后,我们发现金属的防盗门已经被凿出个几十个小坑,不知用的是菜刀还是斧头。
我们立即打电话给长租公寓的管家,没几天,居委会就来了两个人了解情况。我们澄清我们3个女生没人会吐痰,经过楼梯的还有外卖员和快递员,希望他们跟楼下的住户沟通一下。
被砍门之后,我和舍友都有些精神紧张,走楼梯总要左看右看,回家如做贼。
平静一段时间之后,一天半夜,我在睡梦中又被“咣咣咣”的砸门声吵醒。我看了一眼时间,深夜1点53分。我翻出录音笔,打开自己房间门,让不堪入耳的叫骂声穿过客厅飘过来。第二天一早,我就拿着录音去派出所报了警。
民警给我做了笔录,后续就再也没有什么动静。对方表示,半夜来砸是因为我们没关水龙头,还说我们这里“每天来来往往好多男人”。她每天从猫眼偷窥我们,连我舍友几点出门几点回来都知道。
面对这样的安全隐患,长租公寓同意给我们办理无责转租或退租。于是住了不到3个月,我又开始找房子。
第二次租房,安全是第一要务。
考研的女生搬去亲戚家,我和在银行上班的舍友决定继续合租,我们需要电梯、安全通道和监控,这样就算邻居拿刀来砍也有路可逃。最后我们选定了附近最高档的小区里一套60平方米的两居室。

同事帮我搬家 | 作者图
安全是有成本的。我的新卧室朝西,面积也比之前的小,房租却骤升到每个月3900元。我们通过租房中介跟房东签合同,在房租之外还要支付7300元的中介费。女房东把鸡零狗碎的账算到小数点后两位,说电视线路坏了但是电视费她已经交了,所以这个费用应该由我们承担。
在父母的资助下,我和舍友搬进了这套房子,感觉生活提升了一个档次。拥有了小客厅和沙发,我和舍友经常在一起聊天和吃饭,比之前的住处更像一个家。我有了整面墙的实木衣柜,把衣服按照颜色渐变顺序码进去。当时的男朋友送我回家在楼下磨唧的时候,装修精致的大厅还会提供一种都市偶像剧的画面感。
然而,都市丽人的日子也没能长久。我接到单位通知,年后要去云南驻站一段时间。房子还剩下4个月租期,我降到每个月3000元才把自己的卧室转租出去。
从云南回来之后,我搬到了离男友学校比较近的五道口。之前住在朝阳区,跟他算得上异地恋,打车见一次面就要花50元。五道口聚集着好多家科技公司,房租偏高,我通过长租公寓租下了五居室里的一间小屋,11平方米,月租3300元。
因为房间小,我开始研究储物收纳技巧。我的书桌和床之间的距离容不下两个人一起坐下吃饭。男朋友过来的时候,我们只能把床单掀起来,在床垫上面铺报纸和餐垫,把床变成餐桌。
这一次舍友多,我开始体会到合租的麻烦。每天早上,我把洗漱用品拿在手里,竖起耳朵听被占用的洗手间什么时候开门,随时准备冲过去。我在家写稿需要安静,但是每天都有快递员和外卖员咚咚咚地敲门。我从不吸烟,房间里却时常弥漫烟味。
自从隔壁搬来一个美国男生,居家生活就更让人头痛了。他三天两头轰趴,把音乐播得震天响。有一天,我发现一只杯子不见了。我在冰箱上贴了寻物启事,那个美国男生告诉我,那只杯子被他摔碎了。到那时我才知道,长期以来他都在使用我的餐具和筷子。“我以为它们是公用的。”他一脸诚恳地对我说。
一年租期住完,男友也毕业出国了,我没有续租下去。
第四次找房的时候,我已经因为身体原因病休了一段时间,收入减少了,我想在租房上省点钱。
我找到了一个房东直租的房子,不住家的房东女儿空出来一间卧室。房间有些狭小,窗户的一半视野被对面墙挡住,但好在家具齐全,衣柜、书柜、床和写字台都是定做的,严丝合缝地卡在里面。房东按着女儿在外面的租金每月收我2800元,水电费也不用我分摊,对于三环外近地铁的房子来说,这是非常实惠的价钱。

房东家中的卧室|作者图
和房东住在一块,有点像给自己找了个寄宿家庭。我跟房东女儿年龄相仿,管房东叫叔叔阿姨。房东阿姨的父母就住在楼下,让我管他们叫姥姥姥爷。有时候姥姥亲手包饺子,从楼下给我端一碗上来。我出差回来时会收到阿姨的微信,告诉我冰箱里给我留了一个菜团子。男朋友从日本来北京看我,叔叔还专门炖了酱大骨在家招待他。母亲节的时候,我给房东阿姨准备了贺卡,里面写了长长的感谢。
一起生活也有不方便的地方。姥爷每天早上5点半起来遛狗,但凡看见我窗户透出亮光,就得数落我几天。后来我再通宵工作的时候,就把台灯压低埋在被子里头。
阿姨在医院工作,热爱并擅长做家务,每天都要用酒精给地板消毒,把家里归置得井井有条。之前她习惯了把女儿房间纳入收拾范围,我出差不在家的时候,她有次在家大扫除,把我的房间也整理了一遍,我脏衣篓里的衣服也都洗了。
“唉我怎么就忍不住呢。”阿姨给我发了好几条语音,关于擅自进我房间向我道歉,她小心翼翼地说,“你要是不乐意,我再给你恢复原状……”然后她告诉我她没有洗我的内衣,“我觉得那应该是你的底线。”
我笑了半天,回复她说没关系,感谢她帮我做那么多家务。但是说实话,我内心有一点隐私被侵犯的不适感。出差前,我有一颗箍牙用的支抗钉松落了,我把它包在纸巾里放桌上就匆匆走了,回来果然找不到它了。那颗钉子1200元,我没有跟房东提起过。
后来,房东阿姨陆续把我的衣柜、书柜和橱柜全都按照她的习惯重新收拾了,我几乎所有的东西都不在原来的地方。还有几次,我从垃圾桶里捡回好朋友写给我的纸条。那些纸条对我很重要,特地摆在书架上,但是被阿姨当成是废纸扔了。
有一段时间,房东这样好心但又越界的行为让我很困扰。我努力地适应这种相处方式。“可能北方人的性格就是这样吧。”我跟对房东进房间的行为大为震惊的深圳好友解释。有的时候这种毫不见外的热情让人感觉很温暖。小区是回迁房,住的大多是老北京的街坊。有次我穿着运动短裤出门跑步,电梯里不认识的大爷大妈看着我说:“姑娘,晚上已经降温了,你穿这样可别冻着。”
但是有的时候,这个不见外的度很难把握。阿姨上班的时候,通常是我和房东叔叔在家。叔叔早几年脑出血,留下后遗症腿脚稍有不便,平时不工作,在客厅看电视或者出去遛弯。也许是比较孤单,他特别愿意跟我聊天,只要我从房间出来,就会被他招呼过去。聊着聊着,他就会抹起眼泪来,开始跟我说很多家里面隐私的话题,抱怨阿姨,抱怨姥姥姥爷,说他们全都因为他生病了而瞧不起他,各种声泪俱下的控诉。
为了避免这样让我尴尬的谈话,在阿姨下班前,我只能一直闷在屋里,不到万不得已要去洗手间,我都不会从自己房间出来。我想过搬走,但是觉得另找租客太给房东添麻烦,就一直不好意思开口提。
直到有一天,房东阿姨突然来找我,告诉我她准备和叔叔离婚。原来叔叔一直酗酒,之前就是喝酒引发了脑出血,最近阿姨发现他还在赊账从小卖部买酒喝,加上家里其他原因,对他彻底死心了。叔叔不同意离婚,所以阿姨来找我帮她写一份离婚陈述书,她去向法院提交起诉状。
折腾了一阵子之后,叔叔搬出去了。我和阿姨两个人住在家里,感觉还挺好的。但是又有一天,阿姨检查出来肺部有一块阴影,需要做个小手术。她觉得也许房子太阴暗了风水不好,“自从住进来就没有摊上什么好日子”,决定把这套房子卖掉。
“求靠谱房源推荐。”我又开始找房,在朋友圈列出了这一回的硬性要求,“采光好、房间大、书桌宽敞。”
我本来还想省下中介费,但是在豆瓣上看了一圈,房东直租的大都是整套房,二房东手里的要么家装老旧,要么租期很短,长租公寓依然是最好的选择。我之前租的那家爆出了一连串甲醛超标的新闻,所以我选择了另一家长租公寓。
那两年房租涨得飞快,我把找房范围拓展到了东五环。一间由客厅改造的隔断间最符合要求,落地窗阳光充足,面积是之前房间的两倍大,窗帘还隔出了一个阳台。我终于有地方铺开瑜伽垫,平时自己在家活动活动。加上服务费,每个月房租4000元。



作者 | 陈轶男
编辑 | 从玉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