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起源于中国」(晚清版vs当代版)
晚清版「英语起源于中国」 | 短史记
众所周知,中国当代“学术界”有一种流派,宣扬的是“英语起源于中国”,更具体来说是起源于湖南。
最近读晚清史,发现这种论调在晚清士大夫们当中早已有之,且颇为流行,实在是一点都不稀奇。
比如,在光绪年间做过军机章京、被后世称为启蒙学者的陈炽,便认为“文字之兴,肇于中国,而辗转流布,渐达于泰西”
——天下所有的文字都始于中国,后来才辗转传到了西方。
(1)埃及尼罗河流域出土的那些古文字,“大类中国古时虫鸟之篆、钟鼎之铭。会意象形,宛然可指”,和中国的古文字很像,显然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2)意大利两千年被火山埋葬的古城,其城墙房屋街道的形制与布局“率同华制”,与中国完全一样;还发现一种铜乐器,“其声凄壮高清如中土之画角”,奏出的声音和中国的画家一样。这些显然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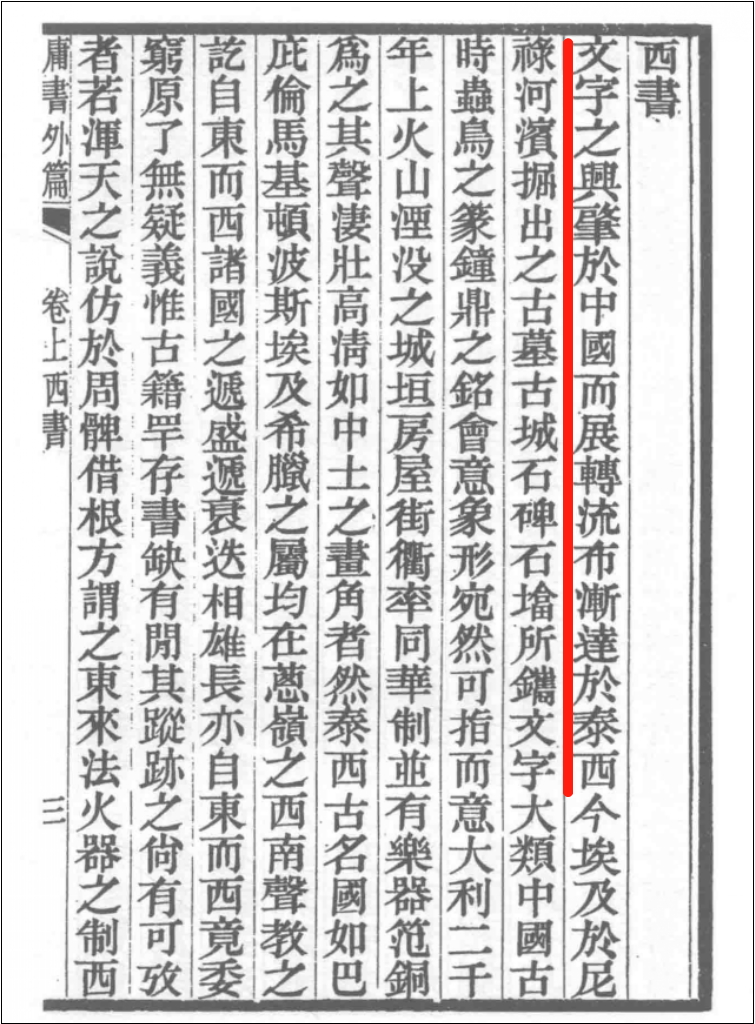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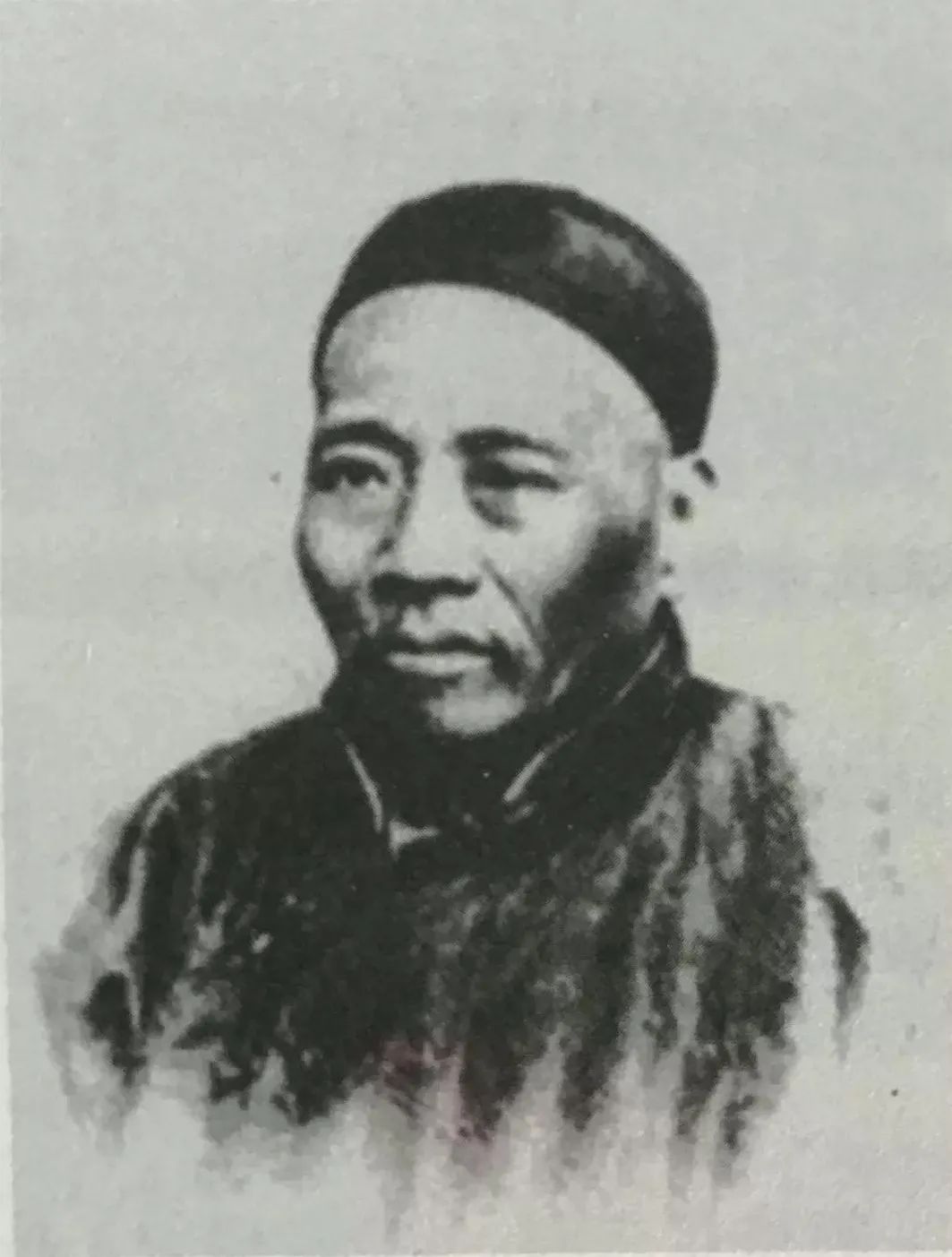
“中文直行主形,与埃及文为一派。埃及为西方文字之祖,其兴在夏商间。中国开辟最先,有结绳传音,易之以书契;外国开辟晚,先由中国流传书契,后易以点画传音。”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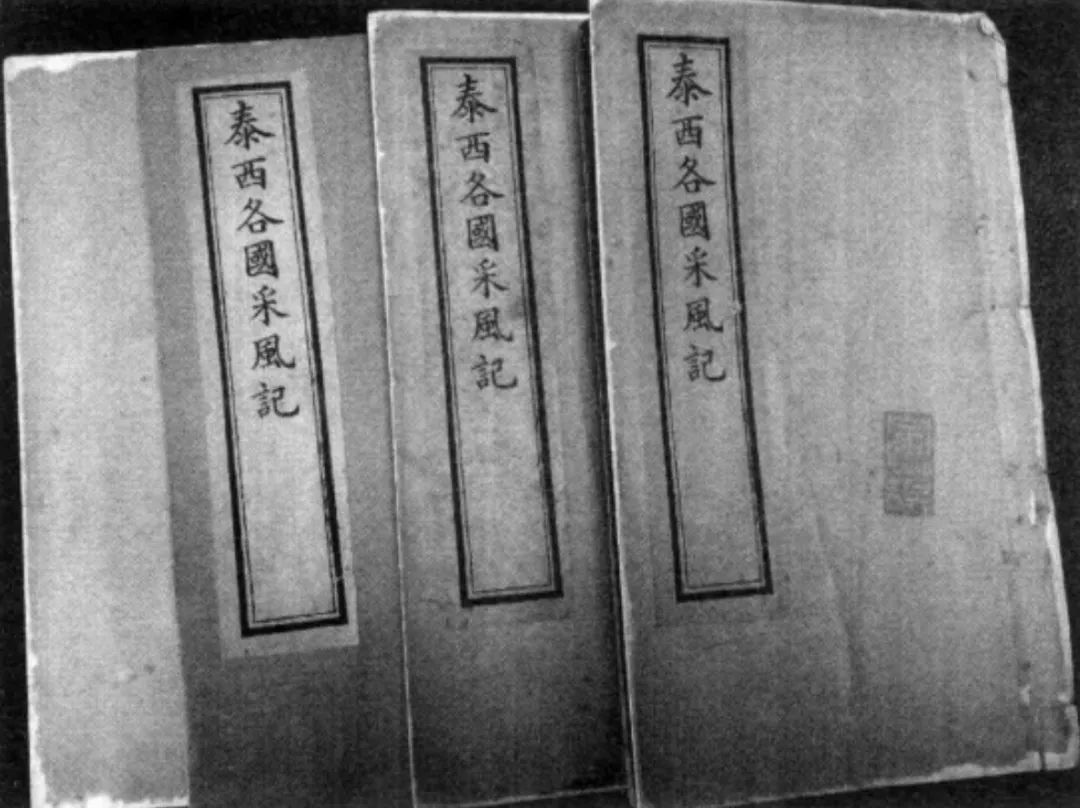
(1)“墨子衍怯卢之绪,……其后传入西域而为右行,即今之西文也”——二弟“佉庐”创造的文字被墨子继承,后来传入西域,然后便形成了今天的西方文字。(2)“蒙古书皆左行,盖用梵体”——大哥“梵”创造的文字流传至今,便是今天的蒙古文。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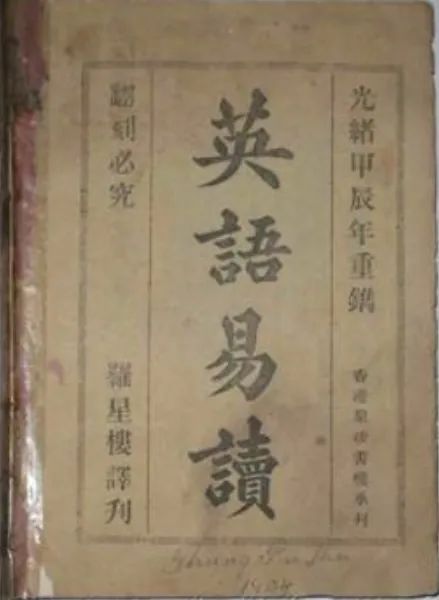
♦ 晚清英语教材
“泰西数学之奥理,根源于中国的《河图洛书》。……英文26个字母,源于中国伏羲以前,与天干地支相合,为没有文字以前的一种符号,后文字渐兴,变简为繁,本源遂无人论及。”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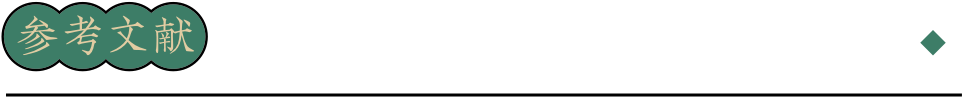
⑨黄应乾、陈祖武、刘克俊:《吴佩孚流寓四川五年间的活动》,《文史资料精选》第4册。
-------------------------------------------------------------------------------------------------------------------
当代版:
“英语起源于中国”:
英国学者在三百多年前也曾有过同样的结论……
“英语真的起源于我们古华夏。”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促进会副会长翟桂鋆日前的这番言论遭到了“群嘲”。翟桂鋆称,黄色是秋天叶落的颜色,英语发音几乎就是“叶落”(Yellow);“商铺”(Shop)的英语发音基本就是其汉语发音;心脏、脑袋,这是人体最核心的最重要的器官,所以英语发音就直取汉语其意:“核的”(Heart,Head),只是稍有变音而已。
不仅英语起源于古华夏,湖南大学法学院原院长杜钢建教授也在3月20日第三届中国“一带一路”博士论坛上演讲公布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称“英国人来自大湘西”。这一成果引起舆论争议。以杜钢建、翟桂鋆为代表的这批学者,还发表过“人类文明发源于中国大西南地区,后来远古华夏人西迁,开创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等观点。
人类历史上出现过许许多多令今人感到啼笑皆非的研究成果——“英语起源于中国”,仅仅就这一结论而言,翟桂鋆等人的“学术成果”并不是新鲜的。在350年前,英国学者约翰·韦伯就曾经提出,中文是世界所有语言的原始语言。
从我们现在的视角来看,这一结论同样显得非常荒谬,事实上,在他的时代,该结论也遭到了同行学者的批评,但也有不少人对此表达了宽容、理解,甚至是采纳。那么,是怎样的动机让身处不同时空的学者关注到这样一个共同的领域?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从各自不同路径得到的类似结论,获得了截然不同的学术反响呢?

巴别塔,老彼得·布鲁盖尔,1563
约翰·韦伯:
汉语是“巴别塔之前全世界的通用语言”
1669年,本职是建筑师的业余学者约翰·韦伯(John Webb)发表了长达212页的《历史论文:论中华帝国的语言是原始语言的可能性》(An historical essay endeavoring a probability that the language of the Empire of China is the primitive language)。在1678年,这本书再版时,题目有所改变,加上了几个字:探讨中华帝国的语言是在巴别塔之前全世界通用语言的可能性。
在旧约当中记载:上帝看到人类建造的巴别塔就要通往天堂,他感到人类联合起来的力量很可怕,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让他们相互之间不能够沟通,这样,众人都分散了。那么在巴别塔之前,人类说着什么共同的语言?这是约翰·韦伯提出中文是“原始语言”的背景。正因如此,《中国对英国文艺复兴文学的影响》(The Chinese Impact upon English Renaissance Literature)一书的作者Mingjun Lu指出,韦伯论证中文是原始语言,其实想要解决的不是语言学问题,更像是要解决圣经的历史问题。上海交通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中心讲师陈怡在她的《约翰·韦伯汉语观初论》当中提到,17世纪关于中国的报道和关于中国语言独特性的介绍逐渐引起了欧洲人的关注,与此同时,寻找原始语言的学者们也在猜测汉语是否就是原始语言,将这一猜测表达得最为彻底的就是韦伯和他的《历史论文》。
17世纪,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他们的传教政策要求他们主动适应中国文化,因此他们对汉语的学习具有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成就。约翰·韦伯没有去过中国,没有接触过汉语,虽然不能像万济国(Francisco Varo)、马若瑟等专门撰写汉语语法的人那样,给汉语归纳出相对科学的语言学框架,但是他也通过传教士著述当中介绍的汉语发音、词汇和语法的特征和规律,总结出了自己对汉语的认识。

利玛窦等人编写的《葡汉辞典》手稿
在他看来,在一方面,汉字具有直接表意能力,在几千年当中变化很小,韦伯也据此相信,汉语保持了古老的纯洁性,保存着原始语言的精华。另一方面,他认为中国的文字也不仅是中国人所独有,他意识到日本人、朝鲜人、苏门答腊人、交趾支那王国还有其他一些邻国和岛国的人也都认识汉字,汉字具有强大的普适性。陈怡指出,这其实是当时传教士和西方人普遍的对中国文字的误解,不仅误解了汉语的时代差异,也夸大了汉字在东亚文化圈当中的作用。
此外,韦伯还觉得中国人的语言有一种其他语言无法媲美的简易性。他指出,汉语没有各种各样的词尾变化、动词变化,没有数、性、态、时等麻烦的语法细节,而是彻底从这些错综复杂的东西中得以解脱,除了自然的启示赐予的,再不使用别的规则。“所以,他们的语言就像天然语言应有的那样平白、容易。”他看到,虽然从信仰的角度来看,中国人是最少接受到神的启示的,可是从语言的角度来看,中国人是所有民族当中“最多或唯一受神启指导的”。
汉学家“热情洋溢的理论”,
是”狂野而奇特的献礼”
约翰·韦伯认为汉语是世界语言之母的说法,遭到了同时代学者的嘲笑——1677年,马修·黑尔爵士(Sir Matthew Hale)在他发表的《从自然的角度对人类最初的起源所作的考察》(The Primitive Origination of Mankind, Considered and Examined According to the Light of Nature)一文当中,批评了约翰·韦伯的理论,认为其完全是建立在推测出来的论据之上。但是,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在接触了约翰·韦伯的观点之后,也对作为原始语言的中文开始感兴趣。

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
莱布尼茨在青年时代就憧憬有一种真正的哲学文字,在与欧洲东方学家、在华传教士的通信中,他多次提到约翰·韦伯认为汉语就是原始语言的观点。莱布尼茨后来还在自己的语言学论文中称,“如果上帝真教过人类以语言的话,应该是类似于中文那样的东西。”他对汉语的痴迷在同一时代也有知音:1722年,法国科学院院士、当时欧洲学术界的重要学者埃狄纳·傅尔蒙(Etienne Fourmout)在《历史和科学艺术通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的演讲,他说,中文里,每件事物都有一个特定的字符,字符结构的优美组合是哲学和几何学的组合,在任何其他语言当中都不存在如此多的类别性。因而他也断言,中文字符的机构是人类最伟大的杰作,没有任何一个物质系统可以达成这样完美无缺的程度。
在1730年,崇拜傅尔蒙的德国汉学家巴耶尔出版了两卷本《汉语博览》(Museum Sinicum)。巴耶尔从19岁开始,每天都在想着怎么能够进入到神秘的汉语世界当中。“如果有朝一日我能够在这一领域取得小小的成就,我便会骄傲地认为自己是上帝之孙、万王之王。”他下定决心要把所有与汉语相关的研究都收集起来,把它们编辑成为一本“类似字典或是介绍中国语言文学规则的入门读物”。
巴耶尔的《汉语博览》在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眼中是”一份狂野而奇特的献礼”。他看到,在这本书中,除了约翰·韦伯以外,还有不少会令今天的读者感到惊奇的说法——荷兰学者佛休斯(Issac Vossius)曾经盛赞中国的艺术和科学是世界之最,声称多么希望“自己是生在中国而不是世界上的其他地方”;
法国学者菲利普·马松(Philippe Masson)“证明”中文其实是一种古老的希伯来语,他认为,《旧约》当中许多棘手的语言问题都可以从中文当中找到答案——例如,上帝哺育沙漠之中的以色列子民的“吗哪”(Manna),就是中文当中的“馒头”的变音;瑞典学者奥劳斯·鲁德贝克(Olaus Rudbeck)则认为,中文是最接近哥特语的语言。史景迁说,巴耶尔将这些“古怪晦涩、浩如烟海”的内容都综合起来,即使他们的理论“模糊肤浅”,或者让人“如坠云雾”,也不应该被轻易否决掉,因为在这些热情洋溢的理论背后,有先驱的“睿智和勤勉”。
结论都荒谬,评价为何不同?
对于当时中国语言学研究当中哪怕是最荒谬的结论,巴耶尔也不愿意完全否定——无论是认为中文是世界所有语言的原始语言的约翰·韦伯,还是用乐理知识构造中文声调的穆勒(Andreas Müller)——因为他看到这些人的学术生涯都展现出了“尝试理解中文的执着热情和令人尊敬的创造力”。史景迁也认为,在汉学研究先辈当中,有对喜爱的事物评价过高的情况,也会有过度的热情和轻率的折中,但是他依然喜欢思考这样的研究。
与巴耶尔、史景迁等汉学家对前辈学者荒谬结论的宽容相比,翟桂鋆的“英语起源于中国”遭到的质疑堪称残酷,不仅被网友“群嘲”,被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向宝云在研究生院2019级新生开学典礼上用作“投机取巧,哗众取宠”的负面学术研究案例,甚至还被《人民日报》点名批评。《人民日报》称,很难想象,在林则徐、魏源等人“开眼看世界”近两个世纪后,在全球文化深度互动对话的今天,仍有人把中国作为其他文明的起源,把世界文明成就附会于中国的创造,“这折射着一种盲目的自大。”
有评论者将杜钢建、翟桂鋆等人的学术流派称为“学术战狼”,其代表作品是杜钢建的著作《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这本书论证了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埃及人、日耳曼人全部都来自中国。公众号“短史记”的评论文章 称,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希望通过证伪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来强调中国文明的古老与先进,将自己的所谓“研究结论”与“提升民族自信”之类的大词捆绑在一起。

《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
杜钢建
光明出版社 2017-12
与这样的做法相比,或许,350年前,韦伯等欧洲汉学家对世界的热情和创造力,就显得更加笨拙和可爱一些。作为早期业余汉学家,韦伯对以前传教士零散的汉语知识进行了概括,并且对汉语作出了阐释。虽然他的论据夹杂着想象和虚构,得出的结论可能有些令人好笑,但是陈怡看到,韦伯是第一个通过长达一本书的系统试图为汉语在世界语言当中确立位置的人。在欧洲早期汉学家那些热情而荒谬的作品被世人逐渐遗忘之后,学术上更加成熟的职业汉学家才逐渐涌现出来。
“在巴别塔之前,人类说着什么共同的语言?”这样的疑问显示出,在韦伯的时代,《圣经》为核心的宗教文化依然占据着统治地位。但是,他的著作无疑也显示出:随着新航线的开辟,西方人的文明观念正在经历更新,他们开始主动了解欧洲文明之外的其他文明。这些不仅体现在研究中国语言的爱好者身上,也体现在其他领域——歌德和伏尔泰曾经受到《好逑传》《赵氏孤儿》等影响;创立“三权分立”学说的孟德斯鸠对中国也非常关注。由于启蒙时代与中西初识时期在时间上大致吻合,在教权衰落与理性精神兴起的过程当中,中国文化的西传和早期汉学也由此参与了17、18世纪欧洲社会大转型、思想大变革。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韦伯在西方早期汉语研究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逝去的童话:早期德国汉学家巴耶尔的中国猜想》张国刚 《中国文化》第37期
《约翰·韦伯汉语观初论——走近一部17世纪的汉语论著<论中华帝国的语言是原始语言的可能性>》陈怡 《国际汉学》2009年01期
《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美]史景迁 理想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年3月
The Chinese Impact upon English Renaissance Literature, Mingjun Lu, Routledge 2015-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