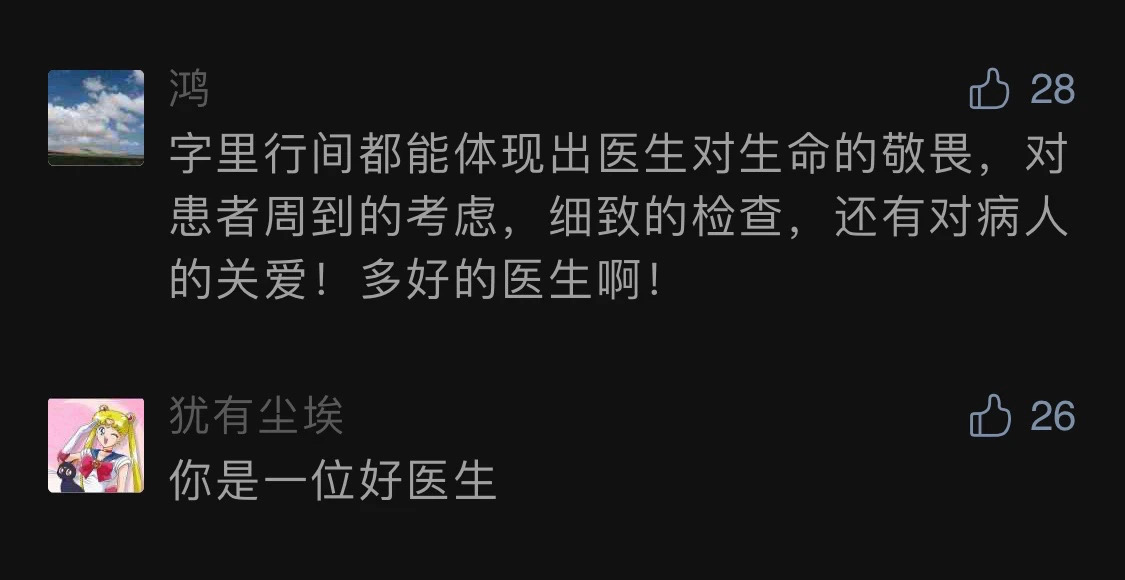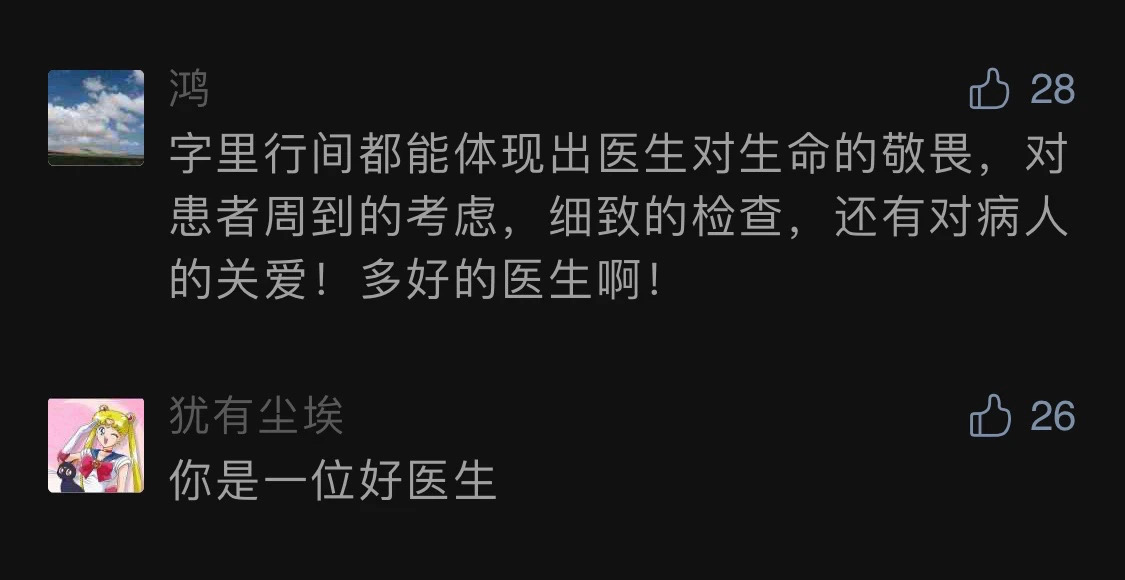说不紧张是假的,即使是作为医生,面对亲人在手术室里,我也只能是盯着钟表,站在老婆的手术门外,我什么也做不了。

他在去年4月份来全民故事计划讲述了他的第一个故事:《癌症病房里的谐星》。
而在那个故事刊发前,也是在去年的3月份,身为肿瘤科医生的他,妻子却患了癌,他说自己也许是一位好医生,但他不是一个好丈夫。
我和老婆相识于大学时期,铁杆异地恋,900多公里苦恋5年多结婚,几年来往返于石家庄和西安的火车票被她积攒起来做了一本纪念册,而大学毕业后她成了一名光荣的列车乘务员,这件事经常被她自己笑称为“久病成医”。
婚后,我们很快迎来了可爱的儿子,享受了短暂的天伦之乐之后,生活又陷入无尽的奔波。一条京广线被她跑得烂熟于心,高速行驶的列车一闪而过时,她可以通过观察一座无名石桥告知旅客下一站还有几分钟到达。
只是昼夜的颠倒、透支的体力,还有车厢连接处从未熄灭过的二手烟,让她几乎每个月都会发一次烧。然而,老婆与我这个医生结婚,从来没有什么所谓的“近水楼台”,往往她生病的时候,我常常是在另一个城市照顾别人。
孩子过完百天,我便回到北京工作,小生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也包括无穷无尽的鸡毛蒜皮和刀光剑影,以至于有一段时间我看到家里来的电话就会心律不齐。
小生命人人都视如珍宝,这也让生活的千头万绪在这小家伙身上系上了死结。异地夫妻本就难做,更何况我这个身在异乡的医生丈夫。
医生是那种经常需要放下碗筷冲回医院抢救病人的职业,沾满鲜血的双手,电话都接不了,更不要提照顾家庭。科室的领导也能体谅我的不易,占用周末的工作再也不安排给我,当然,有时不加担子也就意味着不给机会。
在一次视频吵架后,老婆讲:“我的工作本来就辛苦,你还总气我,我早晚得癌。”
2019年3月,老婆的单位组织体检,超声显示她的甲状腺和肝脏分别有一块可疑肿物,肝脏上的那块甚至达到5公分。年轻人患癌更加凶险,预后往往很差,这次体检让我忧心忡忡,在我的要求下,老婆决定请假去医院复查。
因为在外地医院上班,请假不易,我和老婆商量,等她做完检查我再请假回家。
出于经验,我告诉她,肝脏的那个肿物要查“增强核磁”,甲状腺的肿物要复查B超,去了医院就只需挂普通号,普通号相对人少,做了检查再带片子去挂专家号,这样省时省力。
“记住,做增强核磁前,早晨别吃饭,有人注射造影剂后容易吐,把机器弄脏了不好收拾。”检查前夜,我不忘职业病式地提醒她。
“你就不担心我对造影剂过敏,最后万一挂在台子上啊?”老婆看样子并不领情。
说不担心是假的,想着老婆身上的两个占位,第二天工作时,我的效率很差。
“我肝上的那个是血管瘤,5.1公分,这可怎么办啊?对了,人家医生说了,我这是被你气的。”老婆说。听到这里,我竟长舒一口气,“血管瘤”名字是瘤但并不是恶性,只是一种血管的迂曲,生长缓慢,并无大碍。但她这个血管瘤体积巨大,已经到需要治疗的程度。
“甲状腺左叶低回声结节伴少量钙化,T什么分级4a类。”超声诊断十分专业,以至于她阅读有些困难,但这个分级引起了我的注意。
“4a类的意思是,你这个肿块有5%到10%的几率是恶性的。”顿了顿,我说:“来北京吧,我给你找个专家。”说到这时,我其实有些后悔,病人在等待检查报告时就好像等待一张判决书一样,我不该让她独自面对这种残酷。
“才10%啊?赌一下?马上春运了,不好请假呀。”老婆受我平日的影响,知道甲状腺癌属于并不十分恶性的癌种,语气还比较轻松。
癌分许多种,比如腺癌、鳞癌等等,甲状腺癌再细分,绝大部分都是预后很好的乳头状癌,有不少因其他疾病死亡的患者尸检时发现同时伴发着甲状腺癌,许多媒体上常见的抗癌明星,大部分也是这种疾病的患者。但甲状腺癌也有十分凶险的类型,例如髓样癌、未分化癌等等,所以甲状腺上的肿块不能掉以轻心。
我的态度坚决,老婆听了我的话,乘高铁来到北京,火车上她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作为一名乘客被人服务的感觉真好。我告诉她,作为一名疑似肿瘤患者,她的心态真不错。
辗转到我所在的医院,我找到超声科大拿,老师给的意见是“4b”,意味着恶性的几率更进一步,建议直接做超声引导下的穿刺取病理。
从诊室出来,老婆也有些呆住了,问我:“穿刺?疼吗?如果真的是癌,正反都要切,我不就白挨了一针吗,手术还得再受一次罪。”
日常工作中,这个问题每次都问得我不胜其烦,我一般都告诉患者:不疼能看病吗?良药还苦口呢,直接手术切出来不是癌不就亏大了吗?其实这涉及一个医疗程序的问题,“术前穿刺”用来确诊,给了做手术充分的理由。
当下的医患关系如此紧张,这可以规避一些医疗风险。可即便在工作中我再斩钉截铁,面对自己的老婆时,我还是犯了嘀咕。
为此,我又咨询了超声科的那位专家。“老师,我是本院的,这是我老婆,依您的经验判断,这个肿块是恶性的可能到底多大呢?”
那天晚上,我与老婆谈了很久,把所有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包括甲状腺癌良好的预后、大概率是癌、是否放弃穿刺等等。
最终我们决定,跳过穿刺确诊的环节,直接手术,并且选择我所在的医院,这样我可以少请几天假,也可以亲自照顾她。用老婆的话讲就是“指使别人我不好意思,你比较顺手”。
如果不是在我所在的医院,或者如果我不是医生,或是我在医生面前表现出丝毫犹豫,大多外科医生是不会直接做手术的。毕竟现在恶劣的医疗环境下,没有医生愿意把自己置于做完手术、走上被告席的境地。放弃穿刺意味着我相信那位超声科医生的判断,并且愿意承担他判断失误的风险,毕竟医生是人不是神。
之后我们分头行动,老婆回家办异地医保转诊、联系保险公司、收拾行李;我在医院联系住院科室,并且找到了一位院内口碑非常好的手术医生。这位医生没有名气,有的专家一号难求,而他却是那种隐藏在普通诊室里的专家,这样的医生在医院有不少,原因大多是因为没有像样的科研文章,职称上不去。
我向那位老师说明不想做穿刺直接做手术的想法,并且表示所有风险我们自己承担,即便不是癌,我们也认,也愿意签字确认。
老师看了看我,笑着说:“给同行看病真是省舌头。既然你都决定了,那就来吧。”
甲状腺癌手术早已普及,难度不大,省医保拒绝开出转诊证明,并认为省内的水平完全可以胜任这个手术,想去北京只能自费。医保说的也没错,但老婆又不舍得自费,表示保险赔的钱一分不能少,得留着给孩子报课外班用。
既然决定不在我所在的医院进行手术,接下来挑选医院,还是有些讲究的。
石家庄的省级医院有好几家,但名气最大的医院并不一定是最合适的,挑医院不如挑科室,挑科室不如挑医生。医学是一门经验学科,一名外科医生的技术水平绝对是在手术台上一刀一刀地练出来的,“无他,惟手熟尔”。
经过多方了解,我们通过挂号找到了专家田主任,住进了耳鼻喉科。
住院的前几天,老婆老是拿着手机在网上搜自己的病,“你看,这人做完手术之后嗓子坏了,声音变嘶哑了,我不会也这样吧?”
老婆艺术细胞充足,上学时就经常参加各种晚会,还一度想参加好声音的海选。
我本想去安慰她,但还是严肃地说:“这种可能是有的。谁也避免不了。”
我们把3岁的儿子送到奶奶家里,告诉他:爸爸妈妈最近有点事,可能以后几天不见人。
从家里出来,我们去了一家KTV,我要让老婆唱个痛快,并用手机录了下来。
那天晚上,老婆在KTV发挥完美,“等下一个天亮,去上次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吗。”唱着唱着哭了起来,我也泪眼婆娑地对她说:“老婆,你得的是甲状腺癌,不是胰腺癌,不用这样。”
住院那天,我们起得很早,带上一个小拉杆箱便出发了,像是要出一趟远门。
每个医院都有一套自己的工作流程,即使像我这样每天在医院工作十几个小时的医生都被溜得七荤八素,在管床医生的指挥下,什么门诊楼、住院楼被我上上下下跑来跑去。像学生交作业一样,我将这些跑来跑去的成果交到管床医生的手中。这位医生姓刘,是田主任正在读研三的学生。我将资料放下后,转身要走。
“诶,诶,等一下。你不看看你老婆各项检查的结果吗?”刘医生赶忙叫住我。
刘医生将各项术前检查结果一一看完,又完善了病历,交待了手术可能出现的风险,我又签了三、四个字。最后,刘医生满脸疑惑地问:“病理呢?你们没做穿刺?”
我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对刘医生叙述一遍,刘医生说:“不行,没穿刺不能手术。”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不为什么,这不符合医疗程序。
我说:“要不您给田主任打个电话请示一下。我们的决定就是不穿刺直接手术,一切后果我们自己来承担,我可以给您签免责书。”
稍显激烈的讨论最后,以我签免责书结束,刘医生看我的眼神有些异样,我能感觉出来,估计她开始怀疑我是同行。我不方便透露,在学科高度细化的今天,同为医生也是隔行如隔山,一知半解的同行有时更加难以沟通。
这位阿姨60出头,热心肠、爱聊天,旁边坐着的是她的爱人。
进门时,阿姨正在说话:“小姑娘啊,告诉你,咱们这个病就是太爱操心。你看你才30岁,旁边病房还有个31的,也是个爱操心的命啊,自己干吧嫌累,让别人干吧又不放心,每天就是操不完的心,你说咱们不得病谁得病啊。”
我本以为老婆会觉得这位阿姨聒噪,悄悄问她要不要换个安静一些的病房,不料老婆却认真拒绝道:“我觉得我跟阿姨特投缘,她句句都说到我心坎里了。你要是能干点,我也得不了这个病,她说的特别对。都怪你。”
原来老夫妻俩都是我们这个城市热电厂的退休职工,这次是阿姨的甲状腺第二次手术,10年前切了左侧甲状腺,如今右侧复发,用她的话说是“二进宫”“受二茬罪”,所以她十分建议我老婆把双侧一股脑全切了,“一了百了”。
两人互相倾诉工作、生活中的各种不如意,看人看世界的观点竟十分相似,“爱操心”被她们定义为甲状腺癌最主要的病因。
当然,她们边聊边分别指示大叔和我干这干那,边干边被她俩吐槽。
现代医学认为,肿瘤的发生主要是由先天基因状态和后天环境因素共同导致。“爱操心”究竟是不是病因需要大量研究和统计来支撑。
甲状腺癌发病的男女比例大约是1比3,病房里聚集着很多30到50岁的女性,性格里居然有诸多相似之处,于是患者间的关系异常和谐。走廊里,老婆看到颈部缠绷带的女性就会凑上前去,一番眼神试探后,上前接头:“疼吗?”
刚做完手术的患者还不能说话,有的点头,有的摇头,无论是哪个动作都可以算上接头成功,等到早些手术的人可以张口时,就会操着嘶哑的声音到床边传授经验。
那天,老婆怀着忐忑的心情跟随两位麻醉师进了手术室。手术室大门关上的一瞬间,我们对视一眼,我能看出她的恐惧。
老婆是上午的第一台手术,七点一刻,我俩准备完毕,家人朋友还堵在路上。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手术室的大门无论什么原因被打开,都会有一众家属上前观望。
九点半。不知哪里发出的广播声叫了我老婆的名字,让家属到谈话区。
大家纷纷朝我看来,我告诉大家不要紧张,应该是术中病理的结果出来了。
说不紧张是假的,即使是作为医生,面对亲人在手术室里,我也只能是盯着钟表,站在老婆的手术门外,我什么也做不了。
面对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我也在反思这几年自己在事业与家庭之间的失衡。
现在回想起来,老婆生病半年前,就对我讲过她的脖子有点粗,我没有在意,竟然上手查查体都没做过。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在病人身上寻找哪里长了个结节,哪里长了个疙瘩,居然到自己老婆这儿竟疏忽大意到如此地步。
等田主任手里拿着几个标本袋,对我说:“你赌对了,确实是癌,乳头状的。”
我的心情复杂,谈不上喜悦,毕竟是癌,这是一场没有胜利的赌局。
田主任接着说:“清扫出4个淋巴结,看形态疑似转移,结论还要看后面的病理。现在看来另一侧的甲状腺保不住了,建议全切。”
做完全麻手术的老婆还闭着双眼,呼吸微弱,蓝色的头套配上绿色的被子,颈部缠着的绷带让几位老人哭了出来,我也跟着心酸。
跟随麻醉师同老婆回到病房,她已经有了简单反应,呼唤她的名字可以微微点头,竟然还能微抬手臂迎来送往。很多好友对着老婆喊:“别睡,别睡。”其实没必要,只要患者呼吸正常,想睡就睡会儿,毕竟手术对人体来说是一项非常大的刺激,体力消耗很大,待麻醉药物代谢完毕,她自然就会恢复正常的作息。
等我把各位亲朋温柔坚定地送走后,病房中只留下我和岳母照顾。不一会儿,隔壁床阿姨的手术结束也被推了进来。
病房里一瞬间变得安静祥和,像守护两个婴儿般期待着她们平安成长,这可能是病人家属最虔诚的时刻。
岳母看我熬了3个晚上,让我回家休息。为了术后的妥善照顾,我也没有逞强。
甲状腺手术的创伤相对较小,老婆恢复得也很快,3天后,我们就顺利出院了。
回家的路上,老婆拿出手机,开始计算保险赔付的数额,脸上居然露出了笑容。
“可以给儿子报个英语班,报个思维课,再学个游泳,可以买架钢琴了。我告诉你,
这钱是我用脖子换来的,你可别惦记。”我的心里满是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