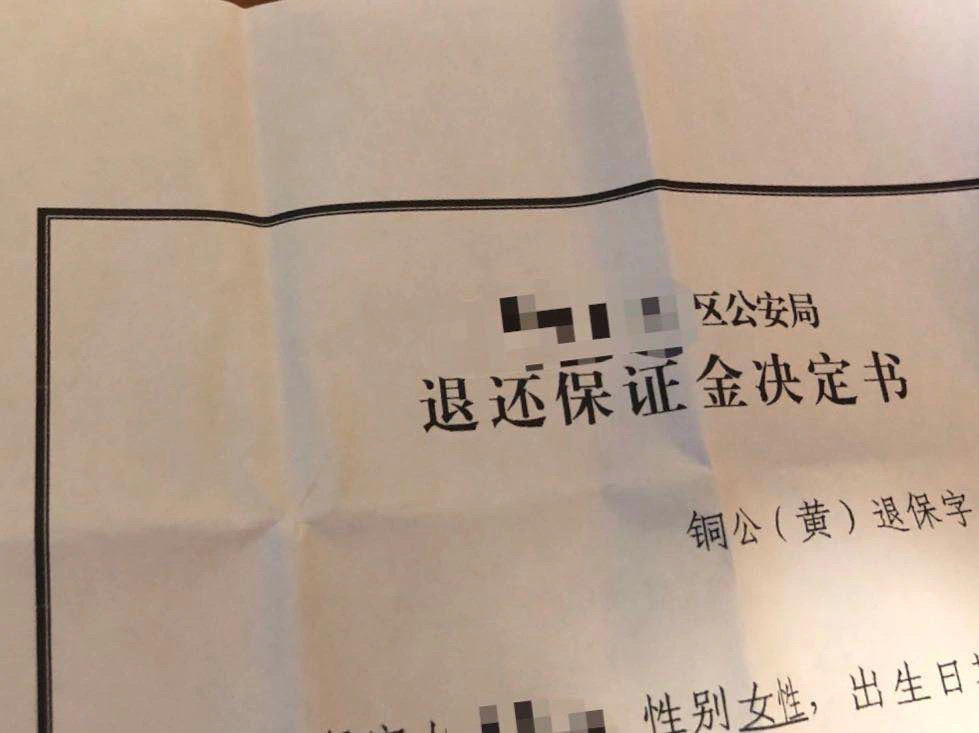穿过一道又一道铁门后,我被领到504监室,狱警拎着一大串钥匙打开监室门,我战战兢兢地挪了进去,我开始疯狂地想家。

— 这是全民故事计划的第509个故事 —
下午五点,监室广播的开饭信号响起,我跟号房的狱友们挺直腰板,各自拿出存在盒子里的萝卜干(每天早餐发,吃不完可以存起来)齐刷刷地面朝铺板坐齐,等待“小红帽”(监室内提供生活服务的嫌疑人)分发饭盒。
统计馒头数量时,我要了两个,她们笑着说我最近的胃口不错,应该很快就可以出去了。我尴尬地陪着笑,心里却难受得想哭,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监室门,幻想着家人来接我。
半个月了,自从上个月会见律师后,我总是频繁地梦见哥哥来接我回家——等待家人接我回家,成了我在这里活下去的动力。
一周四次夜班站岗,使得原本睡眠质量就很差的我,变得更加神经衰弱,每次两个小时的站岗都漫长得像一个世纪。
站岗时要必须站直,不能随意走动,夏天里的蚊子又多又毒,不到两天,我的脚踝便长满了蚊子的咬痕。
由于抵抗力低下、长时间的营养不良,兴许还有点水土不服,一开始站夜岗的时候,我曾发烧呕吐,
甚至两次晕过去,着实把同监室的阿姨姐姐们吓一跳。
漫长而艰苦的日子里,一千多公里外的亲人成了我的精神寄托。
深夜,我总是控制不住地思念父母、哥哥姐姐以及年幼的外甥。
我经常想,如果过去我不那么叛逆,乖乖听话,按部就班地读书,现在也才刚刚大学毕业,怎么会沦为阶下囚呢。
想到这里,我对自己曾经与家人的针锋相对后悔不已。
啃完一个馒头后,我开始低头喝着南瓜汤,眼看着天快黑了,心里特别绝望。明天就是周末了,今天出不去,
那就至少要到下周一才可以出去。难道,真的如她们所说,要待够37天才可以走吗?还是,根本就走不出去了?
“余叡徨,释放!”管教的声音打破了沉寂,整个监室突然沸腾起来:“快,拿上你的钱卡赶紧走!”
“我就说你可以走的吧!”
在狱友的祝福声中,我头也不回地走出监室。走出看守所大门前,我看到墙上的“珍惜自由”几个大字,心里五味杂陈。
我叫余叡徨,90后,出生在广东沿海的一个农村,在家里排行老小,家境不错。
从小,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在所有人看来,我会按部就班考上好大学,拥有体面的工作。
然而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原本在镇上有着稳定工作的父亲被迫下岗,为了养活妻儿,他背井离乡到省会城市打工,
原本计划将我送到私立重点中学的计划也因此搁浅。而我的母亲,除了照顾我的起居,基本不会过问我的学习。
青春期、纪律涣散的学校、突然自由起来的我,交了几个不爱学习、整天逃课泡吧的朋友。
经历了第一次逃课后,一直贴着乖乖女标签的我,尝到了放纵的滋味,开始无心学业。
父亲有时候打电话回家问起我的学习成绩,我总是敷衍搪塞过去。
最终,我浑浑噩噩地过完了初中三年,只考上了一所普高。
在我初中毕业时,哥哥姐姐们已经陆续参加工作,父亲的压力骤减,也是为了方便管教我,
他决定回家乡,做一份收入低微的工作。
高中,我依旧混着日子,学习成绩惨不忍睹,父亲看着曾经被称之为“别人家的孩子”的幺女变得叛逆乖张,心里落差很大,他试图把我拉回正轨,软硬兼施地督促我学习,然而已经自由惯了的我,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被管束。
我开始变本加厉地逃课玩闹,父女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家里经常是父亲的谩骂声、母亲的哭泣声以及我愤怒的摔门声。渐渐的,我跟父亲之间筑起了一堵厚厚的墙。
2014年夏天,高考一塌糊涂的我连志愿都没有报,只身来到深圳打工。
自命不凡的我,认为不读书也可以闯出自己的一片天。短短一个月,我每天在仓库里挥汗如雨,也由此深刻体会到什么叫“廉价劳动力”。
终于到了休息日,我一个人待在简陋的出租屋里吃着泡面,对生活充满了失望。我开始想念家里舒适的席梦思大床、每日荤素搭配的三餐,以及每晚睡前的新鲜羊奶。
高中老师得知我回家,隔三差五地劝我继续读书,那时候正是专科补录的时间,他希望我参加补录,去学校学点东西。我坚决拒绝,直到补录时间过去,他突发奇想地劝说我复读一年,甚至用自己曾经的复读经历来鼓励我。
我依旧谢绝他的好意,表示再过几天会出门找工作。但实际上,我对未来毫无规划。
赋闲在家的日子,我依靠网络度日,每天追剧网聊,时间久了,也觉得乏味。时间很快到8月底,一些同学在社交空间分享即将去上大学的消息,也有一些已经进入各行各业打拼。
心高气傲的我,渐渐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坚决要参加工作的决心也开始动摇了。
后来有一天,一个关系不错的高中同学给我打电话,跟我说她明天就要去新的学校复读了,询问我对以后的打算,我说还没有考虑。挂完电话,我在QQ上询问了几个中学好友,他们一致认定,我应该考虑一下复读。
8月31号,在高中老师的鼓励下,我向父亲提出复读的想法。没想到,一向希望我上大学的他,这次居然直接拒绝了我。
当着老师的面,父亲指责我不过是借口复读想去学校再混一年。他的一句话像针尖般狠狠地刺伤了我敏感的神经,也加剧了我对他的敌意。三天后,我收拾行囊再次外出打工,电话里,我向哥姐指责父亲不舍得为我花钱。
初涉职场,我断断续续经历了培训、游戏等行业,收入勉强可以养活自己。
当然,家人都没把我当初的一时气话放在心上,我会在过年的时候回家待上几天,只是跟父母的关系依旧冷淡。
2017年,姐姐的婚礼在深圳举行,临近过年,我辞去令我身心俱疲的销售工作,父母及老家的亲戚来参加婚礼,我忙前忙后地招待。
父亲听闻我辞职,来了后就训斥我一顿,说我读书时逃课,工作了动不动就辞职,简直就是烂泥扶不上墙。我指责他从来不为我的未来考虑,这再次加剧了我们之间关系的恶化。
到了2018年下旬,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得风生水起,在这样的趋势下,我也加入了一个规模不大的互金公司,任职资产管理岗。
这是一家小型的网络贷款公司,公司员工加上老板不过二十来人,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向用户发放贷款,而我入职的岗位,属于资产管理部的“提醒专员”,主要工作是通过电话提醒到期以及刚刚逾期一两天的用户及时还款。
小公司的人际关系比较简单,由于我入职时公司已经积累一批信用良好的老客户,所以逾期客户并不多,我的工作也比较轻松。
大部分客户在接到我的提醒电话后会表示抱歉,并在一两个小时内自行还款,偶有失联的或者恶语相向的,我会选择放弃,因为逾期时间长了,会有其他专门的同事去负责。
后来我才知道,公司一个D省客户恶意逾期,甚至扬言:“凭本事借的钱不需要还”,在与催款人员争吵后,以“被诈骗”为由举报了公司。
2019年7月3号,D省警方以涉嫌诈骗为由将我们全体员工拷上手铐带至派出所,简单地做了笔录后,我们被关在拘留室里发呆。
4号凌晨两点,警方要求我们提供家属的联系方式,本人签名确认后,警方将拘留三天的通知书寄给了家属。我想,这次我真的完了。
当晚,我们一行人就被押上火车前往D省。第一次坐二十几个小时的长途火车,只有面包和白开水充饥,我刚治好的尿路感染复发了。
由于我频频要求上厕所,一个年轻警察开始恐吓我,倒是一个年长的警官笑着问我是不是生病了,他关怀的语气让我开始想念父亲。
抵达D省派出所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我们被连夜审讯,主要是说清自己在公司负责的工作。我满身疲倦地做完笔录后,我们被男女分开关在一个墙上都是泡沫垫的小房间里。
迷迷糊糊之中,天亮了,我吃过一个冷硬的馒头后,警方又将我们送往医院体检,并各自在被拘留30天的通知书上面签了名字。
进看守所的第一天,我失眠了,掰着手指头数着日子,五天了,家里没人找我吗?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难道他们不想理我了?
后来我才知道,拘留通知书寄到家的那天,父亲一边看一边发抖,最后躲到房间里嚎啕大哭。不知道哭了多久,冷静下来的他给我的叔伯兄弟们打电话商量。有人提出也许可以找找渠道花钱把我弄出来,至少要花几十万。
没想到父亲当时斩钉截铁地说:“有这个可能吗?有的话我马上去筹钱。”
最后是一个当过兵的表哥劝阻了他,表哥说:这种花钱弄人的事情可能性太小了,不如请个律师去会见,多打点生活费,让妹妹在里面过得好一点。父亲才稍稍冷静下来。
6号那天,经历了一系列的常规入所体检后,我们十来个女生被押送至D省某看守所。
穿过一道又一道铁门后,我被领到504监室,狱警拎着一大串钥匙打开监室门,我战战兢兢地挪了进去,我开始疯狂地想家。
那天是星期六,监室内的人齐刷刷地坐在板凳上看电视,这时,每双眼睛注视着我,还没来得及害怕,两个戴着小红帽的阿姨就对我说:“把衣服脱了。”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很多电视剧里牢头狱霸欺压女犯的场景,竟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睛。
坐在我后面的是一位30岁左右的姐姐,轻声告诉我:“进来就别想那么多,守好规矩,有什么事找小红帽或者找我。”
我没有转身,背对着她点点头,瞬间又哭了,我想我姐姐了。
傍晚5点,监室的开饭信号响起,给我裸检的两个红帽起身,其中一个走到洗手池那边拿饭盒开始发放,另一个走到监室门边面向我们招手说道:“统计馒头了!吃两个的举手!”
随后,一辆造型类似于马路上的垃圾车在监室门口停了下来,两个红帽颇有礼貌地向师傅问好,菜汤通过门下方的小口子顺着特殊的管子流进提前准备好的菜桶,接着,坐在后排一个阿姨面带微笑地起身开始给大家打菜。
打到我这里时,她一下子舀了一大勺,我略带歉意地告诉她:“我吃不了这么多。”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直接去给后面的人打汤了。
后来,这个阿姨成了我被拘留期间最好的朋友,她叫张修沁,在这里已经待了很久。
看守所里的生活极其枯燥,没想到的是,这一个月是我有史以来过得最规律的一个月。
严格的作息,苛刻的卫生标准,几天下来,我浑身腰酸背痛。独在异乡,深陷囹圄,我常常睡不着,有时候刚睡下,又被喊起来值夜班。
失眠时,我常常闭着眼睛回忆过去,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错的。
一次,张修沁半夜起来上厕所,看到我没睡,就压低声音与我聊天。
她告诉我,她与丈夫白手起家在H省拥有一份家业,后来他们收购了一家有问题的公司,导致夫妻俩双双被抓。她有一个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女儿,所以第一次见我便心生怜惜。
见我心事重重,她问起我的情况,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值班员就催促我们赶紧睡觉。后来,我失眠的时候,就跟她互诉衷肠。
37天的日期,是她告诉我的。她在得知我的情况后,非常肯定地说,等30天的调查期过后,再就是7天的等待期结束,我就可以回家。
她的一番话让我重新燃起对生活的信心,我开始尽量多吃点饭,睡眠质量也稍有好转。人在有希望的时候,日子会过得快一些,不知不觉,日子到了第30天,在经历一系列的信息核实后,办案人员将我们从看守所领了出去。
真的是哥哥,我日思夜想的家人,看清他时,我控制不住地大哭着奔向他。
我这才注意到,六个人当中,只有我一个人有亲属过来接。
哥哥打了车,送我到附近的酒店,从包里掏出一套新衣服对我说:“这是姐姐给你买的衣服,先去洗个澡,一会儿哥带你去吃海底捞。”
我拿着衣服进了浴室,忍不住用鼻子嗅了嗅,痛痛快快地把全身上下洗了好几遍。
从浴室走出来时,我看到哥哥正在给表哥打电话告知我的情况。随后,哥哥打开微信,让我跟家人逐一视频,当我看着哭得稀里哗啦的父亲,又一次控制不住地泪流满面。哥哥见状找了个理由挂了视频,拉着我出去吃饭。
回到家,迎接我的是父亲亲自准备的一桌菜,等我洗过手上桌,父亲颤抖着双手往我碗里夹了一块卤肉,我鼻子一酸,不管自己走到什么地方,他一直都惦记着我最爱吃的东西。
哥哥开了一瓶红酒,家人们碰了杯,彼此默契地吃着菜,没有人去提最近发生的事。
回家的第一个晚上,我睡得并不踏实,半夜醒来的时候,总以为是轮班的人提醒我排夜岗。像是一种后遗症,那种感觉很磨人。
父亲拿着剥了壳的鸡蛋往我的手里塞:鸡蛋怎么不吃?我想起在监室每天早餐分发的一个鸡蛋,以及关心我的几个大姐经常塞给我的鸡蛋(看守所里,鸡蛋是限量补充营养的食物),说实话,我现在看到白煮蛋就烦躁。
回来后的日子,父亲对我的态度变得有点过分紧张,在家睡觉时,我没有关房门的习惯,恍惚醒来,看到他蹑手蹑脚地在房门处看着我。
整整一个月,我的面黄肌瘦令父亲不安,于是他变着法子给我炖各种汤。我跟他表示自己吃不下,不要再特地开小灶,然而父母对我的话置之不理,依旧给我加餐,并且乐此不疲。
面对他们的过度呵护,我很难接受,甚至时常联想到在看守所里的生活,有些恍惚。
她告诉我,我被抓的那一个月,父亲常常半夜跑到我房间,一个人偷偷地哭。原本是个话唠的他,竟也变成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父亲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得知我快回来,他又时常拉着母亲和姐姐念叨我过去的事情。
那时我才听姐姐说,曾经的父亲希望我靠读书谋前程,后来反对我去复读,只是在新闻上看到很多不堪忍受压力寻死觅活的复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