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我来过两次。第一次是三十年前,1988年,阴冷的冬天,上海因为毛蚶污染,爆发甲肝。 我们一行人,恰恰那时从舟山乘船到上海,准备换乘回北京的火车,需要停留十二小时。第二次,是2017年,我们专门选了温和的秋天,投身到祖国最发达的城市观光。


我虽然对这个城市不熟悉,但平时周围有不少上海朋友。 上海人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不知起源于何时得罪了全中国人民,大家对上海人的印象都趋于一致且根深蒂固。上至影响力最大的央视春晚,下至普通老百姓的朋友圈,所有人都可以拿上海人开涮。在小品里,某个男性角色,如果衣着整洁,尖头皮鞋,油头粉面,上海口音,围裙加身,完美,肯定是个被讽刺挖苦的。

人物设计这事如果搁在几十年前,那更简单了,起个名字就完了——王沪生(《渴望》)。大家边追剧边骂,“一听这名字就不是好人”,“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编剧们卖力地为民间标签推波助澜。习惯于跟着宣传工具走的老百姓看完剧更是得出结论:生于沪的,必是渣男。

如果一个小团体里有新加入的成员,或公司同事,或广场舞队友,恰恰她又有一点点骄傲,有一点点时髦,喜欢把小账算清爽,原来的队员之间必心照不宣,彼此递个眼神就够了,“上海人嘛,你懂的。”更损的是,如果她不是上海人,“啊,不可能吧?”
近年来大家的道德水平提高了,时不常有人会出来反歧视,维护文艺作品里的“弱势团体”形象,比如残疾人,甚至非洲人。虽然上海人一直被树为“反派”,另眼相看,但没人替他们说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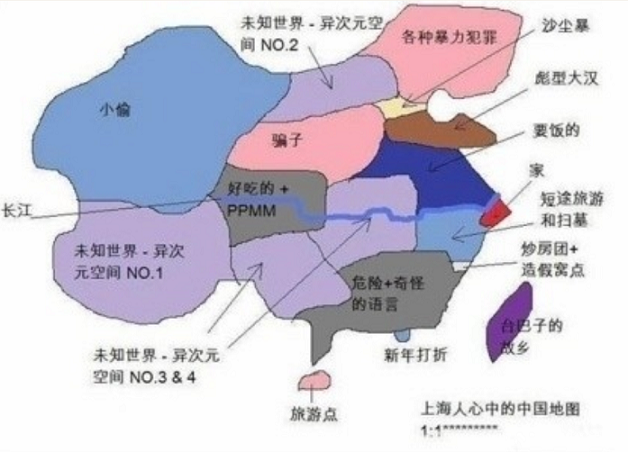
近年,以上海人为正面主角的电视剧里,我最喜欢的是《红色》。这个戏把抗日时期上海人在大是大非前的勇气和里弄过日子的市侩气融在一起,情节张弛有度,海味台词说起来像喜剧,蛮好听地伐。
《红色》剧评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里说:“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这个确实是。那时候谁家不追求永久、凤凰自行车和蝴蝶缝纫机?连圆珠笔都以上海的丰华牌为尊,我甚至不知道别的省份也有生产花露水和雪花膏的。
余的后半句是,“又都讨厌着上海人。”即使全国人民都讨厌上海人,上海人的涵养谁也比不了。我有朋友说,要是谁这么死命的黑北京,早被我们打死了......我相信他的话,如果有人黑河南,黑东北,黑新疆......估计下场也差不多。所以说我最佩服上海人的就是这点:心大。你爱说啥说啥,我该干啥干啥,不跟你一般见识。黑上海人,很安全。


据说上海人在吃上抠门,把钱都花在衣服上了,爱臭美;广州人则是反过来来。有个郭达演的小品《门里门外》,请人吃的上海小菜就是两条罐头小咸鱼,恨不得一根榨菜也能冲成一碗汤。还有过分的是,早餐连个粥都没有,开水泡饭!在我们北方人看来,这日子怎么寡淡成这样了,钱都干嘛去了。

在食品凭票供应的年代,偶尔大院食堂卖不要粮票的锅贴。逢到这种时候,我妈就赶紧拿着钢种锅去排队。即使不要粮票,钱也不富裕;尽量省着吃,每人两、三个,一家四口起码要买十个左右。旁边有两个谈恋爱的小青工,买好了,站在那儿吃,你一口我一口,甜甜蜜蜜的的,总共就一个锅贴。那场面让我妈感慨至今。

我朋友年轻的时候,她父母的好友兼同事曾经想撮合她和自己的儿子。这家儿子人好家境好,祖上更是有名有姓的。按理说都是一个院里长大的,互相知根知底,可事情最终没成,因为朋友的妈看不惯他们上海人精打细算过日子,一个咸鸭蛋还切成八瓣儿全家分,怕女儿嫁过去吃不饱。

上海菜里我最喜欢的是小笼包 。毛蚶事件期间,大家都减少外出,不去人多的地方,更不敢在外面餐馆吃东西。可是我们要等十二个小时才能上火车,光吃饼干也顶不住啊,我们决定吃高温蒸的 小笼包。以屉当碗,每人一屉。那时候筷子还没有一次性的,每人就用那个塑料袋套在手上抓着吃,那真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包子。

 
我以前从来不喜欢吃元宵,嫌它又干又硬。直到有一天,楼里搬来了一户上海人,胡阿姨和叶叔叔。有次过正月十五的时候,他们送来一托盘自己包的小巧玲珑的白嫩圆子。我那时第一次知道这种湿元宵叫汤圆。几分钟煮熟后,天哪,世界上竟然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软糯香甜,连汤煮出来都是清的。我不仅从此爱上了汤圆,还是唯一喜欢的甜食。我们两家做朋友到现在已经有四十年了。

这里大排长龙是为了鲜肉月饼。我们估计了一下至少要排一个小时,就中途放弃了。按照我山东朋友的说法,就是酥皮儿的肉馅包子而已。看来人与人的欣赏标准还是很难统一的。

我们几个聊得来的好友时不常会聚一下,不管是去谁家,或是普通小餐馆,上海的总是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好像要去高级饭店下午茶。她们的另一个本事是把普通的衣服通过小配饰或不同的搭配,穿得不普通。那种时尚感好像是天生的。北京的则恨不得穿着做饭的衣服就跑来了,而且看得出来做饭的时候没穿围裙,胸前油渍麻花的。

小时候,七八岁,有一次我爸拉着我的手走在路上,远远地在另一个方向走过来我们院里著名的“小皮鞋嘎嘎响,资产阶级臭思想”的英语老师。我早忘了她当时穿的是裙子还是裤子,也许人家只是对自己的形象稍有要求,在一片灰黑色系中,把上衣收个腰,把裤腿改细,头发自己做个卷,走路抬头挺胸,就显得很出众。不用说话,上海的“洋”味儿浓浓的。
在当时那个院里,年轻漂亮的除了我妈,就是这位了。我光顾着扭身回头看她,没看路,结果踩着一块碎石子,摔了个大马趴。我爸说,怎么拉着走还摔,认定我缺钙得越发严重了。
 
我有个上海蜜友,地道上海人,往上数至少三辈都是。 按说她凭着天然的地理优越感,大可蔑视我们几个“外地人”,可偏偏她是经常被嘲笑的那个。她做饭手艺好,人也热情好客,朋友聚会的时候,她带来的菜色不仅材料贵,而且都是功夫菜。特别难得的是出手大方,不算小账。她厚道,不精明,不自私,特别好相处。总而言之,作为一个上海人,她简直愧对祖先。所以不仅我们夸她,她也经常自夸,“你看我不像上海人吧。
同样是这位朋友,说普通话话带浓重上海口音,不仅“肉”“漏”不分,用词也不丰富每次我向她请教某道菜怎么做,她总大而化之地说,“把这些放在一起,烧一烧,就好啦呀。”要知道,上海话的一个“烧”字可以代表所有的煎煮烹炸焖蒸炒炖!
另一个困扰是,蜜友说话还经常无意间带“一刚”的音,忽而在句首,忽而在句尾。后来我跟另一位北京朋友专心抓她现行,发现这个神秘的“一刚”有很丰富的意思,可以是语气,可以是“他/她说”,甚至是“他/她傻”。结果“她竟然说他傻”就变成“一刚一刚一刚”。(伊讲伊戆一刚。)为了这事我们笑了好久。

没机会吃到威尼斯的墨鱼面,吃到上海的墨鱼生煎包也是同样的意思。
   


我本来期待在街头听到很多上海话,结果我们去的都是旅游景点,各地口音都有就是没有上海的。直到登记上船那天,很多人都拖家带口、成群结队参团。在人群集中地,基本上都是上海话的声音。之前听说过上海话衰落的言论,看来是多虑了。 后来听临时认识的游伴介绍,上海话也分郊区的和市区的,郊区的又分浦东的、松江的等等。我们外地人听上去,当然就是一片莺声燕语。虽然我只能听懂一丁点,但也享受其中。
上海,既有纽约的繁华又有台北的温馨。最让人感慨的,是在高速现代化城建中,不仅保持干净有序,而且照顾基本民生;诺大都市能做到这样,与这里的人对外讲求公平合理,做人做事拎得清,对己有精致的生活态度是一致的。
从上海回来,我不得不跟朋友们承认,你们上海人成天拽拽的算是有点骄傲的资本啦。
|